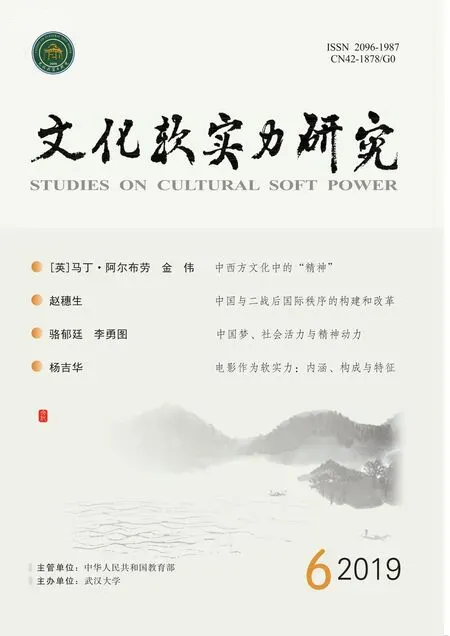中西方文化中的“精神”
2019-12-26马丁阿尔布劳万蕊嘉
[英]马丁·阿尔布劳 金 伟 万蕊嘉 译
对于今天试图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来说,中西方文化间存在着许多悖论。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中国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提到的“精神”。在西方,提及“精神”就意味着宗教。因为公共政策是世俗的,而宗教是留给个人的。那么,西方人可能会问,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为何会在公共话语中赋予“精神”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因为在西方的理解中,“精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相反,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他们也会对西方文化中的“精神”表现出不解:个人主义在西方被高度重视,宗教自由经常被视为一种核心价值观,而在公众辩论中却很少诉诸“精神”。
2000年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他撰写的许多文章中都谈到了精神,这些文章都发表在《浙江日报》上,并于近期翻译成英文,收录在ANewVisionforDevelopment(《之江新语》英文版)一书中。笔者认为精神很好地诠释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这本书中提到“精神”不少于69次,有时候是指人类努力的品质,比如“求真务实精神”;有时是强调集体的反应,比如“台风救援精神”;有时是表示集体的属性,比如“党性”。在对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作更广泛的论述时,我们也做了类似的三重区分:一是个人模范的精神,如雷锋精神;二是典型事迹的精神,如红船精神或长征精神;三是集体鼓舞的精神,如抗洪精神或上海精神。
最能有力证明“精神”在中国公共话语中的重要性的,应该是在2000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全体会议上,会议高度强调了 “精神”的重要性,并由此凝练出“浙江精神”,即“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2006年2月5日,习近平在一篇题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文章中又重申了“浙江精神”,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其中包括对“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等内容的补充完善。他认为,2005年9月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台风侵袭的应对“更是一场弘扬‘浙江精神’的伟大斗争”,抗击台风的救灾精神“与时俱进地丰富了‘浙江精神’”,体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意识,相互协作、自立自救的自强信念”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连续作战的拼搏精神和纪律严明、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优良作风”。(1)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就叙事分析而言,“精神”是一种比喻,指代的是一种经常重复的映射,用以阐述不同经历或事件之间的联系。但是,转向叙事分析层面可能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削弱人们对“精神”在社会科学工作中重要性的理解,这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从开始接触青年黑格尔运动起就坚定地走上了科学之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进行了对比。其中,唯心史观将历史解读为“渐进的精神意识”。众所周知,马克思断然反对青年黑格尔派追随他们的导师,把历史变成了“人类抽象精神”的故事。而这种说法经常被误解,这里的关键词是“抽象”,即“抽象”的东西把“精神”从“真实的人”身上剥离开来。但实际上,“精神”是“真实的人”的一种内在品质,人类的实践能力可以将精神与物质紧密结合在一起。
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历史语境中谈及“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了18世纪法国各个阶级是如何被商业精神俘获的。(2)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MECW 5,p.411.马克思在1853年3月7—8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英国政治和未经改革的议会发表了评论,这些评论在今天几乎仍然适用。他写道,大臣克兰沃斯勋爵的讲话既融合了“辉格党的真正精神”又融合了“贵族主义的真正精神”。(3)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MECW 11,p.517.恩格斯于1857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也发表了有关“中国人民精神”的文章(4)Marx on China:Articles for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Lawrence and Wishart,London,p.48.,并将他的这些文章与1842年的文章进行了比较。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用这些简单的方式去描述“精神”,是源于他早期撰写《巴黎手稿》的经验,以及他对唯心主义者和早期唯物主义者思想的深入研究。他强调了二者对立的人的本质,并指出了这种“对立性”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可以获得解决的方式。事实上,哲学创造了一种理论上无法解决而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得以解决的对立。这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对立性。(5)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MECW 3,p.302.
概括来说,精神和物质是现实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些现实事物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人类事务或技术层面。比如说森林、社区或卫星都是真实存在的事物,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当谈及人类社会时,我们观察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所推崇的目标和价值观,以及人类生产商品和集体设施的实际方式。
那么西方关于“精神”的描述是什么呢?在此笔者尽可能地概括一下,欢迎提出指正观点或反对意见。目前,笔者还没有对西方文化中的“精神”做过详尽的研究,但可以提出一些假设: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摧毁了黑格尔式大厦,使精神作为人类历史驱动力的观点失去了可信性。其次,基督教设法保持了对精神的控制,把精神作为一种只属于基督教信徒的特殊财产。最后,工业的进步和技术文明的胜利给依赖于机械论和原子实证论的实验科学赋予了声望。
对于这些宏大问题,笔者这里不做过多赘述,只想简单提一下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文献”——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发现这本书的标题使用了“精神”一词,但可以看到马克斯·韦伯是怎么处理的——他并没有试图总结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而是通过参考18世纪美国著名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作,阐述了他所概括的理想类型。马克斯·韦伯选取了一些他认为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段落,并将这些段落作为理想范式,随后用于其对世界宗教伦理学的比较研究。
但韦伯在这些比较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是将他选取的那些段落进行分解,而后再在其文章的上下文中单独提及各个分解成分。因此,他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找不到思想共鸣,他认为在亚洲宗教中普遍存在的贪婪是没有限制的,他没有领会到新教所特有的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
几年后,他修订了自己的最初表述,并将其以书的形式出版。在之后的表述中,他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有规范的、有约束的、装扮成‘道德’的生活方式”。“道德”在引号之中,“精神”也在引号之中。事实上,对这些引号的使用,反映出马克斯·韦伯在使用一种非科学用语时的不安。而他在别处关于“官僚精神”和“普鲁士精神”的叙述中也同样使用了引号。
在此,笔者认为韦伯的做法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于引用“精神”时的一种矛盾心理,主要原因在于精神已经从人类实践中分离出来了。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韦伯采纳了当时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一种观点,即中国的宗教是一个虚幻的、精神崇拜的领域。韦伯曾经引用过一位权威人士的观点,这个观点宣称:“中国人从来不懂逻辑上的矛盾,他们无法理解两种形式的信仰是相互排斥的”。(6)A.H. 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p.295.马克思指出,克服精神和物质分裂的必要条件就是对立统一。
今天,当中国政府宣布“丝绸之路精神具有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的文明时”,它所指代的是一种人类产物,一种始终保持着相互联系的人类活动的组合,而并非一套脱离人类实践的观念。中国领导人在号召长征精神或台风救灾精神时,不仅仅是简单地采用马克思对 “精神—物质二分法”的否定,而是表达了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世界观。
我们扎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具有“精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