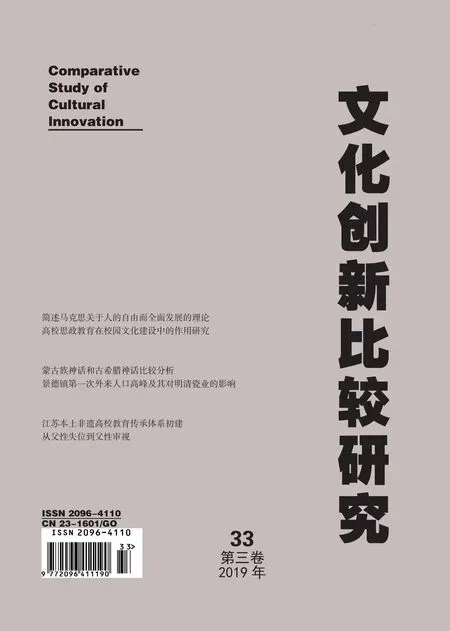从父性失位到父性审视
——论东西小说中的父性主题
2019-12-26潘颂汉
潘颂汉
(百色学院,广西百色 533000)
在家庭伦理中,父性的存在象征着秩序与威权;在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运行的秩序中,父性又象征着传承。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生力量的不断涌现,父性的存在却成为逐渐成长的新生力量——儿子的桎梏与阻碍。在卡夫卡的不朽名著《变形记》里,就通过一则现代性的寓言,叙述了父亲/旧秩序与儿子/新秩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矛盾,同时也是此消彼长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广西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东西的小说中同样投注了作家对父亲、父性的深刻思考。和同时代的作家不同的是,东西将时代的转换和社会的转型融入到对父亲和父性的解读与审视之中,借助于夸张和怪诞的手法,将转型期家庭伦理以及社会存在形态中的父亲形象结合起来,进而阐述了个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际遇和心路历程。父亲以及父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踪,导致了家庭和社会出现了极为荒诞的失序现象,而“寻获”父亲之后,对父亲和父性的审视与反思,又显示出强烈的时代性,凸显了社会转型时期疯狂生长的歪斜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断裂感。那么,在此过程中,父亲以及父性存在的意义就值得读者们的深思。
1 父亲的失踪与父性失位
从东西小说的叙事脉络观察,《耳光响亮》是作家系统地将父亲以及父性在历史际遇和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行充分探讨的开始。作品的叙事时间设置在“文革”即将结束,中国社会将要迈入新时期的历史节点上,伟人离世的历史悲怆叠加着父亲牛正国莫名离家的恐慌,将父性失位和父亲失踪的历史与现实相互映照,透视了在社会转型期到来之时,人们无序而混乱的生活状态。父亲牛正国失踪前,妻儿们对他熟视无睹,似乎暗喻着父亲的存在没有多大价值;但是随着牛正国的失踪,母亲将改嫁的议题提上日程,牛家三姐弟,尤其是二儿子牛青松,才意识到权力交替时代的到来,利益和话语权要重新分配了,于是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为了争夺话语权,牛青松用姐姐牛红梅的身体作为筹码,换取宁门牙对继父金大印的殴打。“《耳光响亮》中父亲的失踪和母亲的出走使牛家顿时堕入文化、道德与秩序的真空,因而造就了强烈的历史断裂感,也助长了文化破碎感与虚无感的升腾。”父亲的死活似乎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利益的再分配和人物“活下去”所需要的物资配给。
父亲的缺席,却使牛家三姐弟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感受到父亲存在的意义,因此,父性“缺席的在场”尤其使人怀恋秩序存在的意义和作用。牛家三姐弟享受着父亲留下的这些财富,却不得不面对父亲已经“缺席”了的现实,所以只能继续在茫茫人海中去寻觅父亲的存在。但是所有的消息都指向了否定,进而显示出文化的不可赓续,或者是使人感到茫然的断裂感。牛家的话语权更替以及新秩序的建立仍然处在交接的过程中,他们无法担负重建社会、重整秩序的重任。有论者指出,“父之死亡、缺位则意味着这种秩序的解体、失范和人的内外生活的混乱和失序,这种混乱和失序又似乎成为了现代人无可逃避的宿命。”在父性失位的现实生活里,作为家中长子的牛青松并没有在关键的时刻成为父性的坚定守卫者和代言人,反而在现实生活中追名逐利,在混乱和无序中手足相残。如果说二弟牛青松将大姐牛红梅出卖给地痞流氓是令人错愕而感到齿冷的情节设置,那么当牛翠柏已经开始劝说姐姐牛红梅去卖淫的时候,更令人感到绝望。这个曾经同情、关爱姐姐的“穷大学生”是在什么时候完成了他的人性蜕变?报复杨春光成为牛翠柏劝说牛红梅卖淫的理由,实在太过牵强——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穷大学生”也和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迪涅一样,蜕变成私欲不断膨胀的野心家。而他的人性埋葬之路,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这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在父性失位的状态下,牛家三姐弟不断地承受来自外界的物质条件的引诱和袭击,直至所有的人性全部阵亡。
书写时代转型中的父性失位和由此带来的生命悲情,东西小说开掘了家庭伦理和社会震荡状态下的共振路径。随着社会演变的进一步推进和城镇化时代的到来,凋敝的农村被城市逐渐地吸纳,子女们比父亲更早、更决绝地离开乡土,那么,执着地守候在乡土和传统里的父亲以及父性的遭遇同样具有审美的价值和意义。小说《我们的父亲》里,父亲从农村老家来到“我”居住的城市,但是却和叙事者在城市里的“家”有着非常大的隔阂感,无法深度融入这个家庭之中。父亲觉察了其中的生疏感,于是离开我家到姐姐家里。姐姐、姐夫都在医院工作,吃饭的时候要拿酒精棉给筷子消毒,但是却故意没有给父亲消毒他要用的那双筷子,因此父亲重重地拍下筷子,离家出走,最终消失在夜幕之中。小说的最后,父亲摔死了,身为医院院长的姐夫并没有发觉,签发了死亡记录的公安局长大哥,也没有发觉,甚至是埋葬了父亲的庆远,也找不到土堆里的父亲的尸首,那么,父亲到底去哪儿了?他怎么能够和牛正国一样,突然就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作家通过父亲的失踪,深刻地反省了欲望时代亲情和伦理的旁落,以及人伦和价值的缺失问题。
2 父性的审视
父亲的失踪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反思,进而审视父亲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新时期到来之后,随着商品经济浪潮滚滚而来,泥沙俱下的时代生活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存方式,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父亲以及父性的遭遇又呈现出新的特色。
如果拨开小说《后悔录》的种种叙事迷雾和“干扰”,其中的一条叙述线索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那就是小说以“我”的口吻,叙述了一个“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小孩,刚开始的时候被“文革”的革命狂热裹挟,告发、陷害了自己的父亲,结果几乎家破人亡。荒诞但是却异常残忍的人间惨剧,终于使叙事者开始醒悟,并开始了自己的“后悔”之“录”,小说的结局正是在叙述者唤醒了已经处于植物人状态中的父亲结束,显示了人性的最终复归和对“父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重新认可。
小说里,曾家是解放前的资本家,解放后把家产全部捐给了国家,但是,当“文革”到来之后,红卫兵们仍然没有放过这样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小学校长赵万年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寻找资本家的儿子,“我”父亲的生活污点加以攻击。当“我”发现父亲和赵万年的妹妹偷偷地在一起之后,却把这个秘密告诉赵万年,以换取“革命组织”和“领导”对“我”的赏识和提拔。不仅如此,“我”还数次告发自己的父亲,显示出“我”,以及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成长的年轻人的荒诞和无知。“大字报”、“高音喇叭”等摧折人性的极权政治符号把“我”给塑形了,使“我”变成一个亲情泯灭、六亲不认的狂热分子。“文革”被东西典型化为儿子出卖父亲的力比多的狂热,典型化为一种秩序的更替和话语权的争夺过程。当父亲挣扎着从批斗现场爬回来,在雪地上留下了两道深深的印迹的时候,“我”终于“后悔”了,于是通过照顾受伤的父亲以换取他的谅解。
从《耳光响亮》到《后悔录》对“文革”的历史叙述,显示的是作家对父性所遭遇的思考路径,已经经历了从混乱无序的状态中逐渐找到价值坐标的渐进过程。始于寻找,而终于审视的父性遭遇,使人物从弑父的悬崖边缘被拽拉了回来。牛家三姐弟的野蛮生长源于父性失位和秩序混乱,《后悔录》中“我”的力比多狂热更显示出这种狂热的“革命”情结的极端化发展。但是,当“我”意识到自己照顾父亲的责任感如此之重大时,“我”不得不审视“父”的存在之于自己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对“文革”里推翻一切、打倒一切的质疑和反思。
审视父亲以及父性的价值,不仅可以置放在历史的罅隙间,而且同样可以将它和时代热点并置,进而观照在疾驶的时代巨轮下,父性在场域位移和文明变迁的过程中的尴尬境遇。小说《篡改的命》通过新世纪中国城镇化背景中“农民进城”和高考被人顶替的网络热点问题,剖析了父亲以及父性在新世纪遭遇的时代苦难。小说通过两个父亲的际遇,思考了生存之痛和生命之悲,当汪长尺承继着“光宗耀祖”的父训,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移植到城里,成为仇人名义上的儿子时,心中百感交集。小说的最后,是汪长尺的儿子汪大志去追查自己的身份,以血缘上的继承人的身份,替父还乡,实际上正是以新一辈人的观点,去审视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还有汪家祖祖辈辈生存的乡土。虽然小说戏仿了俄狄浦斯的故事情节,但是个中人物却背叛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林方生也就是汪大志把记载着自己身世的档案扔进了邕江里,显示出他和这段身世和血缘关系的决绝之心。东西用不能再残忍的事实告诉读者,城市文明已经无情地吞噬了乡村文明和乡土历史,在市场经济时代,在物质条件下异化的人文生态对血缘、亲情以及伦理道德的践踏,已经变得无以复加,正如论者所指出的,“《篡改的命》对存在之境的考辨,就是去察看从乡村到城市所经历的制度及文化的碰撞,乡村人必然所经历的一种思想及行为、人性及意识的蜕变,简单地说,就是在这种境遇中他们是如何应对的,是怎样一种在世的方式。”
3 结语
借助于寻父的叙事脉络,作家东西导引出历史运行的秩序以及社会运行规则的反思问题,而父亲与父性的时代遭遇,更是新时期社会秩序重组给人带来的生活经验以及心灵感悟。裹挟在历史际遇和时代特征里的父性价值反思,体现了作家对文化传承以及社会价值走向的深刻思考,它必将随着厚重的历史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走进更为深刻的艺术探讨层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