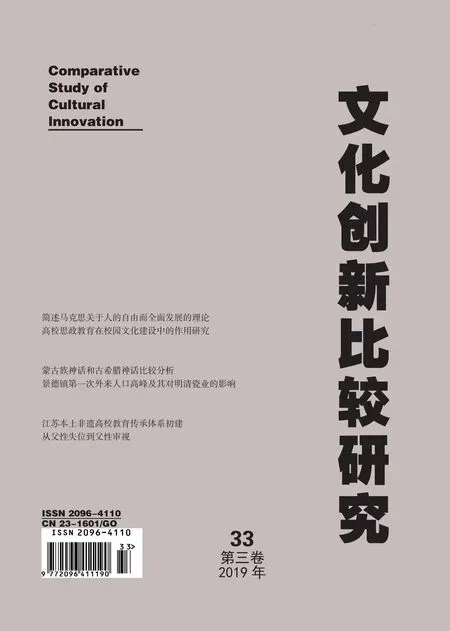论黄锦树的国族书写:寻找失落的族群文化
2019-12-26李婧
李 婧
(海口经济学院,海南海口 570001)
黄锦树,1967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祖籍福建南安。1986年赴台湾留学,并长留台湾成为旅台马华作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小说创作,先后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1994)和《乌暗暝》(1997),获得台湾多个文学奖。正如德国戏剧家、诗人布莱希特(全名: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所说的“艺术是独立而不是孤立的领域。”文学作品总是产生并作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当中。本文将以黄锦树的三篇代表作品《阿拉的旨意》、《鱼骸》、《M的失踪》为主要研究文本,分析黄锦树小说作品对于社会现实的折射和主题寓意的深层次表达。
1 小说的叙事模式与核心创作主题
黄锦树的小说创作不断重复的一种叙事模式是“失踪—寻找”。《M的失踪》(1990年)写的是以M为笔名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糅杂了世界几个重要的语系,创作了一部经典之作,在美国引起评论界的推崇,甚至有文学教授想推荐他角逐诺贝尔奖。而M到底是谁?从马华当代名作家到郁达夫一个个追踪过去,最终没有结果,M也许是一个人,一个群体,抑或是一个作者想象出来的能代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独特地位的经典。《鱼骸》(1995年)的开篇就写了主人翁沿着水道深入丛林去寻找失踪了40年的大哥的骸骨,而这段寻找过程的细致描写无疑为整部小说的主题埋下伏笔,大哥与长白山通过武装革命追寻的是实体中国政权的建立,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则是追寻古典中国文化的延续。《阿拉的旨意》(1996年)则以失踪者的自白书继续“失踪—寻找”的叙事模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马共革命分子因为当权者“文化换血”的实验而生存下来,被迫隐姓埋名、转换身份、流放荒岛,三十年来受到严密的监控和约束,必须按照当权者的指令生活,与家人断绝联系,不能说华语,不能暴露自己华人的身份,对于原身份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失踪”;主人翁虽然被迫隐瞒身份;但即便如此,却依然自觉不自觉地在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寻找与外界联络和沟通的方式。
要了解黄锦树的文学作品,首先要了解黄锦树成长的历史背景: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正式宣告成立,马共直到1990年才宣布放弃武装革命,所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多事之秋。黄锦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1969年马来西亚爆发了针对华人的“五一三事件”,以及70年代开始推行一系列打压华人、优待马来土著的新经济、新文化政策,使得80年代之前大部分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活并不轻松。而1986年才远赴台湾的黄锦树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并有着深切感受。
政策限制、民族同化、文化换血的国家政治意图和社会环境使得东南亚华人的生存趋于边缘化,陷入困境的华人不得不向中华传统文化寻求动力与支持,于是中华文化微妙地成为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凝聚的唯一纽带,形成一种族群力量,避免被分崩离析、继而走向消亡的命运;这种族群文化还将转化为一种政治资本,作为与所在国官方话语霸权对抗的符码。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尤其是马来亚国家独立之后,拉来西亚华人作为新成立的国家公民,已经普遍形成国家身份的认同,然而“国家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却远远不同,这是由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双重因素共同决定的。中国大陆学者齐冰昕认为:“黄锦树站在历史的高处向前望,看到了华裔群族在政治生活中的躲闪、在经济生活中的窘困、在文化生活中的瓶颈。然而,即使是面临着如此困境,他笔下的华裔群族仍是有那么一份孤单的偏执,带着离去与归来的疑惑,被推到了存在的边缘,寻找心灵深处的家园、寻找历史文化的根基。华人之所以会失踪是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心理原因导致;之所以要寻找就是要寻找不明确的国族文化身份。”因此,黄锦树小说创作的核心主题就是马来西亚华人国家身份与族群文化的分离,以及其对于马华族群文化持续不懈的追寻。
2 小说情节设计中的社会折射与主题寓意
这个部分将以黄锦树小说《阿拉的旨意》的情节设计为例,进一步论证黄锦树小说中关于国族身份分离的现实折射和对于马华族群文化追寻的主题内涵。
2.1 强权政治的约束与华人身份的失踪
小说中,马来当权者希望通过“文化换血”彻底改造“我”的华人身份和文化认同。小说中除了合约规定的详细禁令,还设计了诸多情节和细节来体现马来强权政治势力对于主人公华人身份的禁忌与管控。例如:“我曾申请要一本中文佛经,端送来了一册阿拉伯原版的可兰经。扉页上有他夸张的签名和一行工整的字:牢记阿拉的旨意。”——这个情节的设计体现了当权者不仅不允许主人公看中文书籍,更加忌惮宗教的力量,宗教信仰是每个民族文化认同的主要内涵,用“可兰经”代替“佛经”,体现了马来当权者对华人进行“文化换血”、改换族群身份的用心;另外“阿拉的旨意”这句话也是在点题,阿拉既是伊斯兰教的真主,更代表着马来统治者的权威地位,象征着马来统治者对于主人公(华人)具有绝对、不容忤逆的权威。《阿拉的旨意》这部小说生动折射了马来西亚华人在国家政治制度中遭遇到的各种不平等和不合理的约束;以及不被国家信任的尴尬现实。
2.2 华人文化的认同与族群文化的追寻
小说中大量的故事情节和细节都体现了主人公“我”内心深处对于华人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追寻,以及在置换身份约束下的矛盾和抗争。例如:“(我)极力讨好每月定期来巡查的官员,就是为了让他带来一些旧的马来报纸,“每条新闻读两次,第二次试着在脑中把它翻译成中文,却常常找不到对应的字。天哪,我急切的需要一部中文字典,哪怕只是小学生用的也好。”——这里作者通过主人公极力讨好巡查官员的情节以及主人公真挚、急切的内心独白凸显了作者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字的热爱,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于汉语言文字消亡的担忧,表达了主人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追寻;而族群关系的维系就是由个人的文化认同、情感认同维系的。
2.3 生存境况的两难与国族身份的矛盾
小说中主人公“我”上岛后被要求完成一系列的任务,先是开荒务农、建设示范菜园,然后再逐步指导和移交给其他村民,发展当地农业;当垦殖计划完成之后又被要求去新建一所小学,教导当地的学龄儿童念书识字,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后来又负责创建了岛上最大的回教堂,发展了当地的宗教文化。从生活方式、教育、再到宗教,主人公“我”无疑都是岛上名副其实的导师。马来统治者充分利用了“我”在华人身份下掌握的各种知识、技能,用来改变岛上马来族人的生活,正如著名的东南亚华人历史专家、曾历任马来西亚华人事务官员与剑桥大学讲师的巴素博士(Dr.VictorPur-cell)说的:“许多人说华人在东南亚剥削当地土著民族,事实上如无华人的劳动开发,东南亚的富源至今尚未开发。”这也折射出华人文化与马来文化的融合发展、多元化社会已然形成,但华人的社会作用和地位依然得不到认可的社会矛盾。
然而“作为宗教导师的‘我’,在尊贵的朋友的命令下,却不能到麦加朝圣……他解释说:在朝圣的名单上不能没有你,因为你是导师;可是你不能接受,因为这也是项重要的考验。”——这个情节的设计深刻讽刺了主人公尴尬的族群身份,一方面马来当权者希望通过“文化换血”让主人公从华人变成马来人,却又无法彻底相信这种身份改换能成功;另一方面主人公既要被迫皈依回教,又无法被完全接纳。这种国家身份与族群身份的矛盾、生活境况的两难,在小说中反复凸显;无不体现了在现实社会中,马来西亚华人与社会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马来西亚华人国家身份与族群文化的二元化特征。
3 结语
黄锦树的小说作品通过一以贯之的“失踪——寻找”的叙事模式,持续关注马来西亚华人被边缘化的生存境况,并坚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求马来西亚华人族群文化的认同和维系;小说的情节设计则是将作者对于马来西亚华人国族身份和族群文化的深度思考,转化为大胆的狂想、放浪无羁的戏谑、后现代游戏式的反讽;小说中看似信手拈来的一句话、一个人名、一个物件或者一个貌似随意杜撰的符号中都暗藏了历史和现实的渊源。因此,研究黄锦树的小说作品很有意义,不仅是因为他大胆、另类的文字,更重要的是他对于马来西亚华人国族身份的文学思考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