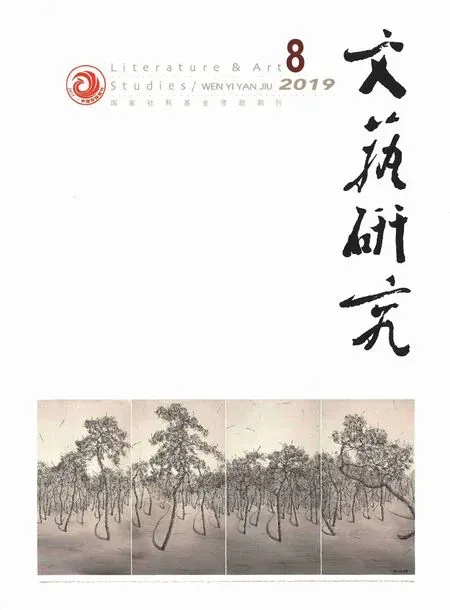“情性”的古今之变
——从儒家政治哲学到“情本体”美学
2019-12-21冯庆
冯 庆
一、传统情性论与“情本体”的古今张力
“情性”是儒家政治哲学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在儒家经典里,有时“情性”或“性情”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出现;有时“情”“性”二字各自有着不同的意涵。
荀子曾对“情性”的整体概念进行定义:
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荀子·性恶》)①
在此,“情性”指的是身体触碰外间世界并产生愉悦感的一种人固有的自然倾向,显得像是对生命在世状态的整体概括②。
荀子还曾将“情”“性”分而论之: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荀子·正名》)③
尽管荀子多连称“性情”或“情性”,将“情”或“欲”视为“性”的子概念④,但在这段话里,荀子显然是将“性”和“情”安置为人生的不同心灵状态阶段:“性”是人的“自然状态”,是“情”未发之时的状态;“情”是这种自然状态的质化呈现,是其未经文饰的表达。“情”的呈现必然是由于“欲”的方向指引。“欲”是人之所不可尽去的,但可以用“心”去节制,这种节制的实践,则是“伪”——人为的规范。由此而论,对荀子的情性论的美学式关注,实则会引出一套修身的伦理学,乃至于制度立法的政治哲学⑤。荀子认识到,情欲的无法满足是世间常态,而人必须生活在“群”当中,遵守各自的“分”,因此“礼义”也就必须存在。而其不至于偏移的基础,则是“心知”的好恶是非之辨。圣人的“心知”能力由此可以为世间立法,这就是情性二分论所通达的政治哲学问题域⑥。
在董仲舒笔下,荀子的观念和孟子一脉的天道性善论得以结合,构成了中国儒家政治哲学关于民人情性问题的典型政治哲学表达:
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栣也。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瞑,情亦性也,谓性已善,奈其情何?故圣人莫谓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⑦
人之自然之“性”禀受阴阳二气,进而有“贪”“仁”两种志气,“天”既然让阴阳二气保持平衡,那么人之“心”也应当限制情欲,使“贪”“仁”保持平衡——“性”的自然之气禀也将在这种“心”的看护中逐渐朝向“与天道一”的境界迈进;重要的是,和荀子一样,董仲舒尤为强调一个在先的圣王作为立法者,他能够凭借制度教化的施行,引导这种性情的潮流在正确的渠道中运行。
根据对荀、董二人情性论的概括,可以看到,在传统儒家语境里,情性论本质上是关注“立法”与“治理”的伦理政治哲学。然而,在当代语境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儒家思想关于情性的讨论空间为源出于西方的美学所接管,关于情性的政治哲学命题则被转译为基于人之普遍感性的美学命题。李泽厚的美学思想是这种转向的典型代表:
人在物质操作的长久历史中所积累的形式感受和形式力量,由于与整个宇宙自然直接相关,便具有远为巨大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这里所说的存在和形式感并不是理性工具,而是直接与感性交融混合的类比式的情感感受,这种感受是一种审美感受。它的特点是与对象世界具有实际存在的同一性。它是与宇宙同一的“天人合一”。⑧
李泽厚这一论断中显著体现出康德、马克思乃至海德格尔的思想沉淀,也充分展现了现代美学的基本诉求:让身体感性借助审美直观能力与理性达成统一,为人类心灵赋予尽善尽美的内容,让个体融入整全宇宙秩序中。用传统儒家哲学尚未被转译的话语来说,就是借助“情性”不断“感应”天地,整饬内心,实现对“道体”的通贯,直至“天人合一”:
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所感复有应,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观之可也。⑨
当然,传统儒家的教化方案还需要“善恶之理”的客观基础来进行调适。甚至,是这种对“善恶”的理论考虑,而非对“天地”的神秘沟通,构成了情性修持论的核心要素: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如此,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⑩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美学和传统儒家哲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切割了面向“自然”的感性生活和面向“善恶”的理性生活。传统儒家哲学基于“善恶”的考虑而试图提出的对情性进行约束调教的理念,恰恰构成了现代情性论美学必须要超越的对象。这种超越并不是否认“善恶”的客观性,而是将“善恶”之理置于人之自然生存的感性进程中,使其化为审美经验的附加物。在长期的审美经验的积淀中,人们能够养成“一种动物本能性”,凭借这种审美直觉“合道德而超道德”。因此,情性论的美学修持不光可以“以美启真”,还能“以美储善”甚至“以美立命”⑪。
李泽厚把美学视为“第一哲学”,其理论基础是“历史中的人”或者说“内在的人化”⑫这一哲学人类学观点。这种观点假设,在历史性的此在生存过程中,“宇宙自然”持续对人的身体施加力量,激发其审美情感,才能够让其由最初的单纯感受不断上升为对整全的成熟感受。没有这样一个历史化的过程(无论是集体的发展过程还是个体的成长过程),也就没有作为情性修养计划的“美学”的用武之地。
其实,这种历史化的人类观,是由康德诉诸审美鉴赏力不断激发道德进步的启蒙史观所奠定的:
理想的鉴赏具有一种从外部促进道德性的倾向。——使人在自己的社交场合温文尔雅,这虽然并不能等于是说,把他塑造成道德上善的(有道德的),但毕竟通过在这种场合使别人愉悦(受到喜爱或者赞赏)的努力而为此做好了准备。
人由于自己的理性而被规定为与人们一起处在一个社会中,并在社会中通过艺术和科学来使自己受到教化、文明化和道德化……人必须被教育成善的……⑬
重点在于,李泽厚会把这种过程上升为本体论化的哲学原理,与儒家传统的“仁”或者“情”的本体概念进行对接。比如,李泽厚曾借冯友兰的话说,“康德只讲‘义’,理学还讲‘仁’”——中国人会“从现象中求本体,即世间而超世间”⑭。因此,尽管李泽厚的理论中有着扬弃传统儒家哲学本体化“善恶之理”的动机,其对道德情感体验过程的重视和再度本体化,又显得是对传统情性论的扬弃和发展。
当然,“仁”或者“情”在传统儒学中的本体化,与现代美学的基本架构,在理论上难以调适。李泽厚也意识到,理学对“仁”的把握确实蕴藏了历史本体论美学的视角,但其中又有着一种暧昧的双重意谓,无法与现代理性与感性二分的哲学框架相协调:
像“仁”这个理学根本范畴,既被认作是“性”“理”“道心”,同时又被认为具有自然生长发展等感性因素或内容。包括“天”“心”等范畴也都如此: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既是超自然的,又是自然的;既是先验理性的,又是现实经验的;既是封建道德,又是宇宙秩序……⑮
李泽厚相信,这种感性因素和形而上学因素并举的双重性,使得理学的心性理论结构格外不稳定,随时会因为义理上的暧昧而引发现实中的伦理争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泽厚认为,只要扬弃掉其中“追求超验理性的失败”,回到某种“道始于情”的“原典传统”,就能够进一步整合出一种“以情本体为核心的中国乐感文化”,由“人际世间的伦常情感”转换出“超世间的宗教信仰或宗教情感”,通过消解“道德秩序即宇宙秩序”的观念,“回到感性存在的真实的人”,也就是回到“自然情欲”这一生存性本原⑯。
综上所述,李泽厚强调作为人类历史生存体验的情性本体,本质上是要以其承担感性维度的价值基底,从而建构一种与节制情欲的传统观念截然相反、而有助于现代生活情感解放的新派伦常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那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对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颠覆远远大于继承。
在近年的《举孟旗行荀学——为〈伦理学纲要〉一辩》一文中,李泽厚指出,有必要延续荀子、朱熹的路径,用规范性的“四端”(仁义礼智)补足作为自然感受状态的“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这种思想填补的工作,将使得具有“更普遍的人类性、世界性”的儒学在未来实现:
中国传统以塑建“情理结构”为人性根本,强调“好恶”(情感)与“是非”(观念)同时培育、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它也可说是一种儒学内部的“儒法互用”,即以情润理,范导行为……今天需要对此传统分析、解构而重建之,即以情本体的宇宙观和宗教性道德来范导和适当构建公共理性的现代社会性道德。⑰
这种以“情”导“义”的观念设计是否可行,姑且不论。从理论上说,如果要让经验性的“情”作为本体之“性”,由其历史发生论和感性生存论上的优先性推论出其价值尺度上的优先性,那么也就必须首先回答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何过去的儒家思想家总是强调对“情”的克制而非放纵?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澄清,那么,当代围绕“情本体”展开的乐观主义的审美道德启蒙设计,也就将缺乏说服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再度回到荀子和朱熹,思考他们的思想中哪些成分构成现代情本体美学渴望吸收的理论资源,哪些成分又会始终和现代文化主流意见构成不可调和的张力。
二、荀子、董仲舒情性—礼法论中的“圣人”维度
基于一种对万物秩序的整全判断,荀子相信,人之天性有同有异。人之“同求”和“同欲”——对应孟子所说的“性善”——未尝能够推导出稳定的政治结构,因为在成全情性、满足欲求的过程里,人和人之间有着智愚高低的差别。如果任由自制力差的、私心重的愚昧之人纵欲无度,则会造成社会共同体失去规范性,走向人人相争的危机局面: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⑱
基于这种实际的政治考量,荀子相信,“情性”是自然欲望的呈现,与人之“恶”的“自然状态”直接对应,这种“恶”是“不待学而知”(杨倞注语)⑲的先天禀赋。正是这种“性情”本身存在的“恶”或者说不足,使得良好的道德伦理诉求显得尤为必要: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荀子·性恶》)⑳
关键在于,大多数人认识不到自己的情性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或是无法控制自己纵欲的自私冲动,进而无法祛除自然情性中的“恶”,走向人为的“善”;因此,荀子认为,应当由少数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这种工作和“陶人埏埴而生瓦”的制作技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㉑。
由此,“情性”和“礼法”形成了一组范畴:情性是需要得到克服的人之自然身体属性;社会化、政治化的“礼法”,则必须承担“养情”的功能,让自然情欲获得外在的规劝,这样一来,容易滑向“恶”的情性——其实质应当是“朴”,作为尚未得到完善的先天状态,需要和礼法结合,在质文互救的秩序里,生成良性政治生活秩序:
(礼)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两情(吉凶忧愉之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断之继之,博之浅之,益之损之,类之尽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终始莫不顺比,足以为万世则,则是礼也……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礼论》)㉒
由此看到,荀子情性—礼法观的重点在于,“礼”的制作者——圣人——是塑造万民朴质情性的首要动力。在由“质”向“文”、由“情性”入“礼法”的教化秩序中,圣人凭借其对天地万物的分辨知识,扮演着核心角色。那么,圣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圣人与常人的区别,在于圣人有“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的心志,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则“涂之人可以为禹”;当然,荀子深刻地指出,“未必然”能够让一切人都选择积学为善的生活态度㉓。对于大多数人,这种“规范伦理”的基础也不是孟子性善论中带有主动积极意味的“德性”,而是带有消极意味的外在教育—认识机制㉔。由圣人立法到“人类”的全体文明化,之间需要一个漫长而现实意味浓重的强制化、等级化的教化过程,与乐观主义的“人类自身的自我教化”㉕有着根本差异。
荀子对常人之情性的现实判断,引发了情性论问题域的第一道难关:“美”或“善”是基于人之自然情性,还是立足于后天由圣人人为设立创制的标准?孟子会坚持人之自然属性本善,荀子则只会用一段虚构的对话,表达他对大多数人凭借自然情性自发趋近美善的悲观态度,但同时,又强调某些“贤者”挣脱这个悲观现状的可能: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唯贤者为不然。(《荀子·性恶》)㉖
情性嗜欲的放纵,会让人远离真正的美善;或许,唯有“贤者”能具有“美”的“情”——方向正确的“情”。荀子相信,这种正确的方向,来自对“分辨”之“知”的修习,而“知”的心法,就在于“虚壹而静”:
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荀子·解蔽》)㉗
“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要求修习者暂时抛开既有的好坏得失判断,进入客观思考状态,显得像是康德所说的“无功利”态度,也很类似现象学所说的“回到实事本身”;“兼知之”则体现出悬置个体主观视角、以全景视角“壹”的态度把握真知的诉求,这种“静”的心态,类似西方哲学对“一”的整全理智直观(nous),同时也是君子——“未得道而求道者”——摆脱身体情欲造就的偏离之知、凭借正确实践理性通向善美目标的修习“心法”。圣人则是这种心法修习的终点状态,他们已经彻底完成了“虚壹而静”的修行,进而能够与宇宙之整全知识相融契:
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恢恢广广,孰知其极!睪睪广广,孰知其德!涫涫纷纷,孰知其形!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荀子·解蔽》)㉘
“君子”则只是这种心法的“修炼中”状态,他们时刻保持自我规训,整饬情性,但在智慧的境界上与圣人有本质差异:
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桥饰其情性,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其行多当矣而未安也,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荀子·儒效》)㉙
如廖名春所说,士与君子的特征在于“行”,而圣人的特性是一种极高的“知”和“明”——尽管前者尝试以“行”来成为后者㉚。“君子”能够在行动中修正自己的情性方向,但其思维并不周密,其关于人事与万物的知识也并不整全。而“圣人”则透过“知”把握万物之理,甚至是上升到“明”的绝对知识层面,进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同样具有高超的辨识能力,把政治事务处理得有如顺应四时一般自然而然。由这种圣人通过极高智慧所设立的礼法,也就不同于一般的世俗约定,而是具有稳定意义的“自然法”。贤人君子需要通过“学”的修身过程,在“行法”中不断朝向圣人的境界迈进,以求最后达到知天地而立大法的境界。
这其实就是后世“知行合一”的君子贤人教养论所要传达的义理。“知行合一”要达到的理想,则是“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对万物之“情性”的正确辨识,和对自身情性的完全理性控制,则是这种理想境界的必要条件:
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此则可谓贤人矣。……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总要万物于风雨,缪缪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识,百姓浅然不识其邻,若此,则可谓大圣矣。(《荀子·哀公》)㉛
君子虽“仁义在身”,在礼法的习俗惯性中生活,却未尝懂得更为精微的万物本体之道,所以在面对突发的例外状况时,难免“辞不争”;贤人行事均中节而不离规矩,但同样没有把节度背后的理论基础阐明的立场和诉求;“大圣”则在智性上达到极致,能够给予万物之情性以分判定位,发现其中的是非取舍之理。这种“理”贯通天地自然和人事百态,百姓、君子乃至贤人却几乎不可能看透这种整全之“理”,这是荀子透过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洞察到的冷峻真理。思孟学派渴望让“圣”本体论化为一种德性状态,并经由《中庸》影响到宋儒的理学建构。这种试图把情性在智性层次上的不齐本相从现世政治状况中抽象出来,并用普遍化的“德性”加以涵盖修缮的态度,与荀子的现实主义冷峻视角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因此,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思孟学派“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㉜,所谓“无类”,就是没有区分人之内在品性的差异。
“圣”能够凭借极高智慧洞察万物之整全,并为世间设立情性协调之法,是一种已经实现的高级境界,而不是一种常人天生具备的德性潜能。我们不难发现,与荀子这一洞识相比,现代美学试图建立“情本体”,让一切人的“潜能”在生活中“积淀”并通向“天人合一”,其实是要让不同资质与才分的人都凭借未加区分的日常生活审美实践中的自我启蒙,努力“成圣”。这种审美实践,显然不同于君子的“虚壹而静”及其相应的求学求知态度,而毋宁说只能与陶冶情趣维度的“乐教”相通,进而只能停留在李泽厚所谓“乐感文化”的层次。当然,荀子也承认,多数人情性的治理要窍是“乐”,但是,圣王的“制礼作乐”,才是让“乐感文化”真正成为社会基底的原因: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荀子·乐论》)㉝
圣人对“乐”的制作,才是“乐教”的根基,也就是说,圣人对至高自然秩序的音乐性理解,是面向众人的文教制度的出发点。如果没有倚靠在圣人对自然秩序的洞识之上,礼乐也将失去其权威性。除非我们基于某种现代人类学的描述,相信民众本身就有礼乐和同的天然美好情性。但是,这种乐观的态度很难面对现实的拷问——何以在文明化的过程里,人性却逐渐丧失了这种天然美好的情性呢?显然,那种对人类最初的美好潜能的描述,或许只是一个卢梭式的“自然状态”假设而已。
在《春秋繁露》集大成的儒家情性论体系里,对具有至高智慧的“圣王”的重视更为明显——唯有经圣王教化的人性,才可谓之最终的“善”;相较之下,所谓的自然之“善”,其实只是“禽兽之性”的质朴起源状态,没有受过圣王之教,这样的“善”也就不成立;不存在万民原初情性就尽善尽美的道理:
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夫善于禽兽之未得为善也,犹知于草木而不得名知,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而不得名善,之知名乃取之圣。圣人之所命,天下以为正,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圣人以为无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当善。善之难当如此,而谓万民之性皆能当之,过矣。质于禽兽之性,则万民之性善矣;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也。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圣人之所谓善者弗许,吾质之命性者,异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以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善,故谓性未善,善过性,圣人过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实性》)㉞
即便有现代民主社会在“政治正确”上的“加持”,“情本体”的美学也很难回答传统儒家提出的一个“政治不正确”的问题:该由何种情性的人来体察天地自然之理、树立道德尺度、制作礼乐教化,以陶冶人民的性情向善发展?对此,现代美学的回应是:在历史的积淀当中,人本身会由感性到理性逐步成长,发育出成熟心智。历史中的漫长实践过程和经验传承,能够以文化陶冶的方式让一切人实现自我完善,这种经验主义的“乐感文化”,会比由圣人所制作的礼乐更加可靠,因为其中彰显的是多数人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智慧。基于历史经验的审美经验,就此成了新的立法手段,而历史中的每一个人,也就未必不能靠个体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和集体生活中的经验分享,达至和圣人同等的境界。但我们明白,这一朝向未知未来的“善良”推论,显然至今未得到历史经验的核实。经验知识的不断积累,未必最终能够推出尽善尽美境界的普遍实现。
儒家政治哲学并不怀疑“情”之于人性的自然实存意义,而十分重视对“情”的考察和看护㉟。只是,他们警惕“情”的放纵可能造成负面的伦理政治问题,所以设置出一个更高的智慧主体,凭借至高理性,对多数人的情欲加以节制。就此而论,儒家政治哲学和现代美学之间的实质性张力,未尝出于“礼法”和“情欲”这二者的冲突(尽管其最终表现形态看似如此),而是出于超拔于众人的圣王智慧和人类全体历史中所积累的经验知识二者对伦常世界立法权的争夺。古典儒家政治哲学认为,高明圣人对自然—人事之整全道体的把握和分辨,是最值得信赖的大前提,“情本体”美学则相信,唯有多数人历史—审美经验的积累,能给人性的自我启蒙和社会的总体进步带来稳定动力。
三、从理学情性论到现代美学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在传统儒家情性论和“情本体”美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中间,有着一段漫长的让“圣人”这一立法主体逐渐抽象化、法则化的观念运动过程。荀子的礼乐—情性论并不“玄学化”㊱,而是有着十分鲜明的务实特征。其施行圣人礼教,除了维持共同体的稳定之外,还有着“节用裕民”㊲等现实关怀,其思想模式以实践理性为主导。这一模式贯穿了整个秦汉时期。魏晋以降,随着佛教思想的浸润,抽象地谈论情性的话语日益增多;儒家试图通过重构情性论,在与佛老诸家的论辩中找回优势地位,进而,“性与天道”这一过去少有人谈论的话题成为思想生产中的核心议题。从李翱《复性书》开始,一种关于性善情恶的本体论理论开始出现,相信人可以凭借自身修习“由动向静复归,由现实向先天复归”的“心法”也不断涌现,直到北宋理学强调“生而谓性”“性道一体”,“将善恶观与天理论连接起来”㊳,一个抽象的先天之“理”及其相应的道德修行,变成了理解情性问题的枢纽;《中庸》“修道之谓教”的君子修行法门,被扩大为士大夫自我整饬情性的“敬而致之”态度,二程所谓“内圣外王”之法就此普及开来;而张载则认为,圣人的高度在于其能够“尽性知天”,以至诚回归至高天理,在“时”之中把握真正的普遍性㊴。
可以看到,在理学的语境里,“圣人”作为“体道”之人直接面向世间表述“道”,而非在把握“道”后回到现实政治差异环境中因材施教、以礼化民。理学中的这种形而上化的情性论和“体道化”的圣人论,在朱熹解周敦颐《太极图说》时,体现得尤为显著:
盖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谓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然形生于阴,神发于阳,五常之性,感物而动,而阳善阴恶,又以类分,而五性之殊,散为万事,盖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圣人全体太极有以定之,则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人极不立而违,禽兽不远矣。㊵
人皆分有“五常之性”,唯有圣人能够“全体太极”,给予这种气质以规定的渠道,由此保证人之情欲不至于越轨。和荀子一样,朱熹认为圣人的意义是探知太极之道,悬之以为法。但问题在于:太极之道和人事礼法之间,应当是何种逻辑关系?分殊之性始于太极,那么,要让万事之气得到调整,是否必须首先本体到位,把太极之“理”彻底澄清,才能让“法”获得依据?如果说对于圣人是这样,那么,圣人“全体太极”的致知之学,又是否能为其他人所模仿?
吴飞认为此处并非在说“阳的原则是善与阴的原则是恶”,而是说“恶,更多是阴阳失调所致,阳过多与阴过多都会导致各种问题”,进而,在中国的思想谱系里,“由于身心之间不是西方式的二分,身体和身体的欲望都没有遭到过多的否定”㊶。往前推一步,我们也可以说,荀、董以降儒学限制身体情欲的现实动机,或许也在这种原理化的“阴阳失调”的情性论解释当中失去了重心。正如徐复观所说,荀子“不着重在‘生之所以然’的层次上论性”,尽管其亦有相关“所以然”的论述,但始终围绕政治共同体中的经验现象来讨论情性问题㊷,而甚少直接援引形而上“道体”来为现实立法策略辩护,这或许是“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上古共识。而理学在会通佛老之学后,则强调要以“自然只是一道”的态度来引导“形而下界”的世事经纶:人之性情及其欲求计度,必须与形而上的“天地之气”圆通为一理,“只要此情意计度合乎理,则此理便会发生作用与造作”㊸。圣人所立的“人极”基于“天理”,而“天理”则可以通过“修道”而企及。置身礼乐、陶冶情性的人间生存状态的重心“圣人礼法”逐渐被更高位格的“天理”所凌越,通过“性”之修习通达“天理”的“我”则能自生自养其天然之性,使得“情”也在“道”的整全呈现中流溢为“中节”之用: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㊹
以这种理学情性论为代表,以圣人为中介制作礼法、合群辨称的传统儒家政治哲学,转化为了让天下人直接面对天理道体进行自我修缮的道德形而上学。用汪晖的话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内在化”道路㊺。相较于荀子、董仲舒的思想,理学家所设计的面向士人阶层的“致学”目标,不再敬守贤人—君子—士—民之“分”,而更多要求一切人都尝试透过心性工夫的修养而“成圣”。张载就曾直言不讳攻击上古儒家在“成圣”问题上的拘谨:“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朱熹则进一步消解圣人和常人在本来禀性上的差异:“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自视为卑,故不肯进……然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㊻
相比荀子“虚壹而静”所要求的纯粹知性状态,在由常人向圣人进发的心性修养工夫论视域里,人之七情六欲开始占据更加复杂的地位,以至于有人认为在朱熹的学说中,“情感居于核心地位……以性为心之本体,但真正体现性的,是情而不是知……情才是存在本身”,所谓“心兼性情”的体用二分,实则落实了“情感在心灵中的地位与作用”㊼。这恰恰也是现代美学的出发点——让变动不居的情感本体化,成为在世生存的依托。这也就是李泽厚强调朱熹思想意义的原因。
的确,理学的“工夫论”具有开出过程哲学的潜能,与审美积淀论有契合之处:
“工夫”只不过是扮演信任内在的“理”、推动“理”、并促进其活化的角色……理学之“工夫”……不是单纯的“意识性”行为;而是以“自然”为志向的“意识性”行为……若“工夫”被赋予达成使“理”显现的此一目的,则“工夫”必然会面临自我消灭的命运。㊽
理学传统强调的修持情性并通向“圣人”的“工夫”,也可能在现代语境里被阐释为一种让自然之理进入自身、并推动生命实现其潜能的历史哲学——其最终目的“成圣”也就和审美积淀论中试图实现的“天人合一”发生了意义拼贴。宋儒的情性修养工夫论及其把天理视为“历史事件”展开过程的观念㊾,让传统儒家情性论发生裂变、并最终延异出“情本体”现代美学的思想转折获得了一种理论依据。朱熹不再重视具有极高智慧的“圣王”的制作权威,把礼乐文艺的确定性和正当性交托给“天理”之下的观念化之“义”,并让私人情欲在这一概念的符号之下获得一种灵活变通的合法性㊿,这是一种理性化、法则化的态度,为现代个体的感性生存基础提供了“隔代遗传”的基因。只是,朱熹对“天理”的判定中还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神秘特征,亦即李泽厚所谓的“宗教”因素,这种特征使得理学实践的范围集中在士大夫阶层,民众只需被士大夫的道德气质“感化”,而不需加入到“工夫”的践行中。试图体现“人”之价值的现代启蒙美学,则必须对此加以扬弃。
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王国维在评述荀子情性论时,曾以怀疑主义态度,对“圣人”提出疑问:
……其说之矛盾,其最显著者,区别人与圣人为二是也。且夫圣人独非人也欤哉!常人待圣人出礼义兴,而后出于治,合于善,则夫最初之圣人,即制作礼义者,又安所待欤?……胡不曰“人恶其乱也,故作礼义以分治”,而必曰“先王”何哉?
在我们今天的语境里,这一追问显得格外“自然而然”。在现代“正当的社会学”视野之下,“圣人”的设定显得像是“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是一个非必要的偶然因素。甚至有人会担心,一旦引入这个因素,作为现代民主生活尺度的“普遍”与“稳定”就必然遭到破坏。
的确,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很难找回荀子诉诸“圣人”的政治语境。即便出现了真正的“圣人”,也未必能够在当今时代获得什么权威。但至少,儒学节情修性的基本态度及其对人性本质差异的现实洞察,依然具有现实解释方面的活力。哪怕是朝向“天理”,也依然有常人“主敬”和士人“主静”的不同态度。而“仁”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维度之间徘徊的暧昧特征,恰恰也使得对天地之理的客观认识和对人间纷繁情性的调节实践,二者之间维持着某种贯通未断的理论气脉,“圣人”之智性观物和仁德立法的一体性,则是这一气脉未断的首要枢纽。
问题是,一旦圣人与常人的客观之分不再得到承认,承担“仁”的“礼法”和“天理”就会变成失去特殊身体性的抽象的形式主义法理,看似具有了某种普遍性,却无法对常人的情感进行权威的秩序化调整,道德伦理生活也将陷入混乱的危机。尤其是近代以来,视“物”为“理”的儒学天理观在视“理”为“物”的“世界公理”面前,必然会沦为不切实际的“宗教”或“神话”。如此,儒学情性论不再有效,其形而上维度被迫让渡给密切关注“物”及其“时势”的现代历史哲学,自身则只剩下庸俗伦理道德教条的一面,成为被激进文化运动轻松扫荡的“孔家店”存货。
从儒家政治哲学到现代美学的古今之变轨迹中,可以看出,民众地位的上升,是导致哲学情性论发生重心转向的核心因素。与荀子和朱子相比,现代“情本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其应和现代民主自由生活的诉求。庄士敦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在一个民主制国家里,不存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乐和礼’的立足之地,而且与礼乐相关的那些古代中国的神秘思想在一个进步的现代国家里会成为人们的笑柄。”的确,正是现代民主的基本信念,让关于“圣王礼乐”的信念变成明日黄花;带有神秘体验性质的“工夫论”,今天也有遭逢“去魅”的危险。正统儒学如果不经历一番“情本体”的美学改造,或许会就此失去其现实生命力。但我们也可以尝试回到荀子的现实主义眼光,审视如今的审美民主化、生活化道路,思考其是否有过于乐观且天真的内在缺憾。
①③⑱⑲⑳㉑㉒㉓㉖㉗㉘㉙㉛㉜㉝㊲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17页,第487、506—507页,第207—208页,第517页,第519页,第517—522页,第419—420、432—433页,第524页,第525页,第467—468页,第469页,第154—157页,第635—640页,第110—111页,第450页,第209—212页。
②㉔ 余开亮:《先秦儒道心性论美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第129页。
④㉚ 廖名春:《〈荀子〉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2—83页,第150—155页。
⑤㉕ 陈昭瑛:《荀子的美学》,(台湾)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页,第226—227页。
⑥ 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126页。
⑦㉞ 董天工笺注、黄江军整理《春秋繁露笺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150页,第147—152页。
⑧⑪⑫⑯ 李泽厚:《哲学纲要》,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26—233页,第158、384页,第368页,第51—68页。
⑨⑩ 吕祖谦撰、严佐之导读《朱子近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第31页。
⑬ 康德:《实用人类学》,李秋零译,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114、115页。
⑭⑮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48页,第253页。
⑰李泽厚:《举孟旗行荀学——为〈伦理学纲要〉一辩》,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㉟ 马育良:《中国性情论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129、145—152页。
㊱林桂榛:《天道天行与人性人情——先秦儒家“性与天道”论考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4页。
㊳向世陵:《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44页。
㊴ 杨立华:《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6、92—104页。
㊵ 朱熹:《太极图说·解附》,《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页。句读略有改动。
㊶吴飞:《论“生生”——兼与丁耘先生商榷》,载《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㊷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3—204页。
㊸ 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5页。
㊹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8页。
㊻本段张载、朱熹引文,均转引自藤井伦明《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理”为考察中心》,(台湾)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40—41页。
㊼ 蒙培元:《朱熹哲学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114页。
㊽藤井伦明:《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理”为考察中心》,第51—54页。
㊿ 赵金刚:《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75—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