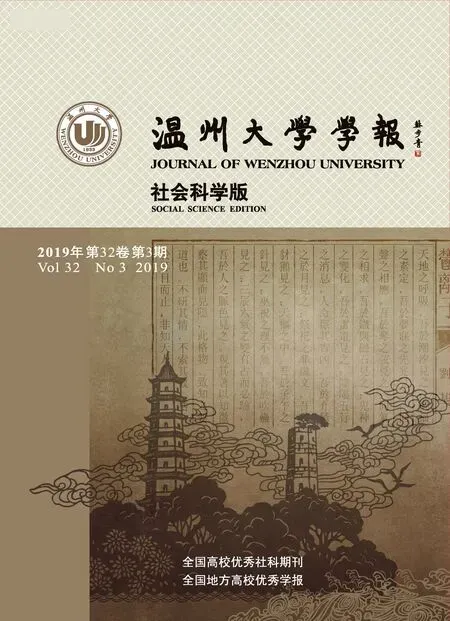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媒介变局中的《小说连播》
2019-12-21刘成勇
刘成勇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周口 466001)
一、媒介变局与《小说连播》的听觉价值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小说连播》进入到一个低谷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收听率的下滑。造成《小说连播》陷入低谷的原因有多种。广播界人士多将原因归结为受众市场[1],但还应看到广播媒介自身处境及媒介环境,其中图像媒介对受众的分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小说连播》自身质量的下降。1993年,叶咏梅批评某些电台文学编辑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什么书都敢播放”,如《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不适宜广播的作品[2]。这是否意味着《小说连播》步入穷途末路了呢?认识这一问题,需要考察作为载体的广播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应对这一媒介变化。在这场媒介格局的变化中,广播媒介的命运复杂而又微妙。
毫无疑问,影视媒介的崛起影响着广播空间。在与影视媒体的竞争中,广播节节败退、举步维艰,听众人数锐减,经济效益惨淡,同时广播内部的竞争也异常激烈。20世纪90年代初的广播体制改革使广播转向了专业化、类型化,中央台与地方台之间、各地方台之间、各台内部栏目之间形成了竞争态势。竞争的激烈引起人们的担忧:广播媒体会不会即将消亡?同为电子媒介,广播有没有与影视共生的可能?
这种担忧很有必要,但也应看到新的技术、环境及受众的多元需求赋予广播新的生机。首先,广播能够与时俱进,通过改进内容板块、提高服务质量、细分受众人群等种种方式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其次,广播能够主动与其他媒体结合,极大地发挥媒体组合的优势。在这场媒介交会中,广播释放出的能量最为明显。就像麦克卢汉所说,在媒介结合中,“没有哪一种能超过读写文化和口头文化交会时所释放出来的能量”[3]68。比如,广播是最早开通热线电话连线的媒体,也是最早利用手机短信互动的媒体[4]。它能很容易融合于互联网中,也能将影视剧转化为声音形象。再次,广播在受众心中已经树立起一个固定的公益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广播比报纸、影视、网络更能忠实地呈现意识形态的意旨。
从听觉文化角度而言,声音在生存论意义上几乎有着核心的价值。听觉不仅指向人的自我感知与自我认同,听觉更是感知和认同群体的媒介。全球化时代尽管拉近了人的距离,但却造成了人心灵的疏远。消除距离感的不是排斥性的视觉,而是高兼容性的听觉。阿多诺认为,在互相隔绝的情况下,凭借机械复制的音乐收听,制造出了虚拟的“我们感”和“相互陪伴下的孤独”,其是对直接进入人群媒体干预式的模拟,无论身边是否有真实的人群和声音“原件”[5]。而对于汉族来说,广播又可能具有别的一种意义。麦克卢汉认为中国人是“听觉人”[6]。麦克卢汉之所以有此判定,是因为他认为视觉不如听觉精细,也不如听觉敏感,而且他还认为:“组成口头文化的人,却不是由专门技术或鲜明标志区别开来的,而是由其独特的情绪混合体来识别的。重口头文化者,其内心的情绪错综复杂。”[3]69这种错综复杂的情绪单以文字而言,可能有些难尽其妙,但模糊性的声音也许是其最恰当的吻合,尤其是声音稍纵即逝的时间瞬间与情绪的微妙反应可能保持在同一频率上。由此看来,“广播的消亡”就是一个假命题。Laven就批评过这种观点:“我们也会幼稚地认为所有的新技术将会自动地取代所有的旧技术,……事实上,尽管有来自更新技术的激烈竞争,声音广播和电影院却不断壮大。”[7]
既然广播前景光明,《小说连播》的未来也就不会悲观。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的电台贡献出一批艺术质量上乘的小说广播精品,如《北京人在纽约》《白鹿原》《毛泽东的故事》《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等。从听众方面来说,对《小说连播》也有着持续的热情和执着的关注。1994年中央台进行节目调整,《小说连播》由12:30改为11:30,引起听众不满,听众呼吁恢复到原来的黄金时间。1999年10月1日再次调整,又引起听众不满甚至是愤懑:“请不要改时间,请把这个节目还给我们这些上班族。”[8]251“你们有你们的理由,但一切总该以大家的心愿为前提,你们说是吗?”[8]252“不要让我们失望,不要失去全国听众。”[8]253
由此可见,“广播电台在‘上帝’心目中的威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有提高。”[8]250正因如此,20世纪90年代的各级广播电台改革中,《小说连播》成为保留节目。1994年4月1日,北京文艺台成立,《小说连播》因其历史悠久、形态成熟、受众忠实而成为少数几个在当天安排重播的栏目[9]。山西省泽州县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是“‘站改台’以来从未间断过的一个品牌栏目”,也是该台收听率较高的文艺节目①参见《泽州县广播电视志》,泽州县广播电视台编印,2011:149。。在受众分流的状况下,《小说连播》以其独特的声音魅力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艺术空间。
二、市场化时代与《小说连播》新变
面对社会、媒介、文学的变化,《小说连播》一直在寻求与时代和社会的对接通道。首先,在选题方面,既“趋新”又“怀旧”。一方面《小说连播》一直在“趋新”——形式方面从单人播讲到两人对播、三人联播、配乐小说、广播小说剧等;内容方面紧追社会热点。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台播出了根据曹桂林小说改编的 22集广播小说《北京人在纽约》。有听众认为:“在‘出国热’不断增温的今天,她的播出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给那些还在做‘美国梦’的人敲了一下警钟。”[10]1997年,反腐热潮中北京台播出根据张平小说改编的《抉择》,几乎就在同时,《抉择》也被中央台和河南台改编,而中央台前后播出达三次之多。热点题材的选取让听众有一种当下感,能让听众保持持续关注的热情。另一方面,《小说连播》又有明显的“怀旧”倾向。一是重新录制了一批“十七年”文学经典,如《红岩》《烈火金刚》等。二是录制了一批契合社会怀旧心理的作品。首先录制的作品内容是对革命氛围的怀旧。1993年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后,中央台录制了《毛泽东的故事》、沈阳台录制了《毛泽东的亲情、乡情、友情》等。其次录制的作品内容是对历史情调的怀旧,如《尘埃落定》(1998年)、《长恨歌》(1998年)、《茶人三部曲》(1999年)等。三是一批20世纪80年代的广播小说精品被点播或重播,如《穆斯林的葬礼》(1992年)、《平凡的世界》(2001年)等。
《小说连播》的“怀旧”倾向是90年代整个社会怀旧的一个方面,其应和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的普遍心理。长篇广播传记文学《早年周恩来》的编辑王葳在提到选材动因时,称这是一个“末代红小兵的怀念”:“我是一个末代的红小兵,周总理去世的时候我刚上学,尽管我从未见过他,但他永远是我的偶像。这种感情来源于父母和当时的环境。”读者来信也反映出其对《早年周恩来》的接受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11]。
在消费社会中,怀旧情绪更容易从一种心理感受转化为可消费和再生产的能指符号。换句话说,经过包装和广告,怀旧可以转化为消费资源。另外,怀旧也是一种生产对象。有学者认为:“现代信息社会,消费者的怀旧消费需求的唤起不单单依赖内部需要,外部的各种媒介提供的信息刺激逐渐成为其需求产生的驱动力。个人的、群体的或社会层面的怀旧通常都与大众传媒有密切关系。电视、剧场、杂志、T型台等不仅是表现怀旧作品的手段,也是烘托、唤醒、传播大众怀旧情绪的手段。”[12]从这一意义上说,《小说连播》的怀旧题材有其存在的受众基础。利用怀旧复兴某种品牌也是现代商业的一种策略,《小说连播》也就利用了受众者的怀旧情结作为节目生产的心理机制,也是商业化社会栏目生存的策略。
创新小说连播机制,也是扩大节目社会影响的策略。首先,《小说连播》栏目增加了与听众的互动,最有效的方式是广播热线的设置。1994年广播小说《尘缘》播送期间首次设置了广播热线,让听众在听节目时设想结局,并及时通话、参与创作。听众对这种互动方式评价甚高:“让听众来共同构思结局,真是独具匠心闻所未闻;让听众展开联想的翅膀,共同参与创作,实在难能可贵。希望继续坚持下去。”因为广播热线带动了听众的参与热情,于是又设置了第二次热线电话,安排了一次听众座谈会和给100名最佳听众举行小说《尘缘》的赠书仪式[13]。这种开放式办节目的办法,跳出了过去传统式的播讲模式[14]。其后,“热线电话”成为《小说连播》与听众互动最重要的平台。到了新世纪,小说广播节目与听众的互动更为密切,内容也更为丰富。天津台的“三六茶座”(播出频率是666千赫)是2006年推出的与听众互动的直播节目,半个小时的时间安排了丰富的内容,如介绍新书,采访作者、编辑及演播者,听众谈自己的感受,朗读听众来信等,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15]。其次,加大宣传力度。早在1982年,中央台朱世瑛就指出《小说连播》宣传不足[16]。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小说连播》的宣传才开始受到重视,利用广播媒介自身或借助平面媒介,如《中国广播报》、制作的画册等推介节目。另外举办各种活动或奖项也是扩大《小说连播》影响的重要途径,如举办电视专题片《飞翔的史诗——小说连播五十年》等专题性节目、设立“中国广播文艺奖”等。2000年以来,小说广播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如天津台《小说连播》有专人负责节目的宣传包装;合肥台的故事广播也制作了很多公益性广告来进行宣传;北京新闻广播的《纪实广播小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宣传到位,开播刚两年已成为新闻频道不可缺少的节目[17]。
三、精品意识:《小说连播》发展的内驱力
精心制作是20世纪80年代《小说连播》吸引听众的根本原因,而20世纪90年代的广播电台因为市场化运作机制,《小说连播》制作和播出了根据畅销书改编的小说。这样的小说以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内容的新奇吸引着受众。针对这种情况,南京广播电台文学编辑陆群批评了《小说连播》节目缺少精品支撑[18]。那么,该如何平衡小说广播“精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呢?深圳台编辑权巍对这个问题有辩证的理解。他认为,作为精神产品的广播节目同时也具备商品属性,但过多卷入市场化会导致广播节目精神品性的削弱[19]306-308。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悖反的关系:精神产品越“精”,市场认知度越低。为了提升认可度,社会上出现了“精神产品应该迎合市场”的观点。持此类观点者认为,强调专业化、艺术化的精品会出现曲高和寡的现象,从而影响经济效益。权巍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其产生的根源是对受众缺乏了解,主观臆断“下里巴人”会对“阳春白雪”避犹不及。事实上,“普通大众才更有对精品文化的追求,而且其欲望更甚。”因此权巍建议,在尊重艺术个性的前提下,重视发挥文学艺术产品的商品属性,以此提高节目的经济效益,“任何企图用降低甚至排斥精神产品的艺术性来提高商品性的做法对我们的传媒业都是有害的,所以,在广播电视节目越来越‘泛娱乐化’的今天,重提‘精品’二字,作用深远。”[19]308权巍的观点在受众那里得到验证,普通大众对小说广播精品也是充满了希望和期待:“与其播一些粗俗低下的作品,不如展播经典名著,这些优秀作品是百听不厌的,是一种艺术享受。”[20]因此,创作精品是《小说连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精品意识是《小说连播》制作的灵魂。
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广播无论从选材上还是制作上,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当代长篇小说仍然是小说广播的主要来源。优秀的长篇小说为广播改编提供了质量保证,而广播又以自己独特的优势扩大了小说的影响,如陈忠实的《白鹿原》,1993年6月,著作一出版就被中央台录制为42集节目在《小说连播》播出。7月份陈忠实在进京参加研讨会时在火车上发现了盗版的《白鹿原》。研讨会上,出版社将《白鹿原》热销的最大功臣归于广播——因为广播使作品当月销售达到了5万册。陈忠实在《白鹿原》播出期间写信给叶咏梅,对《小说连播》在作品传播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白鹿原》一书得以与无以数计的听众交流,这不单是我所无能为力的,杂志的编辑和书的编辑都无法企及,杂志与书的发行量再大也不可企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着眼,我也由衷地向你致以最虔诚的谢意。……”[21]2007年,陈忠实对小说广播的认同仍然情不自禁:“三次连播和此次获奖,让我又添了一份踏实,读者喜欢读听众也喜欢听,《白鹿原》把我创作的原本目的和愿望实现了。”[22]
合适的播读者是将平面文字转化为立体声音艺术的桥梁,也是《小说连播》精品生产的关键。多年的播音经验积累及丰厚的艺术修养使优秀的播读者能够生动准确地传达出原著文字背后的情感意蕴。《白鹿原》的演播者李野默嗓音既淳朴、深沉又豪放、粗犷,恰好符合演播《白鹿原》作为“民族秘史”的史诗风格。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思想性大于艺术性,但曹灿的出色播讲赋予了小说生动的可听性,吸引了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听众。另外,背景配乐、片头片花等方面也都是精益求精,为作品增辉生色,如《尘埃落定》《白鹿原》等片头曲为小说情节的展开奠定了宏阔的历史背景。
当然,精品节目不是形式上的精致化处理,仍需靠内容本身和编辑技巧来取胜,其考验的是编辑的思路、功底和水平。编辑继续延续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改编原则即追求故事性、通俗性、口语化,对小说文本进行单元化处理等。虽看似没有创新,但这种模式化的改编方式适合了受众的欣赏习惯。陆群就非常肯定这种模式化的做法,他说:“在很多人看来,讲创新是艺术的事,讲模式是技术的事,甚至是丢人的事。遗憾的是,他们和其它一些文艺界人士一样,常常忽略了各门类‘艺术’各自不同的本体特性,混淆了模式与创作的辩证关系,把‘创新’的理解表面化、庸俗化了。殊不知广播是一种有着固定路子的媒介,特别是连续广播节目,其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都有非常明确的限制与要求。”[23]可见陆群秉持的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听众所导向的理念。当然,陆群也提醒同行也不要将模式真理化,只是说在追求创新的同时不要无视模式的存在,“就《小说连播》而言,首先是顺应模式的传播,然后才是扬弃模式的创新。”[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