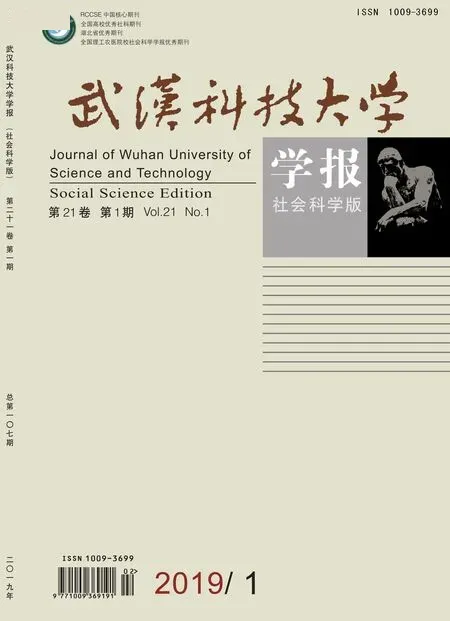楚地、楚风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浪漫主义
——以海外湖北籍作家作品为例
2019-12-21邹建军
邹 建 军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创作引起了学界的特别关注,一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已经相当顺畅,二是因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得到了特别的重视,三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民中有大量人员移民海外,特别是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各国。在这一批新的移民中,许多都是知识精英与商业精英,其中包括不少在国内时就已经有影响的作家与艺术家(严歌苓、张翎、程宝林、王性初等在国内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且有的作品在文坛上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如严歌苓在出国前就著有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人寰》等作品,享有广泛的文学声誉)[1]。当然,海外华文作家受到学界特别关注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因为这批新移民中的作家到了所在国以后,陆续创作出了杰出的作品,许多作品在国内发表以后,在中国以至于在世界上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海外华文作家中,现在看来已经是一流作家的也不少,有的还超过了当代中国大陆的作家。严歌苓、张翎、刘荒田、陈瑞琳等作家和评论家,就其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而言,与国内的一流作家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并且略有超越,为国内学界所公认。以严歌苓为例,其旅美后的作品善于从“他者”文化视角审视、表现东方文化,具有更加广阔的格局与深度。所以,改革开放40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确正在成为国内学术界与批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我们今天讨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与楚地、楚风关系的重要前提。如果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本身没有什么起色,如果从湖北移民到海外各国的作家没有创作出什么像样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或者世界当代的文学史上没有占一席之地,我们讨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也就没有基本的对象,讨论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然而,如果没有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理论,也不足以说明特定地域的文学现象,因此,援用现有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以中国学者自己建构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来观照海外的华文作家及其文学文本,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本文拟讨论以下四个问题,以供方家批评指正:一是地理记忆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时间叙述;二是地理感知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审美意识;三是地理思维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空间建构;四是时间与空间距离与海外华文作家艺术构想之间的联系。
一、地理记忆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时间叙述
在海外华文文学体系的三大部分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当然是移民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一般认为包括早期的台湾留学生文学、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移民文学和第二代、第三代华人用英语所创作的华裔文学三个大的部分,其中移民文学特别是新移民文学占有比较大的比重,作家众多,作品数量大、质量高,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当然,早期的台湾留学生文学中有许多一流作家作品,华裔英语文学也有许多一流作家作品,成为了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与作品[2]。在海外特别是在美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及东欧诸国,那里的华文文学创作与评论,相当活跃与繁荣。第一代华人肯定是移民,第二代以及之后的华人,由于受教育的原因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基本上不再用汉语进行写作,虽然有一些华人后代由于家庭的原因,会产生深厚的中国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然而,他们用英语或其他语种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属于海外华文文学系列,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因此,所谓的海外华文文学,主体部分就是所谓的移民文学或新移民文学。
移民文学是对世界上由于移民现象而产生的文学现象的统称,针对世界上所有的语种与所有的国家,并不只是限于华人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本身是移民国家,第一代人所创作的文学肯定是移民文学,因此,这些国家所谓的移民文学就不限于来自于中国的移民所创作的文学。而“新移民文学”是一个特定的术语,是指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或从台湾、香港、澳门移民到海外各国家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无论是移民文学还是新移民文学,都存在一个时间的问题,并且,他们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里所表达的时间,往往与作家的地理记忆有关。所谓“地理记忆”,就是作家自小开始的对特定地理的印象而产生的记忆,随着自然时间的流逝而形成的种种印象,这样的记忆也许前后并不一致,叠加起来就成为了作家地理记忆的主要内容。如果一个作家其出生地、成长地、发展地、祖居地是同一个地方,地理记忆也许会相对简单一些;如果它们不是同一个地方而是相距很远的多个地方,这位作家的地理记忆则会比较复杂,甚至于相当曲折与繁复。如果一个作家移民海外的时候十八岁,刚刚完成高中学业,或者晚一点如大学毕业的时候,较少机会去到更多的地方,那么他的地理记忆会相对单调一些;如果一位作家在移民海外的时候,已经是人到中年,在人生的中年以前就已经因为读书、服役、经商或从政等原因,到过国内的许多地方甚至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并且所到过的这些地方在地形、气候与物候方面差异甚大,那么,他的地理记忆就会更加复杂,甚至十分曲折。所以,一个作家的地理记忆,不但与所到过的地方有关,并且与在某一个地方所呆的时间长短有关。出生于武汉、祖居湖北广水的作家聂华苓女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因为当时中国已经发生抗日战争,社会动乱不堪,加之外出求学的原因,她已经到过重庆、恩施等诸多地方。解放战争结束之后她先是到了台湾,后来又到了美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这些作品在中国大陆和海外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说她的地理记忆比较复杂,她的作品主要写过去在中国大陆的生活,值得全面研究与深入探讨。聂华苓到了美国以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对时间的叙述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许多从前的地理记忆,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的记忆,成为了其小说叙述的主要内容。她在美国创作的《桑青与桃红》等长篇小说,回忆自己早年在楚地的生活与青春时期的情感,具有重要的地理意义与文化价值。她在台湾创作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叙述的是发生在宜昌三斗坪的故事,小说中对具有恩施地区和三峡地区浓郁特点的地理风景的描写,总是使人想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描写并不比沈从文作品逊色,反而更有特色与味道。至今为止,这部描写鄂西自然山水与三峡地区人文风情的作品,仍然是20世纪以来关注三峡地区自然风情与人物生活最好的小说之一。她在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中,表现自我在抗战期间三峡地区的生活经验以及一批知识分子在大时代里的沉沦与忧虑,保存了特定地理环境之下所产生的地理影像以及那个时代所可能产生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出生于湖北沙洋的诗人程宝林,在老家上了小学、初中与高中,留下了真切的、复杂的地理记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他曾经在《四川日报》做副刊编辑多年,20世纪80年代后期移民到美国。在美国,他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与散文创作,其中许多作品是写他小时候在荆门乡下汉水边的生活,以及那里的山形水势、民俗风情、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所以,地理记忆对于他而言就会简略一些,主要是一种少年记忆和青春期的人生经验与生命历程,没有像聂华苓及其作品中保存的那么复杂。当然,文学作品里的地理记忆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对地理因素特别敏感,有的人对地理因素不太敏感。对于时间的记忆也是一样,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记忆,然而作家对于时间与空间往往都会比较敏感,不然就创作不出全新的作品。
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对于时间的叙述中,存在今天的故事、昨天的故事、昨天以前的故事三种类型。时间越长,也许地理记忆就越模糊,但也许地理记忆就越是清晰、越是深刻,这都是因人而异的,但地理记忆会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地理记忆也会影响作家对于自然地理与人物命运的叙述,则是自然而然的、绝对肯定的和有规律性的。任何作家都不可否认自己的创作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任何海外华文作家也不可否定早年的地理记忆对于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具有重要的意义。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少年记忆,而时间记忆与地理记忆是两个重要方面,同时,时间记忆也不可离开地理记忆,因为地理记忆总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而时间记忆往往是抽象的,如果没有地理记忆,时间记忆就没有依托。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时间记忆与地理记忆往往是一体化的存在,并且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基本内容。每一位作家都会存在地理记忆的问题,然而海外华文作家特别是少年时代与楚地、楚风关系密切的作家,与一般作家相比就会有不同的表现。因为时间因素与空间因素会拉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大,地理记忆与时间记忆会变形,当它们进入特定的文学作品之后,所能够爆发出的力量,非一般文学作品可以相比。虽然不能说海外的华文文学作品全都是浪漫主义的,然而在他们所创作的许多作品中,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亦或包括散文和戏剧,浪漫主义色彩的确是比较深厚的,也许正是在于时间上的距离与空间上的距离,如果没有距离则绝对是现实主义的。而由于移民海外而产生的比较广阔的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则让作家的想象展开了巨大的翅膀,让作家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对人生少年时代的回顾,变得深情而美好。多数作家对过去生活以及生活过的地方的向往,特别是与自然山水环境相关的描写,让许多作品和作家都与浪漫主义产生了必然联系。彭邦祯的诗歌绝对是浪漫主义的,他出生于湖北黄陂乡下,解放战争后期去了台湾,后来又去了美国,还与一位美国诗人结婚并生活了很长的时间,早年的地理记忆在他的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诗歌的形式、语言、词汇、技巧等,与早年的楚地生活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二、地理感知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审美意识
地理感知是地理记忆的来源,没有地理感知就没有地理记忆。当然,对于一位作家或者一般的个人来说,地理感知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经过特别训练,虽然每一位作家的地理感知能力并不相同。地理感知作为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术语之一,意义重要。中国历史上关于地理感知的论述是相当早的。陆机的《文赋》里就有与地理感知相关的论述,并且作了特别强调。《文赋》有云:“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3]揭示了文学艺术对客观世界的依赖关系。四季更替,光阴荏苒,乃至万物变化,都是文学作品内容的来源。作家对地理的感知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作家应该灵敏地感知自然万物的变化,并从中捕捉到万般思绪与感情变化。在时间上笔触灵敏、思绪万端,在空间上要有整体的把控,唯有如此,才能够在整体的关照中更好地认知自然万物。海外华文作家的地理感知,如果没有其移民的经历,与中国大陆本土作家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就是因为作家从原地出生又移民到异地事件的发生。海外华文作家与一般的作家在地理感知上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一个作家没有比较丰富的地理经验,一生去过的地方不多,或者行走的地方本来不少但缺乏对地理的观察,或者对地理认知没有很大的兴趣,也不会因为地理感知的不同而发生重要的文学事件。如果一位作家在国内生活,他没有移民到国外的经历,然而喜欢去各国各地跑一跑,注重地理观察与地理感知,那么地理因素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就会特别显著。海外华文作家对于地理的敏感度,也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然而,由于他们到国外生活产生了空间上的距离,同时也会由于生活得比较久而产生时间上的距离,对于他们的创作而言,就形成了双重的距离,强度相当显著,就会因此而导致一些文学现象的发生。这种文学现象的意义与价值,首先体现在作家的审美意识上。作家的审美意识,是对于表现对象的一种综合性反映,是作家的主体与自然客体之间的对话,是作家的内在思想对自然客体的能动反映。从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审美意识,主要是由以下因素所造成的:第一是自我的民族传统;第二是自我的家庭环境与家族遗传;第三是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地理感知。
地理感知与作家审美意识之间的关系,在海外华文作家及其作品中特别显著。旅美作家吕红出生于湖北武汉,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初中与大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后来移民美国,继续从事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在美从事创作期间,她又回到华中师范大学读博士,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在武汉出生并长大,吕红是一个标准的武汉女子。她对于人物与事件的认识,就带有楚地与楚风的特色,从她的长篇小说《美国情人》、中短篇小说集《午夜兰桂坊》等作品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她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波移民潮中就到了美国,并且长期生活在美国西部大城旧金山,审美意识中又有了一些旧金山因素,热情、开朗、精明、强悍。旅居新加坡的作家孙志卫,出生并成长于武汉,也是一位楚人。《武汉谍战》是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叙述1938年武汉沦陷之后,潜伏在敌后的军统武汉特区和武汉特委组织,分别在李国盛和王家瑞的领导下,与日寇展开殊死的斗争。小说以真实历史事件为线索,将武汉当时的文化传统及历史遗迹自然地融合在故事情节与风景描写中,具有鲜明、浓郁的艺术特色。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武汉的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的描写,准确细致、生动形象,具有一种地理上的真实性和时代上的可靠性。地理因素在一个作家的审美意识中占有多大比重,因人而异。即使在现代交通便利条件之下,有的作家可能只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对于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没有什么观察与感知,有的作家则表现得相当突出。如果一个作家离开了大的环境,只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而了无生趣,如何能创作出杰出的作品呢?能创作出传世作品的作家,总是敏感于自我的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因为从文学的发生与起源而言,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总会有一个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过程。没有外在世界的激发,内心世界的成熟都没有可能,还谈什么思想的深刻呢?出生于山地的作家,其性格中往往会有比较高挺的一面;出生于平原的作家,其性格中往往会有比较开阔的一面;出生于盆地的作家,其性格中往往会有比较封闭的一面;出生于大海边的作家,其性格中往往会有比较空灵的一面。一般来说在二十岁以前,作家的心智就比较成熟,也比较定型。何以为美?何以为丑?取向于正?取向于偏?喜欢男性风骨?喜欢女性风韵?大致已经有所设定。吕红还是比较喜欢明朗一些的东西,而欧阳昱则比较喜欢晦涩一些的东西,这样的风格,与他们从小就开始的地理感知具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地理感知与作家的审美意识的关系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作家的审美意识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里,作品的艺术风格来自于作家的审美创造,作家的审美意识之内涵与特点,与他从小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具有直接关系。出生于楚地的作家,自小生活在楚地与楚风之中,而楚地楚风总体而言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古老的楚国就具有崇火、崇凤、崇巫的传统,不仅在民间文化与文学中得到了保存,并且在屈原与宋玉等人的文学作品得到了保存。楚国的文化传统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在民族文化传统中相当特殊,而海外华文文学里的湖北籍作家,也具有同样的风韵与特征,其来历与来源,可以从地理感知得到合理解释。楚地并不具有统一的、固定的界线,现在的湖北与湖南肯定是楚国的腹地,其文化传统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因此楚地出生的作家,自小开始了自己的地理感知,与其他地方出生的作家就不太一样。古老的楚地,大江、大河、大湖、大泽、大山、大谷,四周高山环绕,中间大河穿行,林木参天、江水流海、云蒸霞蔚,形成了楚地的特有风韵。作家受此地理环境与人文风骨的感染,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就会通过自己的想象、语言、艺术体式、艺术技巧等融合到文学作品中来。旅美诗人彭邦祯的系列诗歌与散文作品,是海外华人文学的重要部分。虽然他一生到过许多地方,包括中国台湾、美国、东南亚国家、法国、英国、德国等,然而他的审美眼光与审美趣味主要还是受到楚地的影响,早年生活所积存起来的地理感知及其内化经验,让他的诗歌想象丰富、空间阔大、情感洋溢、语言华美、长于铺排、气势宏大,形成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楚人的祖先敢于到周天子那里问鼎中原,三年不鸣而一鸣惊人,向往来自天上并不存在的九头鸟图腾,形成了深厚的浪漫文化传统,而这些特性在彭邦祯、聂华苓、吕红等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中,得到了相当的继承与发展。没有当年对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全方位感知,就不会有这样的审美情趣的形成及其审美意识形态的产生。地理感知是地理记忆产生的基础,而地理记忆则可以成为审美意识的主要内容。因此,对于楚地的观察和对于楚风的感知,往往转化为他们文学作品的思想与情感,体现了作家独有的审美意识形态,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浪漫主义的内在证明。
三、地理思维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空间建构
地理思维同样是来自于地理感知,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地理感知,不仅少有地理记忆,也不会有地理思维的完整建立。地理思维是指建立在地理基础上的思维,或者说以地理为主要对象和重要内容的思维。一个人有没有地理思维,首先是看他有没有空间感,其次是看他有没有地方感,再次是看他有没有方位感。如果一个人的思维中没有这三个层面,或者三个层面的东西都比较弱,地理思维就是缺失的、不完整的。当然,一个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完全没有地理思维,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知道一个城市或一个地方的东西南北,完全没有方位感,只是缺失了一定的地理意识。地理思维是指在一个人的心目中有了地理概念,有了比较明确的地理观念与地理意识。如果一位作家对于自己的出生地周围一百公里范围内的山脉与河流,进行过不止一次的实地考察,如果一位作家到过除出生地之外的五个以上的地域,并且对于每一个地方的地理形态有所感知与认知,就具有了比较明确的地理意识,同时也具有了比较强大的地理思维。如果一位作家到过除自己出生地之外的世界上三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并且对于所到国家或地区的各种地理形态比较敏感,他就会具有明确的地理意识和地理思维。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身上,空间距离会对其意识与思维发生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在海外华文作家那里,地理思维的拥有是不存在问题的。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出生地、成长地,来到了自己的发展地,而他们现在的发展地,就往往是其文学作品的写作地。因此,许多海外华文作家的空间感与地方感是比较强烈的。时间的距离越大,空间的距离就越大,在这样的时间与空间中作家展开自己的审美过程,创作出自己的作品,就有别于国内作家。欧阳昱出生于湖北黄州,旅居澳大利亚多年。他的英文长篇小说《东坡纪事》,叙述一位海外华人回到故乡时的所见所感,对黄州自然山水的描述是大量的,对家乡面貌及其变化的叙述是显著的,对家乡当年那种落后、贫穷现状的反思,给人以许多重要的思想启示。在欧阳昱大部分作品中,源于时间与空间距离所产生的意义是相当明确而显著的,不论是写湖北黄州过去的生活,还是写自己在澳洲的生活,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对于其艺术想象与审美构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现出明确的地理思维。出生于湖北武汉的周愚,许多作品是写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然而对江汉之间的地理环境相当熟悉,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地理思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完整地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江汉大地的开阔与神奇,如果没有长江汉水的浩荡东去,其作品就不会有那么宏大的气象与繁复的结构。早年形成的地理思维也因为他移民美国产生了重要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由于时间的距离与空间的距离而发生的。在进行艺术想象与审美构想的时候,横跨太平洋的空间与横跨中西文化的时间,都会产生重要的意义。从中国到北美、到澳洲、到欧洲,从过去到现在,从历史到现实,一个作家的地理思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许多时候都是决定性的。并不是说没有地理思维就不可以从事文学创作,然而没有地理思维而创作出来的作品,恐怕就没有具体的空间感,或者空间感弱小,对文学审美与文学阅读会造成很大的限制。对理论问题的思考也不可离开具体的文学现象,特别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现象。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之所以与中国本土作家的作品有所不同,地理思维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一个是本有的地理思维,一个是处于海外的地理空间,绝大部分文学作品的空间形态就特别显著。彭邦祯诗歌《月之故乡》里的意象,“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不是一种想象而是一种写实。还有如《花叫》这样的华丽之诗,正是一种当代的楚辞:“而春天也就是这个样子的。/天空说蓝不蓝,江水说清不清,太阳说热不热。/总是觉得我的舌头上有这么一只鹧鸪,/不是想在草丛里去啄粒露水,/就是想在泥土里去啄粒歌声。//叫吧,凡事都是可以用不着张开嘴巴来叫的。/啊啊,用玫瑰去叫它也好,/用牡丹去叫它也好,/因而我乃想到除用眼睛之外还能用舌头写诗:/故我诗我在,故我花我春。”[4]浪漫的情思、瑰丽的意象、出人意料的想象,贯穿全诗。在他所创作的系列作品里,诗人以自我的情感为基础,想象奇特、空间独立,与楚国的自然山水之间产生了必然的关联。显然,这样的作品是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因为它们产生的基础是自然地理,并且是在自然地理基础上所形成的强大地理思维。
四、空间与时间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总体格局
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或台港地区作家的文学作品,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体现在严歌苓与张翎的作品中。他们的文学作品视野开阔、思想深刻、格局宏大、艺术精湛,即使写唐山大地震的作品,写20世纪早期美国华人底层生活的作品,写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新移民现实生活的作品,思想与艺术创造也十分明显。就他们自己而言,为什么他们在国外的文学表现,与他们早年在国内的文学表现有如此大的区别?为什么在移民之前与移民之后的文学表现,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不是因为他们在艺术上得到了多大的提升,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与环境,与中国大陆过去的生活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一个是时间上的距离,一个是空间上的距离。不要小看这样的距离,它对作家的审美意识与在创作时的艺术构想,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可以改变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从海外回望中国,很容易是全景式的,当然,也可以是局部性的。他们的艺术视野可以缩小再缩小,也可以扩大再扩大,收放自如,选择的余地很大。所以,文学作品在艺术构想上往往格局很大,同时也有很细小、很深入的地方,感人至深。从现在回望过去,多少年以前的东西都可以回到眼前,并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笔者出生于四川盆地中南部俩母山地区,二千平方公里的穹隆地区。小时候生活在当地,许多事情都看不明白,而当我来到江汉之间,在近40年后的今天,所有的事情都看得相当明白,大部分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来自于对那个地区的人、物、事的重新审视①。如果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距离,许多作品也许就不会产生,因为不会有独特的感觉与独立的认识。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他们与故土之间的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比笔者与家乡的距离要大得多,时间与空间对于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张翎从加拿大回过头来看几十年前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严歌苓在美国回过头来看“文革”旧事,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的人可能会说可以想象,把自己置之度外,似乎是在海外之类的,其实这样的想象是没有用的。一个作家的创作产生于什么样的真实生活,如果想象可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那就不需要我们再来讨论时间与空间。程宝林从中国去到美国,从美国的角度来回顾从前在江汉大地的生活,时间让他产生了美好的情怀,空间让他产生了阔大的视野,在中国所创作的作品与到了美国之后所创作的作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就是一种格局的变化:一是集中于某一方面的题材,二是集中于某一类人物,三是想象的成分加重了,四是对于过去的人与事之性质看得特别清楚。阅读这样的作品,浪漫主义的情怀左右了读者的视线。从表面上来看,每一个作家艺术格局的大小,与时间、空间不会有很大的关系,倒是与自己的人生经历与见识有关,但关键就在于海外的华文作家天然地具有这样的经历与见识,并且由于空间的拉大,让时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距离产生美,并且距离产生大美,产生更加丰富、更加特别的美,是中国本土的作家所不具备的,这就是地理基因在文学创作中所生发的重要意义。海外华文文学在改革开放40年时间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流作家越来越多,杰出作品也越来越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每一次会议,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海外华文作家的身影,同时也感受到他们对于文学的极大热情,这与他们的移民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与他们所在国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地理上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以及时间上的地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对于他们而言是需要直接面对的,每一天、每一地,都是如此。因此,他们的创作格局与从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相比,就更加宏大、更加深厚,并且总是有一种文化上的比较与历史上的混杂,也容易产生对于相关的哲学与美学问题的思考。
五、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浪漫主义
楚地的特点、楚文的优势与楚风的传统,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也具有重要的联系。许多作家与学者一生都生活在江汉之间,楚国的腹地,是楚文化的核心区域。楚地的特点是南北东西大山,几条大河四面奔来,皆从武汉流出,而直至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上游的长江、北来的汉水、南来的湘水,以至于所有的江河都流过江汉平原,滋养了长达五千年历史的楚文化与楚文学。这里的地理环境特别,古之云梦大泽,今之洞庭大湖,以至于湖北的千湖与武汉的百湖,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名称。自古以来,虽然自然地理环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然而云蒸霞蔚、湖光山色、猿啸山林、渔舟唱晚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填湖很多,森林砍掉不少,然而这些年来退田还湖、退耕还林政策的落实,自然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山环水绕、山水相济、森林密布的基本格局,仍然在对这里的文化与文学发生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中,楚风、楚俗之特别,自然而然;楚地多巫风、信鬼神,自古而然。在湖北与湖南的许多地方,傩戏的传统还是保留了下来,并且在最近一些年来,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人的生老病死,地方上有一整套的仪式,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完全丢掉,在这种仪式中往往都伴有鬼神色彩,是中国人古老的信仰所致。同时,地方信仰的范围还是相当广泛的,一个小小的地方都会有自己的寺庙,对于山、水、树、石、沟、谷、火、鸟等,都会有所信仰,称之为神。如果说到楚文,那么它与楚地、楚风是密切相关的,楚文是对于楚地、楚风的文学与艺术的表达。所以,浪漫主义的精神与气度,在楚文化与楚文学这里就是自然而然的,似乎也没有人故意地要去追求,或者专门进行打造。楚文化的传统就是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这个词虽然来自于西方,但对于楚文化与楚文学而言,是比较恰当的一种历史概括。我们从战国编钟、青铜器、漆器与台榭的风格中,从屈原、宋玉的辞赋中,都可以得到切实的证明。
这样一种相当的浪漫主义精神,是不是被湖北作家带到了海外,并且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得到了保存与发扬?根据笔者有限的阅读,可以肯定的是,从湖北去到海外的作家的作品,的确显示出了与其他地方作家不一样的艺术风格与美学追求。我们可以从聂华苓、王默人、吕红、欧阳昱、欧阳海燕、张劲帆、程宝林、杨恒均、彭邦祯、孙志卫等人的作品中,找到有力的证明。彭邦祯的大部分作品,其文辞的华美、情感的真挚、想象的丰富与艺术上的大起大落,与屈原的浪漫主义文学是一脉相承的。程宝林的散文主要写其少年时代在老家的所见所闻,在对于楚地、楚风的记录中,体现的也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聂华苓、孙志卫等的小说,对于情的表现和对于景的营造,与楚地文风是完全相通的。其他地方出生的海外作家,就少有或没有这样的特点。严歌苓出生于上海,所以其作品就不是浪漫主义文学,而是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的。张翎出生于浙江温州,她的作品也不具有浪漫主义风格,而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兼具。所以,楚地出生的作家与诗人,虽然他们的作品也并不完全相同,然而大体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超强的想象力、空间的开阔性、文辞的典雅华美、激烈不已的文风,这就是楚地、楚文和楚风给他们带来的独到的东西。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极其独特的存在,无论从生存方式还是从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外国文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部分。就像中国也有英语、法语文学一样,我们没有把这样的文学当成外国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为作家生活于、工作于、创作于哪个国家,就属于哪个国家的文学,从其性质而言,它们是中国文学向海外的一种延伸、一种扩展。海外华文文学的构成与发展,与中国本土的地理与文化具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作家是从中国出去的,并且在中国留下了重要的生理与心理的烙印。本文从地理记忆到地理感知,再到地理思维与地理时空,以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术语为工具,分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特别是出生于湖北的作家在海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从逻辑上而言是严密的,从根据上来说是可靠的。海外华文文学中存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倾向,其中的浪漫主义倾向的确与楚文化的浪漫主义传统有着重要的关联性,具体体现在从湖北出去的一些作家作品上。在今天的世界,移民文化是一种值得探讨的重要文化现象,通过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分析与对海外华文作家的探讨,说明一种传统文化的移植是可能的,文化在另一个空间的发展也是可能的,但与原生地的自然形态与内在影响也是不可分割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构成与发展,正是世界各国移民文学产生与建构的典型标志。
注释:
①十五年以来,笔者创作了散文八十篇、赋一百篇、十四行诗九百首、拟寒山体七百首,至少有一半作品的题材和人物来自于早年生活和反思早年所见所闻。参见邹惟山:《时光的年轮——邹惟山十四行抒情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邹惟山:《邹惟山十四行抒情诗集》(长江出版社,2012年版);邹惟山:《邹惟山十四行诗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