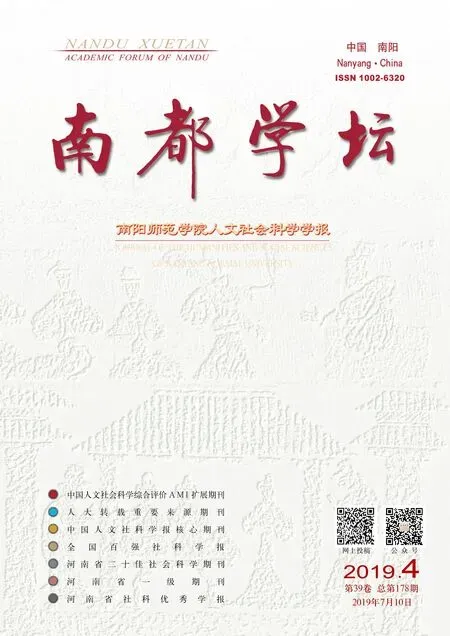《水浒传》的文本演绎与说唱色彩
2019-12-16戴云波
戴 云 波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 100055)
《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奇在何处?奇在它虽历经不同时代,并出自众手,但最终竟成为一部脉络清晰、体系完整,且生气氤氲、富于传奇色彩的大书。今人治《水浒传》者,多从其作者对象、版本源流、评点内容、主题思想等方面用力,至于《水浒传》是如何因其故事原型的不断繁衍、壮大而日臻丰赡严密,其内生原始的驱动力何在,似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阐释。本文力求在这一方面有所见解,或于增进《水浒传》研究上有所裨益。
一、说话、词话皆为说唱兼备之体
说话、词话、平话、话本、唱本,在其原初均为民间说书艺人演绎故事之底本。现代意义上的由文人有意为之的小说创作,要到明中叶以后方逐渐成熟。因此孙楷第先生有言:
宋话本在元末明初,已有重订无词之本,为什么不说短篇小说出于元末明初,而偏说明末才有呢?这个问题容易答覆。因为重订不是作,自作的短篇小说,明末才有。明末人作短篇小说,是学宋、元话本的。因此,明末人作的短篇小说,从体裁上看,与现存的宋元话本相去甚微。但论造作的动机,则明末人作短篇小说,与宋元人编话本不同。宋元人编话本,是预备讲唱的。明末人作短篇小说,并不预备讲唱,而是供给人看。所以,鲁迅先生作《中国小说史略》,称明末人作的短篇小说为“拟话本”,不称话本,甚有道理。[1]
唐传奇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但由文人主体有意为之的创作成分仍然不足,而唐代的俗讲、变文则已然是在向着小说的世俗化、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又如孙楷第先生所言:
唐朝转变风气盛,故以说话附属于转变,凡是讲故事不背经文的本子,一律称为变文。宋朝说话风气盛,故以转变附属于说话,凡伎艺讲故事的,一律称为说话……最可注意的是,说故事在宋朝,已经由职业化而专门化。宋以前和尚讲经,本不是单为宣传教义,而是为生活。唐五代的转变,本不限于和尚,所以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但唐朝的变场、戏场,还多半在庙里,并且开场有一定日子。而宋朝说话人则在瓦肆开场,天天演唱。可见说故事在宋朝已完全职业化。[2]
能够证明唐代已有说话并兼具表演性质的材料,可看《元氏长庆集》第十卷《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自注:“尝于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按注中所说,倘若能够五六个小时不断地宣讲一个故事、演绎一个主题,其中没有表演的成分是不可想象的。
能够证明词话话本可唱的材料,可见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七十五中的一首名为《即事》的七绝,诗前小序并诗作原文为:“歌者屡召不至,汪生狂发,据高座剧谈《水浒传》,奚童弹筝佐之,四席并倾。余赋一绝赏之:‘琥珀蒲桃白玉缸,巫山红袖隔纱窗。不知谁发汪伦兴,象板牙筹说宋江。’”[3]这条材料不仅说明《水浒传》故事文本在其本来的面貌是可以说、可以唱的,也说明小说的原始形态,即话本、词话、唱本等,都是具有演唱、表演的功能与形式特征的。
可以肯定,这个“讲故事”“说话”,已不仅是为了某一宗教法旨的宣讲或劝世功能的发挥,而是要作为一门手艺,在不断职业化、世俗化的进程中,能够吸引到听众,从而谋取衣饭之资。因此除却其表演中的说唱结合,亦需在内容上不断有新的丰富与改进,使之愈贴近、切合于听众的嗜好与品味。这也是何以说话、词话中多奇绝险怪甚或荒唐无稽之内容而较少凿实有据之史实的缘故。当然,按照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中对“说话”四家的划分,其中有“讲史书”的分类,应当是指建立在一定史实基础上的演义。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五种》以及“抄撮旧籍”而成的《大宋宣和遗事》,虽然具体的作者与所作时代均无明显的标识与证据,但根据内容、风格及其所依托的社会背景特征,应当就是宋元之际讲史艺人们的集体创作。
二、《水浒传》系由各种不同的词话、唱本繁衍而来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曾下过一个结论:“《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4]因为出自众手,特别是建立在不同地域与众多的民间说话艺人的创作基础上,一方面固然使得后来所谓的“文人加工”变得曲折反复而且艰难,另一方面却也因此支撑起整个《水浒传》的架构,以一种浩瀚澎湃的气势与生命力,驱使《水浒传》故事不断向前演绎。
言及《水浒传》自身的版本渊源及承袭脉络,不能不谈到“水浒学”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即由鲁迅先生提出的“繁”“简”关系问题。虽然鲁迅先生于《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水浒传》当时所能见及的本子做了详密细致的分析,但得出的结论即“简先繁后”却不为后来的大多学者所认同。究为“繁先简后”或“简先繁后”,笔者以为倘能够说明《水浒传》的核心人物特别是骨干情节系由词话、话本、唱本发展演绎而来,则足证“繁先简后”结论之成立。
一是因为是不同地域、不同书会才人对《水浒传》故事的创作与演绎,从《水浒传》文本在早期演进中所透露出的信息看,《水浒传》的原始形态,亦即《水浒传》的词话本、说唱本形态,表现出更多的地域特征。比如著名的龚开(字圣与)《宋江三十六赞》[注]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见《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虽是仅就宋江36人的绰号上做文章,但中间四次提到“太行”,显系对早期《水浒传》故事话本中“太行山系统”的一种收纳与归集。此外还有宋江起兵淮南的传说[注]明朝吴从先《小窗自纪》卷三“读水浒传”中有“方腊起于睦州,宋江起于淮南”语,见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水浒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5页。。侯会先生亦认为,今本《水浒传》之前应存在着一个“带诗本”,“‘带诗本’应当是一个综合本,综合了早期各派《水浒》故事,包容了太行、淮南和山东三派早期传说”[5]。这应能说明《水浒传》故事传说是在不同地域的民间艺人进行创作演绎的基础上,向着梁山泊故事系统在不断地凑拢与汇集。
二是在这种不断地凑拢与汇集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个相互比较、借鉴、增删、改作等不同形式的修正过程。比如“开场诗”“致语”“引首语”“楔子”等对小说文本起引导、概述甚至渲染等方面作用的内容部分,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水浒传》版本中至少“开场诗”是保留的,但并没有那么多的“摊头”“头回”“楔子”等。一个“洪太尉误走妖魔”即可作为全本《水浒传》的“楔子”。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下》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6]190如果说对这一段话尚可理解为系针对“繁本”情韵之丰赡、叙事之详密而言,那么在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所指“古本有罗氏致语”中之“致语”,“旧本去诗词之繁芜”中之“诗词”[6]133,钱希言《戏瑕》所指“词话每本头上,有请客一段,权做过德胜利市头回……即《水浒传》一部,逐回有之,全学《史记》体。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中之“德胜利市头回”“摊头”[6]135,天都外臣《水浒传序》所指“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中之“妖异之语”,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一“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中之“楔子”[6]137,等等。虽然对这些术语的定义尚有着不同的说法和争议,但一个总的、也是符合小说创作规律的趋势是,与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关系不大的部分,不论是叫“楔子”“摊头”或“致语”等,它们一方面在民间艺人的口头是不断发展着,另一方面在文人加工改作的书面中却是不断减少着。实际就是在《水浒传》由民间艺人表演向文人创作进化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个韵语、骈文不断减少而故事情节逐渐增多并趋于严密合理的过程。
说话的技艺因为皇帝的爱好,需要供给皇帝的娱乐而受到当时人的看重,如郎瑛《七修类稿》就说:“小说起宋仁宗时,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云云。” 何谓“得胜头回”?谭正璧先生曾解释道:
本来,说话人在说话之先,听众未齐,必须打鼓开场,《得胜令》就是常用的鼓调。《得胜令》又名《得胜回头》,又转为《德胜头回》。后来说书人开讲时,往往因听众未齐,须慢慢地说到正文,故或用诗词,或用相类故事,也“权做个《得胜头回》”。[7]
这也可以帮助说明《水浒传》的原始形态。
三是作为世代累积型作品,均存在一个对不同地域、不同系统、不同时段、不同作者所产生的故事的汇集与凑拢过程,其间虽经必要的删削与改造,但仍不免有事理不合或情节龃龉处。于《水浒传》而言,最著名者一为卷首王进之“神龙见首不见尾”,另一个则是“移置阎婆事”。有学者称后来简本插增“王庆举义”一事,人物原型实为王进,但因人物性格相去甚远,仅可聊备一说。关于“移置阎婆事”,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有“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一句话。问题是郭武定本,也就是郭勋改编、增进的本子原貌今天不复得见,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繁本较早者如天都外臣本、容与堂本,简本如《水浒志传评林》《水浒忠义志传》等本子并无“移置阎婆事”,也就是仍然保留了自刘唐月夜送信、送金条与宋江,直至宋江纳阎婆惜、杀阎婆惜之间存在过长的不合理时间差问题,只有后来经过金圣叹删改的贯华堂本处理了这个问题。此应为小说话本在凑拢过程中存在不严密问题的标识。此外因为要凑够108之数,在大聚义前须说动卢俊义上山,于是有了“吴用智赚卢俊义”一节,但随后的关目却过于松散,以致卢俊义不仅身陷囹圄,而且两次均险些丧命,应当可视为作者笔力已经不逮。
四是在不同《水浒传》故事系列的汇集与继续繁衍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时空概念、绰号称谓等不一致的问题。一是关于《水浒传》文本[注]本文引用《水浒传》文本资料如无特别指明,均采自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中应体现的时代问题。在第三十五回“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中提到李逵叫骂:“便是赵官家,老爷也鳖鸟不换!”“老爷只除了这两个,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这口气似为宋时口吻。但在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及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中均出现“故宋时”字样,又显系宋以后时代语气。由此可以判断,《水浒传》故事之成型、成熟当在南宋末年直至元代,书会才人在时代口吻的把握上尚处于一种可宽可严、听众并不会误解的境地。二是关于绰号称谓的问题。比如在成书于南宋末到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已经大致给出了宋江之外36人的姓名、绰号,而在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记载的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中,在绰号、称谓上则更接近于后来成熟的《水浒传》,如“智多星吴家亮”变为“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李进义”变为“玉麒麟卢俊义”,“混江龙李海”已成为“混江龙李俊”,“大刀关必胜”变为“大刀关胜”,张顺的绰号“浪里百跳”变为“浪里白条”,“美髯公朱同”变为 “美髯公朱仝”,等等。这说明一方面在南宋末年那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在爱国情绪与民族斗争的氛围中说书人逐渐将口中的水浒人物赋以时代的背景底色,另一方面在《水浒传》人物的事迹搬演与名称叫法上渐近统一。
五是《水浒传》文本体现出较鲜明的话本抄撮与集纳的特征。对此著名水浒学家李永祜曾指出,高儒《百川书志》中所谓“《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中的“施耐庵的本”,就是《水浒传》达到一定完善程度的祖本,系由施耐庵“集撰”,也就是集合不同的话本材料完善而成,后来又由罗贯中重新编次、增订以及进行主题的提炼与升华。其证据是“武十回”“首尾完整,一气呵成”,关于武松故事的“单传原本即有良好的基础,比较成熟”,同时,其还有两个重要的内证:
一是奇长的篇幅,二是施或罗拟作断章的字样。今本《水浒传》,每回六七千字者共二十一回,七八千字者共二十七回,其余回目少者四五千字,多者超过万字,平均在八千字左右。唯独西门庆偷情部分的第二十四回为一万八千余字,第二十五回为近一万六千字……这种特异的情况,正是说话人为自己所镕铸的丰富的故事情节所激动,滔滔讲来,欲罢不能的自然留存,是水浒故事的原生态面貌。也正是有鉴于此种极端的字数悬殊,《水浒传》的集撰者施耐庵(也或许是罗贯中)才拟重分章回,欲使字数稍加平衡。在第二十四回郓哥将出场时,写下了“断章句”三字,作为重分章回的标志。[8]
因为“断章句,话分两头”这几个字一直被作为正文留下,我们今天也当然可以将它理解为作者重新编排结构、划分章节的一个记号。
遗憾的是,今天由于《水浒传》学界始终没有寻找到一部类似于《三国志平话》那样的具有“祖本”“雏形”“发源”意义的“水浒传平话”,这样我们只能一方面肯定《水浒传》系建立在历代说书艺人话本及戏曲舞台演绎所综合积累的材料基础上,另一方面当然也必须承认施、罗二人所付出的重新勾画的功劳。
三、《水浒传》文本体现出的说唱色彩
《水浒传》就其文本的性质而言,实由词话、唱本繁衍而来,其中的内证资料如王利器、孙楷第等学术名家均已有所发现,但我们还可从文本中找出一些实例,借此说明《水浒传》的表演性质与说唱色彩。
一是《水浒传》文本中处处表现出说书口吻与说话色彩。比如全书开篇“引首词”中的前两句:“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似在明喻《水浒传》乃出自众多书会才人之手。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中,写鲁智深私自卷了金银酒器下山去了,即将转入下回,文中插一句“看官牢记话头”,此显系说书人之口头成习。在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中也有:“说话的,却是甚么计策,下来便见。看官牢记这段话头。”此外在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中,写武松在柴进庄上并不受人待见一节,作者为此做出解释:“说话的,柴进因何不喜武松?”这是典型的说书人在讲说过程中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来交代一些情节原委的口吻,而相同的表述在其他回目中多有出现,如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中,写吴用定计劫法场,前面卖个关子:“说话的,如何不说计策出?管教下回便见。”等等。《水浒传》文本中还时有对一段叙事关目进行主题提炼或名称总结的写法,如上述同回书中末尾即有“这个唤做‘白龙庙小聚会’”一句,在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末尾有“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一句,均是总结上述诸般情节,同时也恰恰证明这些故事原来已经相对独立地在流传,并且有了自己的称谓。
二是《水浒传》文本中虽然历经多重删削但仍存在大量韵语骈文,主要是对山川景色、人物装扮、事物情理等,进行描摹、刻画、抒情。如第二十三回中对武松打虎壮举引述一篇“古风”进行赞美,第四十八回中引用一篇类似歌行的“诗赞”来描绘祝家庄“独龙岗”景象,等等。从今天的创作角度而言,《水浒传》文本中存在的大量的韵语骈文很多意义并不大,对于故事发展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亦非必不可少,但我们可以理解,一方面这是《水浒传》故事在说话、话本、唱本阶段留下的遗痕标识,另一方面这也是在实际的艺人讲说表演中,因为生存的需要,艺人们需要唱诗或吟诵韵语来等待听众、安定情绪,同时说书表演系以时间计算酬劳,不可也无须用足时间去讲解精彩的情节,需要有诗词、韵语以及噱头等,来做缓冲、卖关目、存悬念。
三是《水浒传》文本中出现不少“隐语”“偈语”。如九天玄女娘娘天书中对宋江的四句诗,智真长老对于鲁智深给出的两次“偈语”等,除却喻指人物的前途命运、暗示将来的情节发展外,这也同样是古代小说创作中经常用到的一种手法,以增强小说的悬念,宣扬天道轮回的观念。按照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等宋人笔记中对“说话”四家的划分,应属于“合生”“商谜”或“说参请”一类。对此孙楷第先生曾解释说:
大概合生以二人演奏。有时舞蹈歌唱,铺陈事实人物;有时指物题咏,滑稽含讽。舞蹈歌唱,则近杂剧;铺陈事实人物,则近说话;指物题咏,滑稽含讽,则与商谜之因题咏而射物者,其以风雅为游戏亦同。所以,我假设合生是介乎杂剧、说书与商谜之间的东西。[9]
小说、说话本系从讲说佛经中的“经变”“俗变”演化而来,虽然越来越多地添加了世俗生活的内容与凡间社会的心理,但始终对神灵、神秘的事物仍保持有足够的兴趣,这也从另一方面足证《水浒传》的话本特质。
四、《水浒传》故事如何成为民间传说演绎的核心
为什么《水浒传》或者说宋江的故事会逐渐成为一个“集中悬拟的箭垛”,并在宋末元初有一个大的繁衍与发展?这种内在的力量是由何产生的?无论如何,宋江与同时代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声名气势均要显著得多,但在元曲《同乐院燕青博鱼》中燕青却言:“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宋江与方腊明明是同一时代的农民起义领导者,有何不同?
是否真如李卓吾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所说的“《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但说《水浒传》是一部“愤书”,可能又过于强调民族的立场。对于《水浒传》这样一部“奇书”“大书”而言,其内涵丰富,主题深刻,蕴含着许多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探究和挖掘的社会文化观念与伦理思想,仅仅依靠民族感情的张扬恐怕很难成就其不朽的艺术魅力。
一方面《水浒传》文本中也存在多处与其他农民起义史实进行比附的诗句,这固然可证明书会才人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似可说明《水浒传》在创作演绎的过程中受到了其他农民起义史实的启迪或鼓舞。根据余嘉锡先生《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及孙楷第先生《〈水浒传〉人物考》所述,《水浒传》人物,特别是梁山人物除宋江作为造反首领较为“勇悍狂侠”外,在史籍中有名者(这里必须要排除掉许多重名、化名的因素,能够坐实人物本事者极其稀少)大多并无凸显的事迹与性格。但在《水浒传》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回末出现“有分教: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在第十七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回末有“直教红巾名姓传千古,青史功勋播万年”句。前者似隐喻王彦统领的著名的抗金义军“八字军”,后者则与元末的红巾军扯在了一起。这种比喻的跨度与联想的空间一方面说明了抗击外族侵略、反抗黑暗暴政在任何时代都会是一个永恒且激动人心的主题,代表着一种共同的社会理想与大众情绪;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水浒传》故事的演绎与传播,其内生动力的源泉也正在于这种理想与情感的导引,虽然若认真考究文本逻辑、历史史实等方面常不免有失真悖谬处。
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九中有这样一段话:
绍兴元年十二月,邵青受招安。先是杜充守建康时,有秉义郎赵祥者,为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脱身归,乃依于内侍纲。纲善小说,上喜听之。纲思得新事编为小说,乃令祥具说青自聚众已后踪迹,并其徒党及强弱之将,本末甚详。编缀次序,侍上则说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单德忠之忠义。
对此,余嘉锡评述道:“可见小说喜演草泽英雄故事,所谓铁骑公案也。邵青聚众之时,声势不广,影响不大,且人尚生存,犹得编为话本,况宋江之声称赫然者乎!”[10]王国维亦言:“宋之小说,则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11]28“小说但以口演,傀儡影戏,则为其形象矣……”[11]30注重内容的传奇性与传播的表演性,是小说、话本的特质,这一特质即使在明代末期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进入到较高的层次也还存在并保留着。
事实上,《水浒传》的故事之所以会在宋末元初有一个大的繁衍与发展,及至经过话本的演绎说唱与戏曲的创作搬演,其根源就在说书艺人有意或无意地对宋江性格的不断美化及其对“忠义”品格的塑造上。
比如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中在论赞宋江时是这样几句诗:“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也就是宋江不仅没有僭越“称王”,而且忠心报国,后来因受到奸臣的陷害最终“魂聚蓼儿洼”。这样的悲剧人生无疑是最能够吸引听众并且能够引起社会的共鸣与同情的。
到了元杂剧中,宋江的出身经历与形象趋于固定。以《还牢末·楔子》为例:
宋江[白]:幼年郓城为司吏,因杀娼人遭迭配。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某,宋江是也,山东郓城县人。幼年为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娼妓阎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路打梁山泊所过,有我结义哥哥晁盖,知我平日度量宽洪,但有不得已的英雄好汉见了我,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及时雨宋公明。今晁盖哥哥并众头领,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之后,众兄弟让我为头领。
这段楔子、自白在现存元曲“水浒戏”中大同小异,与现在流传的《水浒传》主要情节也大体相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因为史料的缺乏,关于宋江的事迹包括个人性格与形象在元杂剧前的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与《大宋宣和遗事》中并不具体,但需要认识到的是,《宋江三十六赞》只是对于民间流传画像所作的评点之语,《大宋宣和遗事》是对于当时所流传的各种札记逸闻的综合,都不可能非常鲜明具体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与故事的情节。在元杂剧中我们看到了“平日度量宽洪,但有不得已的英雄好汉见了我,便助他些钱物”这一句,不管这是之前民间传说的产物还是元杂剧所加,宋江之形象趋于完整、丰富可无疑矣,也因此而具有了领袖的气质与底蕴。
总之,围绕着这样的素材与主题,说书艺人们建构起了从《大宋宣和遗事》到《宋江三十六赞》,再到集大成的《水浒传》这样一条说书、评话、传说的繁衍之路,事实上也正是对于宋江这一历史人物的史实内核进行不断积累、放大的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