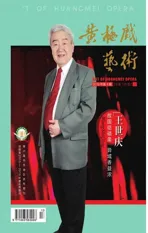此曲原为人间有—— 黄梅戏《玉天仙》观后
2019-12-16□苍耳
□ 苍 耳
笔者看过不少黄梅戏,但《玉天仙》一剧让我眼前一亮,如见活泼健壮、清眸流盼之处子。我的兴奋还有另外的原因。零八年我在《随笔》第四期发表“草台的命运”一文,出乎意料地引起省内戏剧界老专家的热烈反响。该文反思了戏剧史上的“三改”,并对当下戏曲越来越偏离民间和草根提出质疑,提出回归戏曲本体,回归民间母体,回归人性命题。柏龙驹先生从省城来安庆一定要见我,在东升宾馆与我畅聊黄梅戏话题,建议《黄梅戏艺术》转载这篇文章。一晃十一年过去了,黄梅戏在回归的道路上似未见进展,倒是看到不少精心打造的“大戏”,因流于说教而难获观众青睐。《玉天仙》的出现,不妨说是个例外。
《玉天仙》在“三回归”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而重要的一步。在我看来,回归戏曲本体方为根本,回归民间母体和人性命题乃必经之径。
所谓戏曲本体,便是戏曲之为戏曲的那个特性、程式和韵味,是戏剧性所生发、激荡的本源。一部戏像不像戏,看完后直觉会告诉你,这个直觉便是“戏味”。这类似诗歌,好的诗歌必有诗味。戏味也可以说是戏剧性的集中而直觉的体现。无戏味,此戏便失败了,尽管它高大上,路子很正。一旦违背了戏曲之为戏曲的本体性,戏曲性蒸发,戏味从何而来?经典戏剧经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注重戏剧冲突,巧设翻转,在剧情陡转或空间并置的对比中,在双重身份或双重面具的张力中生成艺术传奇;而在场与场的转换中,唱念做打的细节是否精致合理,是否生动诙谐,无不关联戏曲性的强弱浓淡。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李尔王》《哈姆雷特》《奥赛罗》,中国古典悲剧《窦娥冤》《赵氏孤儿》,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小辞店》莫不如此。恕我直言,当下有些戏连基本的戏剧冲突都匮乏,没有跌宕翻转的剧情起伏,无花脸,无小丑,无噱头,无风土俚俗,一本正经,不好看不耐观,戏味从何而来?
回归戏曲本体,在当下首先意味着去赘化、去繁化。最近三十年,附加在戏曲身上的“赘物”有增无减,被光电化、说教化、美术化、高科技化,包装过度,炫丽成风,演出成本超高,躯体越来越庞大、臃肿,不堪其重,戏曲之为戏曲的本体元素反显暗弱了。仅舞台上的布景、道具、灯光、戏幕不断翻新,越来越繁复、奢华,喧宾夺主,且不说令任何一个古代戏班望尘莫及,即便当下县乡水平的剧院也望而却步。新编黄梅戏《玉天仙》既无布景,也无须换“幕”,仅有两根粗大而古老的麻绳,道具不过一桌六椅,场上乐队仅六人。舞台中央悬吊一根麻绳,打了两个扣,令人惊心;台上用一根麻绳圈定一方表演场域,令人意外。可以说,戏里戏外,角色互换,乐队演奏,皆以绳圈为界。但“麻绳”达到的效果却以一当十,兼具布景、道具的功能,更有深化命题的象征意蕴。同时,该剧人物配置也简单,男女主角加上四个配角,配角兼串屠夫、媒婆和“七嘴”“八舌”等众多角色,所有角色均不退场,成了活的“布景”,让人想到从前戏班演出的鲜活场景。
事实上,传统戏曲和草台戏曲之所以生命力旺盛,大受观众欢迎,正在于它们化育于民间,也流传于民间。在现代背景下,戏曲何以要重提回归民间母体?原因在于民间的丰厚渊深,不仅提供鲜活奇异的戏剧素材,更可以容纳艺术的多元性和价值的多维性。巴赫金毕生研究中世纪民间文化及拉伯雷文本,他认为,民间狂欢化“所遵循和使用的是独特的‘逆向’‘反向’和‘颠倒’的逻辑,是上下不断换位如(‘车轮’)、面部和屁股不断换位的逻辑,是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戏弄、贬低、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废黜。”说白了,民间立场看取事件和事物态度不取单面、单一的价值判断,而是在二元或多元之间保持多维、换位、互否的活力。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同体性,诸如旧和新、盛和衰、明和暗、上和下、丑和美、垂死和新生、灵和肉、始和终,均处于共时同在、相互循环的关系中。原初的傻瓜、小丑乃至魔鬼的形象基本是正反同体,内外、智愚、高低、美丑之间的强烈反差并没有偏废一方,而是正与反保持张力,互证互否。愚蠢是反过来的智慧,大丑是倒过去的真美,疯狂是清醒的极致状态,悖谬是真理的另类传达。在官样文学中,傻瓜、小丑乃至魔鬼的形象逐渐变成单面性的了,仅仅成了国王、君子、英雄的陪衬和插科打诨的工具。
《玉天仙》改编、移植于其他剧种,故事原型来自汉代朱买臣被迫休妻的野史记载,历经两千年演绎、流传,生成难以尽数的戏曲版本,昆曲、京剧、川剧、晋剧、梨园戏均有此剧目,如京剧《马前泼水》,讲的是朱买臣妻崔氏不甘于生活清贫,逼夫写下休书离婚,改嫁他人。后来朱买臣中第,出任会稽太守,崔氏乞求复合,朱买臣马前泼水,让他收起覆水就同意复合,崔氏因羞愧而撞死街头。以男主角朱买臣的角度演绎这个故事,其妻崔氏被塑造成嫌贫爱富、逼夫休妇,最终自取其辱,为历代所嘲笑、唾弃的可悲村妇。
《玉天仙》一剧抛弃传统戏曲的单边立场,将男性叙事与女性叙事加以并置,从朱买臣和玉天仙的视角对等展开戏剧情节,从而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上形成张力;尤其玉天仙之独特视角——通过她的唱与对白,痛述一个乡村女性的内在诉求,将因贫弃夫、改嫁梦回、再遭羞辱,以致走向自裁的精神脉络展露无遗,在世人面前揭蔽人性的悲剧尤其女性的悲剧,戏剧性由此得以升华。改编者从传统伦理和男权视角解放出来,回归到多元和多维的民间立场,在人性命题上深入挖掘,搔到引发现代观众共鸣的痒点和痛点。
在我看来,这个痒点和痛点,正是男女主角摆荡于物质欲求(物欲)与精神欲求(灵欲)之间的苦苦挣扎。舞台上悬吊的麻绳打了两个结,可以视为物欲与灵欲的形象暗示。朱买臣和玉天仙并非懒堕、龌龊之人,夫妻俩是良善而勤勉的。然而,朱买臣饱读诗书二十年仍无路受荐为官,食不果腹,衣不暖身,饱受嘲笑,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书生气闹出不少酸腐笑话;但面对赤贫和被离婚,他仍不坠青云之志,继续苦读求仕,这是他广受同情的重要原因。《玉天仙》保留了这一有价值的成份。在朱买臣成为朱太守后,他要求从屠夫手中“赎回”妻子以便破镜重圆,不论出自真心还是报复,仍可以看出男主角摆荡在物欲与灵欲之间的挣扎和扭曲。他竭力在世人面前证明自己,他做到了,但得到的无疑仍是苦果;玉天仙悬梁自杀后,苦果变成了悲果。然朱买臣并不能理解她何以死。正因为他不懂她,其所作所为即便出于爱意,也仍然将玉天仙逼上了绝路。可以说,朱买臣被离婚,玉天仙被悬梁,看似不该发生的发生了,不该悲剧的悲剧了。这是深层错位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
再看剧作家对女主角的处理。该剧一反传统戏曲中那个嫌贫爱富的“崔氏”形象,寄予这个弱女子以深切同情。玉天仙并非一心追求大富大贵,而是梦想过上有灵有肉、温饱而体面的生活。命运偏偏让玉天仙嫁给一个五谷不分的读书郎朱买臣,在二十年做不了官的苦熬中,连温饱也解决不了,以致她身上强烈的物欲摧毁了原本视为高贵的灵欲,逼夫休己实出于想活下去的万般无奈。这固然饱受不同时代观众尤其男士们的指责,但玉天仙并非女中精英,她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再普通不过的村姑,无法做到尽善尽美,而这正是人性的普遍弱点或特征。问题是,当她改嫁给一字不识的屠夫后却陷入另一重困境:物欲满足后,灵欲的饥饿接踵而至,与前夫的感情更是藕断丝连。物欲和灵欲在她身上极端反转,让人感受到命运的戏弄带来的戏剧性和强烈反嘲。这何尝不是人类或者人的基本困境呢?当朱买臣衣锦还乡,玉天仙再度被推到物欲与灵欲对峙的风口浪尖。朱太守以丰厚的田产,“迫”使后夫签下休妻书,这让玉天仙的身心再遭打击和戏弄;前夫要求破镜重圆,更让这个弱女子处于被人指指戳戳、无颜立身的艰窘之境。显然,位于物欲与灵欲之上的更有人格,更有人之尊严。玉天仙最后不是死于物欲得不到满足,也不是死于灵欲得不到释放,恰恰是死于得不到做人的尊严——一个弱女子本应得到的起码尊严。这才是人性的真正悲剧,自然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女主角的人物塑造,分寸拿捏准确、得当,对人性的挖掘尤其对女性内心的展示是成功的。据说,“玉天仙”之名并非新构,而是源自元杂剧《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朱买臣之妻名。改编者用此名,大概不仅出于好听,更为了与“崔氏”相区别,与女主角的命运悲剧形成反讽吧。可以这样说,舞台上从悬垂着两个结的粗绳开始,到众人沉重地收拢绳圈终结,该剧完成了一次剧情闭合,也完成一次思之腾跃。
小剧场戏应该是介于大剧场戏和草台戏之间的戏曲变种。它预示着未来戏曲发展的向度和路径。小剧场戏固然是小制作,对创演者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创作上的独到精粹和表演上的丰厚精致。《玉天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摆在戏曲家面前的难题是,遇古则易响,遇今则易哑。似乎一接触当下素材,便棘手了,戏也变味了。想想看,关汉卿写《窦娥冤》难道不是那时的当下素材?在我看来,如何从丰富多变的当下现实中汲取素材,打磨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作品,才是向伟大的戏曲传统致敬的最好方式,也是加入这一伟大传统的唯一方式。当然,我们有理由期待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