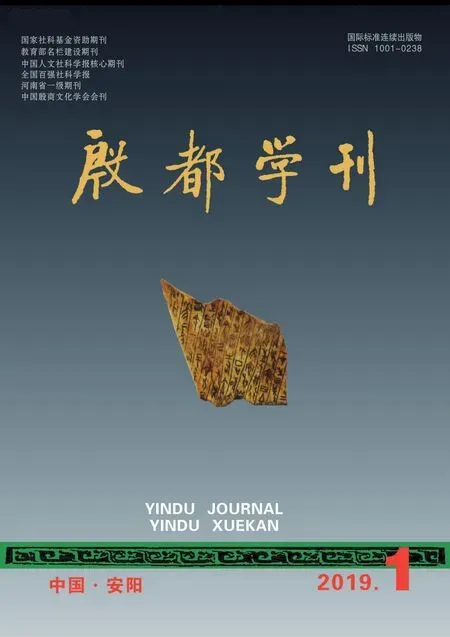从“神韵”到“格调”
——论帝王与康乾时期诗学思想之转变
2019-12-16吴蔚
吴 蔚
(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 北京 100191)
清代前中期诗学思想经历了从王士祯的“神韵”说到沈德潜的“格调”说之转变。王士祯和沈德潜都是主动向清廷靠拢,并受知于帝王的文学家,都是当时的文坛盟主。为何康熙选择了王士祯,而乾隆却抛弃“神韵”,选择了“格调”?关于二者的研究,论者颇多,但大多分别从二人各自的角度加以论述,对于转变的原因,尤其是与帝王文学思想的关系探讨不多,比如《从沈、翁对王士祯的批评看清前中期诗学思想的发展演变》[1]一文提出“诗歌上的这些变化都是由当时各个阶段的政治或文化政策决定的”,但没有展开论述。故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
一、 “神韵”与“格调”的关系
关于“神韵”与“格调”之关系,前人已多有论述,并且形成了各种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神韵”出自“格调”,明代“神韵”说是从“格调”说分化出来的。明末陆时雍《诗镜总论》赋予神韵独立于格调的地位;第二,“神韵”与“格调”有沟通的基点,“神韵”和“格调”都反对“诗以意为上”,“认为艺术比意图更为重要,注重对事物的‘直接处理’,强调对瞬间感觉的捕捉”,认为“作诗不可太切”[2]。第三,沈德潜的“格调”说兼容了王士祯的“神韵说”,“在审美追求上,既崇尚阔大朗健的气象,又表现出对‘神韵’古淡、清远的美学风格的喜好。”[3]
但无论是王士祯的神韵说,还是沈德潜的格调说内涵都十分丰富,都不是明代格调和神韵可以比拟的。王士祯“神韵说”建立起了一个包括作者、作品、读者、世界这四要素在内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包含“传神”与“余韵”的结合,“禅境”与“诗境”的融通,“兴会”与“性情”的共鸣[4]。蒋寅先生称:“沈德潜的诗学观念与其说是发展了格调派的学说,还不如说体现了古典诗学的一般观念,或者说‘为中国古典主义诗学作了总结’”[5]。因此,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这里只拈出其中与本文有关的几点略作陈述。
首先是诗歌的本体和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沈德潜的态度很明确,即强调“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强调诗歌应发挥社会作用,服务政治生活。关于这一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学界多有批判,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不断为他正名。有人认为沈氏倡诗教是汉代经学和宋儒理学调和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是其“人格精神的诗化表现”;还有人认为他将诗教与诗品、人品联系起来,又重视诗歌叙事、抒情、言志的功能,有别于封建卫道者将诗教看成是儒家的教条。[6]蒋寅先生关于古典主义诗学总结的结论也是首先基于这一点。
而王士祯对此没有明确的论述。虽然如此,通过侧面却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即诗歌莫谈国是。既然如此,那诗歌主要功能是缘情,而且此情还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之情。比如屈大均《秣陵》诗中“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有着浓郁的嘲讽意味和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而王士祯的《秋柳》诗采用了委婉曲折、朦胧迷离甚至有些优美的方式来表达,其结果就是:深沉的痛恨变成了淡淡的忧伤,由浓烈变得清淡;“亡国恨”变成了无法实指的似是而非的情感,由切实的可捉摸的现实变得悠远而无迹可求。
其次是关于诗歌风格,王士祯神韵说的核心在于追求清淡悠远的风格,他认为清淡悠远的诗歌就神韵天然,“神到不可凑泊”。所以,这又不仅仅是风格问题,更是一种诗歌的境界。从理论上看他继承了司空图“味在酸碱之外”和严羽兴趣说的宗旨,对他们的以禅喻诗加以继承和发挥,主张“不黏不脱,不即不离”[7]。沈德潜则追求大音壮声、雄浑壮阔的风格。他批评王士祯“于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极”[8]。
再次是关于诗歌的宗法,王士祯和沈德潜无疑都宗法唐诗。王士祯虽然中年曾经一度“祧唐宗宋”,但总的说来是宗唐的,即使兼事两宋,也是为了强化神韵的宗旨。但二人所宗法的唐人是明显不同的。王士祯宗法王孟韦柳,不喜杜甫。王孟韦柳的诗歌正是冲和淡远的代表,而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不符合王士祯的审美理想。沈德潜宗李杜韩,尤其是杜甫。杜甫作为诗圣,是人品和诗品结合的代表,正符合诗教的要求。
二、 康熙、乾隆诗学思想异同
康熙与乾隆两代帝王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歌作品,康熙留存1100首诗歌,乾隆更是存诗43000多首。这些诗歌虽然艺术价值不太高,但为我们研究他们的诗学观提供了基础。总的说来,康乾二人的诗学观基本是一致的。表现在都秉持实用主义文学观,将诗的认识作用与国家的治理紧密地结合起来,都强调诗言志、重视诗教,都尊唐诗。康熙曾在《全唐诗序》中说:“朕万几余闲,回环览咏,寻其指归,晰其正变,而三百年升降得失之故,亦因以可考焉。于是论世观人,即其章句,勒为成书,置诸几席,每勤批阅,加以精研。”[9](三集卷二十一)他研读唐诗,目的是想从唐代三百年变迁中找到治国理政的依据,足以可见他对诗歌功用的重视。乾隆则总是在自己的诗作中不忘表达内圣外王之志,他说:“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10]他尤其重视“视农观稼”主题的表达,以示重农劝农的帝王之志。[11]但仔细辨析,二人的诗学观仍有不少区别。
1.对诗教的理解有所不同
康熙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希望发挥诗歌正人心、厚风俗的作用。他标榜醇雅诗风,亲自组织编选《御选唐诗》《咏物诗选》《四朝诗选》等诗歌选本,并在文章中反复强调诗教观点。《日讲诗经解义序》称:“朕尝思古人立训之意,既有政教典礼、纪纲法度以维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间,鼓舞于隐微之地,使人从善远恶而不自知,优游顺适而自得,则赖乎诗。如天之生万物也,日以喧之,雨以润之,露以濡之,雷霆以肃之,而又必宣畅八风以疏通而条达之,然后万类咸遂其生养,而无促迫矫强之弊。故教至于诗而微矣,治至于诗而极盛矣。”[9](二集卷三十一)从其描述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从毛奇龄《西河诗话》中所述,康熙《望西山积雪》:“积雪西山秀,仙峰玉树林。冻云添暮色,寒日淡遥岑。”也是存粹写景的诗歌,并没有直接的言志和教化。
乾隆也重视诗教,但他个人的诗歌创作相比康熙显得更为直切。他认为只要是为了诗教,可以不计较诗歌的语言艺术性。“亦惟是名教之乐必有言之不足。而长言之者,舍是其何以哉?”他认为不必在风骨体裁等方面与李杜去争高下,而要关注那些“李杜高王所未及而有合于夫子教人学诗之义”[12]。他更侧重纪实性和说理,也很少有单纯的写景的诗歌,要么就是记录自己的政事和见闻,要么大发议论,要么写景也总是要加上一个言志或教化的尾巴。他在《御制诗四集》卷四四《用白居易新乐府成五十章并效其体》诗序中称自己喜好白居易《新乐府》诗,“喜其不尚辞藻而能纪事实具美刺,一代政要略见梗概,有《三百篇》之遗意。”在此鲜明地表示出自己不好华丽的辞藻,而欣赏白居易新乐府诗那种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明白晓畅的纪实诗风。故而乾隆的诗歌相比于康熙显得更为直白,辞藻缺乏凝练,缺少含蓄蕴藉的艺术价值。
相比康熙重视诗歌风格的醇雅,乾隆更为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看重诗人的人品和气节。他的诗教观不仅强调符合儒家礼义,还更进一步要求“发乎情,止乎忠孝”。他说:“古之人一吟一咏,恒必有关国家之故,而藉以自写其忠孝之诚。”[13]卷九诗人诗作能否表现出忠君的品质,就成为了诗歌品评的重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乾隆编选《御选唐宋诗醇》只选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大家,其余均不录,主要因为他们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学识人品为后人称颂,符合忠君的品质,符合朝廷的文化需求和政治需要。《诗醇》并且不重视诗歌的体裁的区分,而以诗歌的内容为选诗的重要标准,也体现了乾隆的诗学思想。
2.诗歌宗法的具体对象不同
康熙重风格醇雅,乾隆重内容重忠孝,由于二人诗教观的侧重点不同,造成了诗歌评价标准不同,宗法的对象也有很大不同。康熙宗唐是毫无疑问的,编选《全唐诗》的目的就是确立唐诗高标。而宋诗因为隐含着对亡国遭遇的同病相怜而受到贬斥。康熙编选的《四朝诗》中宋诗只有七十八卷,甚至比元诗八十一卷还少,完全与宋诗应有的地位不相匹配,足以看出他对宋诗的态度。康熙虽然尊唐,但唐代诗人众多、流派纷呈,他是有所偏好的。从康熙亲自干预编选的《御选唐诗》[注]根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御选唐诗》统计得出数据。中可以看出他的喜好:
从李杜两位大诗人,以及“神韵”派所推举的王孟两位山水诗人所选作品列表可以看出,康熙选择比例最高的竟然是王维,其次是孟浩然,而比例最低的却是杜甫。康熙对杜甫的态度与乾隆颇不相同。《御选唐诗》中录杜甫的诗歌74首,而李白却有114首,而在《全唐诗》中,杜甫的诗歌比李白要多很多。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将杜甫诗中“三吏”“三别”、《羌村三首》《北征》等反映安史之乱并且有很强现实批判性的诗歌给删除了。在康熙心目中这些忧愁感愤的诗歌显然都应划到“变风变雅”之列。而杜甫诗歌以议论为诗,以事为诗,被人视为宋诗的源头,这大概也是康熙不喜杜诗的原因之一。
乾隆以人存诗,秉持忠孝的观点选诗。《唐宋诗醇》中对杜甫评价又最高,杜甫“每饭必思君”的忠君思想无疑成为了最佳选择。《读杜子美集》中赞扬杜甫“之子诚忠爱,遗编足探寻。忧还匡社稷,逸志托山林。”[14]初集卷六并且屡次把杜甫与李白、王维等人相比,认为杜甫始终不忘忧国忠君,其他诗人如李白从永王璘、王维事伪职,都不及杜甫的忠诚。他还赞美杜甫的谦逊的美德,《读杜子美集有感》写道:“卓哉少陵翁,独能秉谦德。当时言诗者,非甫则云白。观其寄李诗,自谓如不及,其实菽粟言,何用誇奇特。兹人嗟以往,谁得其正脉。独嘉不伐心,永言以为式。”[13]初集卷四诗中称杜甫才得诗歌的“正脉”,可见其对杜甫的推崇。再如白居易,历来以白俗称世,有老妪解诗的故事流传,但《唐宋诗醇》认为这是“附会之说,不足深辩”[12]卷十九,明显也是因为白居易作新乐府诗有美刺精神,是忠君的体现,故而为其直白作辩解。否则,白居易的诗歌与其倡导的醇雅诗风实在有一定的距离。
3.论诗歌创作的侧重点不同
康熙论诗歌创作主张取法唐诗。对于如何师法,他在《全唐诗序》中说:“学者问途于此,探珠于渊海,选材于邓林,博收约守,而不自失其性情之正,则真能善学唐人者矣。岂其漫无持择,泛求优孟之形似者可以语诗哉?”[9]三集卷二十一康熙反对学唐诗单纯的形式模仿,言下之意即追求神似。他主张在保持“性情之正”的前提下,把握唐诗的神韵,发挥诗人的独创性,“精思独悟,不屑为苟同”[15]。这也似乎是针对明代前后七子模拟盛唐诗歌而不得要领而发。那么,康熙所说的唐诗的神韵主要是什么?“朕观唐人诗,命意高远,用事清新,吟咏再三,意味不穷。近代人诗虽工,然英华外露,终乏唐人深厚雄浑之气。”[16]康熙欣赏唐诗“吟咏再三,意味不穷”的含蓄隽永、有韵外之致的风神,而对于“近代人”的诗歌“英华外露”进行了批判,可见康熙更看重学习唐诗余韵回响、涵咏不尽的神韵。
乾隆论诗歌的创作重事理切实,反对以禅入诗、以禅论诗。对于标举盛唐气象的严羽多有批评。其作《四集》卷四六《题严羽沧浪集》诗云:“若严羽此集,津津以禅门乘果定诗之品格,其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羽早自犯。”严羽所说的“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指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审美境界,他的“盛唐诗人,惟在兴趣”说的就是诗歌含蓄深远、韵味无穷的意境。乾隆反对严羽,实际上就是反对康熙学习唐诗神韵的说法,只不过没有直接说明。他还说:“严羽沧浪集《诗辨》以为,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不惟引释教以证儒宗,已为冠履倒置”,“夫诗有别裁,偶涉禅趣,固无不可,若宋之苏轼及我朝之张照,每有吟咏,托禅意者十之八九,已失诗之本旨。”乾隆对获得“别材”“别趣”的妙悟说持否定态度,只认同偶涉禅趣,否则就失去了诗的本旨。他所谓本旨当指诗言志与诗教,也就是说他认为严羽的别材、别趣说会削弱诗歌的政治用途。
综上,康熙和乾隆的诗学观念看起来似乎都是属于帝王实用主义的文学思想,乾隆也一向以尊崇先皇来自我标榜,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差别。康熙注重诗风醇雅,乾隆更注重诗人的品德和气节;康熙尊唐诗但不喜杜甫,乾隆尊唐诗推崇杜甫;康熙欣赏唐诗的含蓄隽永、吟咏再三,乾隆却反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认为严羽的兴趣说对诗教无益。
三、 康乾异同与诗学思想转变之关系
由此看来,康熙选择王士祯的“神韵”说,乾隆选择沈德潜的“格调”说似乎顺理成章。
神韵说的出现对康熙来说恰逢其时。从表层看,王士祯宗法王孟韦柳的诗歌,而不好杜诗;康熙喜好盛唐山水诗人王孟,对杜诗的态度二人也是一致的。从深层看,“康熙选择了王士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典雅与温厚的‘神韵诗风’”。[17]基于对唐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的共同追求,王士祯诗歌清淡悠远的风格恰好符合康熙所说的“吟咏再三,意味不穷”的含蓄隽永的标准。而时人“英华外露”恰恰为康熙所批判。施闰章曾说王士祯的诗歌“如华岩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十二楼,缥缈都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从平地筑起”[18]。他一语道出了王士祯诗歌悠远的特点,远到飘缈如在天际,犹如仙人楼阁。对于王士祯来说“羚羊无些子气味,虎豹再寻他不着”[19];对于康熙来说,能够把明朝遗民直露的哀思变得远而淡,是他急切想做到的。
乾隆对“神韵”的态度通过史料对比也很明确。稍加比较就可发现,乾隆的文学思想几乎与王士祯的“神韵”说处处对立:乾隆重切实,王士祯追求虚无缥缈的神韵;乾隆好杜诗,重纪事,王士祯推崇王孟韦柳,好山水诗;乾隆反对严羽“以禅入诗”,王士祯的“神韵”说以严羽《沧浪诗话》为理论基础。因此,乾隆心中必然排斥“神韵”无疑。虽然,我们看到乾隆对王士祯的评价还是很高,但这并不能说明乾隆对他的认同,只能说是对他在康熙朝文坛历史地位的尊重。而实际上王士祯的“神韵”说显然已经不符合乾隆朝的诗歌美学思想。我们从四库馆臣《御选唐宋诗醇》提要的评价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考国朝诸家选本,惟王士祯书最为学者所传。其古诗选,五言不录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七言不录白居易,已自为一家之言。至《唐贤三昧集》,非惟白居易、韩愈皆所不载,即李白、杜甫亦一字不登。……士祯乃持严羽馀论,倡神韵之说……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20]
这一大段简直就是对王士祯的专门批驳。其中多处点明其与乾隆的文学思想不同之处:《古诗选》中竟然不录杜、白、韩、苏、陆的诗,《唐贤三昧集》竟然连李白也不登,与乾隆所推崇的六大家相去颇远;儒家所倡温柔敦厚的诗教不是山水清音可以涵括的,作者甚至把这类诗人称为“畸士逸人”。可以说,乾隆的诗学观念就是建立在对王士祯的批判之上的。
而乾隆与沈德潜的诗学观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沈德潜将“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奉为诗歌的最高准则,与乾隆强调的诗歌为政教服务的诗教观相一致;沈德潜并尊李杜,尤推杜诗,他的《唐诗别裁集》所选杜诗排列第一,远超李白,《杜诗偶评》专评杜诗,这与乾隆对杜诗的极力推崇高度吻合;在诗歌风格方面,沈德潜追求大音壮声、雄浑壮阔的风格,与乾隆追求蓬勃昂扬的盛世之音也相契合。乾隆还认同“气盛言宜”,推崇韩愈,沈德潜则赞赏韩诗“巨刃摩天”的恢弘气度。难怪乾隆写诗称“玉皇案史今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21],并且为沈德潜的诗文集作御序,称虽然“人臣私集自古无御序”,“夫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遇。德潜受非常之知,而其诗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22]。对沈德潜恩宠有加,一时传为美谈,羡煞旁人。
帝王与诗坛盟主之间存在着诗学观念的吻合,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康乾对诗坛盟主的选择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喜好,还有着很深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康熙所处的清初社会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故而诗教的主要任务在于引导汉族士人远离政治,远离对明朝的思念。而乾隆时期民族矛盾已经淡化,诗教的主要任务在于引导士人忠君,故而清远淡泊的山水清音就无法满足需要。这个时候诗教的目的不是让士人远离政治,而是积极参与到清王朝的治理和对皇帝辅佐上来。故而才有康乾的不同选择。
相比之下,从神韵到格调,王士祯与沈德潜的境遇也有所不同。康熙与王士祯的遇合有更多臣子主动迎合的成分,与后者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又折返唐音,以及他入职翰林院有很大关系[23]。自康熙二十二年登上诗坛盟主的地位,王士祯终其一生都得到帝王的重视,其神韵说直到雍正、乾隆朝仍有着很大影响。而沈德潜受知于乾隆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他的诗学思想经过大半辈子的沉潜和思考已经发展成熟,因此登上诗坛盟主的地位有更多帝王选择的成分。晚年因为以诗存人(钱谦益)而触怒因人存诗的乾隆皇帝,沈德潜最后落得“因诗始,因诗终”的结局,更说明他对于诗学思想有着自己的坚守。而他的“格调”说很快也被诗坛新的思想所取代,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与帝王的贬斥不无关系。试想,在当时文网严密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死后被皇帝挖出来鞭尸的文人,谁又敢公然地赞美和遵从?
清代前中期的诗学观念从“神韵”到“格调”固然有诗学本身发展的原因,但帝王的提倡是其中重要因素。康熙与乾隆虽然都倡导醇雅诗风,但实际上诗学思想仍有诸多不同,康熙以“吟咏再三,意味不穷”之深厚雄浑的盛唐元音为尚,重视诗风的建设;乾隆更强调诗人的人品和气格,强调以忠孝论诗,更注重诗歌的思想和内容。而王士祯与沈德潜分别与二人的思想有高度的契合,故而被推举而主盟诗坛。“神韵”本出自“格调”,清代前中期诗学又从“神韵”转回“格调”,不是简单的诗学思想轮回,而是有文学和政治双重的因素,一方面解决了“神韵”说的空疏之弊,另一方面是古典儒家诗学的回归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