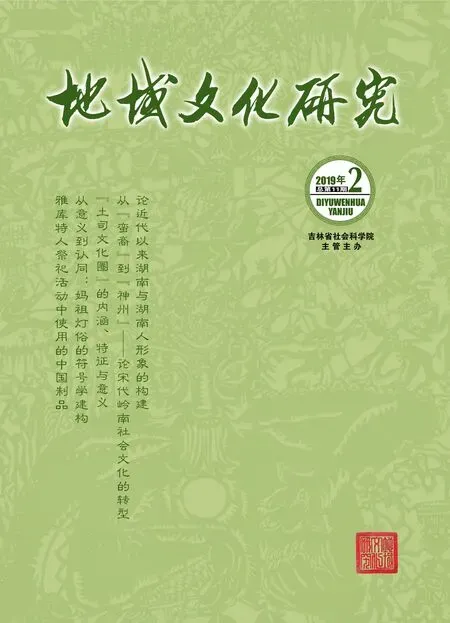论近代以来湖南与湖南人形象的构建
2019-12-14王继平
王继平
30年前,林增平先生就研究指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湖南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属于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①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见《林增平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0页。唐宋时期,湖南还是朝廷流放异见人士的“宁古塔”。清末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欧阳原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骎骎始盛。”②《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05页。在经济方面,诚如王闿运所说:“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至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③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据林增平先生的统计,《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共收入历代名人3,755人,鸦片战前为3,005人,其中湖南籍者仅23 人,只占同期全国名人的0.77%。近代部分共收录名人750人,其中湘籍的85 人,占同期名人总数的11.33%。④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见《林增平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0页。可见,古代社会,湖南及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而“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⑤谭其骧:《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湖南及湖南人形象的建构始自于近代。
一、湘军构建了近代湖南及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杨毓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①杨毓麟:《新湖南》,见《杨毓麟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太平天国的兴起,为湘军的建立提供了契机,而湘军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事功,乃是近代湖南崛起和湖南人形象构建的关键。晚清人士张集馨指出:“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松(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天下事不可太盛,日中则反,月盈则蚀,五行生赳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家乎?一门鼎盛,何德以堪?自古至今,未有数传而不绝灭者。吾为楚人惧,吾盖为曾氏惧也!”②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77页。光绪七年(1881)王阎运撰写完《湘军志》,也很有感慨:“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析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③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据统计,湘军将领官至督抚者达27人(总督14人,巡抚13人)。④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见《林增平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0页。湘军之提升湖南及湖南人形象,除了平定太平天国,挽救了清朝覆亡的危机,还更为深远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造成了汉族士大夫势力的崛起,改变了有清一代近两百年来的政治格局。防范和猜忌汉人,是清代的“祖制”。然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扫荡和西方坚船利炮的进攻,使得清政府的颟顸、腐败和无能暴露无遗。有识见的满族王公大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⑤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卷1下。,“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⑥坐观山人:《清代野记》卷下。,“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⑦尚秉和:《辛壬春秋》卷26。。与此同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和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不但表现出了优于满族官员的才能,更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势力,满族的朝廷似乎也离不开汉族大臣。因而,自咸丰末年开始,清廷不得不面对现实,大量地起用汉族士大夫。所以说,湘军集团的崛起,造成了汉族士大夫势力政治地位的提高,从而改变了成、同以后的政局。使同治年间出现了新的政象。
推动洋务运动,开启了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湘军人物通过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对西方人、西方器物的认识,成为同治年间自强运动的主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与西方侵略势力的交道中,逐步认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也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声光电化所代表的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因而冲破顽固势力的重重阻力,相继在中国建立起一批新式的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创办了新式的学校,派遣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这一切,都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切的活动,促使了社会观念的渐次转变,为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因此又可以说,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肇始,也是湘军集团造成的“同治中兴”的又一表现。⑧参见王继平《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湘军制度推进了晚清军制变革,成为晚清军制变革的中介。绿营、八旗曾经是满人入主中原的悍师,然而经过长期的承平时期,早已丧失了当年的彪悍之势,在太平军面前彻底崩溃。而湘军以新的军制、新的精神、新的装备乃至新的气势,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它的崭新的姿态。因而自然成为同治时期清廷军制改革的参照系统。从此时起至清末新军编练止,期间出现的练军、防军都是依据湘军制度建立起来的,是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对内、对外战争的主要军事力量。所以,湘军制度影响了中国军事制度数十年。
湘军培育了大批人才,是晚清人才的渊薮。曾国藩编湘军首要目的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是作为晚清重臣,他认为清朝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才缺乏,所以“引出一班正人,转移一时风气”,即作育出一批为中兴清朝服务的经邦治国的人才,也是他编练湘军的目的。同治、光绪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活跃的大批人才,大多是与湘军有联系的,或为湘军营伍出身,或曾为曾国藩幕府人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李翰章、彭玉麟、李元度等封疆大吏,郭嵩焘、薛福成、容闳、黎庶昌、陈兰彬等外交使臣,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科学家,俞樾、王闿运、吴汝纶、吴嘉宾、王定安等文人学士,都是晚清社会的栋梁之才,均与湘军有着密切的关系。①参见王继平《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推动外交由朝贡体系向近代条约体系转变领域。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外交观念和近代国际关系理念的传播,清政府的传统朝贡体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近代条约体系。湘军出身的官员,因为与西方打交道较早,故也较早被推出充任驻外使领,活跃于国际舞台,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外交,如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出使西班牙、德国的黎庶昌,出使美国的陈兰彬等等,乃出入曾国藩幕宾,并得到提拔的。这些驻外使领对于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推进中国的近代外交,起到了一定作用。②参见王继平《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影响着晚清文化的发展。晚清众多的科学家,有不少是出自曾幕或曾游幕。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就在曾幕8年,不但为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局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且译著了许多数学著作,为中国近代数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华衡芳也是如此,他译编的《代数术》《三角数理》在当时颇有影响。徐焘、徐建寅父子作为近代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也为近代中国的机械、化工的发展建立了功勋。在传统学术方面,以曾国藩为主体的“桐城派古文”的影响,乃是众所周知的,而湘军人物阐扬的“经世致用”思想,更成为晚清学术思潮变轨的一大契机。在文史方面,俞樾、吴汝纶、吴嘉宾、王闿运、王定安等人,也都是影响晚清文史发展的著名学者。
湘军的事功及其影响,深刻地改变了湖南和湖南人。湖南由“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的省份,一变而为“举世无出其右”的朝廷倚仗,湖南人也由“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变为“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因此,湘军确是近代湖南及湖南人形象构建的契机。
二、甲午战争使湖南人性格由保守向开放转变
湘军兴起造成湖南的崛起,也成就了湖南人的仕途。但湘军的成功也强化了湖南人的保守和骄虚的性格。
关于湖南人的性格,历史上的记载甚多。《史记》说湖南人十分剽悍,《隋书》谓其“劲悍决烈”,是最早有关湘人性格的记载。翻阅湖南地方志,形容湖南人性格的词语,诸如“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人性悍直”“民好斗讼”“率多劲悍”“其俗剽悍”“其民尤尚气力”“其俗好勇”“好武少文”“人性刚直”“赋性刁悍”“刚劲勇悍”“劲悍尚讼”“悍直耿朴”“好勇尚俭”……种种评语,不一而足,大多围绕着强悍的性格而言。①邓运山:《湖南近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又见周秋光,张少利,许德雅,王猛著《湖南社会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08-1009页。近代以后,有关湖南的性格也多有相同的观点。湖南巡抚陆元鼎说:“湖南民风强悍,素多伏莽”;②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6页。朱克敬说:“湖南民气刚强”,③朱克敬著:《瞑庵杂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23页。章士钊也曾经说过:“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心毁誉,不遑顾也。”④章士钊:《刘霖(揆一)七十寿序》,《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1期。湘籍辛亥志士杨毓麟认为湘人:“风气稍近于云贵,而冒险之性,颇同于粤,于湖北与江西相似者甚少”。⑤杨毓麟:《新湖南》,见《杨毓麟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近人钱基博也认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他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交通。远见石赫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⑥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无论如何,由地理环境造成的“风气锢塞”即保守闭关是其固有特征。而湘军的成功使湖南人助长了一种“骄虚不可向弥之气”,保守锢塞更为严重。时人描述曰:
“自咸丰以来,削平冠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⑦陈宝箴:《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49页。
“湘人尚气,勇于有为,而气太盛,则不能虚衷受益。”⑧皮锡瑞:《伏师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
“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⑨参见王继平《清季湖南教案论略》,《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彼时,对待西方物质文明,湖南人也表现出很大的排斥心理。即使像安装电线、电杆这类现代通信设备,也遭到抵御:
“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之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⑩《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
甲午战争打破了湖南人的迷梦,也促使湖南人由保守转向开放。谭嗣同在反省湖南人觉醒的历程时说:
“光绪二十一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①《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4页。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乃是湖南人觉醒的契机。梁启超更认为它是唤醒中华民族的契机:“唤醒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②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页。历史事实的确如此,当时的《湘学报》撰文指出:“自甲午一役,城下行成,割地偿金,数万万人已如酣睡至四鼓以后,蜀鸡一鸣,沉睡方觉。”③《湘学报》,第28册,光绪廿四年二月初一日。例如谭嗣同,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他,“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室彷徨,未知所出”,与好友唐才常“两人对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籍手,泣泪数行”,并写下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表达了强烈的忧国之情。④参见王继平、张晶宇《论1895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从此,谭嗣同开始了他的觉醒之旅。他自己曾经总结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⑤《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9页。“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⑥《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8页。“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⑦《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8页。由此形成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变法维新思想和激进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初步的民主思想,并为变法献出了生命。⑧参见王继平、张晶宇《论1895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另一位维新志士唐才常,在甲午战前也是“低首垂眉、钻研故纸、冥思苦索、自矜为孤诣秘理,粘粘自足,绝不知人间复有天雨,复有诟耻之事”⑨《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0-161页。。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他与谭嗣同“两人对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籍手,泣泪数行”,从此与谭嗣同一样,开始思考拯救民族危机的出路,继而在浏阳兴算学、创办企业,从事开启民智的启蒙工作,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双杰”,最后发动自立军起义,血洒紫阳湖畔。
另一位在甲午战后觉醒的士人樊锥,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受业于儒学大师王先谦,立志“烂经煮史,抑尝为之,秦、汉众子,唐、宋盛集,七代鬼艳,灭不旅宜,考同异,闯条之,通巨谊,透微窥,耻研一字,恒发圣私。目穷黄河,弹指泰山,下及沟渎,旁收嵚巇,窅窅恍恍,漫漫沵沵,行如梗,坐如尸……生死不能夺其志,贵贱不足换其帜。”⑩樊锥:《樊锥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8页。颇有穷究学问的宏愿。在甲午战败的民族危机的严重形势下,乃投身于维新事业之中,积极奔走于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报》等维新活动,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他在《湘报》发表文章,倡导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提倡资产阶级民权立宪思想。他指出,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环伺,瓜分之说甚嚣尘上,千年古国面临“殄灭澌尽”、“蹈波兰、印度、阿非之覆辙”的危险,①樊锥:《樊锥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保种、保教、保国的任务已迫在眉睫:“中国一日存,吾一日必图以济之;黄种一日存,吾一日必图以济之;孔教一日存,吾一日必图以济之。”②樊锥:《樊锥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欲图保种保教保国,舍变法维新无他途。必须应时势,“不穷则不变,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不久,不久则中国几乎绝矣,则黄种几乎斩也,而孔教几乎灭也”,只有“新其所新”、“学其所学”、“政其所政”,“蹙然以振,翻然而悔,皇然以惧,奋然而起”,坚决地实行变法,则可以保国保种保教。③樊锥:《樊锥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显然樊锥的思想,已然接近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了。④参见王继平、张晶宇《论1895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士风的转变,也濡染了民风。梁启超曾描述湖南及湖南人的变化:“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摩萨、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近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⑤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6页。湖南的变化,充分体现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之中。
维新运动兴起后, 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尤其是南学会,颇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时务学堂成为培养维新人才的学校;《湘报》《湘学新报》先后创办。维新人才谭嗣同、唐才熊希龄等崭露头角,成为百日维新的领袖人物。
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之后,继起响应者首推黄兴和他所组织的华兴会。据林增平先生考订,参加7月30日同盟会筹备会的共79 人,居首位的是湖南籍志士,计20人,次为湖北,19人,再次为广东,16 人,以下为广西、安徽等省籍人士。又据1905—1907年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名册统计,湖南籍者为157人;次为四川,127人;再次为广东,112人;湖北106人。⑥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见《林增平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0页。在这众多的同盟会会员中,涌现了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道一、禹之谟、蒋翊武、谭人凤、姚宏业、杨毓麟、焦达峰、陈作新等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家。
清末留学运动中,曾经对郭嵩焘出使西洋、对曾纪泽乘坐火轮船回湘大加嘲讽、咒骂的湖南社会,成为出洋留学的大省。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中国留日学生2,395 人,湘籍373人;1919—1920年中国赴法勤工俭学者约1,600人,湘籍达346人。⑦姚曙光:《乡土社会动员——近代湖南的思潮丕变与社会救赎》,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甲午战争惊醒了曾经以湘军的事功骄虚于天下的保守自大的湖南人,开始了回归魏源所倡导的开眼看世界的历程,勇于探索新事物,接受新思想,从而形成了以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为代表的湖南维新志士群体和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他们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人的形象。正是基于世纪之交湖南人的深刻转型,湖南人的形象得以提振,以天下为己任成为湖南人形象的内核,以下表达反映了湖南人此时的精神:
“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①《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8页。
“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②《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0页。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③《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5页。
因此,甲午战争使湖南人从湘军的神话传统中走出,与先进的中国人一道,融入中华民族觉醒和复兴的时代潮流之中。
三、马克思主义构建了湖南及湖南人的红色形象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转型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趋势,并因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就湖南而言,它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后期湖南及湖南人的形象构建和精神特质,开启了湖南与湖南人的红色之旅,并给予近代中国以巨大的影响。
世纪之交的湖南人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之后,探索新思想的脚步从未停歇。因缘际会,新文化的兴起,为彷徨中的湖南人提供了选择。其中,毛泽东创立的新民学会,聚集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湖南知识分子,倡导“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和“改造中国和世界”,讨论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和当前形势,主要成员有参加新民学会建会大会的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罗章龙、张昆弟、何叔衡)、李维汉、罗学瓒、周世钊等。新民学会还创办了《湘江评论》,在湖南传播新思想,刊登在该刊的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一文,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写文章推荐说,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④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4页。新民学会在五四运动中,组织和领导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后又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新文化运动时期湖南及湖南人追求真理的精神,在当时首屈一指,陈独秀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他引用杨度的名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开头,探讨“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他认为是“奋斗精神”。他用牺牲自我的蚂蚁造桥过河的寓言故事来歌颂湖南人卓立敢死、舍生取义、坚毅顽强、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并表示:“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⑤陈独秀:《欢迎湖南人的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480页。
在随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初期,湖南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0年3月,李大钊与北京大学湖南籍学生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缪伯英、朱务善等人,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全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上海的湖南人李达在1919年就他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三部著作,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与新思想》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道路的代表人物是湖南知识分子邓中夏和罗章龙,他们创办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经常深入农村和工厂讲演,在工农大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刊物《劳动者》和《工人月刊》,提供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工人阅读。他们还在北京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湖南本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则在毛泽东组织下,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间,毛泽东组织一些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创办文化书社,向湖南各地销售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建党过程中,湖南人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蔡和森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之哲学根据”;据雷国珍研究,“从党员人员来看,湖南党员人数在全国党员总数中占较大比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党大约50多名党员,其中湖南人20多名,占全国党员2∕5强。”①他们是毛泽东、李达、邓中夏、蔡和森、何叔衡、林伯渠、何孟雄、缪伯英、李启汉、罗章龙、彭璜、贺民范、萧铮、陈公培、李中、朱务善、陈为人、周佛海、李梅羹、李季、吴雨铭。1921年底入党的湘籍共产党员还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李立三、向警予、李六如、夏明翰、易礼容、任树德、许抱凡、杨开慧、毛泽民、杨东莼、李庠、吴芳、余盖、陈昌、罗学瓒、贺恕、袁痴、夏曦、郭亮、唐朝英、黄静源、彭述之、蒋先云、蒋啸青、雷晋乾、彭粹夫、喻寄浑、王圭、王则鸣、史训川等(雷国珍:《论湖南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6期)在其他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湖南也有程度不同的贡献。例如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成员中有湖南人李达、林伯渠、李启汉、李中、陈公培、周佛海、李季等;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有湖南人邓中夏、罗章龙、缪伯英、何孟雄、朱务善、李梅羹、吴雨铭等;湖南人周佛海在东京建立中共早期组织发挥了作用;湖南人林伯渠、李季在广州中共早期组织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人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立三等人为创立法国中共早期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刘清扬是新民学会的海外会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13 人中有湖南人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周佛海。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深地烙上了湖南的印迹。②雷国珍:《论湖南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6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湖南更是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兴起,成为全国农民革命的中心,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创建了中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嗣后相继建立了湘赣、湘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先后进行了三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常德会战和湘西会战,占国民政府正面战场22次会战的近四分之一。
在近代后期,湘籍革命家、革命志士辈出,据易永卿,陶用舒《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一书根据7种资料统计的结果是:③易永卿,陶用舒:《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中国现代史词典》共收现代湖南人才184 人,其中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才有145 人,占78.80%。①李盛平主编:《中国现代史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
《简明中国近现代史词典》收现代湖南人才59 人,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48 人,占81.36%。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简明中国近现代史词典》,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收现代湖南人才85人,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73人,占85.88%。③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1982年。
《中外历史人物词典》收现代湖南人才96人,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78人,占81.25%。④黄邦和、皮明麻主编:《中外历史人物词典》,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辞海·中国现代史分册》收湖南现代人才62人,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55人,占88.71%。
《中国近代历史辞典》收现代湖南人才136人,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110人,占80.88%。⑤《辞海·中国现代史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中国现代史人物传》收湖南人物49人,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41人,占83.67%。⑥王永均、刘建皋编:《中国现代史人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将上述七种资料综合,现代湖南人才共收录671 人次,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550 人次,占81.97%。⑦易永卿、陶用舒:《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另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共收276人,其中湖南56人,占总数的20.29%、又中国人才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简介》共列495人,其中湖南89人,占总数的17.98%l;又据红旗杂志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中共一大代表共13人,其中湖南籍4人,占总数的37.7%;党成立时期,担任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共有11人,其中湖南籍5人,占总数的45.45%;中共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13人,其中湖南籍5人,占总数的38.4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八大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17人,其中湖南籍7人,占总数的41.18%。⑧此处数据引自李惠康《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特点》,《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1期(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 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10 人,占19.2%。1955年,给长期戎马倥偬,功勋卓著的军事领导人授勋典,在授予元帅的10人里,湖南籍的3人,授大将的10人里,湖南籍的6人,授上将的57人里,湖南籍的19人。⑨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林增平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0页。
由此可见,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年间,湖南及湖南人完成了自身形象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