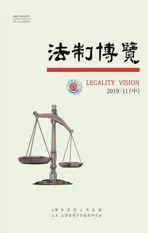刑事和解司法适用中的诘难*
2019-12-14黄凤琦
黄凤琦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0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纷争解决机制,对社会的各谐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其固有的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也面临着强烈的批评。针对某些批评,刑事和解在其自身的学理构建和适用实践中,也在不断开展反思,或从自身角度进行回应,或对自身尽可能弥补。
一、刑事和解削弱了刑罚预防功能
刑罚的功能包括个别预防功能和一般预防功能,前者指刑罚对犯罪人所产生的作用,包括限制或剥夺再犯能力、威慑、感化、改造等作用;后者指刑罚对社会一般人的作用,包括对潜在犯罪人的警戒和威慑作用、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安抚作用等。正如贝卡里亚所言“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犯公民,并规劝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但有人认为刑事和解的“非罪化”、“轻刑化”等效果,不利于惩治打击犯罪,甚至会削弱刑罚的预防功能。因为行为人通过事先权衡自己犯罪的后果并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以通过刑事和解以赔偿代替刑罚,犯罪成本明显降低,这就可能会促使行为人实施犯罪。
虽然从威慑的角度看,刑事和解对刑罚预防存在一定损伤,但并非彻底削弱预防机能。刑事和解只是犯罪诸多制裁手段之一,通常是与其它责任方式例如与缓刑或者与一个减轻的刑罚结合适用,这使刑事和解对刑罚威慑力即便有影响,也只是较小的影响。可见,刑事和解本身并不排斥其它的责任方式,更没有将刑罚威慑力去除。
另外,就现实情况分析,对犯罪人适用刑罚,限制或剥夺了犯罪人一定权益,使犯罪人感受痛苦认识到犯罪会遭受刑罚处罚,从而产生抑制再次犯罪心理,但如果犯罪人没有真诚悔悟自己的行为,是无法彻底打消再犯罪念头,而且缺乏悔罪心理,可能还会加深其与国家、社会的抵触与仇恨,为再次犯罪埋下种子。相反,适用刑事和解,在对犯罪人定罪量刑之前,通过与被害人沟通,犯罪人会认识到自己行为恶性,产生良心的悔罪,从而断绝再犯罪的念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刑事和解不但没有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相反还能弥补刑罚本身预防犯罪功能上的不足。
二、刑事和解违背了正当程序
传统诉讼模式下,国家代替被害人对犯罪人进行追诉,为了避免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力量失衡,产生了“正当程序”观念并形成了一系列相关制度,例如无罪推定原则、严格证明规则、辩护制度等。但是,刑事和解特别强调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必然会忽视犯罪人的权利保护。在适用过程中,难免给犯罪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带来一定的损害,违反正当程序。具体表现为:第一,刑事和解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无罪推定原则要求,任何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得认定为有罪。而在刑事和解中,只要犯罪人承认自己的罪行,他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就被认为是有罪的人,这明显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抵触。第二,刑事和解侵犯辩护制度。刑事和解一味追求的是犯罪人认罪、悔罪,犯罪人只有完全的坦白才会被认为态度真诚,但凡与辩护有关的言行都会被认为是和解诚意上的瑕疵,从而导致犯罪人不敢为自己辩护,这无疑侵害了犯罪人最基本的辩护权利。第三,刑事和解否认了严格证明规则。在刑事诉讼中,严格的证明规则是对犯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但在刑事和解中,只要犯罪人承认犯罪,就被认定是犯罪人,基本上不存在进一步调查收集证据加以证明。
刑事和解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原因在于混淆了刑事和解与传统诉讼程序的关系。刑事和解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诉讼程序,而是一种与传统诉讼模式并立而存的解纷机制,因此,刑事和解并非在传统诉讼模式层面进行,传统诉讼模式里的正当程序难免在刑事和解中是缺位的。首先,无罪推定原则是在追诉过程中保障犯罪人的基本权利,而刑事和解是在公诉机关追诉以外进行的协商处理犯罪问题,缺少了“追诉”的背景,无罪推定原则则难以发挥作用。其次,证明通过是在双方各执一词,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时,才显得格外重要。而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协商和谈解决机制,证明的作用显然会降低甚至灭失。最后,辩护权更是法律赋予犯罪人而对强大的国家追诉时为平衡诉讼局面的一项有力杠杆。而刑事和解强调的是协商和对话,而非对抗,辩护的意义自然不同于传统诉讼程序。
当然,刑事和解与传统诉讼程序也并非完全对立的,正当程序在刑事和解中也有一定的体现。例如,刑事和解中仍要求犯罪人对陈述事实、澄清真相,发表自己观点,犯罪人依然享有辩护权。
三、刑事和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刑事和解面临的另一诘难便是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在传统观念中,犯罪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犯,犯罪由公诉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追诉,一方面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与保障。然而,刑事和解允许被害人与犯罪人进行协商处理案件,不仅将犯罪还原为对被害人个人利益的侵犯,而且将对犯罪的处理权也归还给被害人。这可能产生两个不利后果,一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协商,如果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必然会不顾甚至损害公共利益;二是由于国家机关的退位,必然会消弱对公共利益的保障力度。
但是,从现实情况看,目前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侵害个人利益的犯罪,在这类犯罪中,公共利益并未被直接侵犯,公共利益的保护也就无需特别紧迫和必要。而且,在刑事和解的运行过程中,国家始终对刑事和解进行着监督和控制,以防止对公共利益的过度侵犯。例如,和解过程始终在国家机关的主持和监督下进行,和解协议必须经国家机关的审查和认可。因此,刑事和解损害公共利益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刑事和解助长了“花钱买刑”
但凡提到刑事和解,很多人都会将其与“花钱买刑”混为一谈,认为刑事和解是专门为富人开辟的一条逃避刑罚的通道。由于“花钱买刑”直接指代了刑事和解,人们对“花钱买刑”非正义的责难就自然而然降临到刑事和解之上。刑事和解破坏了刑法面临人人平等原则,侵犯了国家的司法公正,削弱了国家司法权威,放纵了犯罪等担忧、质疑和责难也随之而来。
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刑事和解的基本做法是法院根据刑法规定和量刑原则,将犯罪人的认罪赔偿作为一个酌情从宽情节对其判处刑罚时给予免除或减轻处罚。这种作法虽有“花钱买刑”之嫌,但无“花钱买刑”之实,在刑事和解制度下的“花钱买刑”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并没有超越法律的框架。首先,刑事和解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花钱买刑”,它是以被害人与犯罪人双方的自愿协商为前提,和解必须得到被害人的同意。其次,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并不是随意的去刑罚或者轻刑罚,和解只是作为一个法定从宽量刑情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出相应的刑罚减免。所以,犯罪人花钱并非就是买刑。再次,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认可,以确保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确认其效力。最后,赔偿作为犯罪人犯罪后的一种积极表现,使犯罪人因此获得相应的刑罚减免,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量刑原则。因此,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不同于社会上存在的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私下和解或私了,更不是犯罪人无限制任意的“花钱买刑”,其效力只是将损害赔偿作为一个法定从宽量刑情节而获得刑罚上一定程序的减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