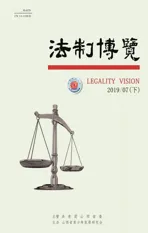论如实供述义务与沉默权
2019-12-13王顺生
王顺生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1
沉默权制度的核心是“不必自我归罪”。十三世纪,英国宗教法庭采取纠问式审理程序,强制性地要求被告人通过宣誓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否则就会对被告人进行刑讯逼供,对其加以处罚。这一不人道的制度极大地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公民为了以弱小的身躯对抗强大的宗教法庭制度,对抗宗教法庭这一荒谬的审讯方法,其辩护理由通常都采用“不必自我归罪”的自然法权利。虽然不能够真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宗教式审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天赋人权。至十七世纪后时期,1641年英国议会废除王室特别法院和宗教法院,并明令严禁“职权宣誓”仪式,从而对普通法院的诉讼程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确了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对于任何指控在任何法院自陷于罪。[1]
早在1789年,美国“权利法案”就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1868年,美国批准通过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进一步规定:“禁止执法人员未经法定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和财产”,因此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就属于违背“正当程序”的行为。于是,“自愿性”就成为了美国司法机关判断被告人供述能否采纳为证据的基本标准,而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询问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享有了“沉默权”。[2]
从权利主体来看,沉默权的权利主体主要为受追诉一方,因此沉默权的意义主要是相对于受追诉方而言的:
首先,沉默权制度的建立维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追诉的对立双方为个人和国家权力机关,个人的力量明显不可与强大的国家力量相抗衡。犯罪活动是罪犯和整个社会与国家的对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独立无援,由于司法活动的“暴力性”和权力的“集中性”,其实际和潜在的强制性是显而易见的。现实中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违法判决情况时常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益更是容易遭受侵害。沉默权制度的核心是“反对自我归罪”,依据了人性中趋利避害的自然本能,排除了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我控告的情况,不会使得本就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使对立双方力量更加不平衡。
其次,沉默权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程序性规则。沉默权的本质就是一种消极的辩护权,通过沉默的方式反击控方的追诉,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以程序上的正当促进实体正义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结果正当,用程序正义消减实体正义不能查明对司法公信的影响。
从《刑事诉讼法》118条可以看出,我国现行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如实供述”义务,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必须如实回答,既包括无罪辩解或罪轻辩解,也包括有罪供述。如实陈述义务是指刑事诉讼中被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法官就案件事实所作的提问,不能保持沉默或者拒绝作答。同时,法律还明确规定了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是指控方不可采取刑讯逼供、威逼、利诱等非法方式,强迫受追诉方自证其罪或者作出对其不利的证言。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要求,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其有罪或者无罪,这一要求从本质上肯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有力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则正是对“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保障。对于司法工作人员违规违法,利用不正当手段、甚至采取刑讯逼供方式收集的证据,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照职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据进行排除。这就使得通过“强迫自证其罪”方式获得的证据失去了生命力,从源头上打断了办案人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而采取“强迫”行为的“积极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了“如实供述义务”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从形式上来看二者似乎处于对立面,但从实质观察,二者的出发点相同,法条精神相辅相成,立法目的具有同一性。首先,“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强调的是“禁止强迫”,要求司法机关不可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供述,是为了减少甚至杜绝采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现象,其目的是维护其正当权益,保证程序正当,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互为支撑。其次,虽然“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但是我们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自愿自证其罪”,鼓励他们自首、坦白、认罪认罚。在他们自愿、主动的情况下,法律给予一个坦白从宽、自首从宽的机会。最后,二者都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自愿地履行如实陈述义务,既包括对无罪的辩解,也包括有罪陈述。其立法目的有二:(1)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弥补自己犯罪行为所带来的损失,作为对自己从轻、减轻处罚的依据(2)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在最快的时间内查清案件事实,提高办案效率,减轻办案压力,节约司法资源,实现司法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利用。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不认可沉默权的存在。相反,现行的刑诉法第118条还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义务”。因此关于侦查人员对有关犯罪事实的提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如实回答,协助控方调查案件事实,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被控方的有罪供述,更是成为了控方指控其犯罪事实成立的有力证据。这样就会使原本力量就有所失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国家力量之间更加不均衡。沉默权制度虽然在中国没有完整建立,但不管从法治发展及完善的视角来看,还是从人权保障发展趋势来看,这一趋势都是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且在司法实践已开始进行尝试。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提出是促进“如实供述义务”履行的一个重要创新制度建设,既是由我国的司法现状决定的,也是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所促进的,应加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配套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和发展该制度,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自觉放弃沉默权,不再抵赖,积极、如实地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从制度方面提供一个基本保障,给司法机关一个有力的抓手。
物质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带动了侦查和取证技术的不断发展,司法机关调查取证的水平逐步上升,物证也越来越容易获得,因此对口供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弱。随着大众媒体的普及与发展,社会公众越来越关心身边事,自发地帮助公安机关进行破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公安机关的办案压力。经济和文化的碰撞与发展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因地缘和血缘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熟人社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往不熟悉的陌生人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交流和联系,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刚开始崇尚国家权力到尊重个人权利,以人为本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保障人权的思想越来越明显,公民意识正在觉醒,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本质相互照应,精神相同,为“默示沉默权”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