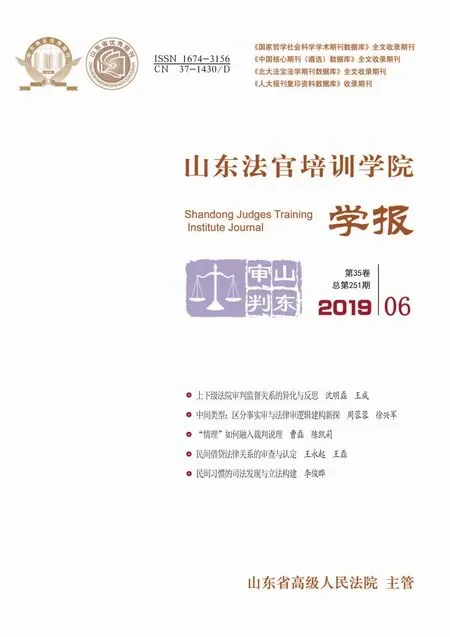诈骗罪中处分意思必要说的不足与完善
2019-12-13王博雅
王博雅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诈骗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对方因为该行为而产生错误认识,继而对其财物进行处分,行为人因此获得他人财物。然而,诈骗罪的成立是否要求受害人具有处分意思、如何界定处分意思成为理论界争议的话题。现今我国就诈骗罪中是否需要存在处分意思存在不同学说,主要代表观点包括处分意思必要说、处分意思不要说。
处分意思必要说认为若无处分意识的存在,则行为人之行为不可谓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诈骗罪不能成立,亦即要求被骗人在客观上转移财物占有的同时,存在着将其财物所有权或使用权转让给他人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当受害人转移财物的占有时,其应当对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若不存在此种认识,则不能认定行为人成立诈骗罪。①[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三版)》,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149页。亦有学者在处分意思必要说的基础上对于处分意思的内容作了较为和缓的解释(缓和的处分意思说),认为即使对于所转移之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数量、价值等存在错误,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受害人还是属于主观上具有移转意思。仍然可以确认“基于意思的占有转移”,从而成立诈骗罪。换句话说,不但应当肯定在受害人对其财物占有的转移不存在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诈骗罪的成立,还应当确定的是,受害人对其所移转占有的财物即便存在模糊的认识的情况下,诈骗罪依然能够成立。①王立志:《认定诈骗罪必需“处分意识”——以“不知情交付”类型的欺诈性取财案件为例》,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1期。
处分意思不要说认为处分行为的成立不需要当事人对其处分的行为具有认识,只要客观上的行为实现财产的移转,诈骗罪即可成立,处分意识并非财产处分必需的组成要素。具体来说,受害者对于其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移转无需具有认识,只要求其实施将财物所有权或使用权转让给他人的具体行为,至于其是否真的具有相应的意思表示则在所不问。在上述情形中,亦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②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目前,处分意思必要说已经成为我国和日本理论学界的通说,该理论的主要支撑点在于认为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标准在于被骗人有无处分意思。但科技的进步,使得新型支付方式渐渐崛起,财产性利益也日渐归属财产犯罪的保护对象,这使得原有的“处分意思必要说”的漏洞得以彰显。
二、处分意思必要说的评析
(一)处分意识必要说的合理性
处分意思必要说存在合理性。首先,如果认为诈骗罪的成立不需要处分意思,那么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分就难以明晰,因为诈骗罪是要求被害人因为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而自愿地处分其财产,但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完全违背对方意志取得其财产。如果采取处分意思不要说,则难以认定被害人存在瑕疵认识并进而处分财产的行为归属。这会混淆诈骗与盗窃罪之间的界限,使得在受骗方在没有处分意识却转移财物给他人的情况下,被视作成立诈骗罪。此外,被害人实施处分行为时应当具备相应的处分能力,这就排除了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孩童、精神病患者等实施处分行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对于这类特殊群体而言,即便其实施了事实上转移财物占有的行为,也会由于其没有意思能力而否认其处分行为的有效性,“骗取”幼儿、严重精神病患者财物的,成立盗窃。而意思能力又与处分意识相关联,如果不要求行为人有处分意识,要求其具有意思能力就显得多余。③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第三,处分行为不仅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容忍类型的处分行为。倘若不以行为人对其行为具有认识为必要,便会否认不作为、容忍类型的处分行为,使得处分行为的范围被扩张。例如在“调包”的事件中,行为人通过欺骗手段转移柜员的注意力,继而将真金首饰换成镀金首饰,在这类事件中,柜员不存在处分意思,属于违背他人真实意思转移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当然不能被视作成立诈骗罪,而是应当成立盗窃罪。如果采取处分意思不要说的观点,本案便可能以诈骗罪论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但又有不少学者对处分意思必要说进行改良,给出了其他的解释。例如前田雅英教授曾说,转移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要求受害人对该结果具有一定的认识,若主观上并不存在该认识,而只是具备一定程度的处分行为,不能成立诈欺罪。”①周铭川:《偷换商家支付二维码获取财物的定性分析》,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2期。山口厚教授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对于所移转的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认识无需是全面的,即便该认识存在一定的错误也可以认定存在相应的处分意思,则受害人的行为可视作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继而肯定诈骗罪的成立。②[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2页。在我国,亦有不少学者赞同上述观点,对处分意思做出了较为缓和的解释。例如,有学者认为,不要求受骗者对财物的价值、性质等具备完全的认识,只要基于自己的意志转移占有即可。③刘明祥:《论诈骗罪中的交付财产行为》,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缺乏对行为对象的完全认识,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④张明楷:《刑法学(下)》(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3页。这在我国理论学界已经成为通说观点。
(二)处分意识必要说的不足
对处分意思的内容做出和缓的解释后,处分意思必要说能够适用于绝大多数情形下的客体为实体财物的诈骗罪的认定。但在行为客体是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处分意思必要说的漏洞便显现出来。例如曾引起广泛讨论的“偷水偷电案”:行为人通过对水表、电表动手脚,获取财产性利益,使得前来征收水费、电费的工作人员对行为人少缴费用的情况并不知情。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形下,由于工作人员对于行为人缴费有一定的认识,只是对少缴费用一事存在认识错误,根据处分意思必要说的观点,应当认定为成立诈骗罪,但也有学者指出,鉴于客体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情形没有差别,因此此处应成立利益盗窃(盗窃罪)。显而易见,这种主张否认了处分意思与诈骗罪之间的联系,认为处分意思的存在与否不影响处分行为的成立。日本也曾有过相似的判例,认为在移转财产性利益时,被害人是否具有处分意思处于模糊不清的判断地带,很难界分。比如为了偷电而将电表指针回拨的案件中,收电费的工作人员并未认意识到财产性利益的丧失,但这种情况下也成立诈骗罪,这便是主张在财产性利益的场合持“处分意思不要说”。⑤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页。此外,隐瞒真实意图让丧失意思能力的醉酒者在文件上签名,而该文件却是免除行为人债务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醉酒者不存在处分意思,那么根据分意思必要说的主张,诈骗罪不能成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显然不存在移转占有的意思表示,客观上却产生了主动将债权移转给他人的情形,该种行为必然也不构成盗窃罪,因此在处罚上产生了漏洞。
通过上述情形不难看出,在侵害的客体为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或存在处罚漏洞,或存在成立利益盗窃罪的空间,处分意思必要说处在较为尴尬的境地。单纯以行为人转移财物或财产性利益时是否对转移的对象存在部分认识来判断诈骗罪的成立与否,难以应对新形势下的财产性犯罪。
三、处分意思必要说之不足的解决路径
(一)处分意思必要说的适用情形
在诈骗罪的行为对象为实体物的场合下,适用处分意思必要说有其合理性,因为在此种情形下,受害人对于实体财物是否具有处分意思容易判断,且应当将处分意思理解为“移转占有”的意思表示,以此与占有辅助的情形相区分。
对于实体财物而言,由于行为人在处分其财物时对于对象能够有一定的认识,即便是较为缓和的认识,此时也应当坚持处分意思必要说。认定受害人在处分其财物时是否具有处分意思,首先应当明确行为人对财物的占有形态是否已经发生终局性的移转。所以,如果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占有仍属于受害人,该行为就不能被等同于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因为处分行为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转移财物的占有,这种情况下,处分意思是否存在也没有讨论的必要性;如果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已经归属于行为人,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判断受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进而在具有处分意识的前提下处分了财物或财产性利益。显然,认定诈骗罪的思路应当是,首先判断占有是否移转,其次占有的移转是否基于认识错误,最后是对受骗人有无处分意思的判断。认定在受害人对于所移转占有的财物具有一定认识的情形下肯定处分行为的存在,进而成立诈骗罪,这也是诈骗罪与盗窃罪的主要区分。
以日前颇受关注“二维码案”为例,根据“处分意思必要说”的观点,行为人将二维码进行了置换,使得店主误认为该二维码是自己的并让客人通过该二维码付账,将财物的所有权转移给顾客。店主和顾客均存在错误认识,但作为受害人的店主并不具有向行为人转移财产的意思,也未实施向行为人转移占有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而非诈骗罪。同样,在“试车案”“试衣案”等例子中,受害人虽具有处分意思,但该处分意思并不以移转占有为前提,显然,在此类案件中,受害人对物的所有权只是发生了占有迟缓,其并无处分意思,因而应当认定为盗窃罪而非诈骗罪。
(二)处分意思不要说的适用情形
在行为对象为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适用处分意思不要说有其合理性。无钱食宿、区间性逃票乘车就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典型类型。
1.无钱食宿
在无钱食宿的情况下,一是本没有付款的意思,却佯装有该付账的意思进行点菜、办理入住等一系列行为,店主由于误认对方的意思表示而陷入错误认识为其提供食宿,便等同于移转了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该行为便是作为形式的欺骗,至少成立诈骗罪;二是本来没有逃单的意思,但之后产生逃单的念头,并采取一系列诈欺行为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使得店主免除其债务,或趁对方不注意逃走的场合。在后一种场合下,因为受害人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处分行为,所以,此行为单纯为盗窃财产性利益,在我国尚没有相应刑律予以规制。①[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第二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页。
成为问题的是,在使用诡计而得以免于付款的情况下,在什么范围内构成诈骗罪。在无钱食宿之后,谎称开车送朋友回家而逃离客店,对此,日本判例在旁论中谈到,“需要存在欺罔债权人的情形,受骗人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并实现为对方免除相应债务的结果,如果仅仅存在逃走并不付款这一行为还不够”,显然,判例是站在处分意思必要说的立场上。其后的下级审判例根据这一判例的观点,对于行为人谎称“去看电影”而一去不复返的行为,认为必须存在免除债务或者暂缓偿还债务这种有意识的处分行为,进而认定为无罪。但也有不同意见的判例:行为人在饮食、住宿后,产生了不付费的意思,使用诡计而趁机脱逃的,在“行为人谎称送朋友,待会儿回来付账”的场合下,由于被害人并未放弃其债权,也没有认识到其允许客人外出的行为将会使自己的财产性利益减少,这种情况下只能认定为对害人对于其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处于“迟缓”的状态,因而被害人允许其外出的行为不能认为是处分财产的行为,不能成立诈骗;在“行为人谎称明晚一定回来付账,却一去不复还”的场合下,被害人做出允许行为人离开的意思表示,可以视为将该财产性利益转移给了行为人,从而使得其对该财产性利益的支配力减弱,可以认为存在处分行为,行为人成立诈骗。②[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153页。
笔者认为,在使用诡计而得以免于付款的情况下,不能根据行为人的表述而判断被害人对于其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处于“迟缓”的状态亦或是将该财产性利益转移给了行为人,进而得出是否构成诈骗罪的结论。首先,依赖当事人的口供进行定罪容易导致司法不公,如果根据行为人的话语来判断受害人对其财产性利益是移转占有还是占有迟缓将会给予司法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其次,在行为对象为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被害人的处分意思难以判断,对于无形的财产性利益,很多受害人被骗时往往处于无意识的状态,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意识不到其财产性利益已经被转移其对于财产性利益的认识程度的判断更是无从下手。最后,诈骗罪的核心在于受害人基于其概括的处分意思自愿或是不知情的客观移转,因此,在诈骗的对象为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只要行为人所采取欺骗的手段达到蒙骗他人的程度,进而“平和”地移转财物占有,即使受害人没有处分意思,也应当认定为诈骗罪。
2.区间性逃票乘车
所谓逃票乘车,是指在乘火车时,购买甲站到乙站的票,在甲站乘车时向工作人员出示已经购买的车票得以顺利上车,在丁检票口再向工作人员出示购买的丙站到丁站的车票出站,以此来逃避乙站到丙站的车票。
对于这种行为,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构成诈骗罪,而另一种观点则否定构成本罪。
首先,否定说的理由在于:从甲站到乙站的车票是有效车票,并且行为人也没有告知越站乘车的义务,因而不能认定行为人在上车车站对工作人员甲实施了诈骗行为;且由于下车车站的工作人员没有意识到行为人没有购买从乙站到丙站的车票这一情况,因而按照处分意识必要说的观点,则不能认定存在处分行为。
肯定说可以细分为两种观点。其一为上车车站基准说:甲站到乙站的车票为无效车票,行为人通过隐瞒事实的欺诈性行为使得上车车站的工作人员误认为该车票有效,因而同意行为人入站上车,可以认为该行为构成对工作人员的诈骗;其结果就是,电车职员向行为人提供了劳务、运送的利益而将其运至丁站,因而可将电车职员的这一行为视为处分行为,并认定在离开上车车站甲之时便构成既遂。其二为下车车站基准说:向出站口工作人员隐瞒其全程乘车的事实,使之相信行为人仅仅乘坐了丙站到丁站的这一段车程,而并不向其提出补交乙站到丙站的差额车费的要求,应当肯定其肯定成立诈骗罪。①[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155页。
笔者认为,行为人在甲站明明没有按规定买票的意思,却装作有此意思的样子,通过检票口的行为,仍有将其视为“诈骗行为”举动的余地;行为人隐瞒其全程乘车的事实,使得出站口工作人员放弃债权请求的权利,属于不作为的处分行为。工作人员对行为人享有债权,其因为受到欺骗而陷入错误认识,未行使费用返还请求权,而在不知情或无意识的情况下将债权进行终局性移转,因而行为人成立诈骗。
结 语
综上,笔者认为,在进行诈骗罪认定的时候应该依照行为对象的不同分别处理,不应一概而论。对以侵害实体财物为对象而进行的诈骗行为,由于实体财物的性质更为直接表面,在认定处分行为时应该要求具备处分意识,且应该对处分意识内容作出较为缓和的理解。而在行为对象为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是否构成诈骗罪的认定不能做机械的判断,财产性利益的隐蔽性和非表面性决定了被害人在大多数场合下处分时难以对其面面俱到,那么对于财产性利益的处分应作出较为和缓的要求,即在诈骗罪中,可以采取处分意思不要说,对于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仍应要求被骗人客观上存在处分行为,但主观上并不要求被骗人对其所丧失占有的财产性利益存在认识。这样不但可以克服难以判断处分意思存在与否的难题,也可以消除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同案不同判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