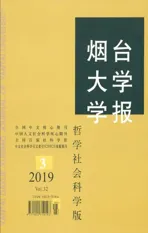“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2019-12-09范丹凝
范丹凝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曾门四弟子”是文学史中关于桐城派的一个重要概念,指曾国藩门下四位古文成就最突出的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人都是曾国藩的弟子兼幕僚,在古文创作方面瓣香曾氏,故称为“四大弟子”。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当下的近代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之中,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研究探寻过“曾门四弟子”名称的由来。相关史料中并无曾国藩亲言此四人为其古文事业后继的记载,也没有来自当事者和同时期人做出的类似评断。然而一个文学史概念的形成,不仅要考虑到史料、作品等物质材料的充分性和可靠性,而且要考虑到文学史知识系统构成上的合理性。在没有明确史实依据的情况下,后世学者对于文学史概念的建立必然是慎之又慎的,需要跨越时间维度重新深入研究文本,比对考量文本材料与文学理论中各方面因素重新解释研究对象。对于“曾门四弟子”这一以作家群体为对象的文学史的概念产生来说,一方面必须充分考虑到四人与其师曾国藩在古文观念及创作上的继承性与发展性因素,另一方面需要客观考量四人并称的概念在文学史结构构成中的合理性,即四人并称在近代古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意义。李详《论桐城派》一文被学界认为是清末的桐城派研究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其中“湘乡派”的提出与构建在桐城派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李详作为清末民初著名骈文家与考据家,论文本不主桐城,他提出的“湘乡派”和“曾门四弟子”等观点并不被当时的桐城后学接受,但却在后来的桐城派研究中被屡次提及,甚至被当时的许多文学史著述直接引用。在这种观点被近代文学史逐渐接受的过程中,钱基博关于“湘乡派”的相关论述为“曾门四弟子”的概念确立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在“五四”新文学突起的年代里,面对已成过往陈迹的桐城古文,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同时反映出近代文学研究者对于古典文学作品批判的角度,从偏向“门户”“宗派”的讨论,渐变为更偏向文章风格的艺术价值研究。“曾门四弟子”从产生到被文学史接受,充分反映了近代学者们在构建古典文学史时的视野转型。
一、“四弟子”并称的历史渊源
曾国藩作为一代中兴名臣,幕府宾僚集一时之盛,其中文名卓著者不胜枚举。被称为“曾门四弟子”的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人,都是曾国藩的幕僚兼弟子,皆受曾氏指导过古文创作。从现存资料看,张、吴、黎、薛四人皆与曾国藩有事实上的师生之谊。张裕钊为曾国藩官礼部侍郎时所拔擢,吴汝纶乡试时的座主是曾国藩[注]《桐城吴先生年谱》言吴汝纶由方宗诚的引荐入幕,但他受到推荐后没有立即去拜见曾国藩,而是在乡试之后才前去入谒的:“(吴汝纶)至乡试后始被强入谒,以曾公座主,不得不见也。”见郭立志编撰:《桐城吴先生年谱》,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494页。,二人称“曾门弟子”名副其实。黎庶昌和薛福成皆以文章见知曾氏,继而入幕。曾国藩官事之余常与幕中群僚讨论文事,也向部分幕僚和弟子传授古文之学。在其《日记》和其他一些资料中,皆存有曾氏教导此四人文法,评点其创作的记载。如咸丰九年九月初八《日记》中记“廉卿近日好学不倦,作古文亦极精进,余门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四有“傍夕,与张廉卿至后园谈论古文,渠所作古文十余首,余于昨夕及本日午刻圈批一过矣”;同治五年十月廿三日记云“二更后与挚甫久谈,教以说经之法”;同年十二月初八日有“傍夕与吴挚甫等一谈。渠本月作《读荀子》一首,甚有识量也”;同治三年九月廿八日“旋与黎莼斋久谈,教以作文之法,兼令细看禀批”;同年十二月初七日“批黎莼斋等文二首”。薛福成在《季弟遗集序》中记载从曾氏授古文云:“其后余佐曾文正公幕府,偕季怀同往,闻公论文之中旨。”[注]薛福成:《季弟遗集序》,《庸庵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8页。可见张、吴、黎、薛四人皆有从曾国藩学习古文之学的经历,在古文创作方面确与曾氏存在师承渊源。
与后世称“四弟子”者不同,时人多以张裕钊、吴汝纶为可承曾氏古文事业者,并称其为“张吴”。《清史稿》中载曾国藩曾言:“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注]《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张裕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42页。薛福成在《拙尊园丛稿序》中言:“(幕府)其治古文辞者,如武昌张裕钊廉卿至思力精深,桐城吴汝纶挚甫之天资高隽。余与莼斋咸自愧弗逮远甚。”[注]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庸庵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第351页。事实上,除“张吴”以外,曾国藩门下的幕僚弟子中以文名为称的还有许多。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叙曾氏幕僚八十三人,其中以“古文”称名者有吴敏树、吴嘉宾、张裕钊、俞樾、莫友芝、王闿运等十三人,而黎庶昌、吴汝纶却被归为“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之“渊雅”类[注]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庸庵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第101页。,可见四人在曾幕之中司职不同,除张裕钊之外,吴汝纶、黎庶昌与薛福成三人并不以古文立身。但这并不能代表吴、黎、薛三人的古文无可称道。吴汝纶曾盛赞黎庶昌文“体势博大,动中自然”;黎庶昌也评薛福成文“辞笔醇雅有法度”。四人同为曾氏弟子,相交甚笃,又同好古文,可以并立相称。如光绪二十年张裕钊去世后,其子张后沆、张后浍为乞墓文而作的《哀启》中,就将其父与吴、黎、薛三人相提并论,这也是四人并称较早记录:
先严(张裕钊)素性严介,寡交游。惟桐城吴挚甫先生,遵义黎莼斋先生,交最笃。至父先生评先严《书元后传后》云:“此文直逼西汉。五百年中无能办此者。”莼斋先生亦以为:“突过姚、梅。”其《续古文辞类纂》至谓:“为夙所严惮”。无锡薛叔耘副宪,亦曾门高弟也。其叙曾文正幕府宾僚谓:先严古文所诣独精,自愧弗逮远甚。文正而后,桐城、无锡、遵义三先生,皆当代知言君子,自当不谬。咸同之际,天下俊彦,咸在文正门墙。论者谓:功业首推合肥相国,文章衣钵惟先严能绍其传。此天下公论,非徒三先生之阿好也。[注]张后沆、张后浍:《哀乞》,《张裕钊诗文集》附录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91页。
“桐城、无锡、遵义三先生”即吴汝纶、薛福成和黎庶昌。在叙述其父生平之际,张氏二子独重此三人对张裕钊古文成就的肯定,并且称三人为“当代知言君子”,可知此三子与张裕钊在当时的文坛地位、声望几乎同等。可见在当时部分人眼中,黎、薛与张、吴可置于同类相比,四人并称也无可厚非。四人在曾氏幕下便有交谊,曾氏殁后,四人或为官、或执教,行迹遍及海内外,虽不常相见,但情谊仍在[注]四人之中,吴汝纶与张裕钊相交近三十年,多次讨论文事,光绪八年至十五年,张裕钊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任冀州知州,二人关系更为密切;黎庶昌与薛福成虽远隔异国,但常互通手书,“莼斋纵迹虽隔而情意益亲,数万里外,往往互答手书有无,未尝不相通也”。见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庸庵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第352页。吴汝纶与薛福成为儿女亲家,平素往来甚密,自谓“与叔耘相处最久”。见郭立志编撰:《桐城吴先生年谱》,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
然而与张裕钊、吴汝纶相比,黎庶昌与薛福成更专注经世事功,不如张、吴常年专心文事,自然也不如二人文名卓著。自光绪八年至二十六年间,张裕钊、吴汝纶二人先后执教保定莲池书院,在北方培养了一大批熟习古文之学的文人和学者。他们以及他们的门生弟子,多将张、吴二人奉为曾氏之后古文之学的两大宗师。依照这些桐城派末期古文家们的眼光,张裕钊和吴汝纶才堪为接续曾氏的一双巨子,黎、薛二位并不能与张、吴抗衡。马其昶称:“(曾)于门徒,则盛张廉卿、吴挚甫两人。”[注]马其昶:《濂亭集序》,《抱润轩文集》卷四,1923年京师刊本。姚永朴谓:“武昌张廉卿裕钊与吾邑吴挚甫先生,同处于曾文正公门下,为同光中老宿。”[注]姚永朴:《予交海内贤士甚寡偶怀逝者得五君泫然成咏》,《蜕私轩集》卷一,民国十年秋浦周明泰刻本,第11页。王树枏在《故旧文存小传》中言:“同治、光绪间,海内言古文者,并称张吴,谓裕钊及桐城吴挚甫汝纶也。”[注]王树枏:《故旧文存小传》,《故旧文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38册,第7页。赵衡《书濂亭文集后》云:“(张裕钊)先生与吴先生为友,而皆曾文正公之门人。”[注]赵衡:《书濂亭文集后》,《序异斋文集》卷二,民国二十一年徐世昌序刻本,第17页。徐世昌《明清八大家文钞序》:“清代文学至姚而后醇,至曾而后大,张、吴两先生力跻崇奥追。”[注]徐世昌:《明清八大家文钞序》,《明清八大家文钞》,民国二十年天津徐氏刻本,第2页。贺培新在《跋武昌先生书札册子》中道:“尝以谓有清一代文学,姚、曾而后,张、吴两先生拓而大之。”[注]贺培新:《跋武昌先生书札册子》,《天游室文集》卷二,民国二十六年北平刊,第43页。马其昶、姚永朴都是张、吴二人的弟子,亦被时人认为桐城派的正宗传人;王树枏与吴汝纶亦师亦友[注]关于王树枏与吴汝纶的关系,当代学者多从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所论:“裕钊、汝纶并皆引(王树枏)为畏友,不在弟子之列。”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4页。;赵衡则是吴汝纶的再传弟子;徐世昌、贺培新皆与桐城晚期人物关系紧密。可见在清末民初,无论是受过系统的古文教育的桐城派文家,还是受古文之学影响较深的学者,都尊奉“张吴”二人为曾国藩之后接续桐城派文脉的正宗。张、吴、黎、薛四人虽位列曾氏门下,且相交甚笃,但并没有形成以古文并称“四弟子”之说。
二、“曾门四弟子”概念的形成
“曾门四弟子”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李详的《论桐城派》一文。该文是较早的对桐城派进行总结性研究的文章,发表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国学杂志》第四十九期。在这篇文章中,李详对桐城派做出了许多经典论述,其中,“曾门四弟子”概念的提出是文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李详作为近代骈文大家,自称其作为“子部杂家之文”,为学倾向扬州学派,论文“扬甬东之波”“宗阮文达文言之说”[注]李详:《与陈含光四函其一》,《李审言文集》下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56、1048页。。其对于桐城古文,本有门户之见,多次抨击其“不通”。尝言“桐城专讲间架,曳虚腔,写一人一事,毫无生气,是与雕绘何异?”其实李详本人与当时桐城派的许多作家都有文字往来,而这些作家多出自曾氏弟子吴汝纶的门下。他曾于宣统二年至皖,在安庆存古学堂中教授史学及文选学一学期,其间与姚永概相交甚笃;又曾与马其昶文字相交,批点《屈赋析微》稿本;晚岁见王树枏文章,又极称许,“见姚叔节之文,推重晋卿,又于他处见晋卿文,不觉叹服”;对范当世的文章也有客观的评价,“范伯子亦故人也,其文极深湛,而规模少狭”。[注]李详:《与张江裁四函其一》,《李审言文集》下卷,第1069、1068页。盖李详虽出于宗派意识而对桐城派古文有极大的意见,但对桐城派后世部分文人的学术、文章造诣仍能做出客观评价。他在《论桐城派》文中写到:
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其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然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吴挚甫、黎莼斋、薛叔耘,亦如姬传先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注]李详:《论桐城派》,《李审言文集》下卷,第888页。
李详认为,曾国藩一方面尊重桐城文统,有意识学习姚鼐的古文创作,另一方面突破传统桐城古文的藩篱,兼习汉唐之文,自铸伟词,以应时实用、雄奇瑰玮之文改造传统的桐城古文。曾氏于史学用力艰深,古文创作受马、扬等西汉文的影响,文辞奇偶并见,不纯为桐城“雅洁”之文,而是独具特色的“湘乡派”之文。曾氏本人未必主动有过以古文另立门户之心,但也有对桐城古文的不满之处。当吴敏树指出他“果亦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注]吴敏树:《与篠岑论文派书》,《吴敏树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95页。时,他也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注]曾国藩:《复吴南屏》,《曾文正公书札》卷九,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第33页。,其论文常常有异于桐城之处。李详的这段论述有意突出曾国藩古文中“奇偶错综”“偶多于奇”等异于桐城古文的特点,并着重在此基础上别树一帜,另立有别于桐城派的“湘乡派”。而在湘乡派体系中,曾国藩是“自成一派”的第一人,自他之后继承并亲身实践他的创作思想的门生弟子们,却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湘乡派的后续创作队伍。为了壮大湘乡派的声势,李详明言“亦如姬传先之四大弟子”选出曾国藩的四位弟子。换言之,李详选择“四大弟子”是以姚鼐“四大弟子”为参照的。“姚门四弟子”一般有两种说法,一是依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中所言:“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注]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85页。即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一是依姚莹所云:“谓若吾桐方植之东树、刘孟涂开、上元梅伯言曾亮、及异之,皆惜翁高足,可称‘四杰’。”[注]姚莹:《感怀杂诗》,《后湘二集》,《清代诗文集汇编》549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59页。即方东树、刘开、梅曾亮、管同。二种选择倾向略有不同,大旨以最能传衍姚鼐古文之学的弟子之四人并称。所选之人既要有受古文学于姚鼐的经历,又要在创作上体现出师门特色。故而李详在选择“曾门四弟子”的人选时,同样也要考虑这两个方面。如同“姚门四弟子”依附于姚鼐的桐城派名下一样,李详以“四大弟子”依附曾国藩名下,使得“湘乡派”拥有了明确的师承脉络。
在构建以师承脉络为主的湘乡派作家队伍时,必须要考虑到弟子与其师在古文创作风格上的传承性,及曾门弟子古文创作的特异性。李详在另一篇文章《曾国藩古文派别》分析:
国藩门下,有武陵杨彝珍、东湖王定安、武昌张裕钊、无锡薛福成、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彝珍、定安,肉多于骨,长于用复,而短于使单。裕钊善于叙事,而规模不免狭小。福成具体而微,首尾完密。汝纶习于间架,其铭词陶铸诗骚,颇堪继武。庶昌读书较多,不囿于法而范围较广。此六君者,虽未能各自树立,然皆湘乡入室之弟子也。[注]李详:《曾国藩古文派别》,《李审言文集》上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57页。
文中一共提及六名曾门弟子,每一人的创作都能部分体现曾氏湘乡派古文的特征。“长于用复”“善于叙事”“首尾完密”“陶铸诗骚”“不囿于法而范围较广”等,皆是曾氏古文标志性的特点。李详在此着力突出湘乡派中除曾国藩之外其他作家的古文风格与曾氏古文的相似之处,目的是构建湘乡派共同的古文理念和创作倾向。事实上,六人之中,杨彝珍与曾氏早年相交,文法梅增亮;王定安谨守师说,辑录国藩言行事绩,二人虽也为曾国藩入室弟子,但文名不著,且不以古文相号召。剩下的张、吴、黎、薛四人,虽志趣不同,但古文成就颇高,文名盛于海内,可堪继武曾氏。吴汝纶本是桐城人,谙熟桐城之学,古文创作诸体融裁,以高古雄奇为尚;张裕钊论文以“因声求气”为宗,推崇“雅健”的文章风格。张吴二人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在李详看来或“规模狭小”,或“习于间架”,但其“善于叙事”“陶铸诗骚”的特点承自其师,无疑位列四大弟子之中。而黎、薛二人为官较早,好经济实学,“雅不欲以文士自期”,“不屑为无本之学”,多论及时政、通达事理之文,甚至有以西方情理事物入文者,正与曾国藩论文的“经济”之旨相合。而在文章风格方面,黎、薛二人的古文“不囿于法而范围较广”“具体而微,首尾完密”,正是湘乡派古文的明显特征,无论从文章内容还是创作风格来看,黎、薛二人也堪称曾门弟子中的佼佼者。总而言之,在李详看来,备受晚近桐城文家推崇的张裕钊和吴汝纶,继承了桐城古文 “间架”和“规模狭小”之病,但“善于叙事”和“陶铸诗骚”等特点更偏于曾氏古文的特征;而黎、薛二人之文,则更突出体现了曾氏在古文创作方面糅合百家、雄奇瑰玮又敷于经济的特点,展现出曾氏古文突破桐城藩篱而大之的整体面貌。四人并称,方可最完整地体现曾氏古文的特点。拥有清晰师承脉络和相对一致的文章风格,“曾门四弟子”才得以在湘乡派的门户下得以存在。
三、“曾门四弟子”概念在文学史中的接受
李详《论桐城派》一文发表后,自言“已受世人陵籍不少”“为海内仇视久矣”“兼有谤及桐城处,为众所不喜”。该文发表时,曾门四弟子皆已作古,但海内桐城古文声势仍大。李详此文无疑不为时流称许,但也未有人进行公开反驳。《论桐城派》在当时没有形成旗鼓相当的论争,“曾门四弟子”之称也没有得到学界普遍认同。在《论桐城派》发表的三十年后的民国十七年,李详在《南通报》上读到钱基博关于桐城派的文章,其中引用了自己《论桐城派》中的部分论述。由于钱文对《论桐城派》中的观点有所取舍,李详认为钱基博有意借自己的文章“张桐城之帜”,故而去信与其争辩。他在信中竭力抨击桐城末流之弊,对林纾特意尊桐城义法之举尤为不满。钱基博回书反驳,声称自己“生平论文,不立宗派,曩时固不欲附桐城以自张,而在今日又雅勿愿排桐城已死之虎,取悦时贤”[注]钱基博:《再答李齳叟》,《李审言文集》下卷,第1051页。,对桐城派持中立态度。他于民国十八年(1929)出版《〈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其中引用了部分李详对曾国藩古文的评价,同时又一次提出“曾门四弟子”的概念:
曾氏论文从姚入而不必从姚出;其自为文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力矫桐城懦缓之失,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特起于桐城之外而自树一派,可名之曰湘乡派。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者门弟子著籍甚众,其尤倬倬者,则有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亦如姚氏之四大弟子。[注]钱基博:《〈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第19页。
文中关于曾国藩古文特征的论述与李详几乎一致,可见,钱基博于“湘乡派”和“曾门四弟子”等观点的意见基本源自李详的《论桐城派》。[注]钱基博在民国十九年(1930)成书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却对《论桐城派》中的观点有所保留,仍以“张吴”为曾门弟子中能传其学者,“(曾国藩)门弟子著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采用了民国时期桐城后学的观点。但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署名梁堃的《桐城文派论》出版,书中称“曾氏门下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为最高”,该书被认为是钱基博的学生整理的课堂讲义。因此基本可以确定钱基博本人对于“曾门四弟子”概念是认同的。而他通过阐释“张吴黎薛”作为“曾门四弟子”在古文风格与文章源流方面与曾国藩的师承关系,使该概念作为“湘乡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证明了它在文学史上存在的合理性。
钱基博对“曾门四弟子”概念的深入阐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古文风格方面,钱基博的立论突出表明“张吴黎薛”的古文风格与曾国藩接近的一面,重在表现湘乡派古文独特的风貌。他认为张裕钊“于曾门四子才最高”;吴汝纶“屹然海内文伯”,“吴之才雄;而张则以意度胜;故所为文章,宏中肆外,无有桐城家言寒涩枯窘之病”。薛福成“致力事功,未遑殚精学问,而雄直之气,无忝于师门”;黎庶昌“上赓姚纂以阐扬师法而救桐城之敝,此于湘乡之学,特究阃奥”。他将“湘乡派”古文风格与传统桐城古文分离开来,使得作为“湘乡派”的代表作家的“曾门四弟子”拥有了独立和相对一致的风格特征。第二,从文章源流上来看,钱基博为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的师承关系构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古文脉络。曾国藩在世时未曾以古文门户相号召,曾被视作“不立宗派古文家”[注]张之洞:《增订书目答问补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26页。。在他殁后,其弟子后学多宗其为文章领袖,“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注]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拙尊园丛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第80页。曾国藩的古文成就在其弟子看来上逐两汉三代,自马、班、韩、欧接引而下。钱基博认可这种说法,他基于对曾氏古文风格的理解,确定了湘乡派古文有别于桐城派的新文统,“湘乡之文,由韩愈以摹扬马,由扬马以参《汉书》,蕲于英华秀发,语有遒响”[注]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00页。。即湘乡派文统由《史》《汉》至韩愈,再由欧阳修直到曾国藩,直接跨过了桐城派。而“曾门四弟子”正是湘乡派这一古文文脉的后继。如果说“姚门四弟子”是桐城派自姚鼐后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群体,那么“曾门四弟子”也对应地成为湘乡派自曾国藩后的力量中坚。将湘乡派在文统上与桐城派区别开来,凸显了其作为独立宗派的一面,而“曾门四弟子”概念在文学史上进一步稳固。
作为民国初期的文学研究者,钱基博精研集部之学,“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注]钱基博:《自传》,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934页。。他对于湘乡派古文风格的定位和文统脉络的构建都建立在研读和分析文本的基础之上。可以说,丰富而具体的诸家古文作品是钱基博提出湘乡派和“曾门四弟子”等概念的依据,而非出于“家学”“宗派”等现成的理论体系。这种从文章风格出发讨论古典文学宗派问题的研究方法,是当下文学史研究中司空见惯的,但在清末民初,不少文学研究者还是将宗派内部统一的理论体系奉为圭臬。比如“曾门四弟子”中的薛福成,其古文因为明显不合传统桐城派“义法”,而长期得不到以桐城古文模式为规范的古文家们的认可。吴汝纶在评价曾门文人的文章风格时言道:“曾张深于文事,而耳目不逮;郭薛长于议论,经涉殊域矣,而颇杂公牍、笔记体裁,无笃雅可诵之作。”依吴汝纶所见,古文题材“经涉殊域”或者内容“长于议论”都无可厚非,但杂“公牍”“笔记”便“无笃雅可诵之作”。可见吴氏论文,仍偏重传统桐城古文范式。黎庶昌“为文恪守桐城义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则以求阙斋为师”[注]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庸庵文集》,第351页。便可与张裕钊相较,“自曾门中,已能自树一帜,非廉卿所能掩蔽”[注]吴汝纶:《答黎莼斋》,《吴汝纶全集》卷三,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安徽:黄山书社,2002年,第100页。;而薛福成笔法杂糅,不为单一的桐城义法所囿,正是所谓“不规规于桐城论文”[注]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拙尊园丛稿》,第256页。。吴汝纶评论古文,重视古文体的雅化与纯化,仍不能跳出桐城宗派固有的理论模式。他的门生如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赵衡等人论文也有此弊。但在钱基博看来,薛福成古文在文体方面虽不法桐城,但在风格方面却继承了曾氏古文的“雄直之气”,颇有其师为文“自成一派”的特征,同时也侧面反映了曾国藩改造之后的古文诸体杂糅、应时经世的面貌。同样是提出湘乡派和“曾门四弟子”概念,李详的立论明显带有宗派色彩,“自两汉迄今,学术皆有党派,皆有竞争”“古人护道如护头目”[注]李详:《与钱基博四函其三》,《李审言文集》下卷,第1052页。,故而列四大弟子为湘乡派张目,各家门户森严。钱基博不排斥宗派,但不以宗派限定其文学研究的视野。这种较为科学的文学研究方式使他对于文学流派问题认识更为客观,也使他所讨论的湘乡派和“曾门四弟子”等观点更容易获得近代其他学者的接受。总体看来,“曾门四弟子”的提出与接受过程,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的过程。文本研究在这一阶段成为文学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据此产生的文学史概念则具有更加客观、科学的特质而被学界接受。
新文化运动前后,具有新思潮的学者,常用否定和批判的眼光看待晚清的桐城派。但有时也因为桐城派主张文章创作应“通达平易”,也会被视为“不妄想做假古董”的“过渡性”文学,曾国藩更是被视为中兴桐城派的功臣[注]胡适和周作人都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派中兴的功臣。详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3),第205、200页;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页。,他和他的弟子大多具有较开明的眼光,对于西学态度较开放。特别是吴汝纶,曾亲身东渡日本,访求教育改革之策,思想较新,影响也比较大,尤其在接引后进、传播古文学方面。近现代许多文人学者都因为受到他的影响而与桐城派产生联系。严复和林纾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他们二人对民国初文坛的影响甚至大过吴汝纶。故而民国初、中期的文学研究者多将吴汝纶与严、林并列讨论,其论点主要集中在三人运用古文体传播新学方面,如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讲: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都以严复、林纾作为曾氏以后桐城古文的传人。其实严复文章上复周秦,过于古雅峻涩,与桐城派主张文章“通达”、“雅洁”不相符;林纾自言“余非桐城弟子”,早年并不喜文章宗派之论,后趋向桐城,为师门扞卫,但其虽借“桐城”之名倡言复古,文章实非桐城。[注]相关论文见王风:《林纾非桐城派说》,《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针对桐城派的古典文学方面的讨论较少,间或有论及桐城古文和曾氏古文的文学史论著,大多依从钱基博关于湘乡派及曾门四弟子的阐释形式,偏向文章风格的论述。如姜书阁的《桐城文派评述》,其中虽然没有明书“曾门四弟子”,但将张、吴、薛、黎之文一并着重讨论:“‘当是时,幕府豪彦云集,并包兼罗。其治古文辞者,如武昌张裕钊廉卿之思力精深,桐城吴汝纶挚甫之天资高隽。’无锡薛福成叔芸之平正通达,遵义黎庶昌莼斋之法度紧严,皆一时之选也。”[注]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73页。作为亲受桐城先辈教诲的老一辈学者吴孟复,也在《桐城文派评述》中,将“曾门四大弟子”列为曾氏之后古文文脉的传人,“曾国藩门下以古文著名的还有薛福成、黎庶昌。旧以薛、黎合张、吴,比之于姚门之梅、管、姚、方”[注]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曾门四大弟子”的说法自是被当代学界接受,重新出现在各类桐城派研究专著和文学史作品中。
现如今,任何一部近代文学史谈论晚清古文都无法绕开“曾门四弟子”这一概念。它不仅完美填补了桐城派之后的古文文脉在晚清的空缺,还充分显示了曾国藩之后古文风格的新变化。其产生和接受过程暗含着近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变,也象征了文学史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可以说,“曾门四弟子”概念的提出是近代文学史上从新的视野解读古典文学文本,并对古典文学中的概念做出诠释的典型,它在保存古文传统的基础上包含了古文这一传统文学样式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变迁,将作为近、现代的文学史著作中的经典概念适用于当下及未来的清末民初的古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