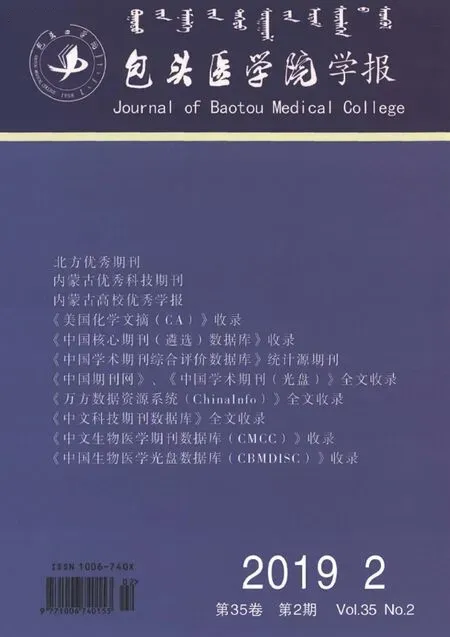阿帕替尼在治疗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2019-12-04,,,,,,,,
, ,, ,,,,,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安徽蚌埠 233004)
肿瘤组织的生长离不开其内部新生血管网的营养支持,而体积巨大的肿瘤常常因组织内部的缺血而发生液化、坏死,消化道恶性肿瘤组织类别中常见的溃疡型即为此种原因[1, 2]。这一结果的发现为恶性肿瘤的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思路,但其难点在于靶向抑制肿瘤组织的血管生成而不干扰人体非肿瘤组织的血液供应。甲磺酸阿帕替尼片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口服小分子血管生成抑制剂,其归属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endothelialgrowthfactor,VEGF)类,可特异性作用于VEGFR-2,两者结合后通过一系列信号转导通路,发挥靶向抑制肿瘤组织血管生成的作用,从而降低肿瘤组织血管密度,切断肿瘤组织营养物质的来源,进而抑制肿瘤组织的发展[3, 4]。实验的成功必须要结合临床应用的实际疗效,由于其在胃癌III期临床试验中使患者明显受益且无严重不良反应[5],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China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CFDA)于2014年10月批准阿帕替尼上市用于胃癌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二线治疗失败的患者。虽然阿帕替尼尚未批准用于其他消化系统肿瘤如肝癌、结直肠癌等的治疗,但一系列II/III期实验正在开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果。本文就阿帕替尼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的机制、应用效果、毒副反应等方面进行综述。
1 恶性肿瘤血管新生机制
自Folkman提出肿瘤细胞的发展离不开新生血管提供氧气和营养物质以来,肿瘤组织的血供方式逐渐清晰,现已知多数恶性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转移与肿瘤组织的新生血管密切相关。其中,VEGF及其受体VEGFR的信号转导通路是促进肿瘤组织血管生成的最为关键的环节[6],这也为恶性肿瘤靶向治疗提供新思路。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VEGF家族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至血管内皮生长因子E及胎盘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endothelialgrowthfactorreceptor,VEGFR)家族包括VEGFR-1、VEGFR-2、VEGFR-3,以及VEGFR共受体神经毡蛋白1、2[7,8]。其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即通常所说的VEGF,在肿瘤组织新生血管过程中其主要作用,而VEGFR-2常表达于淋巴管及血管内皮细胞[9],与新生血管的形成关系密切。研究证实,VEGF和VEGFR-2信号通路是调控肿瘤组织血管生成的关键环节,当两者结合后,使受体细胞内域酪氨酸激酶发生自磷酸化[6, 10],进而使后续传导通路失活。在原未失活的后续传导通路中:Ras/MEK/ErK通路与内皮细胞增殖有关,P38-MAPK与细胞迁移有关,PI3K/AKT/mTOR与细胞存活及血管通透性有关[11]。因此,在起始位点靶向阻断VEGF和VEGRR2的结合,也即高效的阻断了肿瘤组织新生血管的形成,为恶性肿瘤组织的靶向性治疗提供新思路。
2 抗肿瘤机制和药代动力学
2.1阿帕替尼抗肿瘤机制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是我国医药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新型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其实验阶段代码为YN968D1,化学名称为:N-[4-(1-氰基环戊基)苯基]-2-(4-吡啶甲基)氨基-3-吡啶甲酰胺甲磺酸盐。阿帕替尼通过高度选择性结合VEGFR-2的三磷酸腺苷(Adenosinetriphosphate,ATP)位点,使VEGFR-2自磷酸化失效,从而阻断下游的信号传导,抑制肿瘤组织形成新生血管,降低肿瘤细胞的氧供及营养支持,发挥靶向抑制肿瘤组织恶性行为的作用[12, 13]。Tian的研究表明,体外实验中阿帕替尼明显降低VEGFR-2活性,并可抑制Ret、c-kit及c-src的磷酸化,同时观察到阿帕替尼明显抑制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和微管的形成以及鼠动脉环的出芽;体内实验中,阿帕替尼与奥沙利铂、5-氟尿嘧啶、多西他赛和多西紫杉醇分别联用在胃癌、结肠癌等裸鼠移植瘤的效果均优于单药,且不良反应可控[12]。已有研究发现,当阿帕替尼与常规化疗药物联用时,其可通过抑制ATP结合盒蛋白B亚家族成员1和ATP结合盒蛋白B亚家族成员2的外排活性,延缓常规药物的耐药性,发挥药物的最大效用[14, 15]。以上实验结论表明,阿帕替尼抑制血管新生安全有效,值得进一步研究及开展相应临床实验。
2.2阿帕替尼的药代动力学Ding等的研究发现,阿帕替尼在体内主要经3-羟基化后的E/Z-环戊基-3-羟基化,N-脱烷基化,吡啶基-25-N-氧化,O-葡糖醛酸化等代谢途径生成无活性E-3-羟基-阿帕替尼、Z-3-羟基-阿帕替尼、阿帕替尼-25-N-氧化物以及E-3-羟基-阿帕替尼-O-葡糖苷酸等产物,且其稳态暴露法的浓度分别为母药的125%、56%、22%、32%。口服阿帕替尼750mg96h后体内76.8%药物被排泄,其中以粪便形式排出占69.8%(原型排出占59.0%),以尿液形式排出占7.02%(基本未见原型排出)[16],说明进入体内循环的药物基本被完全代谢。在体内阿帕替尼主要经过CYP3A4/5、CYP2D6、CYP2C9和CYP2E1等肝酶分解代谢,其中CYP3A4/5为主要途径,在经UGT2B7、UGT1A4及UGT2B7途径生成E-3-羟基-阿帕替尼-O-葡糖苷酸和Z-3-羟基-阿帕替尼-O-葡糖苷酸。在同一研究中,实验设计28d为一周期,期间给于入组患者不间断服用阿帕替尼片,研究表明阿帕替尼原型及主要代谢产物暴露量均高于第1d。但Li等的研究发现,自服药第6d起阿帕替尼原型及主要代谢产物暴露量不再明显升高[17],提示阿帕替尼在体内虽然能抑制自身代谢酶的作用但并无药物蓄积。此外,Yu等的研究表明,在大样本量药代动力学研究方面,阿帕替尼在不同肿瘤中的药物代谢动力学过程不完全一致,尤其在胃癌中生物利用度较低[18],提示阿帕替尼对不同恶性肿瘤的治疗剂量应有所调整。综合以上实验结果可知,阿帕替尼在人体内并无药物蓄积作用,可分解为无毒性且易于排除体外的代谢物,但应针对不同肿瘤调整剂量。
3 阿帕替尼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应用
3.1食管癌 为探究阿帕替尼对食管癌的临床疗效及毒性反应,Li等研究设计一项临床实验,共入组62例经二线及以上治疗失败的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给予入组患者口服阿帕替尼(500mg/qd),若服药过程中发生3/4级不良反应则降低阿帕替尼用量为(250mg/qd)。研究结果中,完全缓解(completeresponse,CR) (n=0),部分缓解(partialresponse,PR) (n=15),疾病稳定(stabledisease,SD) (n=31) ,疾病进展(progressivedisease,PD) (n=16),客观缓解率(objectiveremissionrate,ORR)和疾病控制率(diseasecontrolrate,DCR)分别为24.2 %和74.2 %,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survival,OS)为209d(95 %CI:165~253),中位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survival,PFS)为115d(95 %CI:97~133),3/4级毒性反应发生率为(59.7 %)[19]。有趣的是,发生3/4级毒性反应的患者较没有发生3/4级毒性反应患者的中位PFS延长(136dvs63d,P=0.044)。结果表明,阿帕替尼对于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二线及以上治疗失败患者的临床效果确切,常见毒性反应为高血压、手足综合征及蛋白尿。樊超回顾性分析了2例晚期食管鳞癌三线化疗失败的患者,其中男性患者治疗方案为阿帕替尼(500mg/qd)联合替吉奥(40mg/bid),女性患者治疗方案为阿帕替尼(250mg/qd)联合替吉奥(40mg/bid)[20]。2例患者均在第30d进行疗效评价,影像学检查显示病灶均较前缩小达PR,且患者咳嗽、咳血、胸闷等症状明显好转,未见明显药物不良反应。阿帕替尼对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二线治疗失败的患者临床效果可靠,且无严重不良反应,但尚需更多实验探究其对早期或其他组织类型的食管癌的疗效。
3.2晚期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 阿帕替尼率先在胃癌及胃食管结合部腺癌中开展一系列临床试验,并取得阶段性成果。I期临床实验明确了阿帕替尼的人体最大耐受剂量为850mg/d,但为尽量降低副反应的发生率,故临床推荐剂量750mg/d[15]。基于此,Li等设计并实施随机平行对照的II期临床实验,入组144例患者均为二线化疗失败患者,随机分为A组(安慰剂组)、B组(阿帕替尼,850mg/qd)、C组(阿帕替尼,425mg/bid)。结果,A、B、C三组中位OS分别为2.5、4.83、4.27个月;三组中位PFS分别为1.4、3.67、3.2个月。B、C组分别与A组比较,无论是中位OS(P<0.001)还是中位PFS(P<0.001)均有显著差异[21]。Li等另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实验中,共入组270例经二线或多线化疗失败患者,其中实验组180例口服阿帕替尼850mg/qd,对照组90例口服安慰剂。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中位OS分别为195d和140d(P<0.016);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中位PFS分别为78d和53d(P<0.0001),两组ORR分别为2.84 %和0.00 %[22]。以上两项研究结果证实阿帕替尼对晚期胃癌确实有效,且不良反应可控,且该研究报告受到国际专家的认可,并在2014年ASCO会议上做口头报告。随后,为进一步验证阿帕替尼在胃癌中临床疗效,在2016年Li等开展的一项III期临床试验中,将入选的267例患有进展期胃癌或胃食管交界腺癌的患者随机分为阿帕替尼组和安慰剂组。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中位OS分别为6.5月和4.7月(P=0.0149);两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2.6月和1.8月(P<0.001)[5],证实了阿帕替尼对晚期胃癌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的确切疗效。目前,关于阿帕替尼治疗化疗药物耐受的晚期胃癌的IV期临床试验(NCT02426034)正在开展。一系列递进式的实验结果均显示了阿帕替尼单药在胃癌及胃食管结合部腺癌中的良好疗效。
为探究阿帕替尼在联合放化疗治疗中的疗效,井小会设计了阿帕替尼联合替吉奥一线治疗老年晚期胃癌的疗效,将42例入组患者随机分为A组和B组,其中A组给于阿帕替尼联合替吉奥治疗,B组单纯替吉奥治疗,2个周期后进行疗效评价[23]。结果显示,A、B两组有效率比较(47.62 %vs23.81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个案报道方面,周阳阳报告了阿帕替尼治疗晚期胃癌合并腹水4例患者,经口服阿帕替尼850mg/qd治疗后4例病人均能有效控制腹水且能维持较长时间,显示了良好的临床疗效[24];一项研究报道了口服阿帕替尼治疗两例化疗耐药的晚期胃癌患者,结果一例患者OS延长了7个月,另一例患者PFS达6个月,截自实验结束时仍在服药,且两例患者的病灶都不同程度的液化、缩小。以上结果均表明,阿帕替尼可使联合治疗的晚期胃癌患者获益,但尚需更多的研究加以验证及明确最佳剂量,以及可能发生的毒性反应及治疗措施。
3.3结直肠癌 为评估阿帕替尼对术前及术后常规放化疗治疗进展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效果,许翠洋等设计入组78例该类患者,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38例患者口服阿帕替尼500mg/qd,同期无差异对照组40例患接受中药支持治疗。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ORR(15.8 %vs2.5 %,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OS(5.28月vs4.22月,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PFS(2.25月vs1.47月,P<0.05),结果均有统计学差异[25],说明阿帕替尼可有效延长进展期结直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延缓肿瘤进展,且不良反应可耐受。Liang等针对难治性转移性结直肠癌(metastaticcolorectalcancer,mCRC)的回顾性研究中发现,36例患者中,1例患者CR,3例患者PR,24例患者SD,8例患者PD,ORR和DCR分别为11.1 %(4/36)和77.8 %(28/36),且患者自服用阿帕替尼后PFS和OS分别为4.8月和10.1月[26],表明阿帕替尼在难治性mCRC临床疗效良好,可使患者受益且不良反应可以接受。一项个案报道了直肠癌伴肺转移经二线及以上治疗失败的患者,给予口服阿帕替尼一周期(28d)后影像学评估有效,说明阿帕替尼对该类患者有效,且不良反应轻微。虽然,以上实验结果表明阿帕替尼在进展期结直肠恶性肿瘤中临床疗效值得肯定,但尚需开展更多的前瞻性随机对照实验加以验证。
3.4肝癌 临床实验中阿帕替尼在胃癌及结直肠癌中均取得突破性成果,而肝癌为我国最常见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为探究其在肝癌中的临床疗效。郑艳等近期研究了阿帕替尼在原发性肝癌(primarylivercancer,PLC)中的临床疗效,将60例晚期PLC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n=30)和对照组(n=30),研究组给予初始剂量为850mg/qd阿帕替尼口服,待症状好转后逐渐减量或至不可耐受毒副反应后停药,对照组给予安慰剂治疗。3个月治疗周期后,研究组与对照组ORR比较(36.7 %vs16.7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一年随访期后,研究组与对照组生存期比较[(7.65±1.52)vs(2.64±0.76),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常见不良反应发生率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27]。结果表明,阿帕替尼在PLC的临床效果良好,且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但在一项阿帕替尼对晚期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HCC)的前瞻性、随机、多中心的II期临床实验中,将入组的121例患者随机分为A、B两组,其中A组70例患者口服阿帕替尼(850mg/qd),B组51例患者口服阿帕替尼(750mg/qd)。A、B两组患者疾病进展时间((timetoprogression,TTP)分别为4.21月和3.32月,中位OS分别为9.71月和9.82月,ORR分别为10.0 %和2.0 %,DCR分别为58.6 %和64.7 %,上述各项指标比较均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28]。以上不同的实验结果可能为入组患者分期及不同的组织学类型所致,故临床暂不推荐阿帕替尼用于肝癌的治疗中,尚需进一步的实验加以明确。目前,阿帕替尼治疗晚期肝癌的III期临床实验已经启动,计划入组360例患者,主要终点事件为OS。
4 阿帕替尼在其它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对于一些发病率偏低,但预后极差的肿瘤类型,亟待有效的治疗方法提高患者的生存时间及生存质量。在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GIST)方面,芦淑娟等发现VEGF在GIST组织中的表达率为66.13 %[29],这为小分子靶向药物阿帕替尼治疗GIST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随后,Jin的一项I期晚期恶性肿瘤研究结果发现,在37例可评价疗效的PR为18.9 %(7/37),这7例患者中包括一例GIST患者,该患者在接受伊马替尼治疗失败后口服阿帕替尼,PR持续时间长达24月至实验结束时仍未出现疾病进展[17],表明阿帕替尼在GIST中可发挥一定的临床疗效。胰腺癌方面,庚同举回顾性分析了18例一线治疗失败后口服阿帕替尼的胰腺癌患者,21例对照组患者采用胰腺癌的标准化疗方案,分析两组患者的生存期,结果发现实验组中位OS为6.0月(95 %CI:5.17~6.84),对照组中位OS为5.5月(95 %CI:4.15~6.85),结果比较两组中位OS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30],说明阿帕替尼对胰腺癌一线治疗失败患者的临床疗效尚不肯定。一份个案报告了1例胰腺癌三线化疗失败的患者,采用阿帕替尼联合吉西他滨化疗6周期,结果显示患者仅维持疾病SD,效果亦不理想。因此,阿帕替尼对晚期胰腺癌的效果尚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加以验证。阿帕替尼可在某些罕见恶性肿瘤中发挥作用,但应在明确评估患者身体状况及权衡利弊后慎重使用。
5 阿帕替尼的常见不良反应及处理措施
阿帕替尼常见的3/4级不良反应为高血压、蛋白尿及手足综合征。此外,较少见的不良反应的有乏力、腹泻、恶心、呕吐、食欲降低、皮疹、疼痛、粘膜损害、肝脏损伤、感染、血液学毒性等[3]。
高血压是口服阿帕替尼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用药前尽量明确患者的基线血压,用药过程中尽量维持血压小于140/90mmHg,做到动态监测血压维持血压稳定,对于合并蛋白尿的患者推荐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convertingenzymeinhibitor,ACEI)类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receptorblocker,ARB)类,尽量避免使用非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剂,但也应遵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对血压正常患者,不推荐预防性使用降压药物。若患者服药过程中发生3/4级高血压,应在专科医师指导下用药或者调整阿帕替尼剂量直至血压恢复正常,若效果不佳则建议停药。对于发生高血压危象的患者,应立即和永久停药[17]。在一系列阿帕替尼的临床实验中,蛋白尿的发生率为44.36 %,其中3级蛋白尿的发生率为1.79 %。患者服药期间应定期检查尿常规,动态监测血压、肾功能及蛋白尿情况。对于肾功能不全患者应慎重使用阿帕替尼。目前,针对蛋白尿尚无特定治疗方法,可调整阿帕替尼剂量或暂停用药及酌情使用ACEI或ARB类药物,并坚持对症支持治疗。若患者出现肾功能损害或肾病综合征,应立即停药。阿帕替尼引起的手足综合征一般在服药2~3周后出现,初始时期不建议调整剂量或停药。服药期间应当做好手掌和足底的护理、避免机械性损伤、保持局部清洁、避免发生感染,可适当外用含有尿素软膏、5 %水杨酸制剂或皮质类固醇的润肤霜,并可适当口服B族维生素。若效果欠佳,可调整阿帕替尼剂量或暂停用药,若进一步加重则永久停药。
6 总结及展望
阿帕替尼作为国自主研发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基础研究证实其作用靶点为VEGF-VEGFR2通路。多个临床实验发现无论是阿帕替尼单药还是联合应用都对多种消化系统肿瘤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可使患者生存获益,尤其是在晚期胃癌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中的疗效已经得到III期临床实验的验证,且不良反应可控。但阿帕替尼对延长晚期恶性肿瘤的总生存时间的疗效上尚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佐证。此外,当前暂无有效指标用以筛选高敏患者和评价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