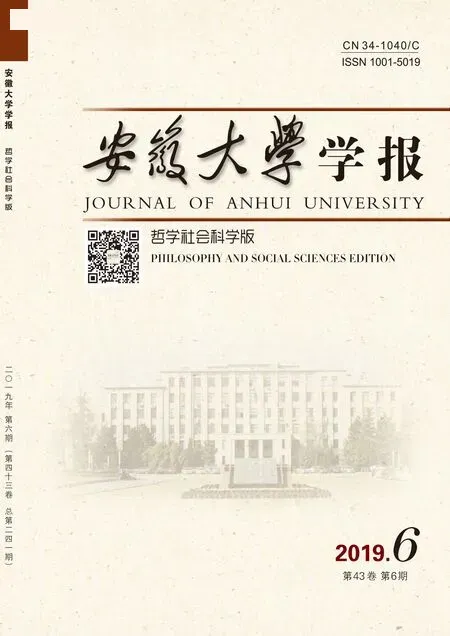论清代皖人宗族诗歌总集传统与文学世家建构
2019-11-18史哲文
史哲文
宗族研究以及家族文学研究是近来学界热点话题,宗族在血缘基础上透过宗谱、族规、家训、婚丧祭礼等一系列文本规范建立起稳定持久的伦理秩序,是古代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概念。历代名门硕族大都试图或乐于将自我塑造为诗礼传家的文学世家,以显示优良家风、风雅家脉与深厚家学。然而,文学世家之所以能够从普通宗族范畴中凸显出来,并非仅依靠上述族内规章文本而成立,还在于宗族成员文学创作与文脉承继的成就。宗族所纂文学总集,或称家集,正是汇聚文学创作与彰显世家传承的典范载体,其中以族人诗作为收录主体的宗族诗歌总集具有独特价值。有清一代,八皖诸多宗族绵延蕃盛,是缔造安徽文学乃至清代文学茂绩的必要基础,大量皖人宗族诗歌总集有待探讨。关于清代皖人文学世家的研究,前人论述不少(1)可参看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徐道彬《清代旅外徽商家族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贡献》、周成强《明清桐城望族诗歌研究》、宋豪飞《明清桐城桂林方氏家族及其诗歌研究》、汪孔丰《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桐城派兴衰嬗变研究》等论著。,一些论著对宗族文学总集也有一定涉及,值得钦佩的是徐雁平、张剑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清代家集丛刊续编》,洵为典籍大观,为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目前来看,以宗族诗歌总集为中心,从总集刊刻、辑纂、影响,以及宗族在总集辑纂中的自我认知与跨文学性的家声昭扬来观照清代皖人文学世家的建构,应还有一定论述空间。
一、地域与堂号:清代皖人宗族诗歌总集私家刊刻传统
清代刻书业发展兴盛,不但意在控制意识形态的官方刊刻发达,而且地方自发印刷更是层出不穷,较为突出的是私家刻书大量出现。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即在《中国书籍史及阅读史论略——以徽州为例》中认为,文学总集是家刻书籍内容除了宗谱外一个重要来源:“事实上,文学作品才是流传最广的作品,尤其是‘别集’(占了总数的半数以上)和‘总集’。它们通常是私家刻本。”(2)韩琦、[意]米盖拉:《中国与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9页。宗族文学总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刻书耗费较多,家刻文学总集体量也颇大,宗族文学总集有别于普通私刻书籍,并不以贩卖盈利为主要目的,意味着宗族须拥有足够资财、人工以及在当地卓著的声望影响,方能使得刊刻得以成行。另一方面,宗族注重薪火相传,而家刻文学总集能够真正在对家学、家风、家脉进行长期传承与总结中构建起世家的文学与文化面貌。马树华在《桐城马氏诗钞》中称:“树华慨然惧其久而愈湮也,爰有志搜辑,自嘉庆己巳至今丙申,垂三十年,乃取所得,谨加选定,编次成帙。”(3)(清)马树华:《桐城马氏诗钞》,《清代家集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14~15页。花费三十年方告编讫,可见工程规模之大。所以,常常只有累代传衍的文学世家才有能力与愿望进行宗族文学总集的刊刻活动,聚焦于清代皖省,以徽州府、宁国府、桐城县等地为宗族诗歌总集的主要刊刻地域。
徽州刻书自明代即有声名:“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州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4)(明)谢肇淛:《五杂组》,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1页。至清代徽州刻书业的传统更历久弥新。吴、程、汪、黄四家被称为“徽刻四大家族”,在明清徽州刻书业界享有盛誉。其中,程氏宗族瓜瓞绵延,分支众多,不仅是刻书世家,也是文学世家,清代程氏宗族有程鸿绪辑《程氏所见诗钞》二十四卷,为嘉庆十二年(1807)浣月斋刻本,收自魏晋至清代徽州程氏族人六百五十七人,其中清代三百四十七人占一半强。程鸿绪(1756—1814),字芑堂,号石琴,休宁人。程鸿绪本人即有《浣月斋诗存》《浣月斋印谱》。
程氏久有刻印文学总集的传统,早在明代,程氏宗族就有程敏政自刻汇集徽州诗文的《新安文献志》一百卷,蔚为大观,又辑宗族总集《程氏贻范集》三十卷,后程瞳再辑《程氏贻范集补》,“成化中,经筵篁墩先生编辑《程氏贻范集》正续二集,嘉靖峩山先生订《贻范集补》,吾宗文献典章,皇然大备”(5)(清)程鸿绪:《程氏所见诗钞》,嘉庆十二年刻本,序第1页。。程鸿绪在《程氏所见诗钞·凡例》中也说:“《程氏贻范集》《程氏贻范集补》所载诸宗哲题咏祖德、先业、祠墓、名迹,工拙备录,兹特简钞其概,以志仪型。”(6)(清)程鸿绪:《程氏所见诗钞》,凡例第2页。可见清代《程氏所见诗钞》与明代《程氏贻范集》《程氏贻范集补》一脉相承而来。程鸿绪在《程氏所见诗钞·凡例》最后两条中称:
国朝诗教极盛,吾氏名集如林。鸿绪僻处山乡,更无从遍采。兹凭所见古今诗,先刊初集,知不免呈一漏百,特启征诗。尚祈诸族彦,邮示家藏珠玉,续称完书,是所望也。
本集开雕,原在征启未发之前,所有同志君子因启到随付稿者,已谨登本集。至若道里遥阻,本集刊成,荷承瑶章,续赠者现在纂订二集,随到随编,俟容卷数汇齐,即行续刻,以备大观。(7)(清)程鸿绪:《程氏所见诗钞》,凡例第3~4页。
程鸿绪在凡例中说,征启发出之前已开始雕版,包括“俟容卷数汇齐,即行续刻”之语,也都表明了程氏宗族雕版刻印已驾轻就熟,早有刻书家法。而同样是在徽州的屏山朱氏,也有刊刻宗族诗歌总集的传统,其族人朱桓在《屏山诗乘二集跋》云:“念戊辰至今仅三十年,而予族两刊诗乘,非诗学渊源代有传人,诚不足以臻此。”(8)(清)朱镜蓉:《屏山诗乘二集》,《清代家集丛刊》,第564页。三十年内两次刊刻宗族诗歌总集,彰显出徽州文学世家的深厚脉系。
不但徽州当地宗族自刻诗歌总集,徽人迁居外地后,依然抱有刻印家集的习惯,甚至屡次刻版。如迁居扬州的江氏宗族有江振鸿辑《新安二江先生集》,扉页即有“嘉庆甲子开雕,康山草堂藏版”(9)(清)江振鸿:《新安二江先生集》,嘉庆九年刻本,扉页。字样。迁居嘉兴的朱氏宗族有朱之榛辑《新安先集》,凡例第一条云:
《新安先集》,道光乙未岁,先伯祖侍郎公刻于淮阴。咸丰辛亥,先君总宪公复刻于袁浦。嗣遭兵燹,先集版片散亡殆尽。之榛窃不自揆,思欲整齐废坠,重付剞劂,将先世各集汇为一编,而作者甚众,不敢妄为去取,乃断自昭代为始。(10)(清)朱之榛:《新安先集》,《清代家集丛刊》,第17页。
《新安先集》是休宁月潭朱氏迁于浙西族人所纂诗歌总集,与屏山朱氏虽为同源,但不属一支,朱方蔼、朱为弼即为此支。此支朱氏家族初迁桐乡,又迁平湖,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咸丰元年(1851)、同治十三年(1874)在淮阴、袁浦、苏州三次刻印宗族总集,正承继了徽州刻书悠久传统,而且第二次重刻因“手民疏率,字画浅剞,版易漫漶,只合重刻”(11)(清)朱之榛:《新安先集》,《清代家集丛刊》,第7页。,从反复雕版刊刻的过程中体现了朱氏宗族的凝聚性与持久性。外迁徽州宗族对前贤所留下的文学遗产不断追溯与总汇,也正是文学世家得以构建的心态所在。
前人研究清代皖省书籍刊刻常着眼于徽歙一带,其实不唯徽州,安徽其他地域家刻亦相当可观,宁国府即为其中翘楚。如宁国府治下青阳王肇奎辑《陈氏联珠集》十卷,为嘉庆七年(1802)华南书屋刻本,泾县董调辑《董氏诗系》十卷,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东门双桂斋汤鼎臣刻本,宣城梅清、梅冲辑《文峰梅氏诗略》二十卷,为道光五年(1825)敦睦堂刻本,泾县王鋈辑《泾川王氏诗辑》八卷,为道光十四年(1834)一本堂刻本等,皆为私家刊刻宗族诗歌总集的优秀范例。其中文峰梅氏较为著名,梅氏为宣州望族,又分宛陵梅氏与文峰梅氏二支,“五代时远公始迁宣城,数传至圣俞,族属已繁。宋淳熙间,太七公始迁柏枧南庄,八世而渐盛,十一世而人文蔚起”(12)(清)梅寿康等:《文峰梅氏宗谱》,光绪十八年刻本,序第3页。。自北宋梅尧臣,至清代梅庚、梅清、梅文鼎等,蔚为望族,桐城派中兴名宿梅曾亮为此支又迁往金陵的后人,其著《柏枧山房全集》即指祖居之柏枧山。梅清在《文峰梅氏诗略·书诗略后》云:
曩岁丙午,族三修家乘,属余谬首其事,群从载笔者十人,计阅两载,中间搜采艺文,得诗稿五十五种,维时同事群从,朝夕商酌,乃建《梅氏诗略》之议。谓七十载之谱牒不可不修,五百年之风雅流传亦不可不辑。盖家谱与诗略,人物文章,世相表里,交藉为不朽盛事甚哉。……诸子集分前后,先亡而后存,前集得人一百有八,分卷十二,已付剞劂,后集当于来岁成之。(13)(清)梅清:《文峰梅氏诗略》,《清代家集丛刊》,第11~13页。
表面上,《文峰梅氏诗略》是编修宗谱的衍生物,诗歌总集前列有世系,标明辈分、科名,梅清也将家谱的意义赋予诗歌总集。但是“盖家谱与诗略,人物文章,世相表里”,刊刻宗谱只能展现宗族血缘世系,梅清直言宗谱与诗歌总集是表里关系,也就说明其更为重视宗族诗歌总集的编刻。究其原因,就在于梅氏宗族只有通过家刻诗歌总集内化家族文脉,才能够使得文学世家之名令人信服。“五百年之风雅流传亦不可不辑”,也体现出强烈的自觉信念,从私家刊刻可以清晰看出宣城梅氏文学世家得以构建的内在动力。
长江以北的桐城家刻也很发达,《中国印刷史》特别指出清代安徽私家刊刻“以旧徽州府……六县及桐城为盛”(14)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1~713页。,桐城世家巨族不必多言,方氏、马氏、张氏、姚氏、刘氏等绵延数百年,皆有家刻总集传世。张氏有张曾虔辑《讲筵四世诗钞》自刻本,吴贻咏在《讲筵四世诗钞》序中即有“蠡秋将携家集刊于江宁”(15)(清)张曾虔:《讲筵四世诗钞》,光绪十二年重刊本,序第11页。之语,蠡秋为张曾虔号。方氏有方观承辑《述本堂诗集》本堂刻本,又有方于榖辑《桐城方氏诗辑》饲经堂刻本,《述本堂诗集》录方登峄、方式济、方观承一房直系祖孙三辈,与方于榖《桐城方氏诗辑》相异的特点是强调直系血缘。马氏有马树华辑《桐城马氏诗钞》可久处斋自刻本,《桐城耆旧传》载:“(马树华)辑《马氏诗钞》七十卷,编定……族谱、家传共数十卷,其自为书曰《可久处斋诗文集》,各八卷,皆已刻。”(16)(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彭君华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372~373页。宗族自刻并非一时之兴,而是持续性刊刻行为。这些宗族自刻其族人诗歌总集的用意之一,即在刊刻上显示出本宗族物力富足,不需要借助于书坊刊刻,这种对宗族实力的自信也正是文学世家在声望地位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剪影。
从各家刻堂号含义的角度而言,更能看出普遍意义上宗族对亲缘维系的期望与文学世家的底蕴。文学世家常以堂、斋、楼、轩、馆、居、山房等为家刻堂号。徽州朱熹后人以“崇道堂”为家刻堂号,于明清两代反复刻印朱子著作,在明代即刊刻《五经四书》十种一百零七卷,崇祯十四年(1641)朱氏后人刊刻《五经四书》,“版心有‘文公祠崇道堂藏版’8字,说明是朱熹后人家刻本”(17)[意]米盖拉、朱万曙:《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71页。。家刻书籍常常被理解为显示个人著书成绩与家族渊源地位的一种行为,徽州朱氏宗族反复刊印朱熹著作,标举对先贤的追慕与家学承递。
需要注意的是宗族堂号、家刻堂号、文人室号之间的差异,宗族堂号与家刻堂号概念不同,如潜山熊氏《赐墨堂家集合编》中“赐墨堂”与“性余堂”,又如刘萃和《澄响堂五世诗钞》中“澄响堂”与“逸心山房”,前者为宗族堂号,后者为家刻堂号,有时二者又共用一个堂号,如《述本堂诗集》明言是本堂刻本。而家刻堂号与常见的文人室号、斋号亦有重合之处,如新安程氏“浣月斋”、全椒薛氏“藤香馆”合家刻堂号与文人室号为一,但又有所不同,文人为自己居住、写作空间如书房、书斋命名,具有个体性与随意性,而家刻堂号代表一个宗族的价值取向,具有群体性与稳定性,如上文徽州朱氏刻书所用堂号“崇道堂”延续明清两代,桐城方氏堂号“述本堂”沿用三代,成为宗族的象征符号。
敦睦堂、述本堂、一本堂这类堂号是宗族家法中世代修睦、忠孝念本等意蕴的凝练表达。敦睦一词也被多个宗族立为族训家法。无独有偶,徽州婺源《龙池王氏家族家法》便以敦、睦二条为家法起首,文曰:
敦孝友。《书》称:“君陈孝于亲,友于兄弟。”夫子称之曰:“是亦为政。”盖家国无二理也,况吾家本孝友信义之门,先世遗训具在,为子孙者,宜世守勿失。苟有故于长上,先责以理。抗而不服者,闻诸公庭,依律治之。
睦宗族。昔张公艺九世同居,范文正公置义田以收宗族,二公高谊,至今深人向往。凡事以逊让为是,不可因小忿伤大义:又况保守身家之道,正在慎之于始。(18)卞利:《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225页。
《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序》亦载:“用能慈孝敦睦,守庐墓,长子孙,昭穆相次,贫富相保,贤不肖相扶持,循循然,彬彬然,序别而情挚。”(19)赵华富:《徽州宗族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而诸如“述本”“一本”意在告诫族人不可忘本之类词语在宗族家法中就更为常见。
而桐城方氏以“饲经堂”为家刻堂号,马氏以“可久处斋”为堂号,更偏重于对其儒学世家的彰显。桐城方氏自明代便专精经学,形成独具特色的家学风貌,方学渐、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方中通、方中履、方式济、方贞观、方苞等人影响到明清学术史走向。马氏之“可久处斋”亦是同理,“可久处斋”之号应出自《论语·里仁》:“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冠之“可久处”而蕴涵以仁治家、以儒兴族之意。我们知道,儒学强调入世,重视儒学在古代传统社会中也意在对科举的重视。清代方氏、马氏子弟科举显赫,单论进士,方氏进士二十二人,马氏进士五人,人数虽不多却不乏名士,如马教思,字临公,号严冲、檀石,康熙十八年(1679)会元,精通勾股九章。马宗琏(?—1802),字器之,又字鲁陈,嘉庆六年(1801)进士,从姚鼐学文,从邵晋涵、任大椿、王念孙等人考辨训诂,著《左传补注》《周礼郑注疏证》《谷梁传疏证》《说文字义广注》《战国策地理考》等。马瑞辰(1782—1853),字元伯,马宗琏之子,嘉庆九年(1804)进士,选庶吉士,以《毛诗传笺通释》著称于世,《清儒学案》载:“先生少传父业,为训诂之学,老而不倦。……撰《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以三家辨其异同,以全经明其义例,以古音古义证其讹互,以双声叠韵别其通借。笃守家法,义据通深,同时长洲陈硕父奂著《毛诗传疏》,亦为专门之学。由是治《毛诗》者多推此两家之书。”(20)徐世昌等:《清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448页。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清代二百余年间,桐城进士也仅有一百五十三人,而方氏、马氏族人诸如举人、诸生之类就更加数量庞大了。故以五经四书之典命名家刻堂号,除了对家族文化的自信表达,亦呈示出对科举世家、儒学世家的标榜。
家刻堂号昭示文学世家的典雅,可以视作世代宗族构建中一个象征符号。古人将家集付诸梨枣,有将国史付诸汗青的同理心态,清代皖人热衷刊刻宗族诗歌总集,此类行为不同于商业刻书,而是宗族世家血缘凝聚的体现。因此,从私家刊刻的视角来看清代皖人宗族诗歌总集,我们可以借以了解清代皖省文学世家不太被人关注的一面。
二、“吾家事”到“家人言”:宗族诗歌总集的诗教训诫与家风承继
早在唐代,杜牧即云:“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可与尔再读,助尔为贤良。”(21)(唐)杜牧:《杜牧集》,罗时进编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0页。罗时进先生评价道:“这是一篇用诗笔写成的‘杜氏家训’。作者从‘家史’‘读书’‘文学’‘人仕’‘德行’‘财货’各个方面劝导和鼓励小侄勤勉奋发,明辨笃行,青云直上。”(22)(唐)杜牧:《杜牧集》,罗时进编选,第34页。此处“家集”指杜佑所撰《通典》,而后世的家集通常指裒辑宗族内部成员所作诗文的集合。在家集范畴中既有文章总集又有诗歌总集,相较于收录内部人员骈散文、尺牍、奏议等的宗族文章总集,宗族诗歌总集独特价值之一就在于以诗教传递家风的文学伦理观。
宗族诗歌总集的编纂,以及在诗作中所体现出的向宗族内部训诫的意义促进了宗族作为社会群体的建构,呈现一种复合的家族文学内蕴。从内向性的承继诗礼传统来说,方楘如《述本堂诗集》序云:
始读少陵“诗是吾家事”语而疑之,何大而夸若是?偶以念至则固先师遗训也,抑诗教也,鲤庭之趋不闻曰学诗乎?而子夏序《诗》谓先王以是成孝敬、厚人伦,人伦孝敬非家事而何?……于戏!此《述本堂三世诗》之刻不可以已也。……其可以成孝敬而厚人伦,固三代共之也,则以为是家人言,即以为是吾家事。(23)(清)方观承:《述本堂诗集》,《清代家集丛刊》,第7~9页。
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也注意到这段话,他在此书导论中认为:“‘诗是吾家事’在世家文学传衍过程中,近似一种神圣的信念。”(24)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页。但其并未说明为何神圣,其实,古人作诗论诗大凡以杜诗为正体,方楘如将杜甫“诗是吾家事”诗句与宗族诗歌总集二者合而谈之,无疑从诗学正统的角度对宗族编纂诗歌总集加以肯定,翁方纲即云:“研求忠孝,必自杜诗始耳。”(25)(清)翁方纲:《复初斋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8页。而序文中引孔子训教其子孔鲤学诗之隶事,恰又将宗族编纂诗歌总集的意义上升到儒家伦理高度,确立其典范性。
诗教与家风在传统社会中是形影不离且互相影响的两个概念,兴观群怨诗教观要求“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从家风衍生出的孝父尊君观念便是诗教的意义之一。在宗族诗歌总集中,接连入眼的诗章是对宗族内部亲缘的书写,无外乎四个方面。以诗人个体为中心,从一族来说要孝礼长辈,恭敬兄弟,在一家来说要和睦夫妻,敦育子女。《桐城马氏诗钞》内有马孝思《屏山诗草》,在其诗作内对亲缘关系有清晰描述,马孝思,字永公,号玉峰,马之瑛次子,《桐旧集》收诗二十首。马孝思与长辈特别是方文感情敦笃,“在先辈中与嵞山最近,盖翁婿论诗甚相契合也”(26)(清)马树华:《桐城马氏诗钞》,《清代家集丛刊》,第553页。,在方文去世时,有诗而感:
外舅即岳父,马孝思娶方文长女。同时马孝思也与兄弟姊妹关系感情至深:
多情留客度寒天,信是人称内外贤。同爨未闻羹可戛,共眠常觉被相连。漫嗟马枥难酬志,自有狐裘足记年。今日一尊诸弟劝,庭前遑问酌谁先。(《寿大兄初度》)(28)(清)马树华:《桐城马氏诗钞》,《清代家集丛刊》,第554页。
马孝思兄弟六人,大兄即指马之瑛长子马敬思,在以上二首诗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方氏、马氏等几个桐城世家的姻娅关系直观反映在诗中。
从一家内部来说,怜妻教子是其诗作重要表现内容,马孝思对妻子的感情更多的是因家贫而透露出怜爱与歉意:
秋声从未出深闺,合是梁生操作妻。月照窗前槐影乱,霜侵槛外竹枝低。身因小病朝慵起,儿为长饥夜惯啼。今日阁中邀女伴,半分脱粟半黄齑。(《内子初度二首》其一)(29)(清)马树华:《桐城马氏诗钞》,《清代家集丛刊》,第562页。
草阁连朝客到空,闲眠贪爱竹窗风。面黄怜汝将成媪,头白嗟予已是翁。小病岂关无肉瘦,长贫莫怪以诗穷。鹿门自昔堪偕隐,况复衰残在眼中。(《偶作示内》)(30)(清)马树华:《桐城马氏诗钞》,《清代家集丛刊》,第583页。
前首谈及妻子生日邀请女伴来做客,却只能以粗粮与咸菜招待,歉意不言自明,而后首更是直接抒发对妻子不嫌家贫,能够偕隐相随的感激。马孝思对待妻子展现柔情一面,对待后代则显示出诗礼传家的优良家风:
敢说藏书三十车,乱余犹未失张华。寒儒膏火窗前雪,浮世簪缨镜里花。对客最嫌狂作态,爱儿勿令蚤传家。许多年少营生理,懒弄丹铅实可嗟。(《训子》)(31)(清)马树华:《桐城马氏诗钞》,《清代家集丛刊》,第583页。
是花人皆爱,汝爱在海棠。年年阿姨家,带蝶移茅堂。瓦盆三四丛,一一手自将。此花异众卉,宜雨偏忌阳。……阿翁于此诗,一咏复一觞。翁意别有属,于汝却相防。杜陵精文选,范家理墨庄。有儿勤读书,身老无愁肠。愿言息此劳,努力穷缥缃。芝兰与玉树,奇葩益芬芳。(《为幼儿种花作》)(32)(清)马树华:《桐城马氏诗钞》,《清代家集丛刊》,第587~588页。
世家巨族常以科举功名来论定声望地位,马孝思却另有见解。前首表明在俗世中簪缨仕宦自然是美事,但官位有时也只是镜中之花,一心求取功名反而容易失去自我,“寒儒膏火窗前雪”才是实学。更为重要的是家族稳定延续,马孝思在诗中也告诫儿子力戒年少轻狂,不可溺爱后嗣,特别要在读书稽古上下功夫。相比前首敛颜训示,后首更有趣味,马孝思指导幼子植种海棠,娓娓道出海棠的习性。至后半段则为之一转,提出种花虽美,但须勤学诗书,方能芝兰玉树,焜耀家门。
马树华在《桐城马氏诗钞》辑录此类诗作数量颇多,其潜在用意无疑是向子弟传递宗族以孝悌为法的信息,而马树华本人也正以孝立身,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对马树华孝行记载云:“太恭人性洁,晚年病脾,泻利一夕数十起,公终宵在侧,不令少有沾污。太恭人每叹:‘孝哉吾子,乃使我不为病苦也。’”(33)(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第373页。因此,前文《桐城方氏诗辑》序文中谈到“诗是吾家事”的内涵即在马氏宗族这里得到很好的体现,宗族诗歌总集以家人之言入诗,也就是“以为是家人言,即以为是吾家事”了。以《桐城马氏诗钞》为例,宗族诗歌总集对宗族内部的训诫意义就通过诗教方式传达给了世代子孙。
位于徽州的屏山朱氏,其宗族诗歌总集也在诗作中呈现出家风淳朴的面貌。在朱镜蓉所辑《屏山诗乘二集》中,所展现的不仅是内部亲缘的书写内容,更是名门之后家风的呈示。朱镜蓉,道咸时人,字和甫,一字普康,自号小懵,师从名儒朱骏声。朱骏声与朱镜蓉虽然同姓,但是朱骏声为元和朱氏,朱镜蓉为屏山朱氏,不属一脉。朱骏声在《屏山诗乘二集》序文称:
大抵一门之内,文采风流,辉暎后先,具有足传于世者。屏山朱氏,为晦翁裔孙,辞章学问,代有渊源,多巨人硕士伏海内,虽潜德弗彰,而流风余韵于兹未坠。……和甫舍人善承家学,念笃宗亲,或录诸楹书,或访诸蓬箧,就名山之业,成一家之言。故家文献,蔚为巨观,佳士名篇,缀于后劲。(34)(清)朱镜蓉:《屏山诗乘二集》,《清代家集丛刊》,第479~480页。
这里“一家之言”就不再是一人之言,而是一家族之言。屏山朱氏为朱熹后代,此处大略梳理屏山朱氏源流。据《朱氏正宗谱》,朱熹第三子名在,字敬之,于南宋官至工部侍郎,宝庆三年(1227)迁居建安。朱在生四子:铉、铸、铅、钦。其中第三子朱铅,字子容,又生三子:泽、澋、清。族人朱春应于嘉靖九年(1530)所作《黟屏山朱氏重修宗谱序》云:“文公季子在公,在公季子铅公,铅公生三子,其仲则我祖澋公也。”(35)王铁:《中国东南的宗族与宗谱》,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96页。朱澋宋末任饶州签判,彼时蒙元南下,朱澋遂寓居鄱阳。澋生莱,莱又生庆,朱庆为避兵燹,举家迁居黟县,其地有山如屏,故名屏山朱氏,朱庆即为屏山朱氏祖。朱镜蓉不仅纂辑《屏山诗乘二集》,还重修宗谱,同样请朱骏声作序,收于其《传经室文集》,朱骏声在《屏山朱氏重修支谱序》中说:
黟屏山朱氏为文公后。……余尝谓谱之废,废于贫且贱者十之三,而废于富且贵者十之七。富者或耻其家世之微,则攀援著姓而强附之。贵者或傲焉,忘先世遗泽,虑族之贫者觊觎其锱铢,则唯恐远之不速也。夫富者既强附人之宗,而贵者又思远其宗,于是谱虽存而实亡。今屏山之成是谱也,子姓各受一部藏于家。部各有字识,乃别编字号为总册,书某号谱、藏某裔、庋诸祠,以备考覈则庶乎。非吾宗者不得附是,吾宗者不得远无,前言之弊可以永永传示子孙法,不尤尽善欤?其族之人多有声于庠,规言矩步,无忝名家子,继继绳绳,昌炽殆未有艾也。(36)(清)朱骏声:《传经室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8页。
宗谱中严肃的族规家法体现出宗族传衍有序,特意强调不可因富贵而忘本。从宗谱一脉而承的家风在《屏山诗乘二集》也有体现,如集内载朱元礼,字敬斯,乾隆九年(1744)贡士,“族邻口角,曲为劝解,不喜人争讼,修桥造路,功德及人者远矣”(37)(清)朱镜蓉:《屏山诗乘二集》,《清代家集丛刊》,第479页。,有诗《村居》,其一云:
绿破春郊雨乍干,麦田风细锁轻寒。老妻颇解归农意,学煮青蒿啖牡丹。(38)(清)朱镜蓉:《屏山诗乘二集》,《清代家集丛刊》,第518~519页。
淳厚家风跃然纸上,又如朱启声,字宣和,号律堂,邑庠生,有诗《田家》云:
纳罢税粮剩买衣,三冬妇子共炉围。桑麻朋好情相得,淡泊家风梦自稀。山径无人村犬卧,园蔬落子野禽肥。香秔酿酒家家醉,不管门前雨雪霏。(39)(清)朱镜蓉:《屏山诗乘二集》,《清代家集丛刊》,第524页。
此诗描述冬夜合家团聚的和睦场景,徽州多山,土地贫瘠,故而纳毕税粮后一年所得剩余无多,不过诗人毫不为意,“淡泊家风梦自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为纷繁世事所扰,追慕功名富贵,为虚浮所累,岂能安眠稀梦?《论语·卫灵公》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朱熹在《朱子家训》云:“随所遇而安之。……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40)朱世良:《徽州月潭朱氏》,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8页。从屏山朱氏家谱、家训到家集,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崇礼家风清楚地展现出一致面貌。
所以,宗族诗歌总集通过诗教传递优良家风,宗族繁衍不息,子孙有礼守节,从而维护宗族秩序稳定,“在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41)[美]W.古德:《家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66页。,宗族守序有力促进了社会安宁。在《屏山诗乘二集》中,虽然并没有直接言语表达对族内子弟训诫,但是家风承续有自,虽然是对日常生活寻常描述,但是举手投足间潜泳的家风内容自现其中,以诗化人,这也正是传统诗教所认同的温柔而敦厚的思想内涵。
三、“岂徒备纪一家章句”:宗族诗歌总集的家声昭扬与跨文学形态
外向性的昭扬宗族荣耀与文学声望,不仅是清代皖人宗族诗歌总集,也是几乎所有宗族诗歌总集的另一面存在意义。一些宗族影响局限于一地,如许新堂辑《桐城许氏一家集》中称:“人之家学厚且茂哉。”(42)(清)许新堂等:《桐城许氏一家集》,《清代家集丛刊》,第11页。而姚鼐作桐城刘氏《澄响堂五氏诗钞》序云:“桐城以宦学垂六百年之旧家,刘氏其一也。……子孙能传其先业,使人得见其先祖之美,不因以卜其子孙之贤哉!刘君萃和……谋刻其先人五世诗集而乞叙于余……余受而读之,窃见前辈典型涂辙。……信足为世言,诗家之楷范。若此集遂行,固艺苑所乐推,而岂独闾里之盛美也。”(43)(清)刘萃和:《澄响堂五世诗钞》,《清代家集丛刊》,第527~535页。在这两种非全族诗歌总集中,其自我夸耀程度显然不及那些更为庞大的全族诗歌总集气势强烈。
这种昂然的自我认同心态在《程氏所见诗钞》中,体现尤为明晰,其序中亦颇有推挹之意:
吾程氏迄今千五百年,其间理学、经济、文章,彬彬然代有其人,至宋元明益称极盛。……成化至今三百年,人文之盛,不异曩时。……在朝固期铭勋简册,在野亦宜阐发幽微,使千载下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则是集也。岂徒备纪一家章句,传诵一时哉!(44)(清)程鸿绪:《程氏所见诗钞》,嘉庆十二年刊本,序第1~2页。
徽州程氏绵延竟达一千五百年,桐城许氏、刘氏显然无法匹及。在序文对前贤追溯话语中,无论在朝抑或在野,并不因世俗地位来区分高下,而是以宗族为一个整体显示家声。需要注意,“岂徒备纪一家章句,传诵一时哉!”直接点明《程氏所见诗钞》不只是文学作品的集合,而是已超出文学意义,成为向后世显扬宗族声名的文化载体。与徽州朱氏《屏山诗乘二集》“成一家之言”相比,程鸿绪对宗族诗歌总集已有更为深远的理解。
又如桐城方氏,汪志伊《桐城方氏诗辑》序云:
吾乡方氏以忠孝文学闻天下,垂三百年矣。……文章为治乱之符,忠孝为性情之本,观于是集,不益信哉?辑中明世诸公生逢世乱,变起君父之间,身当国家兴亡之际,故其诗愤而多感,踔厉悲凉,使读之者犹想见其遭时多难而发乎忠孝,旁魄勃郁不能自已之心,百世下如或遇之。……今而称古岁时俦,与讴歈愉愉,无复悲愤激烈之意,非以所遇之时为之耶?虽然人以德行政事著,不必其有诗也,而忠孝存焉矣。诗不必皆言忠孝也,而忠孝存焉矣。夫顺之则平,逆之则鸣,虽以所遇而异,而其性情之法乎忠孝也,岂有异哉?然则是辑也,传其一家之诗,即谓其家忠孝文学俱传于是可也。存其一家之风气,即谓数百年治乱之故俱存是可也。(45)(清)方于榖:《桐城方氏诗辑》,《清代家集丛刊》,第3~5页。
突出强调方氏宗族的忠孝典范,已经超越“吾乡”而“闻天下”,方受畴作《桐城方氏诗辑》后序亦云:“吾宗自三代以来,世有闻人,其彪炳于史书者,元老壮猷,媲于周召。……国朝崇文振雅,擅燕许之笔,主坛坫之盟,雍容揄扬,风骚继述,负海内之望者,惟吾宗称甚盛焉。”(46)(清)方于榖:《桐城方氏诗辑》,《清代家集丛刊》,第7页。明显表明方氏宗族已不以一地之名望为限,而是以“世有闻人”“负海内之望”更大范围为豪。在这个意义上说,《桐城方氏诗辑》就超出了文学作品范畴,而体现出跨文学性的,更多的是起到社会性的彰扬作用。
诚然,这种对家声的昭扬,一方面是自豪而发,然而另一方面则是自尊使然。马树华辑《桐城马氏诗钞》在《桐城方氏诗辑》刊行十五年之后问世,方东树在《桐城马氏诗钞》序云:“近方氏子孙始有辑方氏诗者,乃合一族之作者,而全萃之人至百余,诗至数千,可谓富矣。余又尝为刘氏序《澄响堂四世诗》,为吴氏序《芸晖馆四世诗》,然皆第私其祖祢,未及旁宗。今吾友马君公实辑马氏诗,成七十卷,作者六七十人,合选诗四千余篇,乃遂与方氏埒矣。”(47)(清)马树华:《桐城马氏诗钞》,《清代家集丛刊》,第6页。方东树认为刘氏《澄响堂四世诗》与吴氏《芸晖馆四世诗》皆仅一房之诗,不足为称,而《桐城方氏诗辑》与《桐城马氏诗钞》则裒聚全族,蔚然可观。徐雁平则认为,方氏、马氏竞相编纂宗族诗歌总集类似于一种在不同家族间进行的“比赛”。固然,在时间先后上,存在马氏比照方氏编纂的竞赛可能,但从马氏宗族自身来说,在“比赛”表象之下,其实是宗族世家的自尊感与认同感使然。马树华在《桐城马氏诗钞》中说:
吾家自四世祖肇兴文学,六世祖太仆府君为时名臣,一门群从,彬彬汇起。七世八世间,遂有“怡园六子”。而八世伯祖兵部府君《秫庄集》尤为巨制,自是风雅代不乏人。……《明诗综》录吾邑二十余人,吾家阙如。《别裁集》亦仅载相如先生三诗,幽隐弗宣,若合一辙。岂不以先世类多厚重,不急务名誉而然耶?(48)(清)马树华:《桐城马氏诗钞》,《清代家集丛刊》,第14页。
他清楚地交代了桐城马氏一门文学渊源与传承,展现了马氏宗族在桐城当地的文学世家面貌,而马序中亦称《明诗综》与《清诗别裁集》对桐城马氏诸人诗作的忽视,激起了马树华为马氏宗族鸣不平的自尊心,可以说是他辑《桐城马氏诗钞》的直接原因。无论是对方氏编纂宗族诗歌总集的“比赛”行为,还是对朱彝尊、沈德潜在总集中遗漏马氏族人的不平之鸣,都反映出马氏宗族的自我认知与世家心态,所以朱为弼《桐城马氏诗钞》序云:“予先世与桐城有姻,夙闻龙瞑故家,文学之盛,马氏其一也。……此钞既成,岂唯一家之美,实足征一邑文学之盛。”(49)(清)马树华:《桐城马氏诗钞》,《清代家集丛刊》,第3~4页。这就彰显宗族外在声望已经不仅局限于本宗族,更关乎所在地域文学发展。
在仕宦功名上更胜一筹的桐城张氏,甚至让其他地域之人有嫉妒不平之音。近人孙师郑在《古里瞿氏四世画题词》序中说:“往者桐城张氏有《讲筵四世诗钞》之刻,然不过人爵之荣耳。”(50)仲伟行、吴雍安、曾康:《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9页。常熟瞿氏家族以累代藏书著称于世,但族人始终未能高登庙堂,此处序文虽含亦讥亦羡之意,但也承认张曾虔辑《讲筵四世诗钞》焜耀家声的意指。《晚晴簃诗汇》亦称:
桐城张氏文端、文和二公以继世之章、平,作中朝之魏、丙。弟昆子侄,竞爽交辉,橿庭弟蠡秋曾虔,辑文端至橿庭四世十人应制之诗,为《讲筵四世诗钞》,石君、覃溪、宾谷诸公为作序,故家乔木,地望犹存,巨集联珠,国华益广,诚承平之盛事也。(51)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56页。
张曾虔,字吕环,号蠡秋,张若需四子,廪生,官宿州训导。清代桐城张氏自张英以下,四世讲筵,在宦绩上为其他桐城宗族所无法逾越,将集内各人生平略列于此:
张英,字敦复,号乐圃,康熙六年(1667)进士。十二年(1675)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二十五年(1686)授礼部侍郎,兼管詹事府,充经筵讲官。官至礼部尚书,康熙三十八年(1699)拜文华殿大学士,谥文端,雍正时赠太子太傅,乾隆时加赠太傅。
张廷瓒,字卣臣,号随斋,张英长子,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授翰林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先于张英去世。
张廷玉,字衡臣,号砚斋,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雍正四年(1726)拜相,历文渊、文华、保和三殿大学士,太子少保,加太保,封三等勤宣伯,谥文和。
张廷璐,字宝臣,号药斋,张英三子,康熙五十七年(1718)榜眼,官至礼部侍郎,督江苏学政。
张廷瑑,字桓臣,号思斋,张英五子,雍正元年(1723)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张若潭,字紫澜,号澂中(52)据张体云《张廷玉年谱》,张若潭字号记载存在出入,《张氏宗谱》载:“若潭,讳廷臻子,字紫澜,号澂中。”《道光桐城续修县志》载:“张若潭,字徵中,号鱼床。”权以宗谱记载为准。,张英四子张廷之子。乾隆元年(1736)进士,乾隆九年(1744)授检讨。
张若需,字树彤,号中畯,张廷璐次子,乾隆二年(1737)进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官至翰林院侍讲。
张若霭,字景采,号晴岚,张廷玉长子,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张若澄,字镜壑,号默耕,张廷玉次子,乾隆十年(1745)进士,授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张曾敞,字恺似,一字廓原,号橿亭、橿庭,张若需子,张曾虔长兄,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授检讨,官至詹事府少詹事。
张氏世系簪缨之蝉联,世所罕见,此支张氏也因备受恩荣,被称为宰相张氏,桐城又有连城张氏,源流不同。《讲筵四世诗钞》所收诗篇皆为应制诗,摘录张英一首:
辇驻甘泉水殿中,清秋时节御堤风。欢承慈圣重闱喜,恩逮群工曲燕同。珍果摠含兰蕙露,嘉鱼新出藕花丛。联翩簪佩蓬池上,影落平桥潋滟红。(《七月二十一日瀛台赐宴诸臣特命臣英同内大臣主席恭纪二首》其一)(53)(清)张曾虔:《讲筵四世诗钞》卷一,光绪十二年重刊本,第20页。
并且,张曾虔在集内张氏各人诗前又附圣旨、召见等事迹,如《讲筵四世诗钞》卷八载张若霭“丙寅扈从西巡,归途患病,上命御医调治护视,回京病笃,上遣内侍日赐询问。卒之次日,奉特旨,着加恩照伯爵品级,赏银一千两,料理丧仪……特遣礼部左侍郎邓钟岳,赐祭于邸寓”(54)(清)张曾虔:《讲筵四世诗钞》卷八,光绪十二年重刊本,第2页。。诸如此类显耀恩典的话语在集中多有所见,从而证明了这些诗作并非因文学性而存在,张曾虔辑选这些应制诗也显然不关注其文学性,而是类似于作为对皇恩的见证材料,成为家族荣光的象征。进一步论之,也就说明《讲筵四世诗钞》的编纂更多意味着对家族显赫宦绩的炫耀,包括集名特意标出“讲筵四世”,可谓荣光之至。朱珪《讲筵四世诗钞》序云:“父子入相,一门鼎贵,人各有集,兹册之编,标衔汇次,尊经筵之巨典,尚讲幄之渥恩,以示子孙,光纪载可谓盛哉!”(55)(清)张曾虔:《讲筵四世诗钞》,光绪十二年重刊本,序第1页。但是他们平日诗作却并非如此面目。如《桐旧集》卷二十二录张廷璐《南归》二首,其一云:
廿载劳人得赐闲,故园风景隔尘寰。潆洄马鬣双溪水,层叠龙眠万笏山。屐履独寻新藓径,烟云仍护旧柴关。林泉潇洒无拘检,大似开笼放白鹇。(56)(清)徐璈:《桐旧集》卷二十二,咸丰元年刻本,第10页。
这种如脱笼之鸟的舒畅心绪与应制时的强作欢颜大相径庭,朝臣归乡之时所赋诗作亦多有此类。《桐旧集》卷二十三又录张曾虔《石门寓斋坐雨和四兄讷堂韵》云:
兄弟天涯百感生,归期遥滞御儿城。寒鸦恋树窥霜信,落叶临窗杂雨声。衣薄乍惊风有力,愁深但觉酒多情。当时亲旧如萍散,争逐轻帆又远征。(57)(清)徐璈:《桐旧集》卷二十三,第24页。
《皖雅初集》亦录张曾虔此首,但“愁深但觉酒多情”句作“愁深未觉酒多情”,似更有寄意。与应制诗相比,宗族内部张曾虔与四兄唱和诗篇文学价值显然高得多了。张曾虔异乡为官,复纂《讲筵四世诗钞》以示宠渥,而自己在复杂人生处境影响下,诗中又是一番厌倦仕途的思乡心绪,心态值得体味。
刘权之《讲筵四世诗钞》序称:“国朝科第簪缨之盛,首推江左。江左之虞山蒋、锡山嵇、桐城张,皆业继韦平,凤池济美,若鼎峙然。其尤盛者,则首推桐城,盖四世十人,或衔列经筵,或身依讲幄,荣遇萃于一门。”(58)(清)张曾虔:《讲筵四世诗钞》,序第11页。从科举仕官层面道出皖人世家在整个江左地区的前列位置,但身处台阁既久,桐城宰相张氏宗族在文学史上并未留下多少痕迹,在桐城派中,也稀见此支张氏后人身影。故而《讲筵四世诗钞》就是张曾虔以昭扬家声为目的而编纂的宗族类诗歌总集,诗作在集中的存在意义并不在于文学层面,而是超越了文学作品的通常意概,与御敕诏令一起,传达出彰显人臣宠渥与宗族声望的心态。其实,其他宗族辑纂本族诗歌总集也或多或少含有这样的意旨,只不过宦绩不及宰相张氏,这种跨文学的意义在张氏《讲筵四世诗钞》中尤为凸显,虽然鸿篇巨制,但是向外传递的信息已与诗作本身关系不大了。
四、结 语
是故,方东树在《桐城马氏诗钞序》云:
明初姚氏、方氏始大,中叶以后,乃遂有吴氏、张氏、马氏、左氏数十族同盛递兴,勃焉濬发,而且先后克以忠节、名臣、孝子、儒林、循吏,光史传者不可胜述。又若祖宗以文学起家,妙能为辞章,而子孙世宿其业,至今五百年,继继绳绳,渊源家法,而益大其绪,于是吾邑人文遂为江北之冠,而他名都望县,恒莫能并。(59)(清)马树华:《桐城马氏诗钞》,《清代家集丛刊》,第5页。
这段话阐明了文学世家对于地域文学乃至文学史发展的重要意义。桐城世家之昌盛,在明清两代,特别在清代令人瞩目,对创立桐城诗派、桐城文派、桐城学派意义非凡。然而,清代安徽以文学闻名,并影响文学演进的名宗望族数见不鲜,桐城文学世家只是各地诸多宗族的一个代表,大量皖人文学世家不应被忽视。
与其他地域家族相较,清代皖人文学世家在具备重视血缘伦理、培育家风、树立声望等共性之外,通过探讨其宗族诗歌总集又得以觇视其特性。概而论之,一是家族世居地域集中,桐城、徽州、宣城等地聚居大量世家巨族;二是家族绵延时间久远,并以总集存留本族历史记忆;三是家族刻书风气繁盛,以刻书优势带动刊印总集;四是家族诗学脉络清晰,通过家族诗学促进地域文脉生发。
研究宗族诗歌总集,既要从文学角度入手,又要出乎文学,因为宗族诗歌总集并非简单的文人别集,也不是完全从审美角度辑纂的文学总集,在宗族诗歌总集中,具有复合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宗族文学总集(家集)将一般文学总集与宗谱、族规、家训的特质糅合为一,宗族文学总集与宗谱相类似的意义在于厘清世系,确立稳定秩序,保证宗族长期繁衍。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宗族诗歌总集记录一氏累代诗作,也有以诗存家史的意概。但宗族诗歌总集与宗谱、族规、家训等宗族轨范文本相比又具有特殊的价值向度:一方面,宗族诗歌总集以诗教传达家族风范,以诗化人,意在从宗族内部构建文脉传承秩序;另一方面,又不限于文学意义,世家硕族通过刊辑宗族诗歌总集向外部彰显宗族的文学声望,以建立本族在地区中的文化与社会地位。当然,这两种含义常互相交织,不存在绝对的内外区别。所以就此来说,清代皖人宗族正是依靠刊刻诗歌总集在内的文学总集,将家风、家礼、家学、家脉代代赓续传衍,一个个文学世家才得以构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