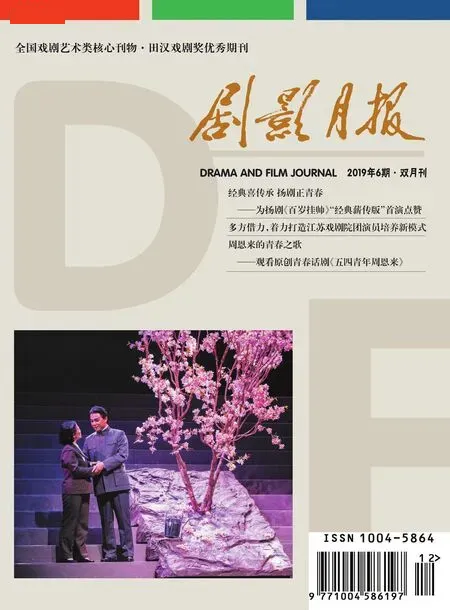清末民初扬州地区电影放映研究
2019-11-15樊昊
■樊昊
中国电影史学界的“重写电影史”的工程一直不断推进,其中电影方志研究作为中国电影史的新视点,被尝试运用在电影史学的研究当中。“电影的方志研究就是将电影进行区域性的研究。”[1]上海作为中国早期电影的重要产业基地,上海电影无论在影片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堪称集大成者,电影史学家毫无例外地将中国电影史的重点聚焦在上海。但是中国电影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局限于上海一地,其格局是以上海为中心呈现散点分布。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中明确写到“电影放映在我国,就逐渐遍于南北,深入内地了。”[2]郦苏元、胡菊彬编著的《中国无声电影史》中记载,除了在上海放映以外,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台湾也是较早的放映地点。同时,“1904年为庆贺慈禧太后生日,电影在宫廷放映。甚至是远在西北的宁夏地区,也因为清王朝笼络皇亲国戚,赠送了世居定远营的塔王布希格。”[3]
一、清末民初扬州概况
(一)经济概况:
晚清至民国初年,扬州虽失去全国性商业都会的地位,却仍不失为地区性的商贸中心。盐业市场虽然衰败,但随着大众化日用消费品的增加,市场商品结构发生变化,许多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仍较兴旺。
据民国十四年撰修的《江都县续志》记载:清末民初,扬州商业除盐业为根源,钱业为首要者外,其次为米业,城内米店专售食户,城外米行为代客交易,两者合计年销银币200 多万元。除此而外,还有绸缎业、布业、衣业、洗染业、帽业、金银首饰业、铜锡器业、烛炭业、烟茶业、药业、酒业、南北杂货业、糟酱业、茶食业、渔业、油业、香粉业、嫁妆皮箱业、工艺品业。还有漆器业,始创芦葵生,继者梁福盛,岁销三万元,梁号居其半。香粉业初以戴春林为最,继起者薛天福,后起者谢馥春。以上各业,年销售量额逾千万元。
作为地区性商贸中心的扬州,因为仍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所以不管是外商还是上海地区的商人都看中了其潜在的商业优势,也因为交通(火车兴起取代运河航运)、政变(1930年,国民党镇压苏北地区的共产党活动)、战争(军阀混战及日本侵华战争)以及自然灾害(1931年里下河地区水灾),使得扬州经济不断下滑,跌至谷底。扬州城内稍有地位的商家,在抗日战争前后纷纷迁往上海、江南和内陆地区,扬州最终失去了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地位。
(二)文化概况:
清末民初时期,扬州虽然已凄凉冷落,但老百姓还是遵循原先的消闲习惯:书照听、戏照看、牌照打、照样“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扬州曲艺中的‘扬州评话’在这一时期,凭借着乡音的优势,凭借着拥有一个优秀的艺术家群体,凭借着拥有一批优秀的传统数目,凭借着几代人在三百多年的艺术竞争中创立起来的表演提携,仍能站稳脚,在民国时间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4]这一时期,出现的艺术家有王少堂、康又华、戴善章、朱德春……就《扬州曲艺志》所记载的扬州书场数量及营业情况来看,扬州地方曲艺“扬州评话”在清末民初时期,听众数量较多,在大众文化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新兴文化产品——电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扬州曲艺在扬州的根基之深,演员不断创新,演出作品优秀,书场数量众多,观众对听说书的生活方式的喜欢,导致电影在扬州的放映传播效果甚微。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也未形成大规模的放映活动。
二、《警钟日报》中扬州电影的放映:
据《警钟日报》记载,1904年即电影传入中国上海约10年后,电影在扬州开始正式放映。
《警钟日报》于1904年在上海创刊,1905年3月被清政府查封。该报由于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登载地方新闻时,以揭露和抨击国内外反动势力为主。在一年多的办报时间里,“据初步统计,《警钟日报》在‘地方新闻’、‘学界纪闻’等栏目内刊载扬州时事达一百二十多条,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5]包括州县吏治、军队与警察、盐枭问题、纺织业、水运。而关于扬州时事多达一百多条,其中既有主观性的原因:当时的报刊主笔是扬州籍学者刘师培[6],对于家乡具有“革命性”或者“落后性”的事件加以报道,为政治主张作舆论宣传;而客观性的原因是,扬州作为上海周边城市,交通较为便捷,且在清末仍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地方新闻可以迅速向上海传播。
《警钟日报》(上海)甲辰7月22日(1904年9月1日)交涉纪闻:署理甘泉县白令承颐,贪渎素著。前月底,有美国商人偕翻译、细崽四五来扬,在新胜街设立电光影戏公司,生涯颇盛。事为白令所知,疑系粤人冒充,遂托洋务局委员厉某,说项。欲将该公司每日所卖之款,提三成归白,该公司不允,白令立饬差役,欲将所贷之屋发封,并欲拏人惩办。美商闻之大怒,随即电致上海美领事,领事即派二人携照会至扬。过镇时,并谒见常镇道。至扬后,立往白令处诘责,必欲与白令为难,闻领事已有电致常镇道云。
《警钟日报》甲辰7月25日(1904年9月4日)扬州,不谙条约之笑柄。英、美、日三国洋人,由本地无业游民之勾,人扬城赁屋新胜街,私开影戏馆,兼售地球牌香烟。夙知两县不知条约为何物,直赴甘泉而见白令,大言挟制,竟为所欺,于六月二十日开演,江(江都)甘(甘泉)两县均不素看洋人护照,又未奉到上司扎准领事照会,反派差勇日逐保护。旋有洋务经承,串通洋务董事,及内地教友,每日看戏,既不付钱,复纠“青皮”行凶闹场。运司忧之,饬县详报常镇道,并函询来历。本月十七日常镇道批云:查无领事照会,玄即驱逐出境。甘泉奉批,犹不敢问罪外人,乃向租房之业主追查,饬即辞租,违于治究。此房系官宦何子韬执业,现有管租之黄少秋收回房屋,辞却洋人。直至十八日既偃旗息鼓,其不至酿成大祸也。畿希。
《警钟日报》甲辰7月29日(1904年9月8日)扬州,县令受洋人贿赂。昨记:两县不谙条约。新胜街影戏,经关到批伤斥逐,已为洋人所知,乃以洋元为甘泉县寿,竟将道批虚应公事,旋即吊回。并允洋人包办滋事棍徒,不恤人言,不遵条约,县令安得辞其咎乎。
不难发现,三则新闻其实是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第一则属于“交涉纪闻”,后面两则主要针对这件交涉纪闻当中的细节进行描述“扬州,不谙条约之笑柄”。两种表述在某些方面有诸多矛盾之处,比如“交涉纪闻”中说“美国商人偕翻译、细崽四五来扬”,而“扬州,不谙条约之笑柄”中却表述成“英、美、日三国洋人,由本地无业游民之勾”。
“交涉纪闻”中发生外交事故的原因是县令白承颐获利而不得,遂要关停电影院。美国商人不愿意并且上报了美国领事馆,美国领事馆派人到扬州来处理事情,事先去了镇江,找了甘泉县的上级常镇道。
在后面的两则新闻中则表述为,外国商人知道中国官员不了解涉外条例,私自开设电影院。后甘泉县令接到上司命令,要驱逐其出境。县令不敢得罪外商,便向租房者追究责任,让出租房者不得再续租给外商。外国商人以为甘泉县令祝寿的名义行贿,县令白承颐每日派师爷向外商取银十元,星期日不取,阴雨减半,如有人滋事扰乱演出,听凭洋人处理。
(一)放映时间:
三则新闻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放映时间上基本一致。“交涉纪闻”中是甲辰7月22日的新闻,“前月底,有美国商人偕翻译、细崽四五来扬,在新胜街设立电光影戏公司,生涯颇盛。”根据时间推算应该是在六月底设立了电光影戏公司,但是从这句话,仅是知道了设立了电光影戏公司,但不确定是否开展了放映业务。因为影戏公司的业务范围不仅仅是放映,或许还有生产和制作。在下面的新闻中则有明确的时间及放映信息,“于六月二十日开演,”与上面的六月底相差无几,“每日看戏”则说明电光影戏公司是一家放映电影的公司。对于“影戏”名词的理解,出现了不同的表述,“用‘电光影戏’、‘机器电光影戏’、‘行动影戏’、‘灵动影戏’等来指电影,以区别自己的前身——幻灯。”[7]故在这里结合三则新闻则可以判定光绪三十年(1904年)约六月二十日,扬州地区第一次放映了电影。
(二)经营情况:
就经营情况来看,“每日由沈师爷手取洋十元,礼拜不取,阴雨减半”则是从电影产业经营的角度来描述,每日“由沈师爷手取洋十元”,结合“交涉纪闻”里面的表述“提三成归白”,估计“洋十元”约为影戏馆收入的三成,而影戏馆的日收入大概30洋元,因为没有票价的统计,故无法得知观影人数有多少。而“礼拜不取”也可理解成两种意思,并不清楚到底是和外商约定周日的营业额归外商独有,还是周日不放映电影。“阴雨减半”则是从市场受众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气候变化,观影人数可能会有下降,故减半。
“在新胜街设立电光影戏公司”。扬州的新胜街也叫新盛街,原称翠花街,是一条与多子街平行的街。《扬州画舫录》的作者李斗就住在这条街上的伫秋阁,他在《扬州画舫录》中说:“翠花街,一名新盛街,在南柳巷口大儒坊东巷内,肆市韶秀,货分隧别,皆珠翠首饰铺也。”[8]从清末一直到民国年间,这条街上的商家经营珠宝古玩、金银首饰、皮货衣帽、胭脂花粉,还有著名的旅社、饭店和澡堂,被称为“不夜街”。可见所处地段极为繁华,而影戏馆设立在此,“生涯颇盛”就不足为奇。
(三)舆论报道:
《警钟日报》除了介绍有关电影放映的消息以外,还有舆论导向层面的内容,比如“不谙条约”中就透露了中国官员贪污渎职的行为,而对外国商人的描述则是他们利用了中国官员的无知,很快熟悉了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并且“见缝插针”行为不端。不难发现《警钟日报》在选择新闻报道时,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与国内外反动势力有关的事件加以报道,以达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信息传递功能,大力鼓吹“抵御外侮,恢复国权”,鼓吹“革命排满”的政治倾向。而当时有关政治性的新闻报道,却成为目前现存的电影史史料。
《警钟时报》是现存报刊中,尚能发现扬州地区电影放映的报纸,至于具体的放映时间,尚无法精确考证。从仅存的三则新闻材料中,大致可以了解扬州地区电影初次放映的时间、地点和营业概况。
三、《申报》中的扬州电影放映
关于扬州最早的电影放映,《申报》中也有相应的记载。晚清《申报》在扬州派驻了记者(访事人),《申报》所载扬州消息都是由申报馆在扬州当地招聘的记者采访而来,其从外埠招聘的记者都是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本地文人,所以报道消息可靠性较高。
1904年10月6日[9](甲辰年八月二十七日清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禁演影戏
扬州访事人云:扬城新胜街有空屋一所,日前忽有甲乙等人开演外洋影戏,门外高悬某国旗帜。中有一二云情雨意,殊于风化。有关地方官因禀请大宪团,商某国领事出示严禁,甲乙等人闻之旋卽他去。不意近日又有接踵而至者,在埂子街南河下等处赁屋开演江甘两县宰遂会衔示禁,云:照得外洋影戏最易导人淫荒,前有外人来演,禀奉撤调离扬;近有游孚之辈,复购机器开场;但知藉以图利,不顾功令煌煌,本应立饬提究以为风俗之防;姑先出示诰诫另图他业。如敢再蹈覆辙,房屋发封公堂;地保徇情,扶隠其罪,亦复昭彰。本县出言不反,切勿以身试尝。
“扬城新胜街有空屋一所,日前忽有甲乙等人开演外洋影戏,门外高悬某国旗帜。”这句话与《警钟日报》中的表述基本一致。而后文所述是什么原因使外国领事出动,《警钟日报》和《申报》中的表述则明显不同。《警钟日报》明确表达对当地官员贪污渎职行为的不满,在《申报》中却呈现为地方官员遵守职责向上级汇报。
《警钟日报》在三则材料后就没有扬州电影放映记录的其他记载,此处的《申报》消息在一定程度是继《警钟日报》电影放映报道的后续补充。
《申报》在1906年、1909年年,又陆续地记载了两则有关扬州电影放映的情况,于其报道的内容均是地方官员禁演影戏。
1906年7月3日[10](丙午年五月十二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禀禁洋人开演影戏扬州
上月下旬,江甘两县宰查有高栋臣者,勾引洋人来扬开演影戏,两县宰以本郡非通商口岸,前有洋商欲演均未果行,因特据情禀请常镇道陶观察援案。
1909年10月26日[11](乙酉年九月十三日清宣统元年九月十三日)
禁止洋商内地演戏之交涉扬州
镇埠法商文明影戏公司,前次移往扬州埂子街开演,经江甘两县,禀明关道,勒令闭歇等情。早志本报,兹,该商谓公司既经封闭则所有损失,须令华官赔偿,业(已)经禀请该管领事与华官交涉。
根据上面的新闻报道记录,扬州早期的电影放映均是由外国商人来扬州放映,且放映的目的都是以营利为目的。且在有清一代,电影放映是被禁止的,从官方的口径来看,是说扬州地区“非通商口岸”,在清政府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除“通商口岸”外,“非通商口岸”依旧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而“通商口岸”则因为签订条约后,外国商人可以到“通商口岸”经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通商口岸,“因此,外商可以在宁波从事电影放映业务,华人也顺势获准从事电影放映业务”[12];而另外的角度来看,扬州地区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作为位于长江北岸的河港城市,不管是中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都看中了其潜在的商业特质。就《申报》刊载的消息而言,其为早期的涉及外商电影放映场所的管理提供一些线索。就扬州地区电影放映场所,属于民政部和地方政府双重管辖之下,但因为涉外,扬州的地方官便无权干涉电影经营。故交由上级裁判,最终因为“非通商口岸”,并未给外商提供特权。
“中有一二云情雨意,殊于风化”“照得外洋影戏最易导人淫荒”这是从影片内容和影片的功效角度来说明禁演影戏的原因,并且对“后来清政府制定取缔电影章程有一定影响,1911年制定的《取缔章程》和《取缔影戏场条例》中都有关于影片内容的规定”[13]。“中有一二云情雨意,殊于风化”可能当时放映的是外国的爱情电影,所谓“云情雨意”可能是指镜头中出现了男女亲密接触的场景;“外洋影戏最易导人淫荒”这样的论断或许是从其他地区放映后产生的效果而得出的结论,这是从电影功能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在清末,电影放映产生“风化”问题的原因,第一是指男女不分座,第二是指影片内容存在当时观众不能接受的男女亲密接触的场景。清末扬州的地方戏曲也被禁止演出,在《申报》中,也记载了许多有关扬州地区禁止演出地方戏曲的报道,很重要的原因亦是“其有坏风化”。[14]因为电影进入中国伊始,就被当成戏剧的一种,在初期被称为“影戏”。正是因为和戏剧的亲缘性,主要原因是放映电影有害社会和有伤风化,但从深层上看,则是传统戏曲禁毁观念和举措的扩展和延续。[15]
从1904年,扬州的确首次出现电影的放映开始,一直到清末,都没有形成相对固定的放映场所,一直到1917年11月29日,《申报》中记载了扬州地区定期放映的消息。
定期开演影戏,扬州大舞台[16]经理杨某[17],现在申租借大宗影戏片来扬逐日开演,已禀准江都县署给示保护,择于二十九日开始营业。[18](丁巳年十月十五日中华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仅从《申报》中,只能理解到扬州大舞台即将定期开演影戏,并不能确定是否已经营业。根据《扬州电影志》记载“从二十年代起,每年夏秋两季都放映无声电影,用烧木炭的发电机发电,手摇的放映机放映,放映人员从上海雇佣,影片向上海发行商租。”[19]《扬州文史资料》中也有相应的记载“1934-1935年,大舞台曾自办发电设备,放过无声电影,片名为《偷烧鸭》、《早生贵子》、《孤儿救祖记》、《啼笑因缘》和卓别林主演的《城市风光》等,放映员王炳南、石香宝。”[20]《申报》和《扬州文史资料》的消息则明确了,在清代的扬州地区的电影放映途径是由外商将电影引入中国,而民国时期的电影放映则是中国人自己放映,其所受到的是上海地区的辐射影响。除基本的放映的消息外,从材料中还可以得知中国早期电影放映场所及电影放映内容的管理情况。
四、其他报刊中扬州电影放映
(一)露天放映:
根据《扬州电影志》的记载,关于扬州地区最早的露天放映场所,并没有完全确定的表述。在此书中的大事记中记载:民国23年(1934年)扬州办报人在参府街“参府大院”开设影戏馆放映露天电影。但是在后面的电影放映章节则另述:扬州中学树人堂电影放映场,从30年代起不定期放映电影。
根据现有《扬州中学校刊》1931年记载,题目为:《校闻:童子军团部开映露营电影》。[21]从现存资料来看,扬州地区的露天放映时间不晚于1931年。
而上述的参府大院的露天放映情况,也有资料记载,“1934年由扬州报人姚雨主办。原为露天剧场,后改为露天放映无声电影,片名有《水火鸳鸯》《故都春梦》《木兰从军》《一剪梅》等,至1945年闭歇。”[22]
(二)影院放映:
根据《申报》和《扬州电影志》的零星记载,对于电影的放映,还只是放映时间的记载,并无其他具体的放映信息。《影与戏》杂志[23]1937年记载了一则有关扬州电影放映的消息,“扬州的电影院有一家日间停映”。从这则消息中,可以了解到电影放映的场次与时间、电影院的空间布局、片前放映情况、票价及具体影片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南京大戏院是扬州的小东门城堤街,他是直辖于上海大陆影戏公司”交代和说明了南京大戏院的地理位置和影院性质。【笔者注:南京大戏院系由公园戏院(原为传统戏曲剧院)改建而成,实为直辖于上海大中华影业公司。上海大中华影业公司老板蒋伯英通过地方名流阮慕白和戴天球的关系买下戏院,委派罗文轩担任经理,聘请代替求为法律顾问,戏院门口悬挂上海青红帮头领黄金荣赠送的玻璃匾额,一时威震扬州】[24]。
“每日只开两场,五点半与八点钟”介绍了放映的时间,“票价是二角和三角,客茶每杯是一角”“或者便利小贩卖东西”点明了票价,介绍了除影片放映以外的营业内容。在电影院里面仍有小贩售卖东西,此时扬州地区的电影观看或许还和戏院观看方式相似。“未开映电影前,先开唱片,这是电影院的老例”具体说明了电影放映前的情况,与今类似。
“一人一张凳,不坐上去便直立地挂着,坐下去时把他反过来很便利的,在隔三排位置下,便有一盏电影在开映时方开的小灯,光线从底下一条小缝儿照在地上”“场里的灯光相当美观,光线纯由雕空的桂(柜)子中射出来,桂(柜)子上雕的是古老的图案花纹,但多少有些好感,两边则是各色年红灯”大致描述了电影院的空间格局。“这影院选片方面常是映两张不十分好的片子夹一张好一些的片子,以前是狼山喋血记、化身姑娘,已相继开过,昨天开的是壮志凌云”交代了具体的影片放映。
上述的材料记载,更多意义是一则新闻消息的记录,但其史料价值对于今天研究扬州地区民国时期的电影放映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五、结论
综上所述,扬州地区在1904年就已经出现了电影的放映,当中的原因和扬州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电影在扬州放映的时间,甚至早于苏州地区的放映时间。[25]而在有清一代,却因为诸多原因被禁止,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才形成固定的放映地点,而对于其中具体的放映情况,比如大舞台的票价,以及放映规模,都因为资料缺少,尚待新史料发掘后才能做进一步考证和研究。从时间段来看,清代扬州地区的放映主要还是通过外商,而民国时期的电影放映已由中国人自己实践操作。当然,之所以要去对最初扬州的电影放映情况进行考证,是为了获得更为清晰的扬州生活图景。对于中国电影史而言,相对边缘城市的放映情况,是对过去研究者较少关注的早期上海之外的地域的电影发展,进行新的史料挖掘和整理,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大中华电影史观”。[26]
注释:
[1][26]刘小磊:《中国电影方志研究—探寻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新视点》,《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
[2]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
[3]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
[4]李真、徐德明:《笑谈古今事—扬州评话艺术》,广陵书社2009年版。
[5]陈仁芳:《谈〈警钟日报〉中所载扬州新闻》,《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6]刘师培(1884—1919),江苏扬州人,培对经学、小学及汉魏诗文皆有精深研究,尤擅骈文。并受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影响,提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新观点。
[7]黄德泉:《电影初到上海考》,《电影艺术》2007年第3期。
[8]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 年4 月第1 版,第195页。
[9]《申报》1904 年10 月6 日,第11305 号第9 版(共12 版)(上海版)。
[10]《申报》1906 年7 月3 日,第11928 号第3 版(共20 版)(上海版)。
[11]《申报》1906年7月3日,第13193号第11版(共32版)(上海版)。
[12][13]王瑞光:《中国早期电影管理史(1896-1927)》,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
[14]张天星:《晚清〈申报〉所载扬州禁戏史料的文献价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5]张天星:《清末禁映电影的原因探析》,《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16]扬州大舞台原址在市内小秦淮河畔,太平码头西侧,南城根54号。
[17]杨子琢,扬州人,系扬州名儒陈重庆的门客,为大舞台股东与第二任老板。
[18]《申报》1917年11月29日,第16091号第7版(共16版)(上海版)。
[19]扬州电影志编纂组:《扬州电影志》1999年版。
[20][22][24]刘一飞口述、陆声洪整理《扬州的影剧院游乐场和书场》,《扬州文史资料第10辑》,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版。
[21]《扬州中学校刊》1931年57期。
[23]民国电影杂志,1936 年12 月创刊于上海,周刊,出至1937年7月第三十四期后停刊,共出34期。由朱善行等编辑,胡以康发行,影与戏周报社出版。属于电影与戏剧刊物。撰稿人有徐冠中、高寒梅、陈瑾之、席与群、李世芳、穆戈龙、周子畏、马永华等。栏目有剧讯、剧照、梨园掌故、每周短讯等。该刊“办刊是要大众化的,进一步讲,刊物的取材,亦应当大众化”,因此刊物以贴近大众为原则,并自称为“综合电影戏剧的百科全书”。
[25]据《苏州与中国电影》记载,电影传入苏州,大约在1910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