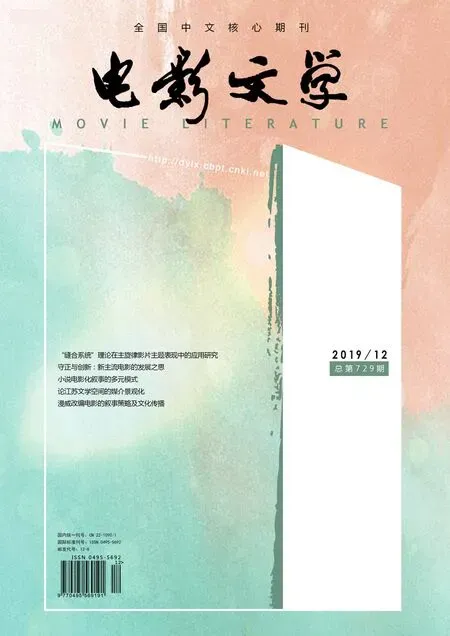《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爱情片的风格化
2019-11-14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重庆400052
刘 高(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重庆 400052)
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影,其创作往往必须在个性化(personalize)和风格化(stylize)之间取得平衡。所谓风格化,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为使之符合某种风格或模式,二为使之因袭。爱情电影在当代类型片中,一直具有较为强势的地位,这除了爱情电影有投资小、回报周期短以及包容力强等优势,也与电影人在创作时有意识地牺牲了个性化,走向风格化有关。电影人的这种创作倾向,保证了爱情电影能适应大多数观众的口味,在院线上能取得较好的成绩。近期上映的,由台湾导演林孝谦执导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2019),尽管翻拍自韩国同名电影,但在内地上映之后迅速引发观影热潮,可以说,影片正是这种爱情片风格化的典型范例。
一、对模式的必要重复
如前所述,风格化首先指的是在创作时,以普遍性的特征来呈现事物,而一旦这些特征被约定俗成地固定下来以后,它们就会为后继的创作者所重复、因袭。最直观的风格化莫过于美术设计,如被一圈发散的线围绕的圆,就是太阳的风格化图标。风格化使得艺术能够跨越文化与语言的障碍。“交流取决于双方是否存在共同点,比如都认可的象征符号、用法或定义,令人难以忘怀的交流必须是双方都愿意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的。”电影艺术亦是如此,为了实现更顺畅的与观众之间的交流,爱情电影往往也会对其他同类电影,甚至是更早的民间传说、文学作品等进行因袭。如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遭遇“第三者”,出现危机,但最终还是战胜危机,走向复合与团圆。这就是一种常见的叙事模式,如明代冯梦龙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讲述的便是这样的故事,妻子王三巧儿与陈大郎偷欢,但最终还是得到了丈夫蒋兴哥的原谅。而在当代爱情电影中,如徐峥的《港囧》(2015)等,采用的也是这一叙事模式,有着“寻找初恋”这一精神出轨嫌疑的徐来最终也意识到了妻子蔡波和家庭的重要性,回归到了原本不满的婚姻中。无论读者抑或观众,始终都有着对出轨者在付出一定社会代价后回心转意,原有婚姻得到延续这一“破镜重圆”叙事风格的喜爱。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采用的并非这样的圆满型叙事模式,但是同样有着属于风格化的重复性。唱片制作人张哲凯的父亲在他幼年时就因患白血病离世,随即母亲也抛弃了他一去不复返。高中的时候,张哲凯认识了叛逆的女生宋媛媛,而宋媛媛同样是一个孤儿,家人在一次车祸中去世,宋媛媛便住在张哲凯的家中,度过了多年温馨快乐的时光。长大后两人又一起进入唱片公司工作,不料就在两人即将对对方剖白情感时,张哲凯发现自己也患上了家族遗传的白血病并已时日无多,他便决定在自己还活着时为宋媛媛找到归宿,而宋媛媛则在张哲凯的刺激下相中了事业有成英俊潇洒的牙医杨佑贤。张哲凯在调查了杨佑贤后,暗中帮助成就了这段姻缘,亲手将穿着婚纱的宋媛媛交到杨佑贤的手中,自己则病发而死,不久知道真相的宋媛媛留下遗书殉情而死。男女主人公情投意合,却遭遇意外打击(如车祸、癌症等),最终被迫忍痛分离这样的叙事套路,在爱情电影中屡见不鲜。观众与电影的创作者之间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经得起意外考验的爱情,才是伟大的爱情,愿意舍己从人的爱人,才是理想的爱人。于是,张哲凯舍弃了自己成婚和病重时被照顾的机会,宋媛媛舍弃了生命,共同谱写了这段“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电影人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得以完成。
又如在人物的符号化设计上,电影也是模式化的。爱情电影常常塑造出颇为完美的、情圣式的男性形象,他们对女性往往有着引导者、保护者的意义,这样便能唤起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向往。例如在薛晓璐的《北京遇上西雅图》(2013)中,来自北京的司机郝志便是这样几乎没有道德缺憾的符号化人物,他对女儿有着无微不至的疼爱,对已离婚的前妻则百般迁就,对文佳佳也给予着温暖关怀。《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中的张哲凯也是这样的“暖男”形象。在事业上,他支持着宋媛媛;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他包容着宋媛媛。如宋媛媛说他名字难听,提出以后就叫他“K”,他全盘接受。在人生大事上,他则力图为宋媛媛安排好一切,不仅暗地里调查了杨佑贤,还亲自出面,恳请已经出轨了的杨佑贤未婚妻辛迪主动退出等。张哲凯、郝志等男性形象,是一种社会期望渐渐沉淀下来的产物,是女性对于某种安全、温暖情感栖息地的需求的代偿者。
二、与现实的微妙距离
除了被重复的具有普遍性的特征,风格化还包含了有意的“失真”的含义,因为创作者往往会使用夸张或简化的方式来实现对风格的靠拢,来实现和艺术理念或习俗的一致,如古埃及的被拉长了的猫的雕塑,理想而完美的人体塑像等,戏剧和电影的创作亦然。有学者指出,所谓风格化,即“以一种简化的形式再现现实的手法。……戏剧文学和舞台写作一旦放弃模仿地再现某个整体或某个复杂的现实时就会求助于风格化”。电影人所要刻画的,并非复杂、千人千面的现实生活中两性爱情关系的样貌,而是一种偏向于理想、完美的爱情关系,为了保证这种理想和完美,爱情故事中的部分元素就要被夸张(如人性的真善美部分)或简化(如现实的困厄残酷等),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往往难以拥有电影中人的情感经历。
在《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中,张哲凯和宋媛媛对于情感的执着,以及他们的际遇,就略显“超现实”,却保证了电影符合浪漫、深情艺术理念的一面。张哲凯和宋媛媛自幼失怙,但两个人都保持了阳光、乐观的心态,缺乏家庭支援虽然使宋媛媛养成了吸烟等恶习,但是没有影响两人的学习成绩。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情投意合,生活上充满了种种情趣,如一起吃冰激凌等,同居期间从未争吵决裂。主人公的生活状况无疑是令观众向往的。而在病魔来临后,由于张哲凯表示希望宋媛媛去找一个能给她带来幸福的人度过余生,不明真相的宋媛媛赌气撩拨了牙医杨佑贤,用送饭等方式让杨佑贤感受自己的温情,而人品稳重的杨佑贤则表示自己已经订婚,但在张哲凯的调查中,杨佑贤未婚妻、摄影师辛迪早已投入他人的怀抱,在张哲凯说出自己的托付意愿后,辛迪竟宽宏大量地表示愿意退出,条件是需要张哲凯配合她拍一组关于死亡的照片。随后辛迪在和杨佑贤摊牌时也极为坚决果断,令杨佑贤备感受伤。辛迪的态度令张哲凯的“成全”成为可能,然而这却是现实生活中极为少见的。更与常人的婚姻观有距离的是,在宋媛媛知道张哲凯的一片苦心之后,竟然撇下自始至终并无过错的杨佑贤自杀殉情,显然,宋媛媛的最终决定,是电影继承了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爱情故事后,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理念设计的一个流行文本。宋媛媛和张哲凯“真爱至上”,不顾一切的行为固然令人感动,但是也有着缺乏思考,道德立足点不稳的一面,对于绝大多数重视婚姻稳定性,认可婚姻责任感、珍视生命的观众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自己绝不会选择的。
必须承认的是,绝大多数的爱情电影并非现实的一面镜子。对于爱情电影来说,它既不能过于脱离现实,违背时代的价值观念,从而让观众对主人公的情感体验缺乏代入感,在心理上缺乏能说服自己的理由;同时又必须抑制个体差异,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给观众一定的梦幻感,满足观众的猎奇心,而这种距离是十分微妙的,它需要电影人妥善处理。
三、爱情片风格化的文化成因
首先,爱情片的风格化来源于人类对幸福生活,浪漫爱情的永恒的、普适性的向往。爱情电影通过男女主人公或是坎坷不顺,或是甜蜜美满,或是团圆厮守,或是阴阳分离、人鬼殊途等经历,来填补观众在情感体验上的不足或唤起其情感焦虑的共鸣,电影中角色必然要陷入戏剧性的事件,如误会、争吵等,观众的诸般情绪才能得到宣泄,如《同桌的你》(2014)中人物的出国导致关系无疾而终,《何以笙箫默》(2015)中的父辈恩怨等。这种心理决定了爱情片的重复、巧合等特点,以及最终的同质化和风格化。《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也是这样,张哲凯和宋媛媛因为各自家庭的破裂而相依为命,在长达十年的同居生活中只发生了“零点五”次性关系,感情浪漫而纯洁,两人都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成全对方,最终虽然没能结为夫妇,却相随于地下。而他们身边的杨佑贤、辛迪和伯妮等人无不都是善良的,乐于助人的人,骄纵任性的伯妮尽管一开始难为过宋媛媛,但在与宋媛媛结为朋友后便全心全意地关怀她和张哲凯之间的感情。一言以蔽之,电影虽然是一出悲剧,但是其情感氛围是极为和谐的,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是极为唯美的,也是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反差的,这正好为观众构筑了一个关于现代都市下“纯爱”的想象空间。
其次,当代国产爱情片的风格化,还与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实现高速发展,人们进入消费社会,逐渐习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有关。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人们消费的目的相对于实际需求而言,更是一种被制造和刺激出来的欲望,人们消费的对象相对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言,更是其符号象征意义。爱情电影就是人们消费的商品之一,观众之所以愿意走进电影院,主要是为了其背后的各种象征意义,例如充满自嘲意味,有着诙谐幽默情节的《失恋三十三天》(2011),就是有着治愈失恋情伤意义的商品,在此之后,类似的治愈系失恋题材的爱情电影便大行其道;又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等,则是以青春岁月为卖点,满足观众回顾纯情学生时代经历的商品,电影人的创作显然需要考虑观众的消费心理,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批量生产。以“唯一观影提示:请带足纸巾”为宣传点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依靠的则是观众对“生死相随”“至死不渝”感情的需求,电影要唤起的是已经走上社会,出入职场的观众的认同,已经拥有社会经验,各自的婚恋观多少被功利目的所影响了的观众需要以虚构的电影,考问各自的内心状况,因此电影中人物的自我牺牲,殉情等故事尽管夸张,激进且套路化,但是能引发观众的震撼,反思与感怀,电影由此彻底成为合格的消费商品。
当我们剖开当代国产爱情电影的发展横断面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显而易见的风格化。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们千姿百态的情感关系被提纯出来,经过具有重复性、失真性的处理后形成了银幕上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影像,而这种重复性与失真性并非爱情电影的缺陷,其背后有着深厚,不可忽略的文化成因。人们对于真挚的爱情有着强烈、持久的憧憬和期待,爱情电影在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正面引导社会价值观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就代表了爱情电影在风格化方向上的创作规律,尽管其依然有不足之处,但在国产电影踏上产业化道路,爱情电影迎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的今天,它的借鉴意义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