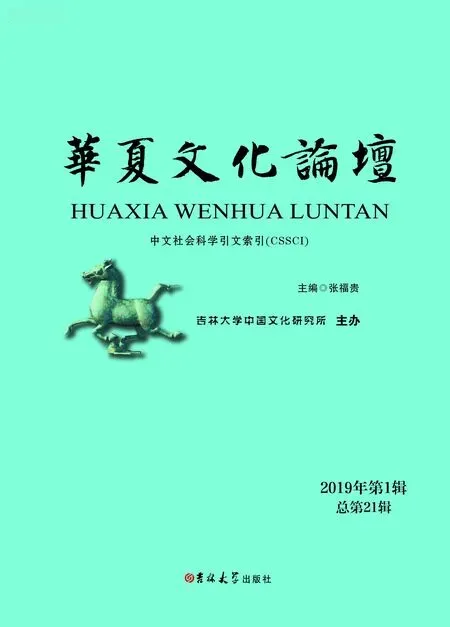从边缘到中心
——论沈从文与穆时英的文学之“器”
2019-11-13陈广通
陈广通
【内容提要】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文学与政治和社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于此出发,沈从文与穆时英以及与之同时代的革命作家有着巨大趋同性,在“感时忧国”的大框架下他们不是现代中国文学的边缘性存在。他们同样践行着现代中国文学的一贯性——功利追求,从这个角度看,京、海与革命文学不是“三足鼎立”而是一脉相承。沈、穆二人都从传统文化精神出发思考民族发展大计,前者偏于保守,后者偏于激进,穆比沈多了一份阶级意识。身处中国20世纪前半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与革命作家一起思考着民族前途,各自以文学为“器”参与进家国重建运动中。
在20世纪的中国,完全割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不大可能的,“远离政治”只能被看成是一种主观姿态。沈从文和穆时英在幻想中的“自由”立场上与革命作家一样表达着关于家国、社会等问题的思考。以沈从文领衔的京派和以穆时英领衔的海派与革命文学阵营的三足鼎立已经成为学界的定论,他们之间似乎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沈、穆“远离社会政治”,一个苦心孤诣守卫着静穆淡泊的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一个张扬着轻浮颓放的现代都市风华,革命作家则在颠覆精神的感召下扎根于乡村,勠力挖掘其中的隐忍和反抗。到了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对希腊“小庙”钟情无减,穆时英坚持复活“小道”文章的媚俗传统,左翼代表作家大多倾向解放区,将农村革命的叙事推向高潮。三者在表面上好像水火不容,但如果从中国现代性的祈望来看,他们则一脉相承——古代中国士大夫之家国情怀,革命文学作家将农村当作夺取政权、再造国家的根据地,沈、穆的现代国家、民族想象也从乡土开始。就“想象”出的方案来看,沈从文是保守的,穆时英是激进的,他比沈从文多了一份阶级意识。身处中国20世纪前半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作为京派和海派代表作家的沈从文和穆时英并没有置身于国家重建的历史潮流外,而是与革命作家们一起再现、思考、批判着现实,各自以作品发挥着文学的功利作用,“器”的追求由此显现。
一
沈从文的拿手好戏是田园浪漫风,但也不乏对社会现实的忧心忡忡。他只不过在自我文艺观念下把现实重大主题做了抒情化处理,所以人们从“审美经验流露”的文艺观出发,认定沈从文一直以来就是一位“敬谨的和平主义者”。他固然是政治的保守派,但左翼作家又何尝不是激进派?二者同处于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阴霾,只不过各自占据着博弈进程的两翼。沈从文“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热情”极力倡导“重造民族品德”,以解民族发展之忧。他对单纯的“同情”无法忍受,要的是“行动”。湘西辰溪物资富足,人却穷相,这一问题如何解决?他的“办法”是与鲁迅相类的改造国民性,所以有了翠翠、夭夭、老水手、满满、龙朱、虎雏等形象。
沈从文并不是存心与革命势力作对,他只是代表着另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的不同观点。他只是想在旧的吟唱里完成对于新的创造,《边城》《长河》《我的小学教育》《猎野猪的故事》等是他对童年乡土的怀念,其中包含的国家重建动力的思考和主流革命作家同样突出。苏雪林早已指出:沈从文“不是毫无理想的”,他“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在沈从文看来,“野蛮人的血液”要从乡村里寻找,乡村的勇武健全人性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源泉。《我的小学教育》里那些故乡的孩子在小小年纪就为械斗游戏着迷,在他们天真灵魂里流淌着作者崇拜的原始野性,他希望这股力量能成为中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的资本。沈从文呼唤的强悍精神也表现在女子身上,《猎野猪的故事》里的宋妈在小时候就徒手捉过野猪。勇武品质是湘西民族精神的代表,它有着“根”的性质,很难消泯,《虎雏》里小主人公的蛮野终是没有被文明人所改造。沈从文珍视着农村人雄强健康的本性,到后来发展成了“城乡对照”的文化世界,《边城》《萧萧》《长河》《柏子》《三三》与《八骏图》《某夫妇》《或人的太太》《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让我们理解了在殊异文明下人性的健全与颓残,这一主题已经被众多学者阐释,此不赘述。乡土浪漫抒情代表者沈从文并不是在理性的高度上考量民族重建的方案,只是基于自我情感经验展开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二元比较,结果是他自小耳濡目染的古老乡村道德占尽上风。然而现代性是普遍的,“各个民族共同体特定的文化性”只有融入普遍性才有可能“合法”地被世界接纳,这一前提下的穆时英可能比沈从文走得远一些。
海派作家的本土性不如沈从文那样明显,需借助一些理论才能将其钩沉出来。学术界一直都将都市景观的再现视为海派作品的首要特色,诚然,如无都市则无海派。可是当我们用“地方色彩”为指标来审视“乡土”概念时,都市就会表现出故乡意义。“上海既有上海的地方特色”它也就“自然有它的‘乡土性'”,中国传统的吴越文化是上海之“地方色彩”之一,它是这个国际都市“洋泾浜文化里面的‘中方'”。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中国经济中心,并由此培养成它对浮靡生活方式的追求。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对生活的“讲究”,吴越文化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淫逸奢靡与精致绵软。“软”首先表现于作品的情感格调上,从张资平、叶灵凤到穆时英、施蜇存直至张爱玲,繁华都市里的小资产阶级精致感伤情调贯串始终。“软”也表现于作品的语言,吴侬软语同时是形式和“意味”,它透露着操持者的文化心态。奢靡的生活和温热的气候养成了吴越人绵软的性格,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们的普遍心性。海派的“软”文化似乎并不适用于国家再造,它与沈从文对于强悍生命力的呼唤背道而驰。但是海派绵软文化的基础在于经济腾飞,淫逸奢靡之前提是物质的丰厚。而物质的富足是文化现代性的础石,所以海派的“软”或许可以被看作知识分子们想象现代国家前途的标尺。
以淫靡的生活理想为由指责海派作家陶醉于颓废的生活状态显然不公平。吴越文化传统在精致绵软外也有尚武的一面,正是在这点上穆时英与沈从文走到了一起。《南北极》的背景依然是上海,但其中充满了底层人民的愤激,在发表的当时就受到左翼作家的重视。小狮子练过武艺,骨子里有着沈从文提倡的蛮性。当玉姐儿他嫁,他孤闯上海,后来的多次搏斗让他感到都市人简直不堪一击,徒手推汽车更见其健朗程度,这与沈从文的城乡对比立场是一致的。小狮子的好勇斗狠和沈从文反对的“凡事与人无争”之处世态度恰堪衬照,小狮子对不平等的世界愤慨入骨,对为富不仁者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这应了“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的俗语。故事结尾,小狮子扔了老爷、打了小姐,扬言“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谁是主子”,这是精神上的刚强不屈。如果沈从文看过《南北极》,小狮子身上的野蛮人血液将给他强力安慰。与沈从文蛰居乡下的“野蛮人”不同,穆时英的“野蛮人”已来到都市,并正面挑战现代文化的围困,他们所仰仗的是吴越文化之雄健遗产。穆时英召唤传统雄强文化的作品并不只有《南北极》,《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里负重的骆驼和《黑旋风》中自比梁山好汉的青年也同样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内心向往的满足。
沈从文与穆时英立足于本土传统文化的雄强,在“蛮”力下展开中国走向世界的图景,实现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中华民族雄起的一片痴心。二者不是逃脱社会的隐士,他们关于民族发展道路的想象在当今仍有意义。他们在自由的立场上实践着对家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对民族发展的现状做出了及时的反思。穆时英的都市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与“后现代”策略接近,沈从文将传统复制入现代,从民族发展前途着眼,二人的努力值得称道。
二
沈从文在《小说与社会》中肯定了《九尾龟》《官场现形记》《海上繁华梦》《孽海花》《留东外史》《玉梨魂》等“新章回小说”的价值,认为这些“作品既暴露了社会弱点,对革命进行自然即有大作用”。1931年,在现代中国文坛已经声名鹊起的沈从文在《甲辰闲话一》中为自己日后的创作列了一串题名,其中三个社会功利意义极为明显:“二、长江,写长江中部以及上下游的革命纠纷”;“四、上海,写工人与市侩的斗争生活”;“五、北京,以北京为背景的历史的社会的综集”。由此可见,沈从文对于文学的社会功利意义是大力推崇的,并始终坚持为家国前途找出路,希望手中的笔能对民族的雄起发挥“大作用”。沈用以“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的手段是传统文化道德与人的品性,并同时肯定了产生这种道德与品性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虽然出于个人“进城”后的亲身经历,有时他也会在作品中发出对于贫穷低下的底层生活的悲叹(如《一个晚会》《冬的空间》《生存》等),但这悲叹里并不包含革命向往。沈从文在“革”与不“革”之间徘徊着。他要以过往人类的美好品性革掉当下众生的不良道德,说到底这只是改良。但他对于“革命”并没抱有抵触情绪,而且在《小说与社会》中还赞许了暴露社会弱点对革命进行的大作用。
在《论穆时英》里,沈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文学观,他说:“一切作品皆因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从此一标准出发认为穆时英的“作品于人生隔一层”,并斥其为“假艺术”。在笔者看来,此一论断有失武断。沈的结论出自穆时英的作品取材,对于都市五光十色的及时描摹也确实是学界广泛认同的海派特色,但沈所谓的“‘都市'成就了作者,同时也就限制了作者”之语有失偏颇,甚至是偏见(其中蕴蓄着沈一贯的对于现代都市的敌对态度)。都市作为书写对象恰恰是穆时英提倡文学“德性”、关注现实人生的另一种表现,与沈从文的乡村题材作品殊途同归。况且,穆的侧重点在展现都市表层生活的作品只有《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少数几篇,在其全部创作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他描写更多的是都市表层繁华覆盖下的苦难大众,对于这些贫民大众的同情表现出了穆的阶级意识,甚而使他的思想有了“左”的倾向,“对革命进行”的作用比之沈从文激进千里。《南北极》集里八篇作品,每篇都是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悯与激励,并高度赞扬了主人公们的反抗精神,出版当时就受到很多左翼理论家的肯定。《公墓》集出来后,理论家们的腔调变了,认为“这里的几个短篇全是与生活,与活生生的社会隔绝的东西”,以此为据判定穆时英的风格变了。其实不然,他本人的回答很明白:“有人说《南北极》是我的初期作品,而这集子里的八个短篇是较后期的,……事实上,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却是同时写的”。对于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注同情、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激抗议其实是他性格中根深蒂固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在当时被“机械”批判的这本标志着海派创作风格的《公墓》集里也收录了《莲花落》《黑牡丹》这种对流浪者、小人物关之而切的作品。《莲花落》在诗意的笔触下、以区区几千字浓缩了患难于兵灾的一对夫妻的漂泊一生,《黑牡丹》祝福了一个风尘舞女的美好生活,他们与本集《夜总会里的五个人》《Craven“A”》《夜》里的角色们同样是“一些从生活上跌下来的”人。受惠于“二重人格”,《白金的女体塑像》集并“没有统一的风格”,《父亲》《旧宅》《百日》写尽了世态炎凉与人心寂寞,人们从一个阶级坠落到另一个阶级,从而产生了繁华与寥落的对比。《街景》里的乞丐仅有的糊口理想被动乱社会所扼杀、《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里的舞女的遭遇、《空闲少佐》关于反战的主题无不显示出同情涨满之后的控诉。于是无产阶级揭竿而起,《咱们的世界》里的穷鬼们“整天的在船上乱冲乱撞,爱怎么干就怎么干”、《黑旋风》里的工人们去了山东、《南北极》里的小狮子扔了老爷、打了小姐。最能表现穆时英阶级意识,也可能是他的集大成之作的作品应该算是目前没有发掘完整的《中国行进》。
《中国行进》扉语的开头是五光十色的上海,然而“我”身后却跟了一个乞丐,他的出现承载的是灯红酒绿背后的深重挣扎,批判意义已露端倪。这是一部与茅盾《子夜》相似的、有着概括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总体风貌的雄心的作品,其中有民族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的斗法、抗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亲临战争后个人英雄主义理想的破灭以及在其中展现出的心理过程和他们的软弱性,而关于农民暴动的描写弥补了茅盾的遗憾。暴动代表着《中国一九三一》里石佛镇无产农民的觉醒,他们已经开始思考:为什么田是我们的,我们却没有粮谷?沈从文绝没有这种意识,他的笔下极少写到阶级斗争,地主乡绅与农民从来都是和谐相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穆时英比沈从文更“左”。深刻的是,穆时英甚至比很多左翼作家思考得更多。我们可以将《中国一九三一》与丁玲的《水》做一比较,同样是关于饥饿的农民被逼造反抢粮的故事,但是二者结尾显现的内涵是不同的。《水》中“饥饿的奴隶”走投无路,“吼着生命的奔放,……朝镇上扑过去”,让人感觉似乎“吃大户”就是作者给我们指出的农村无产者最后的出路,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同样是官逼民反,穆时英则想得更多:抢完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他将麻皮张、李二等人领导的暴动的失败归结于人心不齐以及封建小农思想作怪固然颇有见地,但他的深刻之处在于,并没有如丁玲一样给人民指出一条所谓的“光明大道”。当时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问题、路线问题仍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所以当暴动失败的农民各自回家守着从前的薄田漏屋时,麻皮张一个人出走了。他的出走不是失望后的放弃而是寻找,为了实现:这次打败了“下次还可以来”的誓言。这个结尾有点类似另一位左翼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其中的二里半也是在反抗失败之后出走,不过萧红给出的方向比丁玲更明晰,二里半跟定的是“人民革命军”。穆时英对于无产阶级反抗前途的思考并不限于《中国一九三一》一篇,《断了条胳膊的人》里的“他”被机器轧断胳膊,厂里只陪了三十元钱,雪上加霜的贫困生活使“他”妻离子散,申请复工又被拒之门外,于是“他”产生了杀掉厂长的念头。可是在最后关头终于放下屠刀,因为“他”明白:“扎死了一个有用吗?还有人会来代他的”。虽然这个残废的男人最后好像预备忘记这一切好好继续生活下去,但作品最后一行文字(“他第一次笑啦”)显得意味深长。作者是在提倡一种庸人哲学?如果按《南北极》《中国一九三一》等作品的反抗基调来看,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作者的指向就应该为社会制度的更替,“扎死了一个”没有用,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人,而在制度。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只是作者没有说,也正是“不说”才显现出了穆时英的创作在艺术上比“概念化”作品的高明处。
沈从文也有“对于贫穷低下的底层生活的悲叹”,但他的“悲叹”只是悲叹,到了穆时英笔下悲叹才变作愤激,主人公们进而采取了行动。但是他们的反抗多的是自发,少的是自觉,《南北极》《生活在海上的人们》《黑旋风》《咱们的世界》《狱啸》等作品里的反抗如果成功,结果也只是人们生活地位的贫富轮换,反抗者的心胸不是“天下”,仅限于将富人的财富夺过来据为己有,实质上仍然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流寇”思想。不过,虽然他们的反抗是盲目的,但在发展的眼光下与沈从文比起来,穆时英不能不算是一种进步。可贵的是,他在《中国一九三一》与《断了条胳膊的人》里对于反抗前途的思考已经与当时的“主流”作家接了轨。
三
沈从文与穆时英之所以给人远离政治、脱离人生、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创作中的形象与形式选择。他们没有将政治、社会、家国的诉求明而显之地凸显出来,没有高声喊喝应和时代的大合唱,醉心于艺术创造的初心就成了对立面排除异己的“小辫子”。从“五四”以来的第一个有关社会人生的文学现象“问题小说”开始,到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它们的表达弊端在于概念化、口号化,缺乏形象、形式感,而沈、穆在当时的突出、特出贡献就在于他们对于政治、家国、社会观念的形象化、形式化。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由于艺术形式的独异使他们被挤在了文学史的边缘。
在人物形象的选择上,“主流”文学选取的是劳苦大众或者革命者,即使小资产阶级人物,到最后也会转变成革命志士,早期革命小说代表作家蒋光慈的《短裤党》、洪灵菲的《流亡》,以及左联成立后丁玲的《水》《田家冲》等都是这类作品。海派作家选取的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物,而且他们终日颓废于花天酒地。刘呐鸥《都市风景线》、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的角色们大都是混迹于都市的有闲者、施蜇存《春阳》的主人公婵阿姨是一个有产阶级的少妇。沈从文表现民族前途关切题材作品的主人公们也有很多是上层社会人物,例如《八骏图》里的达士先生、《三三》里的从城里来到乡下养病的“白脸人”等,即使那些湘西题材作品里的底层民众也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革命诉求。但是二者所表现的社会、文明批判的主旨依然很明显——与革命作家殊途同归的家国情怀,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以社会分析学的观点将大变革时期的人分门别类加以辨别,从而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立场,所以被代表人民大众的“组织”排除在外。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几乎是每个评论家、作家都承认的基本事实,但是语言从来就不只是形式本身。革命作家操持一套立场鲜明的政治话语掌握着历史转折期文坛的是非判断标准,《流亡》《地泉》三部曲是此中代表之作。无论这些作品如何概念口号化,它们这种写法已经在事实上表现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一页,并展现出革命者的历史心态。历史在其中得到记录,人心在其中得到释放,这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文学使命的最高实现。相对来说京、海的文学语言则不具备这种尖锐性,他们的创作不是努力“摔打”“扭曲”语言,就是含混不清地展览“客观”存在的“表象”世界,他们认识到改良、变革甚至革命的必要,却从不在言语上直接挑明自己到底属于哪一个阵营,暧昧不明的语言导致了他者眼里徘徊不定的政治态度。为了谨慎起见,在没有确认是朋友之前,革命阵营也就只有暂时把他们当作“异己”来对待,于是有了“官的帮闲”与“商的帮忙”之说。
“五四”以来,为了使文学走进民众、普及思想,达到文学“为人生”的功利目的,“大众化”一直是作家们的努力追求。如何提高革命主力军工农大众的革命思想境界是革命作家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他们的作品多采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适合民众审美习惯的情节型结构,在背景设置上主要以党的革命史为依托,并将事与人、情与景尽可能融为一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借鉴传统文学形式表现新时代生活,在极力获取大多数读者的基础上向民众渗透大变革时代的进步、求新精神。这一方向囊括了早期革命小说、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这三者的文艺追求。京、海的作品都不是以情节取胜,他们采取的结构是与革命文学不同的更具现代意味的抒情型和景观型,二者虽也拥有不少读者,但是他们的接受对象不是工农大众,京派的多是具有古典式审美情怀的文人知识分子,海派的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市民。这就牵扯到了与前文提过的相类似的问题,即创作为了谁、代表谁的立场问题。所以他们在政治斗争营垒分明的年代被“‘组织'排除在外”也就理所当然了。
形式只是方法,内核却是相通。当跳出人为的审美规范,把视野提升到中国20世纪前半期整体文艺风尚下来看京、海两派时,会发现他们的政治、社会追求与当时的革命作家同样强烈。穆时英不仅在文字语言方面,而且在人物形象的选择以及作品结构各方面都“比不论多少关于大众化的‘空谈'重要得多的”。他在《作家群的迷惘心理》《我们需要意志与行动》里号召作家与民众行动起来,共同创造“伟大的,民族的未来”。沈从文对文学救国是坚信不疑的,在付出自己的努力后,他还站在客观的角度对当时为什么不能“联合”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如果各派、各人“不走同一路线,它就会有冲突”,如果“作家间真的要团结联合救国,先得有勇气承认那个不能团结不易联合症结所在,各从本身痛自忏悔”。这是一位心胸宽广、无宗派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对于文学救国方案的深痛告诫,他的出发点实在是对于民族发展壮大的拳拳忠心。如此,分别作为京派与海派代表人物的沈、穆二人也就共同汇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框架下,他们与革命作家一样,不是旁观乱世的隐士与浪子,而是勇于奋战的关于现代中国发展的谋士与斗士。在政治混乱、烽烟四起、道德失序的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两者同样秉持着各自的立场,姿态是与鲁迅如出一辙的“横站”。他们没有徘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边缘,而是在潮流的漩涡里努力搏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