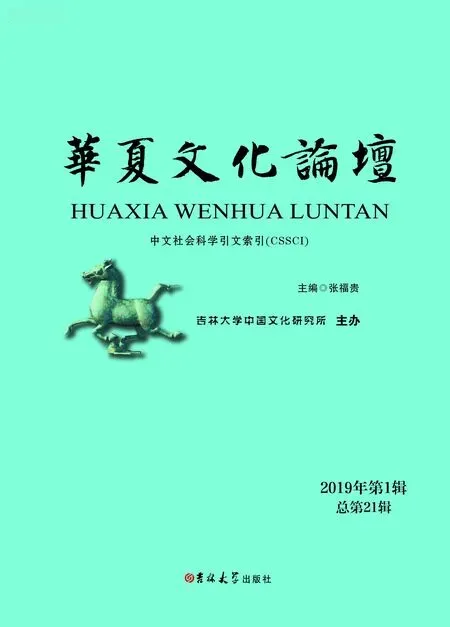文学教育帮助我们判断自身
2019-11-13谭宇婷
格 非 谭宇婷
谭宇婷:
老师,目前国内创意写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请问您是怎么看待的呢?格非:
我其实不太了解什么叫作“creative writing”,这个词在国外就是创作的意思,但是我们这儿都翻译成创意写作。在我来看,写作就是写作,创作就是创作,怎么会有一个词叫作“创意写作”?创什么意呢?这就很像是一个公司,在搞一个文案,搞一个创意。写作本身就包含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创造性,或者说创造力,想象力。所以不需要专门来强调创意。这个词翻译得让人困惑。但是不管怎么说,“creative writing”这个概念在欧洲或者美国很早就在用,后来我们把它这样介绍过来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文学呢,大家都知道,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镜像的文学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当中,非常要紧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文学科学化的过程,文学在原来是一个神秘的终端,它是不可解释的东西。谭宇婷:
请问老师,您觉得文学可以解释吗?格非:
过去文学是不能解释的,也就是说你解释了文学,还是原来的样子,它不会被你消费掉。在以前,像汪曾祺先生说,他当年在西南联大,老师们上课,刘文典给他们讲《诗经》,就是把它读几遍背几遍,一个字都不讲,那个课就结束了。过去中国人讲“冥会”,冥冥之中的那个“冥”。冥会,就是你读着读着,读不懂。读不懂没关系啊,你总有一天会懂的。有些诗歌你记在脑子里不一定懂,但是到了一定阶段你就懂了,需要你和作品之间慢慢去体会,每个人体会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学都是神秘的知识。但是到了俄国形式主义、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概论出来以后,整个世界开始出现一个大的转折,文学被纳入现代学科体制里面,大学也开始设立文学史。在这个过程里面,文学被逐步地科学化、学术化了。大学培养的都是拥有精深理论的一些学者。这样一来就使得文学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一度变得特别重要,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可是这也造成很多问题,就是文学和普通读者之间开始脱节了。文学科学化是为了作品能够解释,它没有那么神秘,我们可以分析。比如新批评,它可以进行文本细读。但是因为它要对文本进行细读,要形式化,要对叙事进行分析,它发明了太多的概念。它在反对一个神秘的同时又制造了另外一个神秘,这个神秘就是理论。你也许能读懂很多小说,但是你读不懂理论,一代一代的大学生都沉浸到理论里面去。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学生进入大学后,是学习对文学的解释呢,还是直接接受文学。这个当中,重新演变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研究的不是文学,而是关于文学的知识,或者说关于文学一系列的话语。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文学作品本身跟读者之间的关系就隔膜了。所以很多大学生他们对理论很熟,但是没有办法来具体判断这个作品,也很难说清自己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开始重新思考。让我们跟文学更近,就不要那么多理论,不要那么多学术化。这个过程中,西方很多高校,引入了驻校作家制度。它开始有很多的与文学直接相关的课程,特别是写作课程。国外像MIT里面,单是写作课,就有十多门之多,非常多。它有黑人写作、妇女写作、传记写作……分得非常细。
我们国家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一开始研究文学都是感性的,文学评论都是一种随感式的。“啊,我觉得不错,我觉得这个作品写得很空灵……”但什么是空灵,大家不知道,大家都凭自己的直觉在发表自己的看法,后来慢慢就规范了。你使用语言要准确,你引入理论要有逻辑性。后来写作也好,文学评论也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80年代以后,各个高校都在科学化、正规化。写作教研室,原来我们各个高校都有的,后来都被砍掉了。砍掉了,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写作这个东西,直接归入文艺理论好了。那么写作课就没有了,没有了就造成非常大的恶果——很多学生连一个基本的文章都不会写。中国过去几千年,你要做官也好、做别的什么事都好,都得首先会写文章。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它的历史变化是怎么过来的。
直到21世纪以后,大家又慢慢发现,写作能力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素质。比如说,你要到一个公司工作,公司交给你大量的文案,你要处理,要写文章,要写报告,给领导起草讲话稿等,都得有很强的写作能力。更重要的一点是,写作能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自身的存在。不是说我们的存在是我们自身可以解释的,而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存在是需要通过写作来发现的。写作帮助我们沉思,帮助我们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自己。写作不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东西记述下来,不是这样,本身写作就是一种发明,它能把你心中蒙昧、黑暗的部分照亮。它是认识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所以写作不仅有实用性的一面,还对人认识自身、对人的成长极其重要。
最近十几年,大家都在谈大学生人文素质,各个学校,比如清华大学,一直在争论大学生是开一门大学语文课呢,还是开写作课,写作变得特别重要。最近一段时间,像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都设立了写作中心,都有作家去高校担任老师。现在作家进入高校也成为一种时髦,我觉得这个过程反映了历史变化中的某种诉求。这是很自然的。
谭宇婷:
请问老师,您觉得写作是可以教的吗?格非:
写作不是教不教的问题,首先设立一个课程,比如清华做这么一个中心的意义不是我们手把手地去教学生写作,不是这个意思。从根本上来说,写作也许是不能教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你给学生开写作课,你来设立创意写作中心,你来帮助学生改作文就没有意义。这是两回事。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看你怎么教了。当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他也是写作老师,他教写作的方式就是他抱一大摞书到学校去,抱到教室去,然后把这些文章发给大家看,让大家学着来写,他也跟学生们一样,也来写,看谁写得好。这样一种方法能慢慢提高大家的写作能力。过去很多大作家,像吴组缃、叶圣陶,他们都在帮学生改作文,我也非常重视修改这一方面。因为我当年的写作也是一个例子,如果没有《收获》许多重要的编辑帮我们改稿子,认真要求我们写好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对写作的认识。这个过程是非常需要的。如果不由大学中文系来完成这个工作,那么还有哪一个机构能完成?当然应该由大学来承担。至于它有没有用,它肯定是有用的。至于它是不是来教写作,不一定。它把写作本身所需要的基本东西都教给你了。比如小说这个体裁,它大致的形式,它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变化,老师把它作为一个背景介绍给你了,帮你扫走很多问题,让你有章可循。然后呢,不是说每个同学在接受了这些基本东西之后,就能马上成为作家,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必须提供这样的教育、这样的训练,提供了这样的训练以后,可能会有些人脱颖而出;有些人能极大地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改善写作技能;还有部分同学能够精通文字;有些同学能读一些作品,能提高自身修养。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写作都非常重要。不是说写作课一定要教人写作,而是它带来的这个训练过程对大学生的素质和成长来说极其重要,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问题。而不仅仅是说它是不是能培养作家,能不能教出学生来。所以你刚刚提的那个问题是不对的,不能这么提问题。
谭宇婷:
开设了创意写作专业后,很多人就在争议这个问题。格非:
这个争议是不对的。他们只看到了皮毛,好像大学一旦设立了创意写作中心,设立了写作课程,开硕士班,就是为了培养作家。能不能培养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这么提出来,而是说这个举动到底带来了什么,这不是一句“能不能教”就能涵盖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偷懒,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媒体很多时候就喜欢把一些问题弄得很简单,这样的话很多问题非黑即白,然后他们给你提一些质疑。但实际上从高校来讲,不管是对一个人心智的成熟、对文学的了解、对于整个文学史的纠偏,还是出于对整个高校培养人才的综合考虑,写作都极其重要。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说它能不能培养作家。很多人没有必要当作家。试问中国每一个读《红楼梦》的人都想当作家吗?不是这样。他觉得读《红楼梦》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这就足够了。他从里面读到一些道理,他觉得对自己的生存有帮助。他有时候遭遇危难,《红楼梦》给他提供很大的安慰,给他提供很多想象,使他生活在一个历史的人文环境里面,让他跟传统、跟现实保持一种紧密的关联,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你刚刚提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不断纠正?这个问题不重要。正因为我们提了这个问题,把很多重要的问题都掩盖了。谭宇婷:
请问老师,您现在上课的话,也是跟学生一起读作品,然后跟他们一起写吗?格非:
我们那个课程叫作“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首先是文学名作,我上课的时候给他们介绍大量的作品,每次课结束的时候我会布置他们读一些作品。谭宇婷:
请问老师,你们布置的作品会有一个体系吗?格非:
嗯,当然讲到某些部分的时候会推荐一些,跟我讲的内容相关的作品。你光讲了某些理论,大学生不一定能理解。你给他推荐作品,他一对比就明白了。比如叙事速度,这个速度有快有慢,你就提供叙事速度快和叙事速度慢的作品给他,他就知道为什么节奏感在叙事中特别重要。你讲到节奏的时候肯定要讲到叙事的快和慢。比如说你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你这个动作本身可能需要几秒钟,你把这个动作写下来需要几秒钟。但是如果是慢速叙事的话,会非常复杂。在文学史中有非常多这样的现象。我上课就是让学生了解关于文学也好、写作也好、叙事技巧也好,它所有的背景知识,然后给他们提供大量的作品,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每门课,一个学期至少也会要求学生很认真地写三到四篇作文。谭宇婷:
请问您也会参与吗?格非:
我不去,都是我的助教在管这个事。谭宇婷:
请问老师,您对写作教育的前景是怎样看的?格非:
这个不存在前景的问题,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首先要判断它有没有意义,它有意义就行了,我们就去做。你说的前景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后要取得很大的成功?谭宇婷:
不是,我指的是它以后的发展趋势。格非:
任何学科的设置,都是在一种知识的平衡体系里面,这个体系需要达成一种平衡。如果大家最后又都鄙视理论了,鄙视这种科学的总结,大家都在创作,那么理论最后也会反弹,它慢慢会达成一种平衡。而现在我们的平衡是在另外一面——这个学科规范化、理论化很厉害,大学生空有一些理论。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大学生本身的经历匮乏。由于他们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了,跟社会几乎是隔绝的。像我们那个年代,十几岁,你就已经在生产队挣工分了。你一个人在外面待个三四天,父母也不会找你。那个年代,你很早就懂事了,就能独立地面对所有事情。今天的学生是做不到的,不管是从情感还是他们对社会的了解程度来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文学非常重要,文学提供了非常多的了解社会的途径。至于前景,我是觉得,“前景”这个词我没法判断。要是说发明一个火箭,我可以说这个火箭将来可以极大地提高中国国力;发明一个航空母舰,我可以说它可以极大地提高中国海军的战斗能力,那这是前景。创意写作能有什么前景啊,它重要,我们就去做,这个前景你是看不到的。只有等这代人的素质提高,这个社会处于一种平衡,达成一种良性的运转,你才能判断。人文方面,很多东西,化成天下,你看不到的。雨落到地里,麦子长出来,水怎么进去,养分怎么吸收,你是看不见的。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前景呢,有的时候很难把握。我们考虑一件事情不是说它会带来什么功利性的目的,而是说它对知识的积累、对学生的成长重不重要。如果大家觉得重要,就去做。至于你说的这些,一定会有作用,这个也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评估。现在这个事情我们才刚刚开始做,就不应该急急忙忙去预测它的前景。
谭宇婷:
老师,您先前提到大学的教育对您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又提到了您的经历对您有很大的影响,请问您觉得对写作来说,教更重要,还是经历更重要?格非:
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原来写作是真的不需要教的。因为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写作课我们从来不去上,写作课讲的都是那些条条框框,怎么写文章,怎么写论文……老师拿来的范文,都是我们认为写得很差的作品。80年代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要比老师走得快得多。你知道的东西老师很多都不知道,你整天在图书馆看的东西太多了。那个年代很特殊,那个时候我觉得写作确实是不需要教的。可是在今天我认为写作是需要教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学科门类的知识非常复杂。在古代,大家考虑写文章主要是为了科举考试。今天写文章,语文只占一部分,作文只占一部分,中学也都是应试教育。学生到了大学里面读书,他会受到各种东西诱惑,比如说游戏啊,网络啊,平面媒体……大量的时间就被消耗在这些东西上面。那么人怎么能判断自身?我刚才说过,文学非常重要,它帮助我们来判断自身在整个社会关系里的位置。这个过程中,人文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一切行为,都需要确定行为的意义,就是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事情,我的生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今天很少有人讨论这些问题。当然,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里面,这些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只要信教,这些意义是本来存在的,你是为了信奉上帝。在我们国家,没有宗教传统,所以我一直认为人文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个工作——提供意义。人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文学,就是写作。而且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讲,他要能够有效地对抗今天这样一个欲望化的社会,他必须有自己的定见。这个当中,人文教育就变得非常重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这么一个课程,一个训练,帮助你多读一些作品。你要知道哪些是好作品,怎么去理解,这个阐释史是怎么过来的,这些都需要教。
而过去呢,是依靠基本经验就可以写作的时代,你拥有别人没有的经验,便可以把你的经验写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创作实际上就是经验的交换。比如我经历过一次海难,你没经历过。我到过好望角,你没去过。我把我的经历写出来,你就得看我的,我把经验发给你。你谈过恋爱,我没谈过,你把你谈恋爱的经历写给我看,让我感动。那么我们就在交换经验。在过去,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在过去,很多人没读过大学,像高尔基、狄更斯等,但他们经验非常丰富,他们读过一些书以后,有一定能力,就能写作了,他们的经验就可以呈现出来。今天不一样,今天大家拥有个人独特经验的可能性越来越少。所有人的经验几乎是一样的,你们都是在学校里读书、做题目,大家对未来的期待、梦想都一样。现代社会对人的掌控越来越严格。这样的时候,你把你的经验写出来没人看,因为所有人经验都差不多,我们把它称为同质化时代,或者另一个概念,碎片化时代。碎片化时代的意思是说,过去的社会是整体性的,比如一个农民,他要烤出面包来,首先要选种子,种麦子,再慢慢浇水,等麦子长完了把麦子收下来,再去烤面包。今天不是这样的,今天是选种有人负责,播种有人负责,管理有人负责,收割有专门的人负责,脱粒、磨碾、做面包全部分工了,这个工序有几十种,没有任何一个人了解全部工序。可是过去所有工序农民都了解,从选种到面包烤出来。今天没有人拥有整体的知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知识碎片化,同质化了,大家都一样。在这样的过程里,人慢慢丧失了自我。你渐渐地发现你跟大家完全一样了,你不知道为什么,便跟着这些人在走。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你怎么判断自身?文学就提供这样一个方面的思考。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文学的训练,你说能不能教,一定要教。在过去,一个人上个大学了不起了,可是在今天,所有的作家必须上大学,你可能还要读一个好的学校,你有好的训练你才会不一样。你得有很多方法,你才能确定自身,你才能看到很多很难看到的、自身存在的隐秘的东西。这个东西不再像过去,五十年前那样,不言自明。比如过去在农村,像赵树理这样的,听听故事啊,农村谁和谁谈恋爱,闹了纠纷,把它写一写,城里人看一看,觉得这些很好玩,他就成了大作家了。今天你能做到吗?做不到。所以呢,今天大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训练的情境,大家水平普遍提高了。我觉得将来不太可能有什么没读过大学的、没有什么知识积累的人能成为大作家,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时代不同了,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
谭宇婷:
老师,作为一个学者去研究东西的话,他的思维可能偏理性,作为一个作家,他需要感受力,请问你觉得这两者思维之间会有什么冲突吗?格非: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其实不存在这样一个分别,这个问题被别人夸大了,好像人有两种能力,一种理性思维能力,一种感性思维能力,你仔细想想,这不可笑吗?难道你在需要感受力的时候,你没有理性思维吗,你没有逻辑吗?你在写作的时候,你不知道开头、结尾、中间,这个故事怎么写吗?不需要理智吗?难道你不知道别人作品写得好是因为什么吗?你不分析吗?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综合的。只有中国人才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西方没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像纳博科夫、艾柯等都是大作家、大教授,艾柯还是符号学专家,国外没有人问这个问题,说理性思维会跟感受力冲撞。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大部分人都受过同样的教育和训练。即便你没有上过大学,你可能也在互联网里,跟大家受到一样的知识熏陶,大家看到的新闻都是一样的,都是某种新闻供应商供应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可能有另外一种真实,但是你看不到。一个单位、一个村庄随时都在发生无数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新闻供应商是不让你看到的。新闻供应商一定让你知道黄晓明怎么样、周杰伦怎么样、他的岳父怎么样……一定是让你看到这些东西。就是说你接受的东西是被别人控制住的。因为这是资本生产的一个非常大的逻辑,它可以融化很多含义在里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其实大家接受的东西都差不多。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首先是不要害怕,说你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会妨碍你的写作,另一方面我觉得这种分析对写作是必要的。在今天的社会,如果没有这种分析能力,你连找到自身起码的真实的可能性都等于零。人就是一个欲望的奴隶,跟着所谓的时尚在走。所以当年章学诚说“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如果一个人要跟着时尚在跑,这个人就完全不可能思考。时尚比抓你去监牢的人更可怕。你怎么建立起自己的独立能力?你一定要有分析能力,一定要对现在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对控制你的话语要有分析能力,要能够去刺穿它。写作也一样,写作这个刀、这个针一定要扎穿这个帷幕,然后你才能看到那个真实性,写作才变得那么珍贵。而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缺乏分析能力,有些写作就按自己的意愿、基本的经验写了。写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固化了那个资本的逻辑。你没有办法对社会提供帮助,反而是助纣为虐。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觉得你干了一个好事,因为你作品写得很差,提供了一个消费的很糟糕的作品。大家都陷入一个麻痹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好的分析能力。所以理性思维也好,感性思维也好,还有那种想象力、勇气等都是综合的,是不能分开的。你问我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你想问,而是大家都在问这样的问题。没关系,我不是说你问得不对,是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谭宇婷:
嗯,老师,我们知道您之前参加过爱荷华写作计划,请问那里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格非:
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触,爱荷华写作计划是邀请了三十多位世界各地的作家到一起,住在一块儿,然后唱唱歌、喝喝酒、看看电影,大家在一起住一个月,然后还分成好几拨小分队,到美国各地去旅游,钱都是美国政府或者亚洲基金会之类的提供,待遇很好啊。但是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基本是足不出户,待在房间里睡大觉。因为我觉得他们那种东西花了很多钱,作家们到了一起,真正能进行研讨的东西不多。搞一些朗诵会,它的目的很明确,但我觉得这个交流并不是很有效。如果是我要请你来,我一定是把你的书先读一下,然后挑出你的书里最好的一些书;我要请来的另外的作家,一定是把你的书先读个好几遍,对你充分了解,然后大家再做一些专题的讨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交流。你把三十多个人往那里一放,有的是克罗地亚来的,有的立陶宛来的,有的法国来的,还有印度来的。这些人语言五花八门,而且它也不提供翻译。大家交流只能靠一些蹩脚的英文。比如那个韩国人,他的英文比我的还差,但是他被要求用英文演讲。他的演讲除了他自己之外别人都听不懂。这样呢,我觉得它有一些细节的设置是形式化的。当然它有一些青年作家项目,也不能说人家毫无乐趣,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是我了解了美国,我在那里观察了一些美国人,我到美国家庭里面去,在那个环境安安静静地待下来。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它整体还是做得比较粗率。
谭宇婷:
嗯,我们国内现在一些高校觉得那边做得比较成功,然后把那边的研讨会之类的组织形式引进来了。格非:
中国人,实际上,我觉得有些地方已经做得比他们好了。中国人呢,很崇拜西方,但是西方呢,是不崇拜中国的。西方人也不崇拜立陶宛,不崇拜非洲人。它把你请过来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我不讲你们也清楚,这背后很复杂。它觉得把你请过来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大家到了一起。中国人不一样,中国是你把一个国外大作家请过来,是当菩萨来供的,研讨会非常深入,会有大量的翻译,不会浪费时间,会有无数人来。这在美国是做不到的,它就是把一大帮作家招过来,你爱干吗干吗。它还有很严格的规定,每个作家经常会做一些研讨,这些研讨都是非常皮毛的。我现在感觉没有一次研讨会让我有深刻的印象,爱荷华的那些在我看来是很需要改革的。我在那里最大的收获就是聂老师,聂华苓老师。我基本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整天猫在聂老师家里,聂老师就请我喝香槟酒,然后把一些中国作家、朋友请来,一天到晚海阔天空聊过去,真过瘾。这是中国人的做法。但是它们那个中心IWP,我觉得过于形式化,机械化,没什么意思,就玩一些游戏。
最后的时候,他们提出来,要我跟一个伊拉克的作家去演一个电影,扮演一个角色,我们当时觉得不去也不好,就去了。去了之后,他们要我们俩站在一个山坡上,我们就站在一个山坡上,要我们走过来,我们就走过来。然后有一个美女走过来,背着一个吉他,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他们叫我们转过身来,去看那个美女。这个视频在网上还能搜到,我有段时间还能搜到自己演的那个视频。它做得很好玩,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它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我觉得作家不需要这个,作家重要的是思想的碰撞,就是你的问题在哪,我的问题在哪,怎么面对我们共同的文化境遇,这是非常要紧的。他们这样显然是面对中学生的做法,如果搞个夏令营这样做是可以的。
谭宇婷:
请问老师,您对现在的文学教育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格非:
我很难说,因为我不了解清华大学以外的学校是怎么做的。虽然我也是北师大的驻校作家,但他们怎么做的我确实不是特别清楚。你们将来可以去访问张清华教授,他是那边负责人。复旦怎么做的,北大怎么做的,人大怎么做的,我都不了解。我只了解清华怎么做的。清华刚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给你们提供。这个中心刚成立,还没有开始运行。但是我们的设想是这样的,从大的方面来讲,我觉得需要去和世界的重要的作家去进行某种沟通、交流。而重要的作家,我们过去的一种想法就是,所谓的,他们开玩笑说是一些功成名就的、得了诺贝尔奖的大作家,把他们请过来。但是我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有很多作家,可能要等到一百年后,他们的名字才会被别人知晓,就像卡夫卡死后几十年别人才知道他;就像耶茨这样的大作家,美国的,差不多过了五十年,世界才突然发现,这里还有棵大树。我们不仅要关注那些已经被肯定的、重要的作家,也要关注那些真正的、还没被肯定的大树。所以,从大的方面,我比较希望跟五十来岁这个年龄的作家交流。第二呢,我觉得国内的创作界有很多不被人知晓、非常重要的年轻人,我觉得我们需要来进行对话。再有一个就是校园文学,清华大学自身的学生的创作。我们这个中心成立以后,所有同学都可以向我们中心提交作品,我们随时请作家给他们修改,给他们提供反馈的建议。当然我们也会有中心的开放日,一个月一次,邀请学者、作家还有学生来座谈。当然我们也会设立一些文学奖项,面对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这样有助于校园文化的开展。至于其他学校写作中心的问题我不太了解。
谭宇婷:
请问老师,您对我们这个年龄的学生学写作有什么建议呢?格非:
有一个词叫“多元化”,这个“多元化”我们今天谈得很烂了。我们今天说什么东西的时候,你都用多元化来为自己找借口。你爸爸妈妈要说你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说我多元化,你有你的一套,大家彼此共存,别来干涉我。美国人要叫你干什么的时候,你说不不不,我们多元化,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一套。这种多元化慢慢就变成一种相对主义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一种被伪装起来的多元化。我希望你们不要被这种虚假的多元化所迷惑。在这个多元化里,占得最多的可能还是流行文化的东西。我们小的时候也崇拜流行文化,崇拜影视歌星,都一样,但真正的多元化除了这些流行文化的东西,也包含了很多重要的、正规的知识,比如经典的文学作品,大量的关于戏曲、绘画、音乐等方面的知识。我觉得我们今天修养、视野等方面都很狭窄,我们需要扩大我们的视野,这样的话,才会对写作形成真正的帮助。举个例子,比如张爱玲这样的人,基本上不怎么出门,比较傲慢,比较清高,脾气也比较怪,但张爱玲的知识面还是很丰富的。中国传统历史章回小说、中国的笔记、戏曲、大量关于民间文学的东西以及很多西洋的知识等,她都很用心地去了解。当然这跟她的家庭有关,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多元化变成相对化了,所有知识都被分割了。所以我觉得在你们大量阅读网络科幻、悬疑、穿越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应该多关注关注真正的文学史的重要作品,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千锤百炼的精品。我们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边不看,而去看一些缺乏营养的快餐式的作品,你想你是一个理智的人吗,你根本不是。并且你的压力非常大,你是被这个社会所裹挟的。如果你不了解经典作品,你跟很多人没法对话。不是说你不能听那些流行音乐,是在这同时,你要知道音乐史上那些更重要的作品。当你在网络上浏览那么多摄影照片、艺术作品的时候,你要了解整个艺术的发展过程,了解艺术史的脉络,西方的、印度的、中国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东西,你的人生是有非常大的缺憾的。你要调整你的知识面,只有调整了,你的知识才会在一种真正多元的结构里面。然后所有这些流行文化也能给你提供帮助,流行文化能够帮你直接了解现在人的情感、基本状态,那也很重要。我觉得我们现在太偏,偏于一隅,这样的话,就谈不上写出好作品。
我觉得现在同学的写作能力都很强,很聪明,大家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孩子的成长倾注了太多心血,在各方面要求都很严格。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远远达不到你们现在读大学时的文字能力,这是你们非常大的优势。可是你们也有你们的问题,问题就在于没有那么丰富的知识系统,太受流行文化的影响,这样的话,这个文化的状况聊起来就让人担忧。这种担忧不光存在于中国一个国家,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想在美国社会里面很多人不读莎士比亚,这很正常。谁读莎士比亚?大家都在读那些流行的东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韩国人也一样,我觉得中国人比韩国人好一些,我在韩国教书一年,都快憋死了。在韩国,没有一个人跟你谈稍微严肃一点的话题,没有人感兴趣。在中国,你可以聊聊福柯、德里达等等,你要到韩国,找人去跟你谈福柯,当然不是没有,有,很难很难,他永远跟你谈的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行的东西,那些网络新闻整天曝光的东西。所以我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系统,不要被我们今天所谓多元化的东西迷惑。今天我们说的多元化其实就是相对主义。而真正的多元化是需要你的经验与他者的经验互相碰撞,碰撞以后你能够及时发现自身的特点,然后不断改进自身,使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有助于个人的成长。我们中国人过去说的就是致良知,或者说修身,这个特别重要。这些东西都会对你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今天学习途径非常广阔,如果你想学习什么东西,今天的社会所能提供的便利是我们当时的不知道多少倍。举例来说,我们当年一本书出版要等很多年,今天没有这个问题,今天所有书你都能在网上查到。而且查资料我们要到专门的地方去翻,然后用相机拍照,拍出来之后慢慢地查,再弄出来复印,很困难。今天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大量东西在网上都有。正是因为你们的条件很便利,使得大量的时间被消耗了。你们都知道你们专有的知识在哪个层面,你们最拿手的知识在哪个层面。我现在跟我的学生在一起接触后,我发现我跟他们确实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们一拿到手机之后哗哗哗哗,一些东西就运过来了。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神奇,他们说太简单了。一旦要我在淘宝上购东西的时候,我就特别恐惧。所以我们跟你们不一样,在这些东西面前,我们有我们的局限。
所以我们要能够发现他者。如果在一种自以为得意、甜蜜的、永远在肯定自己的虚假的东西里面,你的自我就迷失得更快,而且更彻底。它没有办法促使你反省。《红楼梦》里面说“眼前无路少回头”,是因为人在欲望里面,你不到眼前无路的时候你是不会回头的。眼前无路的时候就是“他者”。为什么当一个人生了病,这个人马上就会反省自己?因为这个病是“他者”,这个东西是你不愿意要的,它强制进来。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没有多久了,你会反过来思考一些大问题,平时你是不会思考的。当然我觉得不必要等到那个时候,文学作品里面有很多你原来根本不适应、不喜欢的东西。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根本没有鹿晗那么好看,那么漂亮,那么赏心悦目,但是他等着我们去理解他,一旦你理解了之后,你会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天地。这个东西是鹿晗不可能提供给你的,鹿晗是会让你舒服,他肯定你的动作,肯定你的选择。
说到年轻人的文化,我的想法比较多,可以提供的建议也很多,说不完。但为什么要挑“多元化”?我不反对大家对流行文化有兴趣,我刚才说了我们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要在一个真正的多元化过程里会比较好。比如说我要有能力来肯定我的生活,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天跑到温泉旁边买了一栋房子,他与世隔绝,跟所有人都不来往。我突然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个地方需要你去干一个什么事,能挣很多钱,他说不不不,他不干。当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他要有能力肯定他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个动力是哪来的?是基于他对世界的了解,生命的理解,他才可能做出这个有意义的举动,并且他承担了这个后果。
我们今天往往要挣扎一下,你要选择你的生活道路,你的依据是什么,你哪来的动力,谁在支持你,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这都是问题。假如所有问题都不想,那么好了,我们走一条最舒服的道路,你跟着别人跑。这样对年轻人的危险更大,这个责任不在你们,这是我们这个社会造成的。目前我们这个社会欲望化的过程还远远没有过去。我觉得年轻人对这个要警惕。今天有很多网络作家,写了好几千万字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价值吗?就是一堆废纸而已。挣了多少个亿的钱,有用吗?如果我们真正热爱文学,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文学,然后在这个过程里有自己不可动摇的对于文学的见解。要建立这个东西,你没有真正多元化的知识,你是很难做到的。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就没必要写作了。因为写作是一种重要的发现,写作的重要功能绝对不是提供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