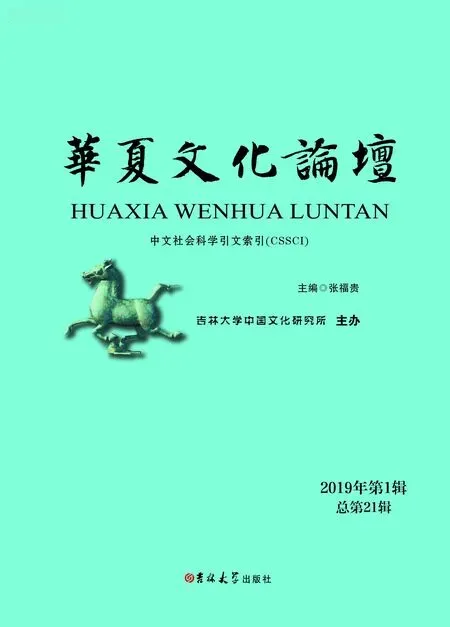新闻专业主义的文化政治
2019-11-13盛阳
盛 阳
一、引 言
新闻专业主义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在现代通信技术升级改造、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不断发展的转型过程中,传统新闻业在技术、政治、伦理和正当性层面也受到诸多挑战。在这些不确定条件下,新闻专业主义既被用于充当巩固行业合法性的理论武器,这一概念自身也持续遭到解构和挑战。作为不断延伸和拓展的知识范畴,新闻专业主义内部不乏客观性、中立平衡等重要的价值理念,但是,如果将专业主义视为整合新闻实践及其价值判断的基本前提,作为标尺存在的专业主义本身就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
事实上,新闻专业主义是历史性的话语构造。根据哈克特和赵月枝对新闻客观性的观念史研究,在19世纪的北美,正是商业报刊对劳工报刊民主话语的吸纳,客观上奠定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石,造就了工人阶级报刊的迅速退化。在20世纪后期的西方社会,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推动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发展。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安排下,新闻专业主义不断扩张,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如果类比丹·席勒(Dan Schiller)对传播技术政治性的论述,新闻专业主义不是天然存在的哲学概念,而是保守性的政治力量:新闻专业主义的出现,“正是打破社会力量平衡的激进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本文将从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潮切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文化政治展开分析。首先,本文从新闻与文化政治的角度,系统梳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涵。作为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思想背景和历史语境,新自由主义的行动诉求和政治原则,为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文化政治及其政治经济学意涵提供了结构性框架。其次,本文从媒介技术变革的历史与当代语境,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诉求与现实困境。最后,本文从中国语境出发,批判性地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
二、流动的学说:新自由主义知识考古
作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分支,新自由主义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作为对社会主义理念及其制度的批评,新自由主义在米塞斯、哈耶克等小范围的经济学家内部传播。这一思潮最初秉持的理念是,“不必对人类需求进行探求,只需用科学规划的方式把握住买主偏好”。作为理论设计,新自由主义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简要来说就是把经济从政治中剥离,用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程序正义等手段替代高度组织化的经济生产模式和实质正义,批判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
新自由主义不是通约式的公理,也从没有在现实政治中获得彻底执行,是一种“不完整”的历史和政治实践。作为实用主义的政策设计,新自由主义被国家政府部分提取并选择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它被认定为强有力的反社会主义理论资源,这里的社会主义既包括世界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元素。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一项激进的政治议程。
需要历史性地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威慑力。在理论诞生的最初,它并没有进入西方的主流政治议程,却通过单向度的知识输送、政策引导、技术支持、舆论宣传等多种方式,参与到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解体、拉美军事政变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中。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试验帮助新自由主义完成了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得它通过“理论旅行”的方式从“试验场”再度回到欧美政治舞台中心,成为里根—撒切尔时代执政的主导资源。
在世界范围内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理论落实为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建构性目标,其中包括在行政体系、经营管理、财务审计等宏观制度层面去组织化的改造;也包括微观层面,对于去技能化的、竞争型生产关系的塑造。哲学层面用个人主义、普遍主义理念替代全球结构性不平等条件下激发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技术层面,新自由主义政策通过对生产率、比较优势、法制程序等经济、政策、法律指标的强调,替代管理自主、技术主权、阶级政治等实质正义过程。新自由主义表现为有着强烈政治对手——发生在被外部化的内部和被内部化的外部的,想象的或实体的激进主义。
可以借助政治社会学进一步理解新自由主义。哈佛大学批判法学家昂格尔(Roberto Unger)对政治有广义、狭义两种区分。在他看来,政治可以被狭义解释为“政府机构及其权力配置”。一般而言,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对政治的传统定义,进而通过政治科学公理化、量化研究和概率论等对社会政治的不确定性进行开放分析。另一方面,政治也可以被广义地解释为“统领于社会生活、个人生活所有方面的组织形式和交往方式”。在他看来,应当更多地从广义方面来理解政治。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视野中的政治体现为双重性:政治首先被框定在狭义的行政范畴中,再寄希望于国家政策的进入、推动和落实,用政治进入的方式反政治。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将国家的意义全部挤压在狭义政治的密闭空间,再用广义化政治行动的方式,发动对国家政治的反叛。
新自由主义政治议程在抹去国家政权丰富意义的同时,又以要求国家推动市场化的方式拓展了政治权力的边界。在新闻实践中对应着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这种广义化政治不是人民民主意义上的政治实践,而是被资本和权力捆绑住的政治议程,也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过程。
三、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新闻专业主义
切换到传媒行业,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为“去规制化”的政策手段,即通过降低媒体准入门槛、开放市场准入权利,让多样化资本进入原来封闭、垄断的媒体行业,从而改变原有公共服务的垄断格局。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1996年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从全球范围看,这演变为一场“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资产集体转让”:“从1988年智利电信运营私有化开始到2005年,不少于80个欠发达国家进行了网络私有化”,巨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对私人投资的开放,将美国“曾经最大的工会化雇主变成了股票交易量最大的商业公司”。根据北京大学吴靖教授的分析,电信法案的发布,直接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21世纪初期出现的大量媒体兼并。这一兼并过程不仅在资本规模方面越来越大,内部更出现了跨行业的资本整合。而原本基于公共服务的考虑,媒体不能一家独大,例如虽然电视行业存在垄断,但它的另一面是广播或其他媒体渠道对电视行业的竞争。凭借政策推动和资本执行,新自由主义被注入美国媒体专业主义的观念体系中。
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进入公共服务的正当性,建立在“新闻媒体不应当被赋予过多的角色期待”的行业定位,以及“制约公共生活的真正障碍来自体制结构”的双重认知条件中。“中立”的新闻专业主义被积极调动,改造被体制束缚的公共服务体系。相反的观点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不是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的观念,它恰恰建立在对新自由主义体制结构的认同上:“新闻专业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反意识形态、“后政治”(post-political)的意识形态话语。
更为重要的是,新闻场本身就是公地(commons)的一部分,内在于社会关系中,因此“新闻专业主义进入公共服务”这一议题牵涉到谁是新闻传播的主体这一问题。如果承认新闻事业本身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中国的新闻事业是与人民民主专政在主体性方面高度统一的,那么新闻专业主义试图“进入”公共服务的议题则至少包括了两层含义:第一,新闻专业主义首先要割断新闻事业与国家制度的联系,即新闻“离开”公共服务;第二,在完成行业独立、资本化运作改造之后,再重新“进入”公共服务市场,瓜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及其文化领导权。所以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新闻专业主义如何走进、参与公共领域,而是公共性如何在新闻报道中得到体现,“无论用哪种最前沿的理论或最新潮的视角来看,‘走基层'报道的实质都是让新闻报道回归其‘人民性'和‘公共性'的主体,让普通民众成为新闻生产和传播的主体”。这再次说明,新自由主义并不能仅仅从市场原教旨主义、极端消费主义以及绝对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层面去理解。
事实上,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辨析,无法脱离开传媒资本运作等权力体系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传媒机构中的展开,自有其政治经济土壤和社会文化语境。与新自由主义相同,新闻专业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想象,从来没有完整地得到执行。以西方媒体中大量存在的“恐怖主义”宣传报道为例。西方思想界已有对《纽约时报》、CNN新闻台等主流媒体的深刻反思。《美国的恐怖主义成瘾症》(America
's Addiction to Terrorism
)一书就指出,对“恐怖主义”的混用,恰恰是造成社会和思想失序的根源。事实上,如果媒体配合当权政府,对当代中东、伊斯兰等复杂问题一概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仿佛只要把社会矛盾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恶的“恐怖主义”,就可以停止追问、停止思考,一切就得到了合理解释。这种思想的懒惰造成了对其中蕴含的阶级分化、贫富差距等全球性议题的视而不见。进一步说,新闻界的思想快餐和眼球经济只是专业媒体缺陷的表象,更重要的是,那些把持信息和思想生产权,同时以客观中立为标榜的资本化媒体——它们客观中立性的前提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直接抹去了对社会问题进行严肃辩论、分析和思考的公共空间。实际上,专业性只是西方媒体报道在操作层面的规范,而这种专业性的行业规范不是专业主义所断言的去政治化的、排他性的绝对主义。进一步说,专业性理念本身就有自己的前提预设和政策主张,即它是在特定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土壤中生长的,因此主要是对这一制度的默认和维护,并通过信息传播、改造资源配置的方式保持和推动这一制度的运转,是一种保守性的政治力量。这并不匹配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政治语境。
理论上,新闻专业主义可以理解为在新闻生产环节中对生产过程、工作伦理的规范化要求。但若我们仅仅从本质主义层面对其进行辨认,那么我们对它的认识就基本止步于“真实、客观、平衡、全面等天然正确的理念”。然而新闻专业主义运动是在新闻伦理和政治社会学范畴内展开的一项政治改造运动。它通过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所言的“美国新闻史的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 of American journalism)的批判,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我们需要在动态的政治关系和更开阔的社会空间中论述这一过程。它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在西方传统媒体中,新闻专业主义首先将存在着劳资对立的行业群体抽象为一个整体的“新闻人”,忽略了作为劳动过程的新闻生产内部的雇佣关系和劳资关系,抹去了政治经济分析的空间;
第二,专业主义将广义上的新闻生产裁定为编辑部内部的专业化职业生产。编辑部行业门槛和自我隔离,切断了与制版、印刷、分发等传播产业链之间的联系(在新闻生产的数字化时代,传播产业链延展至全球范围),理论上拒绝了整体性分析的可能;
第三,法权层面,新闻专业主义对使用权的强调,以及对所有权转移问题的遮蔽,催生了新闻领域内的雇佣劳工职业群体。“从阶级撤退”的劳动分工方案,使得文化政治与阶级意识形态的辩证分析变得不可能;
第四,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世界劳动分工体系与全球市场的形成,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史观、意识形态的形成,共同培育了阶级情感与国际主义意识模糊的西方中产阶级群体,这一群体在供给侧孕育了作为职业群体的新闻从业者,在需求侧再生产了意识形态模糊的都市消费主义群体。
问题是,在西方大众媒体议程中,很少能看到对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思考,而中国都市媒体除了对传播消费过程——例如点击率、收视率、票房、移动通信和新媒体终端销售状况等——给予关注,媒体视野中的中国南方生产线以及产业工人几乎都被纳入国家与市场对立的分析框架中。用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解读,这与西方媒体处在全球传播生产体系相对优渥的核心地带,中国媒体处在亚核心地带,因而处在各自特定的政治经济视野密切相关。西方媒体看到的非洲,不是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依旧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盘剥的、苦难深重的不平等地区,也不是日复一日将通信产品原材料运输到全球南方进行再生产的产业链底层,这个具有全球意义的跨国劳资问题被翻译为文明等级与文明冲突问题。
四、媒介变革视野中的新闻专业主义
传播技术的发展再次将新闻专业主义推上议程。在新媒体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如何看待新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主流逻辑是,互联网技术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平台媒体等科技手段,在国家产业政策倾斜条件下,将信息传播的产业化不断纳入互联网产业内部。传统新闻业不得不被动地展开新媒体技术转轨,否则将遭遇无情的行业洗牌。这被广泛解读为技术问题:技术发展对传媒业来说不是令人欣喜的文明进步,而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生死存亡问题。不仅如此,技术变革和普及还带来了“后真相”的道德恐慌,坚守专业主义则是这一逻辑下的必然产物。
如果单从技术发展史来看,技术升级本身只意味着技术间的迭代,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进步性在于提高了传播生产力。那么,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何以造成媒体行业内部恐慌,甚至在现实层面造成了实践转型和大规模的失业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首先回到《资本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生动地讲述了百年前的欧洲“人机大战”斗争史:在1758年,英国首先制成了水力剪毛机,但是它随后就被10万名失业者焚毁;19世纪初期,蒸汽织机的应用又造成英国规模浩大的工人破坏运动,即著名的鲁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在那里,新技术的发明对掌握旧技术的工人来说不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提高,而是劳动机会的替代。工人与技术之间不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马克思从“劳资关系”展开人机斗争史的分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他特别指出两点:第一,工人反抗机器和技术是不理智的,工人学会区别开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从而把攻击的矛头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它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第二,工场手工业内部为工资进行的经济斗争,是以这一生产关系本身为前提的,因而是不彻底的,“根本不反对它的存在”。根据马克思的判断,与资本捆绑的技术发展,只能带动新兴资本对原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挑战,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对原有市场结构、资源配置、劳动分工等多方位的冲击。因此,技术的发展才会一方面表现为现代文明的进步、新的劳动分工的形成,另一方面同时表现为对部分劳动机会的摧毁。
数字平台技术对市场化传媒业的改造也是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个体的斗争,比如斯诺登对美国新闻业和秘密政治的揭露、反对知识私有化的“著佐权”(Copyleft)运动、政治权力对网络知识共享倡议者的压迫,以及《点共产主义宣言》(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
)、《开放存取游击队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
)等数字媒体工人革命纲领等等,它们都是21世纪的鲁德运动。另一方面,技术政治史叙事也广泛存在于最普遍的日常条件中:资本主义商业竞争的条件下,技术对人的牵引,迫使部分传统媒体人离职,或转型为以互联网为生产资料的网络自媒体。与此同时,政治蜕化为权力控制,最直观的表现是互联网媒体平台的删帖现象(例如左翼言论也常常被暴力删除)。在宏观层面,媒介融合也可以被理解为新闻生产方式、劳动分工方式对数字技术——技术发展本身由资本带动——的妥协。
在这一意义上,如果依旧用新闻专业主义的道德放大镜考察传媒业困境,只能造成对困境根本原因的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条件下发生的新闻专业主义运动中,行业独立、经营自主、资本化恰恰成为其首要诉求,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甚至都不是根除中国商业新闻业困境的配方,而恰恰是症候本身。用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话说:“真正需要承当责任的,恰恰在社会组织和政策内部——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幻想通过‘技术'治愈西方社会病,就如同奢望天上掉馅饼”。
在此我们不妨畅想,只有从资本化的新闻业内部的生产关系和劳动方式等问题切入,重新阐述联合化生产、技术主权、管理主权、剩余资料分配等政治经济学问题,从结构层面对这一系列危机进行反思,才能真正理解传媒业困境。这是因为,新闻行业危机是以新自由主义危机为内核的表象;新自由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
五、小 结
如果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本要求在于通过变更产权关系的方式,改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固然起到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新时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在于物质文化生活,更在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个方面。这恰恰提醒了当代的中国新闻实践,在改进传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外,必须重新挖掘“公平、正义”平等政治的落实方式,重新思考党群与新闻事业的辩证关系,重新探讨新闻实践如何全面切入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
如果把新闻学作为参与社会历史进程的进步力量,必须重新思考新闻传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发展进程中,群众办报思想、人民通讯员制度、农村电影放映队到当代的打工春晚、新工人网络文学等都是文化领导权具体的体现。坚持新闻媒体的社会主义性质,不是在国家权力/市场的二元论框架中对国家制度的排除,而是广泛吸纳政策制定者、新闻工作者、城乡群众,共同参与到传播制度设计和新闻书写。因此,如果说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新闻实践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内卷化,是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结构内部的批判,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那么在中国语境中,新闻专业主义无法担当指导新闻实践的行动纲领,对新闻业的构想应该置于更为开放和建设性的历史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