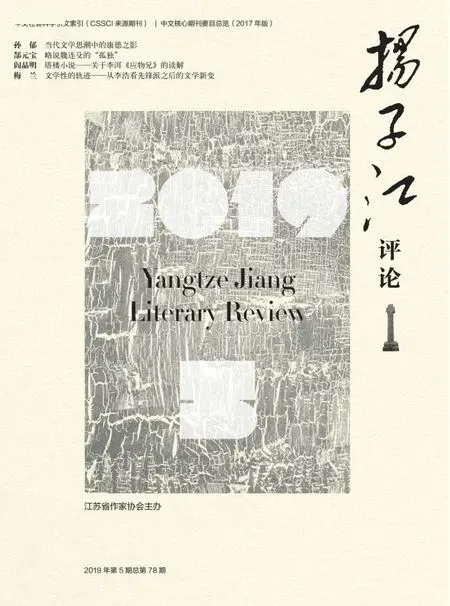远行与回归
——“局外人”的文学生成和普玄的写作
2019-11-13陈若谷
陈若谷
“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本雅明的阐释让这句德国民间俗谚走遍万水千山。远行人的故事这个简单的譬喻指代风景和际遇所代表的古典光晕。“如果说农夫和水手是过去时代讲故事的大师,那么工匠阶级就是讲故事的大学。在这里,浪迹天涯者从远方带回的域外传闻与本乡人最捻熟的掌故传闻融为一体。”
远行和故事有什么关系呢?距离将经验、技巧乃至观念的差异带入视野,是将其“横向平移”或者融会贯通,决定了远方是奇观还是切己的另一项经验。正如成长小说和公路电影里所体现的那种随着距离和时间的拉长而获得的见闻与收获,从西班牙的流浪汉小癞子开始到凯鲁亚克(《在路上》的主人公),再到美国80年代的“公路片”和同时期充满惊惶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远行一直都是启蒙所必经的关键事件。在历史的背景板下,这群远行人走过了从反叛到和解的成长弧线。
在现代社会,距离已随着提速的生活褪去了难度,故事的光晕剥落,逐渐漏出它消息、讯息、传闻的原料本色。因此,如今距离和远行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空间,而是时间,也就是对经验的获取和内化。现代小说在困境中还要坚持讲故事,就必须要走向幽深,放弃一部分奔跑和喘息,去传递难以沟通的经验、感受和思索。作为“离群索居的产物”,当前的小说总是浸泡在曲高和寡的焦虑之中。小说家、读者共同预设了一种完美的小说:既有纯文学的内面自我和深层意涵,在文学史和意象群里拥有自己的谱系,也要讲究现实感。
前警察阿乙、前国税局公务员张楚等人的写作都离不开生活的蓝本。不过,在后期他们都有了纯化的努力,仿佛职业生涯和笔下千秋的深刻关联已是前尘往事。将这一倾向推至极致的还有现役吊车司机鬼金,在半空幽闭空间急就的字眼让人闻不出金属的味道。当然,在类型化文学板块里,作家一般会保存本职工作对于写作的供给状态,如写悬疑推理的法学教授何家弘,以及蓬勃的科幻界与网文群。民营老板普玄也大致属于此类,只不过他的写作立场和建构意识一直相当鲜明。这是由于他下笔勾勒的文学世界几乎内在于自身社会关系的半径之内。他所写的,在经济生活潮头昂首而立,或者被拍打乃至被淹没的私人老板们,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个分身,那些和自己的生活融汇在一起的经验,就这么似虚构又非虚构地结合起来,这是外在于文学“圈子”的“局外人”写作。
一
二三十年代,最早诞生于周作人之口的“鸳鸯蝴蝶派”已经生成为涵盖深广的通俗文艺范畴,当时的武侠小说因为被树立在与新文学相对立的地位上遭受批判。郑振铎、瞿秋白、沈雁冰等都从国民性角度论述武侠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但张恨水看到了强取予夺背后的现实构成。之所以生出侠邪盗奸这些狂放的文学想象,其实正是因为社会失序带来的结构性断裂,甩出了大量无法被安顿的游民,“被迫着只有走上两条路”,在当代,同样存在大量被主流政治经济群体排斥的人,比如“盲流”、地下社会的打手和跟班、没有营生的深圳“三和大神”,他们都诞生于社会管理的松动时期,却无力获取真正的自由。
对于这个群体,文学和历史有自己的拣选标准。在近代武侠小说兴起之前,司马迁《史记》就以人物“传”的结构奠定了基本的书写面目,《水浒传》《三国演义》以更丰沛的篇幅塑造出性格各异的英雄、枭雄、游侠、谋士。对于他们,礼赞的笔法其实都有一个核心:强烈的道义感和大气的行事风格。他们所传递的教谕正是民间的生存文化。但久而久之,江湖故事被降格到了通俗文学阵营里。反之,纯文学几乎诞生不了这种气质,比如,即便在最可能充满热血理想的军事文学板块,董夏青青呈现的军旅故事,也不是智力、角力和争斗,而是平静低徊的生活流。粗野中有优雅的曹寇,虽然写了不少糙汉子的故事,但他同样欣赏《红楼梦》里摇曳其间的婀娜身影。因此,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后英雄时代,王占黑大方指认平民阶层的熟人社会是街道江湖,可见正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勇气。那么,爱看《水浒传》的作家普玄说自己爱那些短兵相接的对话和狭路相逢的命运,“多过瘾”。
普玄本是文坛外的作家,在社会熔炉中的冶炼,酿造了他鲜明的“江湖气”。如果说《水浒传》带出的是和朝廷分庭抗礼的民间江湖,那么《逃跑的老板》等小说讲述的是一群私人老板撑开了一个充斥着野蛮智慧的空间。
主人公胖子陈就经历了中国转型期,经济搞活,政府放权,造就了许多奇才、大哥、混混。在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从油漆工摇身变成地产商的闽老板、依靠扛包积累了第一桶金的知青,就连胖子陈自己,也是国企离职人员。胖子陈之所以逃跑,是因为他看见的社会是这样的:现代社会的法律限制的只是一般的良民,却无法遏制资本快速流动的欲望,黑社会的拳头比法律程序更快。在机会瞬息万变的资本场域、在龙蛇混杂的治外之地,法制精神显得过于文明和软弱。《安扣儿安扣》里的城中村村长喻克春,并非自幼顽劣,他曾经也想“我辈亦当弄潮头,他年英雄成传说”。但他是为了对抗不公的歧视,依靠青皮兄弟,最后成为黑白通吃的绝对领主。
因此,高考状元出身的小老板胖子陈只能投奔江湖大哥。恰是在这些社会缝隙里,暗流涌动的义气给予胖子陈充分的保护。他见识过那些想要东山再起的破产老板们有着怎样的狠劲和蛮力,知道原始积累里有多少极端和苟且。但同时,这群人也多半是重然诺、至情至性之人,虽出身卑微,却生气蓬勃。开矿的王老板记得他师傅的一句口诀,即不欺老弱病孕残。断臂妈咪更是女中豪杰,她的叛逆和自救,虽有客观原因,本质上还是因为她的江湖人格。
普玄在书写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这种气质和人对金钱与知识的占有无关,而主要是生龙活虎的气魄。在《虚弱的树叶》中成绩独占鳌头的张高举,逐渐被生活惯性所淹没,成为虚弱无聊的中年人。与之相反的,《逃跑的老板》里讨债的混混头目丁直眼,竟然是县文科状元。这二人很有趣地展示出了两种人生:文雅地衰弱和野蛮地生长。这群民间的强人共享着一种水浒式价值观,靠着原始的力量活着,迎头还击命运的挤眉弄眼。
当代文学画廊里“混混”的脉络是丰满的。王朔的“胡同串子”,徐则臣的“北漂”,朱文、曹寇的“混混”,总是传递出怀疑和虚无的情绪。自然,这些人不屑于接续传统的江湖,因为他们的不羁和颓废是一种充满现代性的反抗。但是普玄是在意的。他的江湖多遵循一个套路:守规矩懂谋略讲义气的胜出,优柔寡断两面三刀的落败。正是对勇力、蛮力的探索,对于江湖义气的尊重和敬意,才成就了普玄的小说,并使他的文学成为对《水浒传》文学传统的当代“演义”。
二
在现代小说进入物质社会后,文学空间也就进入了爆炸增长时期,因为知识和视野的分化及愈加复杂的状况让不同的领域几乎形成平行的扁平条块,通往不同的方向。普玄用一个命运跌宕起伏的老板,将他所能涉足的所有经验串起一个复杂的社会。在这里,读者可以粗略了解到,“一个企业改制需要几个环节?国有企业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什么效益大面积下滑?”这些随时能将人碰得头破血流的生活的钝物或锐角,读者可以撮其大致进行了解,但这样的书写依然是浮在表皮上的材料而已。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地域差异、阶层和行业之区隔,并非天堑一般的存在。我们已经有了无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这些知识可以合拢起关于世界的总体认知。至于小说,米兰·昆德拉说:“它们游离于这一历史之外,或者说:这是一些在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这样看来,小说的失败无需辩解。但另一方面,在一个知识可以付费获取、未来可被数据建构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所谓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的空气中,无法进入商业和效率转换圈层的人们,或者看穿资本主义逻辑的人们,得依靠什么来重建他们的共同体生活,用什么阐释自己的人生信条?
《逃跑的老板》《晒太阳的灰鼠》《安扣儿安扣》和《一片飘在空中的羽毛》有内在的一致性。一个自闭症孩子把理智的成年人从生死边缘拯救出来,因为一个无助生命的依赖竟然有着以弱胜强的力量。“朋友是人生最后一把米”,这是说,一个人讲情义守诚信,就永远会从困境中挣扎出来。《酒席上的颜色》用一个私生子的百日宴,写出了不同人群的价值观,有论者在更广阔的纬度上评说道:“传统与现代家庭价值观的对冲已经有了鲜血淋漓的展开,并呈现出一种巨大的悖论”。两位年过半百的老板决斗,只为了争抢地下小说《少女之心》的署名权,少年时期精神结构的象征物不能被轻易放弃,他们要证明,意气风发的个人史是历史浪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在他们和命运搏斗的表层背后,是在寻找一种正当性情感和稳固的人格信条——胖子陈的疲惫和幸福都是依托于这个东西。这其实是人生的悖论,一个人需要在行走中学会世事洞明,可伦理是他的千斤顶,以解救自己于困顿。游走在“行将崩溃的生活方式”,他的目的是逃避和隐匿。一边去行踪、去价值化,一边思考有所寄托的总体化人生。在这个路途中,他逐渐意识到命运表层背后的逻辑,如地产商门里虫的阴沉命运,是由于“一个人坐牢,家里会有三代人不安,会有三代人受影响。他已经送了二十多个人进去了,往少里说也有四五批。这几十个家庭在哭泣,上千号人在奔走求人,他的财富却在迅速增长”。在马酉和马午解不开打不断的手足情中,最重要的维系是他们二人皆执拗和善良,对诚信的诺守坚若磐石。
“活得都不是人”的人应为自己哀泣,无论多么卑微的人都必须挣扎着得到承认的尊严。胖子陈一直不能放弃的就是尊严和理想。“对,我们就是一群苍蝇,可我们就是要谈人生和梦想。”这种自强精神,其实就是人的总体精神。散漫和琐碎的日常书写,在90年代文学足够“及物”之后,已经变得无法自己生产意义了,这其实是纯文学写作最严重的触礁事故,并且一直无法重新远航。因此,尊严是被变形处理的,和湮灭常常联系在一起。
黑格尔从古希腊人那里见证过总体性的显现。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总体”属于最初原因和内在本质的“绝对精神”,是由国家、宗教、市民社会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简单统一体。统一的“总体性”就是人的精神活动主动走向对象世界。如果每一种知识、立场都只能解决能被公约的一部分现实,那么小说,仍然可以写那些命运主体的主动精神,即便他能提供的只有一个边角的差异。在当代,小说很难再像巴尔扎克以时代书记员的雄心壮志去描摹一个世界,但能够采取相对主义的方式,迂回地进行观察。
因此可以理解,翻开《逃跑的老板》第一章就是主人公在烈日下的意识流、榆树着火的童年回忆、以及病孩子的视角。这是现代文学经典文本的味道,倒映着纯文学影子:福克纳的多重视角、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意识流、巴赫金的多声部。现代性分化之后,小说家只能因陋就简,对于外部世界的真实性诉求让位于内里世界的可信性,让读者依靠“可见而不可知”的知解力形成同理心,这也就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完整的精神主体。“现实似乎是一种写实意义上的‘似真幻觉’,一种显而易见的秩序的反省与重构,一种有着多重‘褶皱’的神秘所在。”像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和《万物花开》,虽可解释为是泥土与植物的关系,但实际上二者的样貌依然诞生于作者对感性知觉的极度依赖,是世界“片面真理”的表征。
为了调和四分五裂的时代,黑格尔发明了伦理总体性,但是普玄也许是为了调和自己几乎四分五裂的生活,才回归到前现代的、朴素的伦理总体性之中。“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无论如何,我们都看到了他为命运找到的正当性结构。
三
写作者容易堕入形式链和意象库的圈套之中。也就是说,当你倚靠着文学史写作,很可能写出来的东西仅属于过去的文学。普玄的文字表述很有意思,看得出来他一直在建构自己的素朴与感伤的叙述语言。比如“有什么东西在滴落,似乎是烧茶器里的山泉水,似乎是天花板上滴落的水滴,这个声音来来回回,在一片乌茫茫的空气中,如沙漏如时间,如人的万千的念头,弥弥漫漫”。再比如他在小说《培养》里说:“一个不时兴蜡烛的城市是一个现实的城市。没有真正的痛苦。”氤氲水汽和微茫烛照,其实就是他在小说的容器和外壳上,选择的现代叙述和表达方式。他说,“要朝不变的事件内核层面前行,避开信息层面,朝精神层面过滤前行”。这是一种十分自觉的小说家意识,因此,他粗粝的生活和干练的理性经济人身份,并未影响他对于文学的认知,他仍然能够用自己的语感,为世界赋形。
写小说是一种劳作,但当它成为一份工作,作家的世界就变得平稳有序多了。我们应该欢迎这样一个风风火火的闯入者,他可能满身疲惫又充满坚定地说:我要用文学给血管补点盐水,或者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表示,我歇个脚喘口气就走。这是我们乐见的现象,因为它揭示了文学的价值,即在于:“生活的意义”的确是小说动作演绎的真正中枢,也正是文学的难度,正如以赛亚·伯林说:“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我们能潜入表层以下——这点小说家比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构成却是黏稠的特质:我们没有碰到石墙,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每一步都更加艰难,每一次前进的努力都夺去我们继续下去的愿望或能力。”这种难度对于普玄而言,可能很直接地就被心中的目标简化了,他认为,我们有必要把上一代人对抗苦难的经验传递下去。
几乎普玄所有的故事都是从真实的生活中汲取素材,相当一部分来自早年经历带来的精神创伤。也就是说,那个高中因早恋而终止学业的少年、那个身体有残疾的父亲和兄长都确有其人。最令人哑然默然的是,病孩子本是现代文学里一个特殊的设置,他的无知却充满神性的视角是最锐利的骨刺。事实上,病孩子正是作者生命中无法拔除的存在,紧紧地楔在他的心脏上。是孩子带给他的挣扎让他远离了文学,又最终促使他用文学去设计出这样的形象。
普玄不依靠阅读的知识世界写作,他不断往职业作家们无法涉足的远方行走,在具体的商人式的“行事”之外,他同样也是一个热情有力的调查者,最后凝结成调查结论《五十四种孤单》及小说《日落庄园》。反过来说,也许他静默气质不足,没有将每一部小说都百分百提纯,比如非虚构作品《疼痛吧手指》就比《逃跑的老板》有更均匀的坡度。大致说来,普玄的作品不是可以做永不厌倦的文本细读的幽闭结构,因为小说是一种生活,而不是技巧和观念的展演。村上春树有随笔《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详尽总结自己的职业化写作,但他也提到保险业人员卡夫卡和英国邮局高管安东尼·特罗洛普。对于多副面孔的作者而言,小说是一个留存自我的空间,只是不会完全和外在世界割裂。所谓圈内人、局外人,都不是立足于文学生产机制,而是提出来一些问题,比如有生活阅历的作者有没有可能被经验反噬?再如,为什么一些能够安心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他们的精神输出最后可能变成一种生产,而另一些偶拾笔墨的人,却能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进行真实的创造?
跑路老板胖子陈最终将自己身上“英雄”的潜能收编到亲缘责任和伦理精神里,重新陷入物质绝境,却并不等待垂怜,而是在给自己赋能。因为他的行为保持着对于道义的尊重和对世俗的敬意。知识分子的“离去-归来”模式,写的都是启蒙之虚妄,而老板的远行和回归,则讲述了一个坚定的故事。胖子陈和作者普玄本人,都不让自己遭受道德焦虑。不轻易下道德判断是当代人的美德,不敢勾画自己的道德理想则是当代人的虚弱。可能是在这个意义上,普玄敢于疏离开话语的圈子,因为他更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生活的纹理。虽然卢卡奇认定,小说这种向总体性的回归的努力必然失败,但是普玄还是坚强地提供了新的“发现”,尽管这个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溢出历史常识,但对那个最真切的主体却极为关键。在违反天道的日常生活中寻觅到常道,可能就是一个写作者最大的意义。
【注释】
①[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科夫》,见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6-97页。
②张恨水:《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新华日报》1945年7月1日。
③[捷克]米兰·昆德拉:《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版,第18-19页。
④汪雨萌:《我们需不需要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中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4期,第205页。
⑤徐刚:《小说如何切入现实:近期几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札记》,《南方文坛》2017年第1期,第36页。
⑥[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