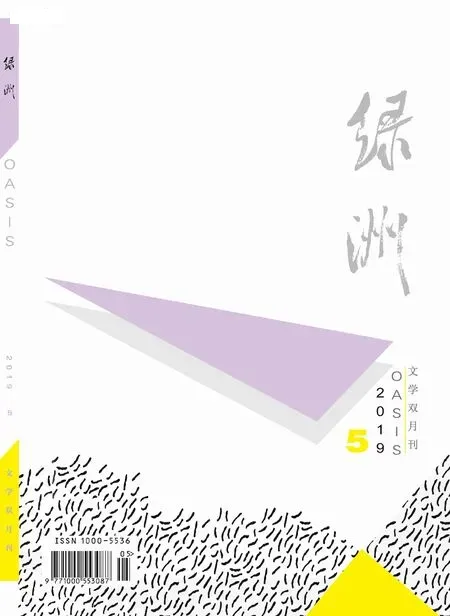云端下的毡房
2019-11-13黄水成
黄水成
一
“咚”的一声,遇上强对流了。忽上忽下,飞机像一叶小舟在浪尖上出没,这种失重感令人十分不舒服。浅睡中的我一下被颠醒过来。
人是脆弱的,特别是在飞机上,失去大地的支撑,总让人感到不踏实。而长途飞行能干什么呢,除了吃还是睡,睡,让累人的旅途显得短暂一些。然而,遇上强对流让人一下睡意全无,每个人的神经都揪得紧紧的。
我拉开舷窗望去,窗外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原来我们正在雪山上空掠过。年龄或者岁月总会隔开一些重要的东西,在悬浮颗粒物难以抵达的万米高空之上,天空蓝得有些不像话,那童年深秋才能望到的景象,原来都躲在云层之上。
云是山造的浪。飞机下方气流冲击着连绵的山脉,山顶上云朵汹涌澎湃,和积雪互相映衬,以致模糊了对远处山峦的辨识,那片纯白的世界到底是云还是雪。
这白色我并不陌生,我在江南见过多场积雪。但我惊异脚底的世界,这些起伏的山,每一座山头都被刀削斧劈一般。是什么力量,能把山打磨得如此棱角分明?在雪的映衬下,远远望去,锐利无比。我贴着舷窗向下张望,每座山峰都延伸出无数个山头,每座山脊都有分明的际线,看似无序,却纵横相连,就像一片溶解的叶子,只剩下筋骨,脉络清晰的映在眼底。
有人告诉我脚下是祁连山。突然倒吸一口冷气,东西横亘两千里、南北纵横八百里的祁连山脉,此时竟在脚下。不要说眼睛难以丈量,就连想象也难有一个隐约的轮廓,难怪气流在此都要翻上筋斗。西北这座最重要的分水岭,一生能看上几回,何况在它上空掠过,我把脸摁扁在舷窗上朝下方观看,此时,我看清脚下大片山脊,以及漫长的天际线,看到日落天边的寥廓,才真切感受到这个星球经度与纬度的辽阔。
白雪皑皑,放眼望去,看不见丁点绿色,脚下的每一座山头是那么的傲岸、苍凉,但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壮美,好像一旦站住了,就是一副傲然屹立的身骨,不要说常年风雪,就是刀削斧劈也大义凛然。除了白就是灰黑,它们,仿佛都是筋骨毕露的汉子雄赳赳,这里的山像极某个地方的人,可以不水灵,甚至粗糙,但个性鲜明,有棱有角,站住了,就是一个令人膜拜的姿势。这和南方的群山是多么的不同啊!南方的群山多婀娜多妩媚,但葱郁之下却少了一份大义凛然的风骨,祁连山,颠覆了我对山的认识。
二
飞机一直在颠簸,翼尖处抖得厉害,钢铁与气流持续对抗,人类前进的翅膀,在祁连山上空弯出一道美丽的弧度。
越过群山之巅,山峰如浪峰般徐徐退去。舷窗外的气流逐渐平息下来,飞机又恢复平稳的姿态。此时,前方是大片开阔的丘陵地貌,在积雪覆盖下,灰白相间,像大面积的皴染,把这片隆起的高原清晰而立体地呈现出来。
不一会儿,山峰和雪景几乎同时隐去,云层也不见了,阳光直直地倾泻下来。不再颠簸,很快又来了困意,正想拉上舷窗,突然,我看见了一片“海”。感觉有阵风,正掠过那粼粼的水面,斑纹状的浪一波连着一波,齐齐向山岸边涌去,海风吹拂,碧波浩渺,远处的雪山一下成了漫长的海岸。
怎么可能?西北哪来的海?
仔细辩认才看清,竟是一片沙漠。高原地貌带来太多的视觉冲击,群山腹地竟出现沙漠,让人一时不知所措。不禁想起之前飞机掠过陕北时所看到的沟壑纵横的高原地貌,那缺少绿色覆盖的土地,成了失守的国土,风雨日夜冲刷那裸露土层,纷纷脱落,辗转,漂泊,漂染了一条大河的颜色。那流浪的黄土,改变的何止是一条大河的方向,还有世代万千生灵的命运。
脚下这片沙漠,应该是气流长年冲刷加上雨雪剥蚀而留下的泥沙,在群山的包围中,气流经不住座座高山的阻拦,终于在开阔的群山腹地停下疲惫的脚步,被裹挟的泥沙也就此落下脚跟。缺少大河的帮助,它们冲积在一起,最终形成一片片小沙漠。
看到这片沙漠,让我对这片土地又多了一层敬意。大自然的残酷厮杀分秒不停地上演,苍凉或者风骨,这背后都有着沉重的分量。只有经过残酷的摔打,才能练就强劲的筋骨。电视画面见到的高原生物总是那么彪悍,不要说狼和雪豹,就连岩羊都强悍无比,那奋起的蹄,还有那高高举起的大角,能让峭壁上的雪花飞抖。
此时,我无法分辨狼和雪豹的踪迹,眼睛死死地盯着脚下这片沙漠走神。我见过沙漠,一望无际的沙海,就像一个凝固洋面,每个起伏的沙丘都是凝固的波浪。然而,只要下一阵强风袭来,它便再翻出新的面孔,沙漠总在不经意间更新自己,永不疲倦。
每一座沙漠都是一片远逝的海。恍惚间,觉得它就是一片海,起码,它曾经是海。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从海水换成了沙子,从蔚蓝变成金黄,从柔软变成了坚硬,这片土地上的生命需要重新面对,坚硬地面对,在另一个形态上重新演绎物竞天择的故事。想到这些,忽然觉得几千里的祁连山,更加伟岸苍然。
又一串激烈的颤抖,飞机落地了。带着一身凛凛寒气回到坚实的地面,远去的祁连山却像一块苍然砺石立在心头,神圣,高洁。
三
落地的翌日,鲁院同学李健便邀我们进山,到牧区转转,这是来新疆前他早就谋划好的事。出发前,他在电话中三言两语地说了几个地方,去牧区是其中一个重点。
这位新疆汉子话不多,但只要说出来他势在必行。
天灰蒙蒙的,好像要下雪的样子。一行八人,同学约好友帮忙,两部车来接我们进山。
同学说,新疆的文化精粹其实不在画册里,更不在舞台上,新疆的文化精粹流淌在一代代民间艺人血液里,在世袭的民俗中,在冬不拉的弹挑中,在牧人的鞭子上,在篝火旁的长袖里,新疆的故事在白花花的胡子上凝起霜花,代代相传。同学话中的新疆风情,在大家心里鼓起大大的风帆,一路伴随北风前行。
同学好友的家在米东区柏杨河哈萨克族牧区。车子一直朝乌鲁木齐的东边前进,历经几次寒流的洗劫,沿街的白杨和白蜡树一片金黄。越来越近,刚到郊区,便远远望见起伏的山峦,以及远处高耸的雪山。缺少林木的阻挡,眼前起伏的丘陵露出宽阔的脊背,这样一丘连着一丘,一直向着远方延绵起伏,这片隆起的高原再次展开它辽阔的画卷。
这辽阔的画卷上,却不见成群牛羊,只有零星的几只羊或马在山梁上自由地吃草。入冬了,草木枯黄而稀疏的山冈,似乎敞开了胸怀准备迎接严冬的风雪,这里很快将变成一片白色世界,它,绝不是越冬的理想场地。成群的牛羊应该在更遥远的大山深处,那茂密的林区才应该是它们越冬的牧场。
沿着柏杨河山谷前行,翻过几道山梁,很快到了同学朋友的哈萨克牧区定居点的家。一下车,热情的女主人便迫不及待地招呼大家朝院子后面的山上跑。站在山梁上,她一指远处的雪山说,瞧,那便是天山东段著名的博格达峰,天山天池也在那边,女主人说我们来得不是时候,且天色太晚,错过了新疆最美的季节,也错过了途中忽必烈的敖包和丘处机的喇嘛庙,还错过了三千多年前的塞人岩画……
女主人的指尖瞬间流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顺着她指尖徐徐展开的,有空间的纬度还有时间的长度,她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细究起来,新疆这广阔的土地,我几辈子也看不完,而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匆忙的过客,能站在这片热土上看一眼,再吹一阵山风,便什么都值了。
站在这片开阔的山梁上眺望四周,我再次想到了海,只有海的辽阔才可比拟眼前这片无际的丘陵。尽管世界上还有很多无边的大平原,但那缺少起伏的平面,反而让人没有纵深感,它不能完美地把这种大而远的空间立体地呈现出来。
我们太缺少自然的抚摸了,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让人终日陷在犬牙交错的闹市中,神经绷得紧紧的,目光一刻也清闲不下来。每次在电脑前待到眼花时,总会对着旁边那盆绿萝看上一会,让眼睛重新聚焦。眼前这无边的风景于我是一种奢侈,同伴们都回去了,我却留在原地贪婪地张望,眼睛终于没有任何阻挡了,尽可纵目驰骋,让目光尽情舒张,终日疲惫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
此时,真有一股策马扬鞭的冲动,顺着这一道道山梁一直往前冲去,冲向时光深处那无边无际的草场,然后坐在空旷的山梁上,当一个安然自在的牧人,这一刻,恍若一个被尘世遗忘的自然人。
四
暮色渐浓,野风生硬扑到脸上感到有些疼。我有些不舍地朝山下走去,远远便闻到一股羊肉的香味。其实刚来时便闻到了,只是没在意。这时我看到架在院子外的那口大锅,炉里还煨着柴火,锅里不断地冒着热气。
虽没见到毡房,但眼前成片房子中,清一色的白,每个院落都保留一间圆形、穹顶毡房风格的房子,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在这片聚居的营地,我想象着它过去的样子。
一进屋,女主人领着大家在穿羊肉串。同学说,今天主人家宰杀了一只羊,用水煮全羊招待大家,男主人和孩子已经忙乎一整天了。羊可是大牲畜,更是草原人家赖以生存的命根。全羊,历来是牧民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我们何德何能受此盛情,竟以最高礼仪招待我们这帮初来乍到的南方人,顿觉得有些愧受。女主人不断地和我们拉家常,仿佛早已认识,如阔别重逢的亲人。她的每一句话都饱含温度,让我们毫无生疏之感。或许在新疆人的观念中,朋友的朋友依然是朋友,他们,压根没有我们南方人那些弯弯绕,他们即便对登门投宿的人,主人都会拿出最好的食品招待,我们开始领教了新疆人的热情与胸怀。
我们所在的是哈萨克族定居点,主人以哈萨克族风情接待我们,她选择那间“毡房”招待晚宴。这“毡房”其实是主人的卧室,一张暖炕占去房间的三分之二,再摆上一张桌,显得紧凑而温暖。土豆丝、卤蛋、大盘鸡、羊肉串陆续登场,大盆大盆的煮全羊紧跟着一一端上来,鲜香四溢,熏得一桌的人不自在。经常对电视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情景流口水,试想,那人生该有多豪迈,哪敢想有朝一日,我也在这样的情景里大快朵颐。
我仔细看了盘中的大餐,羊头、肠、肝、肺、肚……都摆在桌面,地地道道的一只全羊。主人交给同学一把小刀,同学很谨慎地接过刀子,瞬间一脸庄严地对着羊头横竖划了几刀,并象征性地从羊头剔下几块肉分给大家,晚餐就正式开始了。
南方人讲究清淡,怕膻腥。最让大家欣喜的是,煮了一天的羊肉非常鲜滑、爽口,竟一点也不腥腻。主人告诉大家,什么诀窍都没有,什么料都没加,就是纯水煮,最后放点盐,纯正的哈萨克族的手抓羊肉。在家炖羊肉时,除了姜、葱外还要加上许多佐料来除膻,这样做其实早已失去羊肉的鲜味了。前些年恰好从内蒙回来时参加一个派对,主人用烤全羊热情招待大家,皮脆肉嫩,看得出厨师没少费功夫。但拿起羊肉时,却闻到一股烟熏的焦味,和内蒙的全羊完全两样,才知道闽南人做不出地道的草原风味。不是厨艺不精到,而是每个地方的物产都有独特印记,那是泥土的记忆,永远不被篡改。
闽南话是幸存下来的古汉语方言之一,它保留了上古的古音古韵。有意思的是,闽南话里,“人”字发音正好和当下普通话的“狼”字同音。如今,我们这帮闽南人到了草原上,眼前羊肉鲜美,大家左右开弓,腮帮鼓鼓的,大口大口地吞咽,一个个真像饿极了的“狼”。我看同学和女主人也和大家一块吃羊肉,却吃得一脸虔诚,不分肥瘦,也不管是肝、肠、肚、肺,只要是盘中的食物,他们都吃得津津有味,他们把每一块骨头上的肉都剔得丁点不剩,然后把骨头齐整地码在跟前。主人说,吃过的全羊,把全部的骨头拼起来,就该是一只羊的骸骨,只有这样才算是吃尽了。
在这里,一枝一叶都历经岁月,生命充满传奇和艰辛。其实,大地上的任何一种食物都得到尊重。看着眼前成堆的并未剔尽的骨头,顿觉羞愧,相比他们,我们就是一帮无知而粗俗的食客,终日挑肥拣瘦,缺少礼仪不说,我们对食物缺少虔诚,更谈不上对这土地上所有生灵的一份尊重。“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其实传统文化中不乏这种自律,这缺失的背后,我看见巨大的信仰空白。由饥而饱,由贫到富,从面黄饥瘦到油头肥耳,我们似乎忘记了过去的饥饿,我们不再珍视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我们背叛了土地,我们只是食客。
那天,同学和主人原本还约好一对说唱的民间艺人,谁知他们刚好出远门了。主人和一位叫安子的好友临时客串,酒酣肉饱之际,她俩为大家跳起哈萨克族的舞蹈,舞姿曼妙,迎面如吹来一股草原之风。
五
临走前,热情的女主人再次挽留大家小坐片刻。这时我才注意到主人的家居装饰特别简朴,红柜、树根、花束、干麦,简单点缀的背后,透出主人崇尚自然的内在文化气息。我对石头有着天然的感情,最引我注意的是书架上各色石头。
女主人说,新疆是石头的天堂,石头太多了,和田玉、戈壁石、观赏石……只要到了野外,俯拾皆是。架子上的石头就是她从各地拾来的宝贝,其中几颗是从她家院子旁那条柏杨河淘来的石头。
临走前,女主人执意要赠我一颗石头,着实吓我一跳。每颗石头都历经地质年代的漫长孕育,又历经千万年风霜雨雪盘剥,它们是宇宙的精灵,是修行的佛。对于爱石之人,每颗石头都是隔世的一段未尽情缘,一个个惜石如命。她不仅要赠我,还要赠同伴们每人一颗石头,这豪举再次让我们震惊,大家不敢夺人所爱,都不敢答应。
世间绝无雷同的两粒沙子,何况是石头。我仔细打量书架上的石头,形态各异,姿态万千。我从架子上众多石头中,一眼看中那颗小青石。它其实并不显眼,吸引我的是那两条很特别的白色纹路,一上一下,如盘龙出海,如彩练当空,如白云出岫,我说不出它具体像什么,拿在手中直愣愣朝它发呆。女主人走过来了,她说,看,它们多像长江和黄河。仔细端详,还真像两条大河图形,但它似乎更像什么,一时觉得眼熟却又说不出来。
我既不藏石,更不玩石,虽拾过几块石头,但都是随手从路边捡来的无心之作,只是觉得有缘,遇上了就带回来,绝无把玩之意。眼前这颗小青石,刚照面却被它一下黏住了,难以说清其中滋味。女主人说它是柏杨河里拾回来的石头,只要我看中,她坚持要赠我当个念想,突然有一种夺宝的感觉。她却说,不是夺,是换一个主人在陪伴它。
世上每颗石头都具有灵性。回到宾馆,我拿出小青石细细把玩,越看越觉得眼熟,似曾相识却一时难以记起,它像某个熟悉景象印在脑海中一般。我爱不释手地把玩着,那两道白色纹路像一道灵光,把我引入梦中,千里祁连山一片清澈,几朵祥云盘绕峰间,晚霞中,一片苍茫。梦醒了,我才明白,这块小青石上的纹路多像祁连山上的云彩,它和我梦中的景致完全一样,如今却被凝固在这块石头上,心中一阵欣喜。
好石头都是养出来的,越养越温润,越盘越剔透。我把它揣在口袋里,一有空闲就把玩它。回来后,我把它放在每天工作的电脑前,在劳累的间隙不断地盘摩它,看到它就想到那里的山水,那里的人。我带走的何止是朋友的情谊,那是她家乡柏杨河的古老结晶,还有祁连山上的神秘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