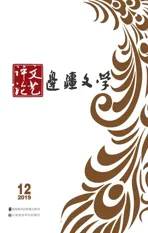以青苍的文字,走向汗青竹简的郁郁
——从耿立的历史散文说起
2019-11-12刘艳
刘艳
耿立,原名石耿立,山东鄄城人,是国内有影响的知名散文家,学院派散文家、作家。出版理论著作《新艺术散文概论》《新艺术散文美学论》和散文集《遮蔽与记忆》《藏在草间》等10余本。主编年度散文随笔选本,多次荣获国内知名文学大奖;散文作品屡登中国散文学会等国内权威散文学会和知名刊物评选的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和“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广州文艺》的张鸿在推荐阅读耿立写父亲的散文《匍匐在土》时曾说,“起初,我一看是耿立的稿子,就先放在一边备用,因为我以往编发过他的稿子,比较成熟,是上乘之作。”(2016)张鸿又述说了改这篇散文的辛苦,而且体会到耿立是因为经历着情感和心灵的折磨写父亲——父亲当年所遭受的种种不公的场景、屈辱的场景,让他在下笔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写父亲,写黄土,让耿立难以掩抑心中郁结与激愤,以致影响了他对笔力素来的掌控自如。在他,“青苍是颜色的标示,也是一种借代。”他说历史是青色的,而土地是苍黄的。他这样评价自己的散文创作:“自走向文坛,我笔下的文字向来是写史和乡土两线并行,从黄壤平原深处走出,走向历史的邃深处,从颜色的苍黄走向的是汗青竹简的郁郁。”我以为,耿立的散文写作,扎实稳健,但他对当代散文最大的贡献和意义在于,他在历史散文创作实践方面的积累和造诣,可谓是当代散文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对于重构当代散文的写作伦理,是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的,他以独具耿氏(石氏)特色的历史散文,和呼唤散文的精神含量与精神高度的散文观,而终将能够“以青苍的文字,走向汗青竹简的郁郁”的历史散文而名世。
一、从黄壤平原走向历史的邃深处
耿立以颜色来标示自己的写作,认为苍黄是写乡土、故乡的人与事,散文集《消失的乡村》《向泥土敬礼》等所收散文莫不如是。耿立在散文中说,“无论怎样,你也改变不了乡村是泥土做的”,而在耿立心中那个曾屡屡承受屈辱但是有着让他入骨看重的父亲,是耿立心中矗立和屹立不倒的一座山。耿立无数次写到父亲对于土地的顶礼和深爱:“对于泥土,我曾看到父亲用手扒开泥土,看泥土的成色,有时他竟然把泥土放在嘴里,看是否咸淡。木镇的泥土不能说每一寸都有父亲的脚印,但每一寸土地都有他注视的目光。对泥土对节气,父亲一直敬畏,即使他老年病了。有一次回家看望父亲,在家里没有见到他,我到田野里,看到父亲用抓钩敲砸土坷垃,一下一下那么专注,有时砸不开,他就蹲下,用手,那土块攥在掌心,一下一下揉搓。太阳就在头顶,泥土被晒得白花花。”(《木镇的事物》)
木镇的一切都在泥土上,“我读过父亲的手,虽然如树皮一样皱褶苍老,有点变形,手上的青筋如蚯蚓,但他在泥土里多年相互扶持,有着泥土的温暖,我一握的时候,就像庄稼的汁液传到我的脉管和血管,这是泥土的温度。父亲的手粗糙吗?但这样的手在泥土里绝对灵活。他锄地时,绝对不伤害庄稼,而对草,也是尽量照顾,只要能和庄稼和谐相处,父亲是不会对草痛下杀手的。父亲的手上长了一双灵眼,只要灵眼一觑,草留几棵,庄稼留几棵,那是一定可巧的。”“父亲在庄稼地腾出来茬以后,就想着为泥土养身子了。到了秋收罢了,父亲还会到田地里去,他像逡巡的士兵,把泥土里的瓦块砖头剔除,怕这些骨头硌着睡眠的泥土,怕在地里漫游的小动物们闪了腰,怕来年开春撞坏了犁耙。”即使是在冬季,父亲也离不开田野、土地和农具,“冬季了还去锄地?母亲说这是为了保墒,父亲到地里翻土敲打土坷垃。”(《向泥土敬礼》)耿立将这形容为父亲为土地做按摩,为贡献了一茬一茬庄稼的土地,“父亲心里最清楚,土地糊弄不得”。“从地里回来的父亲脸上有一块泥巴,母亲想用手抠下,接着就想卷起衣襟擦,父亲招呼了一下说不用了”。耿立由此还引诗人雅姆的话说:“如果脸上有泥的人从对面走来,要脱帽致敬先让他们过去。”
耿立是毫不讳言自己对泥土、黄壤的深深的挚爱和尊重与敬仰的,他在自己散文集《青苍》(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的序言中,明确说:“我知道,在现代,尘土是世间最卑微的东西,但无数尘土的集合成了最本真的基础和基数,汗青的崇高只能建立在苍黄的尘土上,才是价值的所在。”耿立自言他自走向文坛,他笔下的文字向来是写史和乡土两线并行,从黄壤平原深处走出,走向历史的邃深处,从颜色的苍黄走向的是汗青竹简的郁郁。耿立的散文以其情真意切,和能够重建当代散文一直罹患和缺失的精神向度见长并取胜,让人读了常常有激动心怀、感天喟地之感。读者会跟散文和耿立一起心潮澎湃,似乎成了阅读耿立散文的标配和必然的阅读感受。究其实,这样的精神力量和精神向度,我想应该是来自耿立的童年、乡土的熏染,和他对黄壤毕生都将所怀的、发自内心的一种钦敬。历史散文,不可避免要写到山川巨澜和历史沧桑,能有从《史记》那里得来的浩然之气,恐怕离不开他“自己从乡村走出,父母的骨殖还在黄壤深处”的乡土,所赋予他的血脉和骨气。
在《匍匐在土》里,耿立写尽了他对父亲的追怀与记缅,几乎是以“匍匐在土”的、近乎滴滴血泪的感情,来记录下了父亲的一点一滴和父亲那一代人的生存状态。耿立在散文里,不止一次地写到了那同一幅让人心里惨痛的场景:“在我出生的时候,偏巧,我们生产队里一个在大队当干部的人的父亲死了,此人拿着生产队仓房的玉米、麦子、大豆成麻袋地送去,让他们待客。而我出生时,家徒四壁,盛米面的瓮与陶土的缸里无有粒米,于是就想着借队里一点谷子,脱下皮子弄点小米,为我的母亲温补一下身子。但生活的坚硬和冷漠拒绝了父亲,这个年方四十的男人,无力抚养妻子无力抚养刚出生的儿子。那是雨天,深秋的雨天,早已没有了雷声,但他喉咙里像是有轰鸣的雷声从肺腑爆出,人们看到了这雷带来的水,他的脸颊汹涌的泪水。他不愿再在这个世道无尊严地活着,他像要倒净这如苦胆般的生活的汁液一般,冲向机井,被人在井口强行救下了。”(《匍匐在土》)尽管不是第一次读耿立追忆和描写的这个场景,还是会有锐痛加钝痛在我的心里蔓延开来。能够以不同的笔触,在数篇散文里回溯这个场景,可见此情此景在耿立心里的分量。杨绛曾说:当你身处卑微,才有机缘看到世态真相!人生在世,即便出身不卑微,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一生平顺,有起就有伏、就有跌落,即便你自己的人品和心性足够好,也有可能被脏污的人性和人心伤害,在人祸中跌入深渊,备感人间冷暖……是故,人即便出身不卑微,也往往能在一种后天的卑微处境和时段,有机会看到世态真相和人心人性最真实乃至丑陋的一面。
耿立散文中的这个让人揪心的场景,不仅让他本人刻骨铭心,令读者也会为之动容乃至揪心。被残酷的人性和生活剥夺了一个男人尊严的父亲,当年为了妻,为了儿,跪了下去,仍然讨不到能活妻儿的米,这个男人是不是卑微到了极点?被压迫和凌辱到了极点?但是,父亲其实一点也不卑微,卑微和卑鄙的是那个大队干部,那些可以给生产队干部死了的父亲而大办丧事、大吃大喝、动用公共粮食的人!被逼到最卑微处境的父亲身上,却有着一个男人和父亲最坚忍和伟岸的一面,为了妻儿能够舍下膝下的黄金,绝望中甚至要投井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这样的出身、这样的成长环境,耿立未必能够拥有他在自己的历史散文中所凸显出来的精神力量。耿立的历史散文,完全没有文化大散文常常罹患的弊病,他拥有他自己一直所追求的精神高度和力量,像写杨靖宇将军之死(《缅想的灵地》),写秋瑾慷慨就义(《秋瑾:襟抱谁识?》),写出与妻两情相悦、给予《与妻书》而慨然就义的林觉民(《绝调》),还原武训当年的行乞兴办义学(《仅见的灵魂》),还有《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不忍逼视的细节》《悲哉,上将军》《雪与路》《梦醒者的悲剧》,等等。如果说余秋雨的作品里,贯穿着一种严肃的理性精神与深刻的文化批判的意念,他更多呈示给人“精神的苦旅”;耿立的散文较之,更多人性、人情的体贴和关照,耿立在找回当代散文缺失和一度丢掉的智性与精神含量的同时,他的散文总是以一种胸怀的磅礴和真切深挚的感情力量,深深地感染人——也就是他本人所说的“精神的在场”。精神的在场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耿立选择了最为人与文融为一体的方式:从中,你可以看到一个追求人文精神含量的耿立,看到一个深深坚守道德理想和寻求精神超越的耿立,看到一个将他的痛切和人生体悟与写作对象水乳般交融的耿立,看到一个对英雄满怀景仰、对小人极端鄙夷、将怜惜美好痛恨丑恶与伪善浑然于己心的耿立——看到耿立的铮铮铁骨和屹立于世的雄心壮志里,仍然包裹着一颗善感和富有情义的心怀……耿立的历史散文,在提倡精神的在场和重建当代散文的精神向度方面,是独树一帜和具有示范意义的。
二、重建当代散文的精神向度
十几年前,就有研究者在对“文化大散文”进行反思,言及要“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当代散文在“文化大散文”这一写作潮流的影响下,日益青睐历史重述与文化感慨,从而渐渐遗忘了“记述”的传统。散文正在成为“纸上的文学”,正在丧失和生活现场、大地细节、故土记忆之间的基本联系。此研究者(2007)认为:“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散文的主流是文化大散文。这种散文,大量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力图通过对旧文化、旧人物的缅怀和追思,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应该说,这种散文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改变了当代散文的一些面貌,尤其是在扩展写作视野、建构文化维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文化大散文有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那就是在写作者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往往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以致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像空间就显得非常狭窄,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怎么说呢?可能是为了突出“记述的”“艺术性的”文字写成的“美文”,研究者极言文化大散文如何已经大行其道,如何已经罹患失去感官、记忆、在场感和无法使找 “心”、寻“命”并使灵魂扎根的散文传统依然存续的弊病,等等。
但是,在我的感觉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并非是文化大散文成了中国散文的主流,而是各种琐细、平面和心灵鸡汤式的文字,过多充斥了我们的耳目。耿立本人对散文理论也深有钻研,他将之概括为当代散文的琐细化、平面化和犬儒乡愿化等。当代散文的琐细化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周作人在他那篇著名的《美文》中,称这种“记述的”、“艺术性的”文字为“美文”,并说“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周作人的散文观对后世包括当代影响深远。影响的结果就是当代散文喜欢专注和流连于琐细的物事,饮茶闲聊,衣饰吃食,细小物事哪怕人、物、事纤微如毫发,也值得写作者一笔一划甚至大段大段地去品评和玩赏。一棵柳树,乡间的散步和萤火虫,自己深以为有趣而别人读了索然寡味的“童年趣事”,等等,都可以成为抒怀的对象。散文作者貌似很用心地在抒发自己的情怀,细细读来,作者的感受和情怀其实都是有点自作多情,既不细腻,也无所长,更不要说有什么感人之处了。当代散文的平面化写作,也与此相关,更与现在的媒体、自媒体都发达有关,任何人都可以写批评文字,换言之,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手机上撰写文字,文学批评渐渐被媒介批评湮没,散文也向新的媒体随感式文字、媒介散文让渡。写作散文式的文字,绝真率性、自由无碍的散文传统遭遇了最为不堪的当代嬗变——信笔而来,信马由缰。快餐文化和缺乏精神向度,成了很多散文共同罹患的病疾。当代散文的确是把个人化趣味和对于闲适的追求,做到了极致。
历史散文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在扩展写作视野、建构文化维度上,很容易罹患文化大散文常会具有的弊病。“那就是在写作者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往往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以致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像空间就显得非常狭窄,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与散文写作者缺乏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品性和精神的在场有关。耿立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讲述那些灵魂高贵的典故: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及王后上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刽子手的脚,马上温和礼貌地对刽子手说:“对不起,先生,我踩了您的脚。”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路易十六留下的则是如此坦然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傅雷夫妇半夜上吊,还在凳子下面垫上棉被,免得倒下去时惊扰邻居,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时,还处处为他人着想。伟大作家托尔斯泰为世袭贵族,独自离开辽阔的庄园消失在野外,临终把家产分给穷人,离家出走,病死在一个小火车站。甚至他的墓地也特别寒酸,就在一个树林里,没有坟头和墓碑,只有野花野草。他的不朽作品也穿越时空留给了人类。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英国戴安娜王妃一直到最后都在从事慈善事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灵魂的高贵。
耿立清晰表达了他对于散文应该具有人文精神含量、具有人文精神的广度与深度的观点:而判断艺术的最终标准是具体作者、作品的人文精神含量。也就是一个成品的“含金量”。作者的人文精神含量指的是作者的艺术高度,成就大小;作品的人文精神含量指的是作品的“器量”,也就是作品所表达出的人文精神的广度与深度。缺少特色,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缺少“含金量”,作品就难以“回味”,也就不会引起人们持久的兴趣。所以说:判断艺术的基本标准是特色;最终标准是人文精神含量。《缅想的灵地》将杨靖宇将军的殉国真实感人地还原出来,场景的描写不可谓不惊天地泣鬼神。将军罹难前的场景是这样的:“猖狂末日的攻击开始了,四面都是敌人的子弹,如蝗虫翔舞。杨靖宇又打倒数名冲在前头的敌人,但敌人怨鬼毒蛇般纠缠他,蛛网一样的人墙围拢了。接着他左腕中弹,手枪随之落地,但将军的右手还在,他仍拼以力气应战。最后人们都感到了将军血液里发出的金属撞击时的那种鸣响,将军轰然倒下!”杨靖宇将军牺牲了,生前他令日军胆战心惊,死后他也为侵略军所敬畏。岸谷隆一郎为杨将军棺椁盛殓,于将军殉难处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并以杨靖宇将军为例训诫部属,同时亲自主祭下葬。耿立禁不住发出灵魂一问:“我们民族的血性,我们民族的尊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突然走失了?”“杨靖宇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人格力量仍然令敌人胆战心惊。日本人把杨靖宇将军放到了一个历史悲剧的祭坛上。他们不只是以胜利者傲慢者的姿态对待将军,他们也是以自己民族热血和强悍的生命作为牲醴,来祭奠一衣带水的所谓的支那人那生生不息、傲然而立的民族精神和品性吧。”
《秋瑾:襟抱谁识?》中,耿立也是满腔对良知和正义的倾诉和呼唤。“秋瑾死后,荣辱的变换,使我们不能不怀疑某些所谓的正义的良知,怀疑秋瑾何辜,被折腾再三,所谓的死者为大的民间的高义,却被当做了腐朽,烈士的血和历史一样在某些人的眼里再没有了敬畏,历史成了戏弄和戏法,烈士的血渐渐凝固成了虚无。”耿立为秋瑾死后仍然尸骨多次受辱——多次被掘出,被辗转,而郁痛于心。也为友人在风雪茫茫中为秋瑾的身后奔波,为“风雪渡江,一种道义的精神在流贯”而慨然嗟叹!此篇结尾:“辛亥百年后的元日晚上,和友人从杭州乘火车穿行绍兴。那时的绍兴早已是灯火隐隐,看不见秋瑾被砍头的古轩亭口,也看不到鲁迅的旧园。火车的铿锵越过了钱塘,现在也仍是冬日啊,我感到一种风雪渡江的苍茫。”
耿立的历史散文,一直在要求和追求这样的人文精神含量。他明确表达了他追求散文的尊严和散文的精神品性的散文观:“散文的尊严,来自她的精神的品性,这是散文在当下创作最应该关注的部位。做精神的探险者,精神的独立者,在精神上不作伪,诚实,把看到的、体验的、内心的最本真的拿出来,做生命的见证,让灵魂变得柔软,这是散文区别小说和诗歌的关键。散文凭借什么?就是一种精神的高度,和民族一同思考,受难,诚实记录,不撒谎——不对自己的心灵撒谎,不对历史撒谎。”他并不欣赏“伤痕文学”作家在作品中除了喋喋不休地诉苦外,就是将苦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外在的环境。他将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视为至境和散文写作的内在追求和精神品相——能够揭示着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体现了对不可摧毁的人之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企图之批判。《仅见的灵魂》当中,将黄壤平原里冒出来的武训,武训在亲戚——他的姨父李举人家里做了三年长工,受尽残害和被剥削压榨,破庙悟道后,武训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乞丐:“武训如蚂蚁在尘土里爬着,尘土里有他背负重负的印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训病逝于义塾,凡是经过的村庄,大家都拿出赏钱来送武训一程。“沿途六十里各村民众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这就是最后的武训。”
写得平和随意,自由不拘,又让人回味无穷的散文,固然是读者需要的一种散文体式,但是一味追求“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散文,一味追求闲适和涩味、“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的周作人散文,是不是涵盖了散文的全部面向呢?就像耿立自己说的:“通过索尔仁尼琴,我们知道散文在审美之上还应有一个维度,不能在现实的苦境中闭眼一味地玩味生活,或者苦心孤诣地用文字美化生活,游戏心态、趣味把玩、所谓的净化与距离、无功利的审美自适,这不应是散文家所津津乐道的一切。”在历史散文中,寻出被遮蔽的、去伪存真,重塑当代人和散文的精神品质,是当代散文亟需重建的精神向度。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郁达夫等现代作家所具有的文人情怀:事情是由沈从文而起的。1922年,20岁的沈从文,带着几块钱从湘西凤凰走出,只身来到北京。据说有人问他:你来北京干什么?沈从文答:我来找点理想,读点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样的沈从文,不得不说是真正的文学青年了。但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原来是听闻可以“半工半读”的北京的大学,实际上根本不接收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但这个倔强的年轻人不怕困难:“只要肯勤学,总有办法的。”他想尽办法旁听北大的课程,住在便宜狭窄的公寓中节衣缩食。他给自己的住处起名“窄而霉斋”。有个轶闻,不知确否,沈从文甚至有一天决定去街上讨饭。没想到一个老乞丐对他说:“这个街道归我管,你想讨饭可不行”。走投无路,饥寒交迫之中,沈从文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当时的名人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当时的郁达夫27岁,刚从日本毕业回国,他所属的文学阵营“创造社”锋芒初露,而自己也是一名大学教员。谁能想到,郁达夫能够走进沈从文那间窄窄的房间,瞧见整个家里炉子、御寒的棉衣全无,沈从文却还在写作,竟一时语塞。而后,郁达夫与沈从文聊了整整一个上午,直到中午,他请沈从文吃了一块七毛钱的饭,一张五元票子剩下三块多。他将余钱全给了沈从文,连同自己脖子上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后来过了许多年,沈从文对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也是在郁达夫的介绍下,不久后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见完沈从文那天,郁达夫顶着风沙去给同学们上了课,回到自己的住处,“我今天上你那公寓里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想趁着大家已经睡寂了的几点钟工夫,把我要说的话,写一点在纸上。”——写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后注明此文写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二时),发表于次日《晨报副刊》,言辞激烈,所给的建议也是太不同寻常:“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制造炸弹去吧!……”“你的没有能力做土匪,没有能力拉洋车……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无论什么人的无论什么东西,只教你偷得着,尽管偷吧!”——这还真是真率的郁达夫,方才能够具有的郁达夫式的、义愤填膺的对社会的“控诉状”。沈从文当然没法按此行事,但他还是坚持写下去了,次年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遥夜》。而这篇文章被北大的哲学教授林宰平看到,予以盛赞甚至把沈从文带进新月社诵诗会,使他有机会认识了徐志摩。在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荐下,沈从文的才华渐渐被发现——徐志摩对沈从文也颇为欣赏和多有提携。我之所以在文章结尾用了独句段:“这样的文人情怀,是属于五四的。”意指今天我们知识者文人情怀的失落。由此也很可以理解令耿立郁郁于心、难以排解的当代散文失却精神品相和精神往往不在场的原因所在了。作家如果文人情怀都无,精神焉能在场?
三、文体探索:重申当代历史散文的写作伦理
我们知道在中国,散文的传统非常源远流长,它成为一种文学上的自觉和事实,其实应该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但是散文的名称是形成于宋代,最早有记载散文概念的典籍是在南宋时期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在此之前散文不叫散文,叫“文”,其实也就是散文。散文与诗歌不同,诗歌依赖于音律,但是散文在因字而生的魅力方面是不输于诗的,它具有一种音韵之美,炼字炼意与意象意蕴等方面,皆不输于诗。我从耿立的散文当中,深刻感受到了耿立在遣词写句方面的语言天赋和古典文学以及文化的素养。细细揣摩其文字,常常有“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珠则太赤”之感。“秋瑾死后三日,李钟岳即被撤职。钟岳志在救人,但力有不逮,对此心怀耿耿,终至衷怀纠结、缠绕盘桓,遂乘家人不备之际,自缢于旁舍,享年五十三岁。”(《秋瑾:襟抱谁识?》)自古散文炼字炼句不输于诗,但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语言的粗鄙化(李洁非曾经专门在会议发言中着重谈过这个问题及其是如何生成的)。当代散文写作,语言文字是门槛,但真正迈过这个门槛的人,不多。耿立能够写好历史散文,先就在于他极好的语言文字功底。
散文的英文文学术语是“prose”,但是自现代以来,中国现代、当代的散文,更取自“Essay”——民国间,名作家章克标等人编译有《开明文学辞典》,里面“散文”不是作为 Prose,而是作为 Essay 出现。“Essay 在西方,确系文艺复兴、启蒙主义的产物,随思想者们以所思启发民智、普及人文价值观的需要而生,故自蒙田、培根等辈之手大放硕采。Essay 这种近代属性,对中国新散文的精神特质的影响与改造最深。”现代以来,公安派、竟陵派越来越被作为散文的正统,像把散文规范为抒情的和叙事的美文,这是周作人在一篇名为《美文》的文章里提倡的,对后世更是影响深远。晚明小品对后世的影响有多深呢?甚至影响了现代以来的小说创作,让中国的现代小说从发轫之初,就不似西方小说是叙事和史诗的传统,中国现代、当代的小说里面,蜿蜒和蓬勃着很强和具有充沛生命力的抒情的传统,笔者曾有专著《抒情传统与现当代文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来条分缕析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当代小说的关系。陈平原曾说,“五四”作家不会像“新小说”家那样把史书当小说读;但“五四”作家也有一种“误读”,那就是把散文当小说读。“五四”时代的小说杂志上常见标为小说的散文,“五四”作家的小说集更常常夹杂道道地地的散文。这种小说散文化的情况,在沈从文身上甚是明显。他的每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都可以当散文来读,他的小说抒情性和散文化倾向明显,比如同样是写多情水手与多情妇人的故事,小说《柏子》文体归为小说,而《湘行散记》里《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就算作散文。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的汪曾祺,也是这样,他的短篇小说更像是散文、美文。汪曾祺受晚明小品的影响,受归有光及其“文气说”的影响,崇尚才性、欣赏极趣、独抒性灵等的美学理念都深深影响了小说家,更何况是对散文的影响呢?
耿立警惕于此,清醒地认识到:“因周作人把中国的古典现代散文定位为抒情叙事,忘掉了散文的智性。”又说:“五四”时期散文演变的“小品”,排斥了智趣和谐趣,造成散文文体的先天不足和封闭的自循环,“叙事与抒情”的诗性审美观念,审美的狭隘和操作的狭隘窒息了散文的精神生命,束缚了散文的发展。晚明学者文人极重才情、智慧、技艺,强调文以自娱,对现代、当代散文的影响深远,耿立在《荷塘月色》式的抒怀,《荔枝蜜》式的寓物移情之外,呼唤:“散文应融入更多的思想和良知的品质,除了生命美学和感性元素,更应融入理性的功能智性的功能,应在题材上问题上更贴近当代生存的实景,应放扩文字的关怀力,让更多更严峻的事物进入视野……”由武训,耿立想到自己曾到乡下去,看到很多的留守儿童,在山西雁北山区一口窑洞里,有这么一个小女孩,家里实在是很穷,低矮破落死寂的窑洞里,脏黑的灶台上,七零八落放着几个说是吃了好几天的熟红薯。父亲让她退学,小女孩跪在妈妈面前哭着说:“妈妈只要答应我上学,我以后就不吃饭了。”这话敲击着耿立的心,也纠结着读者的心。而由武训,联想到父亲当年的经历,耿立感到的是锥心和刺骨的痛。
庄子的为人,绝真率性、自由无碍。这种性情,正是散文内在天然的品格,由此庄子其人与散文的品格,恰似天作之合,浑然如一。而李贽的“童心说”,讲存心纯朴的可贵,被认为不妨将它当成一篇散文基本理论的好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不作伪,不矫饰,“修辞立其诚”。耿立把散文求真的一面,在他的历史散文中作了新的文体探索。他声讨出卖杨靖宇将军的“这号中国人”,他声讨欺辱武训的人,他与林觉民一起慷慨激昂和吟唱内心的悲歌……在耿立的历史散文里,完全不用担心写作者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深刻和深挚的地方,不用担心散文作者仅仅求助于历史史料的援助,不用担心作为背景的史料,成了文章的主体,湮没了散文的精神担当。耿立的历史散文中,精神始终在场。
在散文文体探索方面,耿立希望把散文做大。怎样才能把散文做大?他认为应该学习西方散文的没有文体边界,这样就“没有自我阉割、不被狭小所锁定,所以散文在西方无远弗届,一直像大雾一样弥漫,像阳光一样辐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表述与精神相一致,她更自由、流畅、从容与丰满”。散文写作者和文学批评者始终在争论散文应不应该虚构,这样的分歧好像从来也没有消失过。散文的写作伦理应该是“真”“求真”,但对于历史散文,就要在史料里面进行合理的虚构,文体探索和扩展散文的文体边界也是号的散文家需要努力的。以《绝调》为例,关于记事的一部分,耿立开篇即倒叙,后面还来了一个小说叙事文本惯用的内部倒叙,他散文中的记事一线,不是按时间顺序的单一线性叙事,很有技巧和章法,增加可读性和让散文更加气韵生动。散文不是小说,它主要是抒情和记事,不虚构故事,尽量不对原始的故事作过多的虚构变形。但这不意味着在记事的部分,不可以借鉴小说叙事的技巧和技法,这也是当代散文在形式和文体探索当中的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耿立的散文,让我看到了他在做积极的文体探索,并且卓有成效。
《临终的眼:萧红记事》《绕不过的肉身》(胡兰成和张爱玲)等篇,读之,于我心有戚戚焉。虽说是从较为晚近的历史、史料和材料中成形的散文,却显示了写作者掌握了翔实的、丰赡的史料和材料,有着一支穿梭自如的散文之笔。能够写好萧红,能够写好胡兰成的张爱玲之间的爱恨情仇,没有一颗善感的心和作家基于能够深彻理解人性,解读人性和表达人性的能力,不可能写出那样活生生的萧红,更不可能写出那样真实的胡兰成和张爱玲……懂得一个男性历史人物,不难;写作和写好一个女性历史人物,写得让女性读者和研究者都认可,乃至都钦佩,这是耿立的了得之处。期待耿立在散文文体探索,与重申当代历史散文的写作伦理等方面,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更好的散文作品。我愿意相信,在耿立的散文中,他的精神,会始终在场。
【注释】
[1] [2] 谢有顺:《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3] [4] [5] [8] [9] 耿立:《散文的精神含量与高度》,“在场主义散文”微信公众号,2016年7月20日。
[6] 参见刘艳:《新文学精神与文人情怀——写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一百周年之际》,《名作欣赏》2019年第4期。
[7] 参见李洁非:《散文散谈——从古到今》,《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