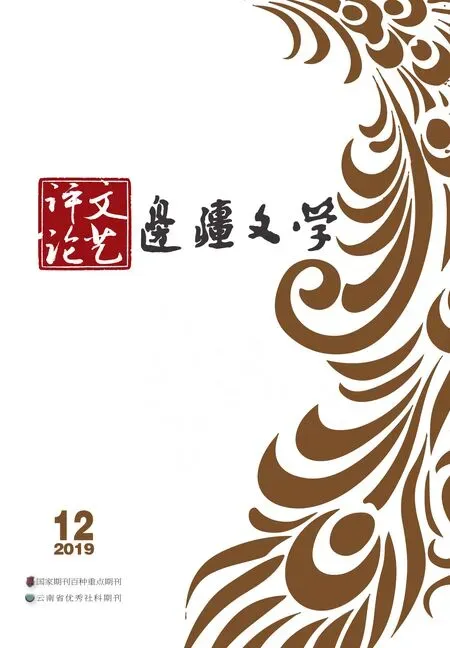2019夏季文学名刊扫描
2019-11-12宋家宏
宋家宏 等
形式的探索还是内涵的坚守?
主持人宋家宏:
这次评刊,我们稍作调整,增加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刊物。看得更多,能聊的也更多,同时需要判断和甄别的好作品也相应增加。我们依然本着“有话则说,实话实说”的基本原则,开始今天期讨论,先聊《人民文学》。赵小爽(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
我想先聊一聊包倬的《新婚快乐》。叙事者是一名婚礼司仪,在一场婚礼上,中年彝族男人老莫对即将成婚的新娘有着超常的关爱,但是这种关爱又一直处于压抑之中,小说围绕这一线索展开。小说对人物情绪的把控做得很到位,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缺少了直击内心的冲击力。他的内在逻辑不清楚,看完会让人摸不着头脑,结尾处理又略显断裂,虽是开放式结尾,但着实让人无从知道这个结尾是怎么由前面的关系线发展而来的。田彤彤(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
我同意小爽的观点,对结尾部分的处理也有所疑问,但听完小爽的发言后我在想,或许作家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就是想让读者对文本有所拓展与思考。赵小爽:
我认为作家的意图比较好揣测。从文本分析中我能感觉出老莫是新娘的生生父亲,这虽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是是具有合理性的。作家到最后也没有揭秘,可能就是想故意制造悬念,但这种悬念却并没有直击心灵的冲击力。主持人宋家宏:
可小说中写了老莫是他们家的恩人,你怎么又会觉得他是新娘的父亲呢?我认为文本中缺乏一种连贯的现实逻辑,以至于无法解开悬念。作家这个结尾设计很好,但可惜的是,没有将文本中的现实逻辑关系交代清楚。田彤彤:
如果作家尝试转化一种叙述的视角呢?换一种非旁观者的视角,比如新娘的视角或老莫的视角来书写这个故事,也许读者就能更轻松的理顺文本中的线索,揣测出作家的意图。赵小爽:
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到《上海文学》中有一篇很好的小说,荆歌的《田黄印章》,一个关于贪婪的故事。这一篇的叙事线就处理得很好,他虽然给读者制造了悬念,但他最后又以附录的形式重新表述了一遍,这个附录就是彤彤所说的换一个视角来写,揭秘的同时留了悬念,这种处理可能会更有趣一点。主持人宋家宏:
行,那这个就过去了,说另外一篇。赵小爽:
另外一篇是80后作家彭扬所作的《练习生》,这篇小说很压抑,通篇只分了七个段落,大段连续的话语,给人一种逻辑琐碎,语言堆积的感觉。但我还是耐着性子读完了,因为我想了解一个80后作家如何看待这个社会现象。在阅读中,我确实也感受到了作家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思考,我认为可以给这样的题材多一点的社会关注。主持人宋家宏:
谁看过这篇小说?也请来谈一谈。田彤彤:
这篇小说我看了一小段就没有继续看下去了。题材不吸引我,作家的文字也无法打动我。主持人宋家宏:
那你们认为这样的写作有意思吗?赵小爽:
这篇小说确实形式化严重,但我今天很想提出一个思考——形式化的作品是否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还是说我们觉得无趣就可以不去看它?何微(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
我认为小说的主题“练习生”,它本身就是当下时代一种“流量”的产物,这个题材本身就没有多少内涵可以挖掘。所以作家也只能写形式无法写出内涵,这篇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将这种社会现象展现给普通读者。主持人宋家宏:
这也与这个时代阅读的轻浅化、碎片化的审美趣味有关。赵小爽:
我觉得这不是轻浅,如果只是轻浅的话作家就不需要往思考的方向引。何微:
你认为这个作家的价值立场是什么?赵小爽:
就是批判与揭示。看完你会觉得这个群体我们熟悉却又陌生,不会想去尝试却又对这个多了一层了解。主持人宋家宏:
行,你还有别的小说想谈一谈的吗?赵小爽:
这期《上海文学》总体比较有意思。短篇中,叶兆言名气比较大,我看了他的《舟过矶》,但没有感到特别惊艳,故事讲了一个保洁员在她的工作地点目睹了一个死亡事件,但没有具体讲死亡事件,而是将叙述的重心放在讲述这个地方从古至今有许多人死亡。死亡变成了一个结果,一个既定事实,所有人对死亡都很重视,但也很漠视,没有人对死亡进行思考,只是在说死亡的可怖。主持人宋家宏:
小说中没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吗?赵小爽:
我认为作家想表现的只是,所有人看似对死亡很重视,实际上是漠视的。主持人宋家宏:
好的,其他人也聊一聊你们觉得值得一谈的小说。余彦冰(现当代文学2017级研究生):
我看了《花城》,想谈一谈陈希我的《普罗米修斯已松绑》。首先这篇小说对《花城》杂志而言意义非凡。今年是《花城》创刊40周年,在40年前《花城》的 创刊号,第一篇作品是华夏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一部典型的“伤痕文学”作品,呼应于那个时代有关于启蒙、人的主体性等话题。40年后陈希我的《普罗米修斯已松绑》则消解了这个“英雄”。这篇小说由三个剧本组成。其中两个剧本是主人公“我”作为导演推翻原本的“抗日神剧”的剧本后的即兴创作。第一个是典型的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革命叙事。第二个剧本谈理想主义者的现实境遇,救赎者被被救赎者背叛。最后一个剧本是围绕“我”自身展开的,“我”本身也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反叛者”。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自身信仰的崩塌和溃败。普罗米修斯已松绑,但在这个人神俱灭的时代真的还有普罗米修斯吗?小说质疑了“理想主义”是否有生活下去的土壤的同时质疑了所谓的启蒙。主持人宋家宏:
那你觉得小说存在什么缺点吗?余彦冰:
我觉得缺点在于两个方面:反讽不彻底和情感不知节制。罗莎(现当代文学2017级研究生):
我说一下《山花》,这次《山花》上的两个短篇,一个《朋友圈》,一个《恒温城》,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形式上的创新。《朋友圈》,全文如其名,由一个女人三个分组可见的几天内的朋友圈组成,此外没有其他任何连接的叙述,从头到尾只由一条接一条的朋友圈组成。是一种用普通形式无法排版呈现,需要用PDF形式呈现,里面还有点赞评论符号的形式。《恒温城》的全文则是全由内心独白组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独白穿插起来,组成整篇小说。虽然两篇小说中都可以看出形式创新的尝试,但将形式的作用与意义两相对比,高下立现。主持人宋家宏:
行,那你一篇一篇说一下吧。罗莎:
先来看《朋友圈》中的几条朋友圈。第一条分组所有人可见,这一条朋友圈她发了一些建立自己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形象的内容;第二条分组仅同事可见,这一条她以一个管理者的身份下达一些命令;第三条仅自己可见,诉说自己对一个有妇之夫的爱。这样的叙述形式,非但不能为小说情节增色,反而将一个完整的东西切割成了三个部分。我能明白作者想向我们传达人以及社交环境的复杂,在不同的社交环境中,人有不同的应对姿态这样一个道理。但我觉得这个道理是人尽皆知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又把这个浅显道理用这种直白的方法表达出来,我会觉得作为一个作家,这是在偷懒。很明显,用一个完整的事件或者情节来呈现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的复杂性以及一个人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写作难度会大很多。我认为这一篇中的形式是花架子,是为了弥补选题的空洞和无价值所做的一种努力。主持人宋家宏:
也就是说,文学表现反而低于生活了,那这样的写作有什么意义呢?罗莎:
是的,所以我才说,相比之下,《恒温城》中形式对内容起到的作用就大得多。《恒温城》所要展示的是出轨男女内心的复杂,纠结,孤独,毕竟出轨是一件见不得光的事情,所以男人和女人各自在这段感情中的心理变化实际上就是小说的核心,尤其是两人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这种瞬息万变的心理变化最好的展现方式就是心里独白。这一篇小说的形式和选题内容配合得很好,为小说添彩,所以我认为这一篇在形式上所做的改变,其意义和作用远大于前一篇。刘敏(武汉传媒学院教师):
我想说一说《招月》,段爱松老师的这一篇《招月》,故事的背景依然是在晋虚城,招月的出生与成长,像是围绕在她与自己亲人之间的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夹杂着种种非自然现象下的原由,传达出人们精神的焦虑。段爱松作品总有一种神秘、鬼魅般的吸引力,尤其是诡谲的地域魔幻色彩,你必须反复阅读才能摆脱叙事的魔障走近作品深处。但是我有个疑问,这种过于重视营造私人经验的写作,是否消减了作品的精神承担能力?桂春雷(北京大学2013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
我接续一下《招月》的讨论。段爱松老师的这篇作品,明显使用了环形叙事和复调的多视角,我认为在对诗化小说的理解上,可能存在模仿的意图。但是他对故事的本质,和对诗歌和小说边界的理解,我觉得我个人是受到冲击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在阅读注重形式的小说的时候,会有一个基本的诉求,就是我要么看到小说的表意结构,要么它的语言能产生神秘感,或者是在我看完了以后,觉得某个发力点很好,但是在段老师的小说里我看不到这些。小说最后甚至附了诗歌,我也不太清楚诗歌出现的意图,这些意象组织起来的世界,我同样不能参透。所以我当时读完了以后,有点难过。因为能看出来段老师在写作当中,对语言的斟酌的敏锐度,但是他对小说这个题材的适应性和理解,可能是不太符合读者的预期的。另外,他似乎没有摸到他这篇小说的任务,而这一点我觉得在我们这次讨论当中,在很多其他的小说中都能看到。小说到最后,必须能看到“是”小说的东西。主持人宋家宏:
这部作品被转载了。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和爱松谈过,他认为年轻读者一定能接受这种叙事风格,但我个人是持怀疑的态度。我认为你说的这些话很中肯,会对他以后的创作有一定的启发。关于成熟作家的创作任务、追求和困局
主持人宋家宏:
轶群,聊一聊你看的小说。谢轶群(文学硕士,云南艺术学院教师):
我想着重谈谈本期《十月》上的一个短篇,叫《五指山》,作者骆平。这是一篇高校题材小说,比之这些年来繁盛的同类小说,这篇作品的内容中有两个新意,一个是关于目前各高校正在进行的人才引进,另一个是网络自媒体不时对高校中人命运发生的影响。小说以一个颇有才学的大学教授工作调动的过程为线索,勾勒出大学学院一级基层权力场与当下学术圈的生态,一个个阴暗庸俗的场景。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高校题材小说几乎都是基调阴暗、氛围压抑的,现在的高校好像已经叫人不好意思写它应有的理想和神圣了。小说中曹子非跳不出姜院长的五指山,其实也喻指了大学教师、知识分子跳不出时代现实的五指山。主持人宋家宏:
小说的新意聊完了,有没有可批评之处?谢轶群:
虽然在选材上有一些新意,但写法却和以前的高校小说一个路数:不带感情色彩地呈现,不惊讶,不痛心,不疾呼,依旧很容易追溯到刘震云《官场》那种“新写实”。这里表现出的,固然有作家见怪不怪的“成熟”和对现实涵思的充分,也体现了人们对高校现实从恼怒到无奈、认同的过程。但相比十年前的高校题材小说,比如黄玲老师的作品,以平静的笔法叙述,有越不动声色越叫人震撼、心惊的效果,今天这样的态度,已不叫人震撼心惊,因为大家都接受高校彻底世俗化的现实了。那么文学的警醒、反思、批判方面的冲击力在哪里?不能说读者自然会有抵触、厌憎等积极反应,因为社会读者、包括高校师生读者对这些已经熟视无睹了,作家不过把现实搬到纸面再让人熟视无睹一次。主持人宋家宏:
大家应该都看了包倬的《老如少年》,谁先来聊一聊。桂春雷:
我想谈一下《老如少年》。读的时候,一开始我就会注意到其中的怀旧意趣的感伤的东西,我对此稍微有抵触。因为小说有个游戏性的开头,荒村里有一群老人,他们希望认一个年轻人做儿子,或者做爸爸也行。这些情节设定很有讽刺性,让我很期待,可是到了中段,他们的很多行为和言谈其实都涉及到对自己过往的清理。而基于它是一个小说,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认为,这些东西里是否包含着作者对历史的某种态度?所以当我读到文本中段,并且正在猜想作者的态度的时候,读出来的一些感伤情绪就造成了我的困惑。我认为在一个成熟的作家对过往的清理中,应该会有一些尖锐的东西。而前半段,有点钝感。但另一方面,前面聊《招月》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发力点”,我觉得《老如少年》有个明确的发力点,就是在最后,它的叙述者,提出要和老人的儿子做交换,我可以告诉你存折密码,但条件是你必须把我带走,带离这个村庄。因为我怕老人们去世以后,我成为村子里最后一个人。这个点绵里藏针,图穷匕见,痛感剧烈。它向我们揭示了人的本能在最后一刻对抒情的突破。它在这里表达了,叙述中难免“谎言”,而这个小说实现了对谎言的刺破,这其间的对“人”的理解是很决绝的。何微:
这里我想接入聊两句。在我看到结尾的时候,就是刚才桂春雷提到的小说发力点,傻子在小说里他提供了一个观看视角,他看到荒村现象和留守老人们的悲惨境遇。同时他又是叙事推进者,陪同老人们一起回溯过往,解决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还共同除草修房等等,让人感觉傻子是对农村这个实体,或者说对传统的农耕文化有认同和留恋的,结果最后他逮到机会就突然要走,似乎有损这个角色的连续性。但是仔细一推敲,这个结局就是作者的意图在发力,小说的精神力量也就显现出来了。桂春雷:
到小说最后,他发现了离开的机会,他决绝的要离开,这个过程中没有给到读者去理解去体认的机会,人物的选择,或者说作者的选择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冲击明明白白的在说,历史往往是结果,当我们看到结果的时候,一切已经是“必然”的了。但是“必然”背后的脉络,其实在一开始的小说叙述中,是不太显现的。所以包倬在这里,其实植入了他的某种历史观,这一点我们待会儿聊到《猪嗷嗷叫》的时候可以再聊,我觉得他们的历史观的高明之处是相似的。主持人宋家宏:
我认为包倬的这篇《老如少年》比《新婚快乐》写的要好很多。整篇小说的叙事和结尾都呈现出一种绝望,为什么让傻子走?因为作家也无法找到解决“荒村”现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为什么设计成傻子叙事?代表了包倬对当前中国农村的一种忧虑。当下的农村只有傻子才会回来,但最后连傻子都不愿意待,可想而知当下中国荒村的现状多么让人窒息。陈林:
包倬的小说向来关注社会现实,《老如少年》也不例外。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都是近些年引人热议和深思的重大社会问题,往大了说,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失落,人类生存根基和基本伦理瓦解的问题。这类小说容易给读者痛感,但我觉得要写好需要更大的思想和心灵力量穿透“问题”,并以有创造力的文学形式转化“问题”,这是个考验。主持人宋家宏:
接下来,何微聊一聊你看的。何微:
我看了第四期的《小说界》,这个期刊似乎每期会有一个小说主题,这一期是科幻元素吧。打头第一篇是小白的《婚姻风险》,就是借助人工智能视角,把人类的婚恋关系放置到科技高度发展的未来图景中去审视,但是高科技的新意又不足,对婚恋关系的剖析也不见有多深刻。我觉得,要在高科技的超现实语境中来探讨现实问题和复杂人性,看这个小说大概还不如看一集《黑镜》更有趣味性和反思的空间。主持人宋家宏:
那就说你觉得值得看的、有话可说的小说。何微:
我还看了《收获》,在短篇小说单元里,我推荐邵丽的《天台上的父亲》。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患抑郁症的父亲欲自杀以及自杀之后,由“失亲”所引发的家庭成员的情感动荡和种种抉择。邵丽这篇小说无意从哲学层面去探讨关于“自杀正义”的内容,但是它将“自杀”放置到一个普通家庭中,让读者可思考关于自杀、失亲、亲子关系等现实问题,有现实反思意义。小说中母亲形象也刻画得很好。母亲本来一直处在叙事边缘,但是结尾有一个反转情节。母亲在结尾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压轴,为父亲自杀这件事画上句点,让笼罩在阴影中的整个家庭都得到了解脱。小说里母亲这种静默的承受姿态,让我想起里尔克的《秋》里有一句诗“然而有个人,用她的双手,无限温柔的捧接万物的坠落”。罗莎:
我与何微的观点一致,邵丽在这篇小说中处理感情时用的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方法,那些最点墨无痕的地方实际上蕴藏了最沉重最复杂的感情。主持人宋家宏:
邵丽之前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节日》,和这篇《天台上的父亲》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一个成熟的作家不应该出现这么大的反差。罗莎:
其实还是能看出来邵丽在处理上复杂亲密关系上的相似性。不直接点明,而是用一些象征性的小细节,用隐含的线索来带着读者窥视水下的冰山。陈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云大驻站博士后):
读邵丽这部小说时我想到以赛亚·柏林的著作《扭曲的人性之材》。扭曲的社会之下,人性也无法幸免。小说中的父亲是扭曲的,儿女也是。由父亲关联起的是那段历史,这个我们文学史写得很多,小说淡化了父亲的社会历史背景,而直接突出其精神后果——自杀。由子辈关联起现实,“我”与大哥的精神同样出现严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小说有邵丽的困惑和探索在里面,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精神处境是否恰恰与精神上的无父相关。这是这部小说引人深思的地方。由一个自杀事件,牵连出历史、现实、人性的种种疑难,完成度不错。就我看过的几部作品而言,感觉大多还是浮于世相,作者停留在想方设法讲好一个故事的层面,我不知道仅仅是巧妙地设计一个故事有什么意义。以部分问题小说为例,我没有读到对问题深刻独到的理解和新颖独特的表达。主持人宋家宏:
你的发言很有意思,很有价值,非常犀利地指出了当下作家创作时的缺失。陈林:
当然,只要我们不主张闭上眼睛,回避矛盾,我们就应当肯定直面现实的写作。形成鲜明对比,《人民文学》发表了两组作品,一组是儿童文学,另外一组是神话。如果说问题小说浮于表象,那么那些童话、神话则似乎与我们的精神处境没有联系,我们好像可以遁身于远古时代或漂浮于真空,而不是生活在大地上的此时此刻。这是非常两极化的两种写作。主持人宋家宏:
这还是属于我们上一次“心灵现实主义”所谈论的范畴。问题小说仅仅停留在问题层面,写得太浅薄了,无法进入人的心灵世界,也就无法打动我们。何微:
师兄刚刚聊到儿童文学。我也想说一下这一期的几篇儿童文学,荆歌的《小米兰》我挺喜欢。我觉得阅读感受与读者期待、个人阅读趣味关系很紧密。所以从读者期待来说,我没有要求它显露多复杂,或者多么周全深刻,孩童视角是会讨巧一些,但是这个小说呈现的世界有它的完整性和自足性。我读完之后就会感觉是一篇让人觉得松弛疏朗的文章,阅读感受还不错。主持人宋家宏:
郭诗亮也看《收获》了,你来聊一聊。郭诗亮(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
我先聊一聊中篇。《女神牛开丽》这篇小说一开始就给了我惊喜,语言简练,比喻巧妙,叙述节奏明快,很适应大都市给人的感觉。但是后来写崩了,故事太俗了,俗到我能在电视剧里找类似的桥段,最值得挖掘的个人媒体账号没有深入,反而成了几个俗套爱情故事中穿针引线的工具,一大败笔。对外貌的描写很虚,甚至出错,150页写“嘴唇四周蓄满山羊胡”,山羊胡只在下巴上啊!(众笑)郭诗亮:
双雪涛的《杨广义》和他其他的小说一样,很难去阐释。但仍能看出其过人之处,小说前半段所有被叙述出来出来的事情都是“我”耳闻的,耳闻就是不确定,不确定就是叙述者的不可靠,由不可靠的叙述者叙述出的后半段尽管有些“真实”的意思,但显然也是不真实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一个支点,所有的意义都是漂浮着的。桂春雷:
我接续一下师弟的话题。确实,如先前师弟说,双雪涛的小说很难去阐释,相对应的是其实它又提供了很多阐释路径。因此我就会产生一种忧虑,就是双雪涛的小说技法已经非常成熟了,他有创作的敏锐度,很明确知道什么样的小说可以获奖,或者《收获》需要什么样的小说,但是他又缺乏使用这种敏锐度的勇气。或许相似的,对现在的很多作家来说,他们的成熟恰恰伴随着他们有意识的“配合”或者“迎合”。这种有倾向的选择,会让他的小说写得越来越好,或者说,越来越容易被认同,但是也会导致某种疲软,离现实越来越远。我就有一个困惑,会不会一个小说家走到了一个境遇的时候,就会成为ー个小说活动家,会成为自己的小说素材的组织者。或许成熟作家的路难走,一方面因为可开拓的内容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也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小说走向“影视化”,借鉴与抄袭的边界何在?
主持人宋家宏:
好,有人看了《中国作家》吗?来谈一谈。史渊(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贵州师大教师):
我先来谈一谈。我个人阅读感受很深的作品孙未的《大象的单行线》,一般作品中“死亡”常是冰冷且感伤,但在这部作品里“死亡”是夏天火红色的大象带着亡灵们去参加庆典,热闹且欢快,轻松的氛围中也透露了生者对亡灵的不舍。作者用童趣、温情的文字来写死亡,希望告诉人们时光一去不复返,珍惜欣赏美好事物的时间。道理浅显却也深刻,“死亡”也有了别样面目。主持人宋家宏:
嗯,还有其他篇章吗?史渊:
还有二湘的《珍珠》,读作品的时候会想到《边城》,两部作品时空虽然不同,但都展现了人物的人性美,悲剧多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但作品中有的情节设置过分巧合,让故事的部分显得有些生硬,比如两姐妹在省队和国家队的选拔中都因为双胞胎的身份脱颖而出;月珍因为车祸离世,恰好成全了妹妹月珠的爱情田彤彤:
看完《珍珠》这篇小说我首先想到了一部电影《摔跤吧,爸爸》,只是小说里的体育运动从摔跤换成了乒乓球,许多设定也和电影颇为相似。这篇小说本身是不错的,就是模仿痕迹太重了。除了情节借鉴外,小说中有一个叫唐跃华的角色,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存有质疑。这个唐与两姐妹都有情感关系,但作家对这个人物又着墨不多,我认为作家对他们三人之间的情感发展处理得不够合理。当然,这篇小说也有闪光点,比如爱情、友情这些情感因素的加入使得小说的内容比起电影更为丰富,父亲与两个女儿的形象也更加丰满、圆润。主持人宋家宏:
如果没有《摔跤吧,爸爸》,我们单看这个小说写得确实不错,框架和叙事逻辑都相当的完整,对人物的命运以及悬念都处理得很好,也写出了运动员运动生涯的悲剧性,清丽的文字下流动着悲壮的情绪。赵小爽:
我认为,可以写的话题就这么多,并不是说你写过的话题别人就不能再写,重点还是在于你怎样再次表述一个同样的题材。比如《珍珠》就是有属于它自己的亮点在里面的。反观我们读者自身,总是在拿后一篇看到的与前一篇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作品来比较,这对后一个作家是不公平的。主持人宋家宏:
其实从比较文学所说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来看,这就涉及到一个共同母题的问题,《珍珠》与《摔跤吧,爸爸》也可以看作有一个共同的母题。赵小爽:
并且这个题材中最打动人的点也就只有这么多,运动员的生涯都是相似的,所以作家可以挖掘的这些点也是具有相似性的。罗莎:
《摔跤吧,爸爸》里有一个内核是和这篇不一样的,电影中的爸爸培养这两个女儿成为运动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爸爸要帮助他们摆脱印度那边对女性的歧视,与这篇目的性是不同的。其实我认为是借鉴还是抄袭很好判断,细节的东西是很容易重合的,但是如果像上一期出现的那个作品那样,每个推动情节发展的关节点、逻辑,最后的结局都相同,那就是抄袭,所以这一篇,只能说是借鉴。创作者的灵感来源、生活经验真的是很容易重合的,并且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潜意识中受到了影响。余彦冰:
而且两个作品想表达的重点也不一样,《摔跤吧,爸爸》主要在塑造爸爸的形象,传递出父爱的伟大。而《珍珠》书写的是一个家庭三代人的追梦故事。田彤彤:
对,而且《摔跤吧,爸爸》有点传记典电影的感觉。还有就是在电影里面,两个女孩的母亲一直处于失语状态,但小说里母亲却拥有着话语权。主持人宋家宏:
是的,这两个作品从核心立意上来说,电影是塑造爸爸形象,梦想只是它其中的一个部分,而《珍珠》讲的则是实现梦想的艰难。这篇小说的结尾处理得很好,没有落入俗套。外孙女是否能完成外公的梦想,作为乒乓球运动员走上国际的舞台,作者最后是留了空间的,蕴含着很大的可能性。赵小爽:
其实这也是电影的一种营销手段,一个“摔跤的梦想”可能不会像实实在在的“父爱”那样引起人们的共鸣。云南“90后”作家——扎实写实与直面问题
主持人宋家宏: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云南青年作家李司平的《猪嗷嗷叫》。刘敏:
一场由杀猪引发的闹剧,可笑可怜又可恨。作者了无痕迹的人物刻画,令人犹在境中。精巧的情节设置下,囊括了当下社会的许多焦点问题,忍俊不禁后又引人深思,让作品有了凝厚沉重的力量。史渊:
作者关注到了农村的现实——扶贫,刻画的农村生活入木三分,尤其开篇的闹剧活灵活现。通过个性化的言语将笔下人物的性格充分展现。作品接地气,但也有现实的思考,从李发康的个人经历可以透视出扶贫干部在村镇开展工作中困境。陈林:
《猪嗷嗷叫》也可以理解为一部问题小说,作者抓住了近年最热的话题之一——“扶贫”,语言有特色,到处是调侃、戏谑。赵小爽:
我认为李司平的写实功夫值得肯定,他把这种农村生活转述出来的时候,读者不会觉得有隔膜。他的语言是有趣的,会吸引读者继续往下阅读,我认为这是他最出彩的地方。余彦冰:
我赞同小爽的观点,并且在这篇小说中作家还写出了国民的劣根性,贫困问题的深层根源其实是劣根性的问题。罗莎:
我认为这一篇最大的亮点其实在于,他写扶贫但不仅仅停留在扶贫,他还向内挖掘探讨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贫穷,同时也探讨了彦冰所说的劣根性的问题,他真正地去思考了贫穷与扶贫的关系,而不是停留在写扶贫现象这一表意层面。另外结尾也很妙,作者在前面所作的所有铺垫和叙述,以及所有的讽刺戏谑全都压在了这最后一笔,很有力。何微:
我觉得小说还质询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脱贫?贫穷可以得到解决吗?小说最后发顺一家实现了脱贫,实际靠的是在深山老林里繁殖出的野猪崽,阴差阳错的野路子让贫困户脱贫,而并非是认真执行脱贫政策的李发康的功劳。最后玉旺给自家养猪场里的猪都取名叫“李发康”,就是一种巨大的反讽。田彤彤:
这篇小说还有一个讽刺的地方就是领导在审查扶贫工作的过程中,一开始将李发康吹捧上天,后来因为发顺家种猪走失的事情就将李发康的工作成果全盘否定,不允许有一点点的失误出现。主持人宋家宏:
这就是当前扶贫工作的常态,不允许出现一点纰漏,这其实根本就做不到。赵小爽:
我感觉大家在探讨时已经潜移默化地将之看成问题小说了,说的是他挖掘了反映了思考了什么问题。桂春雷:
我没有把它当问题小说在看。首先谈语言的问题,我觉得作者在基本的语言准确性上,是有问题的,包括他对杀猪场面繁复的描写没有多大意义。我读的过程中,就很想知道这篇作品为什么得到那么多赞誉。看完以后,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我认为这是一篇隐喻小说。我觉得他讲的不是扶贫问题,他是在用扶贫的事件和场域来指向更宏大的历史。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写作意图,还是歪打正着。但这篇小说摸到了五四时期的启蒙、救亡的话题。小说中,二十年后,李发康在外地打工,他不愿意领受阴差阳错的“扶贫”功劳。小说的尖锐就在这里——那到底是谁改变了这个村的命运?小说题目叫《猪嗷嗷叫》,是因为猪在这里是某种意义上的“主角”,它改变了这个村。可是谁行动,谁吃了责任,谁得到荣誉?我觉得它很像启蒙话题的乡村版演绎。我认为是在这一点上,李司平在这个小说中展现出了他的写作素养,小说能被解读出一个“空间”的话,就实现了小说一个最根本的任务,那就是探索出问题内部的可能性。因为问题是会长出问题的。《猪嗷嗷叫》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非常出色。作者找到了小说的任务,就是发现问题,生成问题,并且把问题映照进读者的心里。主持人宋家宏:
你这么解释就显得这个作品过于伟大了,但你这样的阐述又是有道理的。小说写的很细腻,但他的主观意图是否到这个程度我有些怀疑。陈林:
我补充一点,我看到王蒙、徐坤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很高。王蒙的大多作品也是既关注现实政治,问题意识很强,同时又具有消解、解构的力量。李司平这部小说大概也可以放到这个传统中。这部小说语言上多繁富的、有膨胀力的长句,这也是王蒙语言的特色,语言在文本中不断自我繁殖。桂春雷:
小说最后,叙述者说到李发康就是他父亲的那一段,节奏一下子慢下来了。感觉像是之前所有的风筝满天飞的叙述,最后都拴在了一个石头上,那个石头就是他父亲。这个地方很打动我,我想到一个90后作家,能对历史、对父辈有这样的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评价是否足够准确,因为会有点情感倾向:他有满天飞风筝的去叙述的冷酷,也有让我们看到石头的温存。这个视野,存在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的心上,是很动人的。他并不是只认写作技术,也不是说我强求与众不同。他的态度是,没错,我就是看到了一个石头,然后我要把它摆在那儿。这是在写作上极强的个人追求和与之匹配的极强定力的表现。他有能成为一个文学生命上“长寿”的写作者的潜质。罗莎:
我觉得他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这样的年纪,敢于直面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延续传统的写法不玩花活。90后作家在怎样才能新,才能与众不同上面的思考太多了,但不懂传统何谈创新,即便是通过一时的创新突然从人群站出来了,那站出来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什么有力的东西支持其长久地创作下去了,从这一点上看,李司平是与众不同的。主持人宋家宏:
李司平确实是扎扎实实在写作,这恰好是“90”后作家最缺少的东西。我们回到“80”后这一批,为什么甫跃辉在“80”后作家中显得特别出彩,就是因为写实功力比较扎实。罗莎:
相比于另一些通过建立新的世界以及世界观,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写进去的写法,我更喜欢李司平这种“落地”的写法,敢于用最传统的方法写最普通的日常,但这故事背后可以任意挖掘出更多更加深刻的东西,我认为这种写作其实更具难度也更加难得。陈林:
作为一个年轻作家,有思考大问题的抱负本身就值得鼓励。主持人宋家宏:
特别小桂对这个作品这么一解释,这个作品的高度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这样的解释也是有道理的,李发康就变成了一个启蒙主义者,他的失败就是一个启蒙主义者的失败,这个小说就暗含着隐喻。陈林:
但当我们说李发康是启蒙主义者的时候,是不是强行安置给他的身份,他不就是一个官员、一个政策的执行者吗?主持人宋家宏:
但是你要注意,小说中还有其他的政策执行者。乡长也是呀,他直接担任扶贫的第一责任人,但他显然与李发康是两种人。桂春雷:
说到这里我想把小说的故事脉络再补充一部分,首先李发康是贫困户发顺的兄弟,这里有一个身份问题:进步青年,同时又是贫农的兄弟。猪是在李发康的主导下,政策下发的,玉旺从山里找回了野猪,“建档立卡”的“政策猪”又结合了野猪,才有了后来的脱贫。最后虽然李发康担了责任,但玉旺心里明明白白,所以小猪们都叫李发康。这个线索提供的解读空间很大。陈林:
这恰恰是写实作品的想象力,是扎实的写实与想象力的结合。主持人宋家宏:
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胜利。现实主义的作品真实的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去创作,完全可以超出作家和一般读者的预设。优秀的作品客观意义一定是大于主观意图的。桂春雷:
在这里我有一点困惑,就是说,作者的笔和他的意图,是否能始终保持一致?主持人宋家宏: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李司平是清楚的,他认为李发康是真正能解决贫困问题的人,但是他不一定有启蒙这个意识。陈林:
刚才讲到作者意图,我比较关心的是李司平如何理解扶贫这件事情?主持人宋家宏:
我认为他肯定觉得这样的扶贫没有意义。他的故事本身以及结局都告诉我们目前的扶贫方式没有意义,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问题,你靠物质是无法拯救的。陈林:
这个问题比较敏感。这也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修辞策略,嬉笑怒骂调侃戏谑,作者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以保持适当的距离。主持人宋家宏:
行,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这次讨论会很成功,有观点有深度!谢谢大家!【本期推荐篇目】
· 李司平《猪嗷嗷叫》(刊于《中国作家》2019年第5期)。
· 邵丽《天台上的父亲》(刊于《收获》2019年第三期)。
· 包倬《老如少年》(刊于《江南》2019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