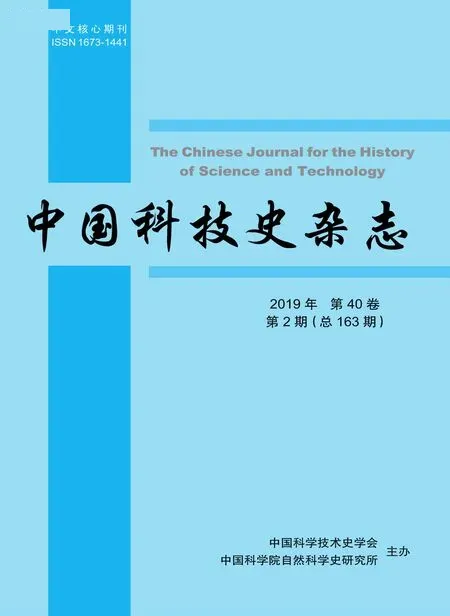传世著作《星命溯源》与五代至明中国星命术的发展
2019-11-11宋神秘
宋神秘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
1 问题的缘起
自星命术于南北朝或更早时期经佛教等途径传入中国以来,这类星占术就在中国发展起来[1]。由于星命术与佛教、道教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具有亲缘关系,同时作为研究基础的原始文献多散杂于传世或出土佛道教文献、星图、敦煌文献中,目前对星命术的研究多以追溯星命术的传播源头、过程为导向,沿着传播源头——传播过程——传播后果的思路进行探索,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成果[2—10]。
在这些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试图探索星命术本土化的过程,发现后世的传世星命术专著与早期佛经、道藏、敦煌文献中的星命术材料在内容和方法上有明显的区别,这些晚出的星命术专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域外星命术本土化发展的一部分结果。对这些著作进行分析,无疑有助于星命术本土化过程的研究。因此,笔者尝试对这些传世星命术专著进行分析,从传播结果出发,逆向勘察星命术本土化发展的过程,并将这一传播结果与沿前一思路对传播源头、传播过程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利用这一新思路来辅助沿前一思路进行的本土化过程研究:一方面希望深化对星命术体系的认知,另一方面希冀推进对星命术本土化传播和发展进程的研究。
目前已知的传世星命术专著一部分保存在《四库全书》“子部·数术类”中,包括《星命溯源》、辽耶律纯《星命总括》《演禽通纂》、明万民英《星学大成》等,另有《星平会海》一书传世,为明代著作[11—15]。此外,《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星命部”收录有多部专著,然而其中有许多是八字算命术专著,并不涉及星象,所录以星象推算人命的著作有《张果星宗》《耶律真经》《壁奥经》《望斗经》《琴堂步天警句》《琴堂指金歌》等[16—21]。这些名目繁多的著作内容各异,对星象的侧重点不同,推命方法也多有不同,很可能代表了星命术传播及其本土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流派,实有必要对其考察一番。其中,《星命溯源》托名唐张果所作,比起大多数年代或作者不可考的星命术专著,似乎有可能体现了星命术发展相对早期阶段的内容。本文作者发现,该书内容几乎全部为《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张果星宗》收录,但次序不同,后者还包括了许多《星命溯源》所没有的内容,为考察和分析前者提供了更多的对比材料。因此,本文以《星命溯源》为例,试图从星命术在明末以前发展的结果之一,逆向探讨星命术这一星占学分支和数术门类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和发展。
2 《星命溯源》的作者、内容及形成时间
《星命溯源》伪托唐张果所作,这一点四库馆臣在提要中就已指明:“独是编以五星推命之学依托于果。”书中称其星命内容源于张果,并多以唐玄宗赐张果的号“通玄先生”进行指称,如“通玄遗书”等,然而,就历史记载中的张果而言,他与星命术没有任何关系。四库馆臣进一步指出,将星命术依托于张果,是因为唐代已经出现用星象算命的方法“实以五星宫度推休咎”([11],页45)。新、旧《唐书》记载有张果其人([22],页5810),此前唐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李德裕《次柳氏旧闻》、郑处诲《明皇杂录》均记载张果事迹[22—27]。这些记载中没有一处显示张果与星命术、甚至其他类别的推命术有何种关联,但明显体现出张果与道教的密切联系。此外,《旧唐书》记载张果著有《阴符经玄解》,《新唐书》记载张果有《阴符经太无传》一卷;又《阴符经辨命论》一卷(1)以“辨命”为题的著作,可能为论述命运的综合性论说,最早可追溯至《文选》收录的刘峻《辨命论》,这类著作并非为讲述某一种或几种推命之法的专门著作。([22],页1521)。这些以及道教文献中记载的张果或托名张果的著作也都未涉及星命或推命之术[28]。宋金时期,张果与蓝采和等人被纳入八仙行列,其事迹和形象得以在社会中广泛流传[29—30]。除文字描述和书籍外,还出现了图像崇拜,然而这些材料刻画的张果形象也与星命、推命之学无关[31]。
另一方面,以《秤星经》为代表、叙述十一曜推命的五星术著作在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中已有收录([32],页1659),且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阴阳家类”中收录有《五星命书》一卷;《五星三命指南》十四卷;《五星六曜约法》一卷;《诸家五星书》一卷(2)据钮卫星推测,《秤星经》可能为晚唐五代之际作品,见钮卫星.唐宋之际道教十一曜星神崇拜的起源和流行[J].世界宗教研究.2012, (1): 90.[33]。但这些五星术著作并未与张果有联系。除《星命溯源》外,晚至明代,才正式出现将张果与星命术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证据,明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记载有《张果老星命大全十卷》四册,陆位辑;《果老子平大成》三卷[34]。显示出张果与星命、推命之术的联系。因此《星命溯源》将张果与星命术相联系,又具有了新的意义,它的内容及年代,对于张果流传形象的变化至关重要。
《星命溯源》全书共五卷,各卷体例、行文、作者和时代均不相同,因此必须分别加以剖析。《古今图书集成》所录《张果星宗》中收录了《星命溯源》的所有内容,但各卷及下属各小节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中,且先后次序完全被打乱,标题和作者稍有差异。最大的区别在于《张果星宗》收录了许多《星命溯源》所没有的内容,而且《张果星宗》的章节安排逻辑清晰,按照不同主题将包含《星命溯源》各卷在内的星命术内容分门别类,明显是人为系统化整理的结果;而《星命溯源》各卷以内容的不同来源进行区分,主题的排布颇为杂乱。
《星命溯源》第一卷题为“通玄遗书”,“通玄先生”为唐玄宗赐予张果的号,正文前的简述对此进行了交代。该卷分设三小节,分别为“五星论”“四时论”和“玉衡经”,均用诗赋的形式阐述星命术的具体内容。《张果星宗》“第七”篇章对其分别以“五星歌赋”“四时赋”和“玉衡经”命名,突出其歌赋的体例,除这三小节外,该篇章还收录了许多其他歌赋,如《历象赋》《元通赋》等等。
“五星论”记载了许多天象的命断结果,如“五曜连珠”“二星合璧”“太乙抱蟾”“水星伴月”等等,这些天象命断被称为“星格”,即星象呈现出的个人命运格局。《张果星宗》“第五”专门收录“灵台星格”一节,对各种天象及其命断进行了阐释。郑樵《通志·艺术略》“五行·三命”类录有《灵台歌》一卷,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五行”命书部分收录有《灵台三十六歌》一卷,应为以歌诀形式论述“灵台”天象类的星命内容[35]([32],页1695)。鉴于“五星论”的歌诀形式,加上十一曜在五代时已经兴起,其大规模流行可能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后,阐述完整十一曜星命论断的“五星论”,其内容的形成可能在五代至南宋1161年《通志》完成之间;“四时论”“玉衡经”也包含完整的十一曜,其形成时间应在五代以后[36]。
卷二“果憕问答”有四小节,卷末记“问五十二数”。该卷除第三节“五星先天口诀”外,均以问答的形式论述星命内容,若将第三节的每条口诀记为一问,该卷四节的问答数目约与五十二一致。其他三节中,第二节“至宝论”和第四节“后天口诀”中的对话人物相同,分别为老仙和李憕,但对话的内容和形式表明它们是各自独立的,“至宝论”多用“问”和“果老曰”(或“曰”“答”)的叙述体例,而“后天口诀”用“老仙”(或“仙曰”)和“憕曰”来组织内容;更大的区别在于“至宝论”重点叙述的“斗杓”“唐符”“国印”等用某一曜或相应地支表示的神煞在“后天口诀”中又有论述,“后天口诀”中还论述了第一节“评人生禀赋分金论”中已论述过的“四日”“四火”“四水”“四土”等宿度命断。此外第一节的对话人物为“通玄先生”和“李憕”,此节中的张果尚未成“仙”。
本文作者推测,卷二的四节内容不是出自同一来源,而是各自独立成篇,再由明代的“李憕”加以整理并附上自己的名字。前已述及,张果在宋金时期位列“八仙”之一,唐时的张果主要以一位现实中的道教人物形象呈现。因此,卷二第一节以玄宗御赐的号“通玄先生”指称张果,此节在形成时间上应早于称呼张果为“老仙”或“大仙”的其他三节。由此类推,卷一题为“通玄遗书”,用的也是张果的赐号,在形成时间上很可能也早于卷二的后三小节。卷二末有“时维嘉靖二年九月朔旦中都石室山下李憕记”,可见该卷的形成时间下限为1523年。
卷三“通玄玄妙经解”,与其他四卷相比,内容简短,共列出50个四字短语,并加以详细注解。这些注解为郑希诚所作,在郑氏看来,这些四字短语为前辈张果所作,因此以“经”命名,它们在郑希诚生活的年代早已存在,也许是早期星命术的内容。
《张果星宗》收录的该部分内容只有42个四字短语,所缺的7个在其他篇章以单字列出,另有1个“拱夹不起”可能因为其“拱”“夹”在“第一·入门看法”的“朝/拱/辅/夹”部分已有解释,因此没有列出。拆分成28个单字的这7个四字短语与其他42个进行比较,均为论述星曜运行位置或位置关系、表示天象的字,每一单字描绘一种状态,如朝拱辅夹,朝为向日,三合曰拱,身命主及诸强宫辅弼日月之前后曰辅,日月夹身命主及诸强宫曰夹([11],页62)。对于这些天象的具体解释,《张果星宗》用语略有差异,但内涵一致。其他42个短语不能以单字成义,必须四字结合才能产生出含义,其论述的内容颇杂。
郑希诚者,《四库提要》称其为元人,“自署其官曰主薄,其籍曰瑞安,其号曰沧州,始末未详。”([11],页46)《张果星宗》第十八、十九收录“郑氏星案”共40例,附图并文字解说,图前有论述“至元时浙温之安固郑希诚氏,曾遇异人授以通元[玄]之学,用诸禄命……”([16],468册,页28B—36A)《温州府志》附“方技”亦载“郑希诚”:“瑞安人,年八十入山,遇异人与语,授果老五星一帙为别,自此晓书史意见。旋发一日,举五星推之辄验,求推者填门。其法,问人生辰,即书所生之七政四余及干支化曜于盘上,倒悬之仰观,至旬月,人之寿殀祸福、穷通锱铢不爽……”[37]叙述的星命内容与郑希诚吻合,但该志将郑希诚位列明代,并记载“永乐中,汪庭训效其术,亦多取验,视希诚为次。”且不论汪庭训生活于正统年间,去永乐中似乎稍远,若果然如此,永乐中其术还在为世人效仿,则郑氏应生活于永乐前,因此他应为元末明初人,在元代生活年代更久(3)《明英宗实录》卷132“正统十年八月壬子”条记汪庭训时任南阳委同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2624.。
卷四“郑希诚观星要诀”列出131条详略不等的星命推算规则,个别杂以实例推算,文前提及这些内容为“与果老所传大不侔矣”的可取条目者([11],页73)。这些内容不是张果一派原始的内容,而是元末、明初时郑希诚后添入的其他派别的星命内容。这131条星命内容中,所涉最多的主题是神煞,共76条,占一半以上,其次为命度56条,再次为行限32条,依次为身27条,星格25条,其余涉及行限、流年、时节、女命等主题。
卷五题名“类次郑氏诸家观星心传口诀补遗”,应为郑希诚以后形成的内容,至少应为元以后形成。共21小节,与前四卷相比,逻辑条例清晰,前7小节论述十一曜,后14节分别论述十二命宫以及女命,许多论述与前四卷重复。
从各卷形式和内容可知,该书是一本汇集之作,各卷内容出自不同的时期,最早可能在五代十一曜形成以后,最晚至明嘉靖二年1523年。卷一、三正文部分形成时间稍早,为伪托张果之名的术士所作,是所谓张果一派早期比较原始的内容。卷三注释和卷四为元代内容,为元末明初郑希诚所作。卷二、卷五内容较晚,卷五为元至明代形成,卷二为明代形成,且该卷各小节形成时间和来源不一,为明李憕汇集整理而成。
通过对《星命溯源》各卷形式和内容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该书与唐宋及唐以前汉译佛经和其他文献中呈现的星命内容多有不同,由此可以追溯星命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下文将具体论述这些发展和演变过程。
3 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的五行化演变
与唐宋及唐以前的汉译佛经等文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该书的显著区别之一在于对宫、宿的运用不同。《星命溯源》中的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非常五行化,在形式和星占学内涵上日趋体现出五行的特点,而非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原本各自的天文和星占内涵:即对个人出生时刻星象的命运推算,从形式上看是依据星曜与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的位置和位置关系,然而除保留一部分有关位置关系的域外星命内容外,相当一部分是根据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分别与七曜进行匹配、从而可一一与五行对应,由此出发,再对比、或依照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休囚旺相死、与季节的对应等多种原则,进行吉凶推算。这种五行化主要源于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都被赋予了七曜属性,即与日月五星进行配属,从而进一步与五行相联(4)汉译佛经中二十八宿各自的星占内涵可见参考文献[44]李辉博士论文。。
对于黄道十二宫,与七曜的配属可以追溯至唐《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下文简称《宿曜经》),每一宫配置七曜之一,其中太阳、月亮各配一宫,其余五曜各配两宫,如:
第一星四足,张四足,翼一足,大阳位焉。其神如师子,故名师子宫。主加官得财事。若人生属此宫者,法合足精神富贵孝顺,合掌握军旅之任也。
第二翼三足,轸四足,角二足,辰星位焉。其神如女,故名女宫。主妻妾妇人之事。若人生属此宫者,法合难得心腹,多男女,足钱财,高职,故合掌宫房之任。[38]
黄道十二宫与七曜的配属来源于域外,其源头可追溯至托勒密的星占学著作《四书》(Tetrabiblos),每宫根据其位置所在和冷热干湿等特性,都有相应的宫主(house),即七曜之一(5)可参考该书英译本中的“Book I-Of the Houses of the Several Planets”部分,Ashmand, J. M., (ed.) Tetrabiblos[M]. London: Davis and Dickson, 1822. Reprinted, Bel Air, MD: Astrology Classics, 2002.。《星命溯源》中,这一配属没有直接呈现,只是在指称黄道十二宫某宫时,不直接称宫名或相应的十二地支名,而以相应的七曜属性来代替,以进一步阐释其推算原则,如“金垣之木,木垣之土”,金垣指七曜属性为金的天秤宫或金牛宫,木垣指七曜属性为木的人马宫或双鱼宫,这些宫中出现了木星、土星,当如何推算,等等([11],页50)。若七曜中的某曜位于同属性的黄道十二宫宫中,即为“正殿”,如日午月未,即日行狮子宫、月行巨蟹宫一类([16],468册,页35A)。各宫与七曜的配属在《张果星宗》“第一·入门起例”之“宫分所属”中有明确的说明,详情如下([16],468册,页11A):

表1 《张果星宗》中黄道十二宫与七曜、十二地支的配属
《张果星宗》中的配属与《宿曜经》完全相同,从表1可知,《张果星宗》将黄道十二宫与十二地支一一匹配,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星命溯源》中,各卷在描绘具体的宫时多以地支表示而不用宫名,如“太乙抱躔于酉未,计都朝斗于丑牛”、“戌垣之火取用与卯垣不同,酉宫之金行限与辰宫有异”([11],页48、49)。须注意的是,中国的十二地支原本有自己的五行属性,如子亥属水,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辰戌丑未属土,与黄道十二宫的七曜属性完全不同。
二十八宿的五行化与黄道十二宫类似,即将二十八宿各宿与七曜匹配,《张果星宗》中同样列举了二十八宿的“度数所属”(见表2)([16],468册,页11A)。这一属性在《星命溯源》中也未直接呈现,只是在指称某宿时有时直接以七曜属性代替,如“四日度坐命,昼生忌火罗是也”([11],页53),这里的四日度即指房虚昴星四宿。在议论一个人一生中的“行限”运势如何时,直接以行水度、行日度等来表示“行限”位于相应的箕壁参轸,或房虚昴星四宿时,该如何推算运势(6)详情可见卷2、4。。若七曜中的某曜位于同属性的二十八宿中,则称“偏垣”,如日居虚房卯星四宿,月躔危毕张心四宿([16],468册,页35A)。与黄道十二宫类似,直接用七曜属性来指称具体的宫、宿,实际上便弱化了宫、宿自身原本的星占含义,而突出了七曜属性,七曜中五星可直接对应五行,而“日火也,月水也”,这样便可以直接与五行相联系,对此下文还将有进一步论述([11],页53)。
二十八宿与七曜的配属来源尚不清楚,一条重要的线索是出土历日中存在二十八宿与七曜注历的固定搭配。邓文宽曾发现黑水城出土的汉文历书残卷TK297(1182年)中每日均有二十八宿注历并将“虚”与“密”注于同一日,同地出土的汉文历书TK5285、8117、5469(1211年)在虚、昴、星、房四宿均标注“密”字,更早的敦煌出土文书P.4071(974年)和S.2404(924年)也出现了将宿(房、危)日与曜(日)日固定搭配的情况,华澜在讨论用六十甲子与二十八宿注历的七元甲子法时谈到了这一固定搭配,这一搭配与二十八宿和七曜的配属一致,详情请见表2[39—41]:

表2 《张果星宗》中二十八宿与七曜的配属
星命术中这一配属与历日中这一固定搭配的一致性,袁利在研究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占卜文书5722(1206年)时已经指出[42]。用七曜注历源于域外,这已是学界共识[43]。二十八宿注历中国古代和印度都有,有朔宿法和望宿法之别[44]。用七曜注历,七曜的排列次序为日、月、火、水、木、金、土,分别对应周日至周五,对比表1中黄道十二宫与七曜的配属,七曜的排列次序为土木火金水日月,其次第顺序明显与七曜注历没有任何关联,由此可推测这两类七曜配属应出自不同的来源。二十八宿这一配属明显是以七曜注历的次第顺序为基础,因此星命术的这一配属应来源于历日系统。
对于二十八宿与七曜的配属,陈万成将它归为中国本土产生,证据在于它第一次完整地出现在署名辽耶律纯的《星命总括》中[45]。但从该书序言可知,这部书的内容受到高丽星命术的影响,石云里认为它是传自高丽的星命著作[46]。体现二十八宿和七曜注历这一固定搭配的历日多出土于西夏地区,星命术中的这一配属很可能也源于域外。考虑到目前最早体现这一固定搭配的敦煌出土文书S.2404(924)或P.4071(974)的年代,《星命溯源》内容的形成最早应在此时期或之后,即五代时期(7)S.2404的推算结果与这一固定搭配有所不符,见参考文献[41]华澜论文,414。。
通过与七曜的配属,原本在唐宋汉译佛经中尚且具有独立星占内涵的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逐渐以七曜属性标识,在《星命溯源》中这种七曜属性还逐步转化为五行,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的这种演变在实践中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形式上的本土化。由于黄道十二宫与中土十二地支的对应,宫多用地支表示,然而这些地支宫的五行属性没有沿袭中国十二地支原有的五行配属,而是继承了黄道十二宫与七曜的配属。《星命溯源》卷一“四时论”一节中,曜、宫的命断论述充斥着地支和五行术语,如“丑宫安命不可以木为刑囚,星柳为垣亦不可以木为难。”刑囚、难明显为描述五行生克制化关系的术语。丑宫七曜属性为土,柳宿亦属土,土木在中国传统数术中原本相互克制,这里的否定反映了此处的命断不是以中国传统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则进行推论,而是用中国传统数术术语来表示与传统数术规则不同的星命内容,这反证了这些与中国传统数术相异的星命内容应来源于域外。
第二阶段,随着形式上的本土化,内容也逐渐与本土融合,五行自身的生克制化等原则逐渐替代了原来的域外星命内容。这突出地体现在“木打宝瓶、水漂白羊”等星命歌诀上,宝瓶宫七曜配属土,白羊宫七曜配属火,在中国传统数术中五行中的木土、水火均相互克制。从卷二“通玄先生评人生禀赋分金论”一节对李淳风、袁天纲、张果三人及其著作的引用来看,这类星命歌诀出自袁天纲,或者为袁天纲一派星命术的体现。该小节引述袁天纲派的观点共有10处,许多内容为歌诀式的命断,如“火烧牛角”“水漂白羊”等,以及行四日/四火/四水/四木/四土/四金/四月宿度的问题,袁天纲一派对这些宿度的命断,全部依照五行生克制化来推算,如“四火惧见漂流,四木怕逢金健。四金坐度惟怕炎火,四土何则为忌,强梁之木要得金刚。四水何则为妨,壅遏之势要得木执。”([11],页54)
第三阶段为用中国传统数术综合域外星命术和中国本土内容,形成新的本土化星命术。典型地以卷二“通玄先生评人生禀赋分金论”一节中张果的言论为例,有7处他引用了袁天纲的观点,其中多为谈论行宿度的问题,张果应用五行“旺相休囚死”的属性,对袁天纲依照五行生克制化规则作出的论断进行了全新解释,认为当王之时不怕克制,当死之时即使逢生也无力,一一对4处袁天纲的论断重新进行了解释和发展。不仅如此,对于源自域外的星命论断,以李憕引证《天纲集》中的“一生侘憏对官,怕逢罗火”为例,张果说其“得其说,而不知其所以说”,用实例对其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况分别进行了叙述,并给出了相应解释,文中有3处谈论火命人不忌讳命宫出现罗火的情况,因为火命人“乃是星照本家,反为吉论”。这种全新阐释应是对星命术初次本土化之后的再次深化(8)该论断源于与域外星命术有关的“昼忌火,夜忌土”规则,见宋神秘, 钮卫星. 唐宋时期土星在军国星占术和星命术中的善恶取向[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 98—99.。
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的五行化演变,由于与七曜的配属,在唐、五代时期已经具备了条件,第一阶段至少可以肇始于此。随着宋金时期张果位列八仙、其形象在社会中的广泛流传,术士借张果之口来传播星命术,第三阶段的发生最早也应在宋代,最晚可至明嘉靖二年。而第二阶段则处于这两个阶段之间。此外,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的五行化很可能有先后之别,黄道十二宫与十二地支的匹配在唐宋的佛道藏文献中已经出现,其五行化演变在宋或宋以前已经产生,而由于二十八宿与七曜的配属出现得相对较晚,其五行化演变可能较晚发生[47]。
4 宫宿之争
星命术中用作坐标体系的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在它们通过与七曜的配属逐渐五行化的第二、三阶段,产生了在定位每个人的命运和运势时谁的权重更大的问题。以命为例,有命宫和命度之分,如出生时太阳所处位置是以宫来论断,还是以宿度来评判。从唐宋汉译佛经可知,黄道十二宫各宫和二十八宿各宿分别具有独立的星占内涵,理论上存在的分歧并没有在汉译佛经中体现出来。《星命溯源》中,当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都与七曜配属后,同一个坐标点同时具备宫的七曜属性和宿的七曜属性,两者互不相同。
从《星命溯源》各卷内容来看,卷一各节多谈论宫,卷五也以论宫为主,似乎以宫为重;卷四由于内容杂乱两者均有涉及;卷二、三中对这一问题有直接的说明和讨论。卷二第一节“通玄先生评人生禀赋分金论”开头便以张果的口吻对此阐述道:
前辈袁天纲号为善知天文象纬,曾会诸星宿于竺罗,察祸福犹病鸢鱼,及得予旨,方知专用宫主为非,度主为是。初又以宫主度主互用,在命或三方者用之于宫主,遂专用宫主,验之愈疏。
这段话体现了星命术中对宫、宿度的使用存在不同观点和派别,起初专用宫,然后为宫、宿度互用的第二阶段或第二种,第三种更重视宿度,而且发展于第二阶段或第二种,这三个阶段在当时的社会中表现为不同流派之间的区别,如前文提及该节中所谓的袁天纲一派。
早前通过佛经输入中国的域外星命术,主要依据命运十二宫来推算,应是专用宫的第一阶段。唐杜牧《自撰墓铭》有“予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工杨晞曰:木在张于角为第十一福德宫,木为福德大君子,救于其旁,无虞也。”[48]可以看出杜牧对自己命运的推算都是根据宫来进行,即便他用角宿来标记自己的命位,但祸福的推算都是依据宫进行,而不以宿度为基准。
宋时,苏轼也谈及自己的命运“吾命在斗间,而退之身宫在焉,故其诗曰:‘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且曰‘无善声以闻,无恶声以扬。’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耳。”[49]可以看出,他虽然用斗宿标记自己的命位,但命断的依据是宫,即斗宿所在的摩羯宫,据《宿曜经》,磨竭宫“主斗诤之事”(同[38]),正与苏轼的命断吻合。苏轼认为自己的命运与韩愈相似,韩愈的命运,据其自述为“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无善名以闻,无恶声以攘。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三星各在天,什伍东西陈。嗟汝牛与斗,汝独不能神。”[50]这一命断主要由出生时天象中的箕宿决定,而与牛、斗宿无关,同据《宿曜经》,箕宿的星占含义为“此宿生人,法合游涉江山经营利闺,为人耐辛苦”,可与韩愈生平中的“无时停颠扬”相对应,但有关声名的论述,则与箕宿无关,可见此处韩愈虽然声称是以宿度来解释命运,很可能运用的仍是摩羯宫的占辞(9)此处笔者还查阅了唐及唐以前的其他星命术文献,如《摩登伽经》等,其中对箕宿的论述也与韩愈的生平不符。([38],页390)。
对于这类命运,南宋文天祥也有自己的论述“磨蝎之宫星见斗,簸之扬之箕有口。昌黎安身坡立命,谤毁平生无不有。我有斗度限所经,适然天尾来临丑。”[51]诗中,他同时用摩羯宫和斗、箕宿的星占内涵来重释韩苏二人的命运,同时提及自己的星命,也是以度和宫两者为基础进行推断。据《摩登伽经》“月在斗宿,不宜忿诤”,似乎除摩羯宫外,斗宿也主斗诤之事[52]。这一方面表明韩愈和文天祥所依据的星命文献或当时流传的具体星命观念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体现出南宋与北宋、唐代的星命推算方法已有差异,韩愈是单独应用宿或宫的占辞,苏轼用的是宫,应用的是星象的直接星占内涵,而文天祥已经将两者结合起来,与前述的第二阶段或第二种对应。
敦煌文献P.4071(974)对人出生时星象的描述兼及宫宿两者,如“太阴在翌,照嬖女宫;太杨在角八度,照天秤宫”,同时还记载了宫宿的推算规则,其“推五星行度宫宿善恶”有“土在本宫,白日生,多温和下心于人,若夜生,多难足病,若在本度亦煞;木在土宫……;火在水度,一生多施恩……;日在木度……;金在木度……,水在本度……”[53]。文中对宿的表现方式与《星命溯源》类似,用所属的七曜属性来表示具体的宿度并进行推断,该文献中大部分星命推算仍是以宫为基础,可见北宋敦煌地区流传的星命术已经发展到宫宿并存的第二阶段,而且此时的宿已经不是天象意义上的宿,而是用七曜属性表示的宿度。
综合以上,考虑中原传世文献和敦煌出土文献的时间,以及最早记载二十八宿与七曜配属的《星命总括》自身的域外特征,可以推测专用宫的第一阶段为唐至北宋时期,宫宿或宫度并用的第二阶段为北宋至南宋时期,宫度并用很可能率先出现在敦煌等西北边境地区,然后再流传至中原。道藏文献《灵台经》中多以宫为基础进行推命,但也论及宿度,很可能这部经的形成时间也在第二阶段[54]。
重视宿度的第三阶段应出现在南宋至元代之间,在元代时已经大为流行。《星命溯源》卷三“身命为元”条下,郑希诚对重视宿度的原因进行了详细解释,
命主即坐命处二十八宿之所属是也。……又曰:宫主州也,命主县也,莫不自县而州。愚常谓:宫主犹人家也,度主犹家之主也。一宫之内,大率有三等星度,犹一家之中子父兄弟,不同坐度之星,犹家主一人独掌家务,则凡家人亲友随一人之好恶为亲疏。故度主是木,则以水为恩,以土为仇,以金为杀。若度主不是木,则又有别样好恶,譬之家人之中,人殊则情亦殊。若只以一宫之主泛论祸福,必无切验,故知诸家论宫主而不论度主者,皆不若果老之说为亲切体要也。愚断以果老书为经,以诸家为纬,以度主为先,以宫主为次,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歌曰:世人未识星家理,不务心传务口耳。生时坐度作虚名,只把命宫星作主。阴阳经纬何纵横,俗眼无由见始终。诸宫皆可论宫辰,命元切以度为主。此是先生玄妙机,须得高贤方说与。
郑氏分别用州县、家主和家人的比喻阐释了度主应重于宫主,并指出这一结论他是“从果老书为经,诸家为纬”,综合各家言论后得出的,结合卷二呈现出的不同派别如前引袁天纲派,可知张果一派很可能以重视宿度为特征,而郑希诚是继承和发展这一流派的重要人物。卷四“郑希诚观星要诀”的131条星命论断中,有56条涉及命度,论行限甚至流年时也多以宿度为基础而不是以宫来推算,可见其所处的时代更加重视宿度。
宫宿之争发展到第三阶段,可以看出无论是强调宫、还是宿度,其本质是强调宫和宿度的七曜属性,这种七曜属性从前述第3节的论述可知,是星命术发展向五行化演变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一争论的结果是五行的生克制化、旺相休囚死等推算原则最终取代了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自身的星占内涵。
5 星命术对神煞的引入
星命术本质上是一种以天象为基础的占卜体系,这种天象抬头实际可见,或可依据星历表推算得出,这种推算则以实际存在的天体如日月五星或天文概念罗睺、计都为基础。在中国传统的数术体系中,根据干支、八卦等符号发展出的用于军事、生产、墓葬、疾病等目的的神煞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星命术传入中国后,与这些概念和规则融合,在中国本土星命术的发展过程中它们逐渐成为与十一曜天体并列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神煞的使用遍布《星命溯源》各卷。卷一有关神煞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五星论”一节中,如“大耗小耗值天地耗,忌守田财;官符死符见岁月符,怕临身命。”这些神煞有许多在中国传统数术中早已存在。以大耗为例,清《星历考原》卷二“年神方位”中记有“大耗”:“大耗者,岁中虚耗之神也,所理之地不可营造仓库、纳财物,犯之,当有寇贼惊恐之事”[55]。该书记载大耗的推算方法为“常居岁冲之地”,即所谓的“岁破”[56]。若太岁为“子”,则大耗为“午”[57]。敦煌历日《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S.P.6)每月都标出大耗所在,其推算方法相同,为每月月建的对冲地支,只是这里的大耗从岁神变为月神[58]。月神的这一规则和运用可追溯至汉《太平经》“当月建名为破大耗,当帝王气冲,为名死灭亡”[59]。这里,大耗尚未形成独立的神煞概念,但其与帝王气所在相“冲”的推算规则已经形成,至唐韩鄂《四時纂要》“正月”中,这一规则和名称已经正式使用,正月建寅,其“移徙,大耗在申。”[60]大耗便是月建对冲所在之地。《星命溯源》中“大耗”所在,“忌守田财”,这一神煞昭示的内涵与中国传统数术一致,其规则据《张果星宗》“太岁第七宫为大耗”,即为对冲宫的地支([16],468册,页16B、18A)。
除中国传统的神煞外,《星命溯源》中还有许多中国传统数术中没有的神煞,这些可能来源于中国传统数术与星命术发生碰撞后产生的新神煞。上述引文中的大耗小耗为中国已有的传统神煞,天地耗则不然。《张果星宗》记载了一种月天耗,规则与“大耗”稍异,为“正七二八子寅方,三九四十辰午当”,即正月、七月在子,二月、八月在寅,这类月天耗主雷霆杀,若当之,必有雷虫虎咬亡([16],468册,页16B—17A、19A)。月天耗的规则与大耗非常相似,可以推测是借用了大耗的推算方法,以表示一个新的主雷虫虎咬亡的神煞。
但“天耗”仍可以是一个主“破耗”的神煞,《张果星宗》和《星学大成》还记录了另一种天耗“此星耗财之星,忌在田、财二宫”([14],页299)。其表现形式不是地支,而是“金土月水炁计罗火孛木”十曜之一,分别对应“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年干([16],468册,页17B)。用十曜表示的神煞,并不只有天耗,星命术中称其为“变曜”,包括天禄、天暗、天福等,匹配规则为“禄暗福耗阴,贵刑印囚权;火孛木金土,月水炁计罗。”([16],468册,页15A)若甲生人,荧惑为天禄星,月孛为天暗,太白为天耗,依次类推。所谓“变曜”是因为这十曜分别由十天干变化而成,不包含太阳,后世对此的解释为“盖十曜皆由阳君所授,分配十干而化为禄,一定之序也。”([14],页297)
卷四记载的“官魁例”即为变曜“官星”和“魁星”,其推算以天干为基础,两者规则不同。以官星为例,《张果星宗》记载甲以辛为官,辛对应的变曜为炁,因此甲以炁为官星([16],468册,页15B)。甲以辛为官,即八字算命术中甲的正官辛,依据原则为阳干克我者,或阴干克阳者为正官,甲为阳木,辛为阴金,金克木,因此甲的正官为辛[61]。至于辛的变曜为炁,《张果星宗》说辛以炁为禄,考中国传统数术中禄的概念,为天干对应的阴阳与五行属性相同的地支,即甲为阳木,其禄寅亦为阳木,乙为阴木,卯亦为阴木等等,但辛为阴金,对应地支禄应为酉,而炁从五行上来说为木余气,无论如何在阴阳、五行上也无法与辛相配,因此这里禄的概念与中国传统中的禄不同([16],468册,页15B)。《星学大成》注“十干变曜”,说其所以然之理无可稽考,因此这一搭配的来源尚不清楚([14],页297)。
“魁星”的规则为“阴阳和合相生而成魁,独不以土为魁者,以土愚浊故也。”([16],468册,页15B)若以中国传统数术中天干的阴阳五行属性论,甲为阳木,其与阴水相生,月为水,属太阴;乙为阴木,其与阳火相生,日为火,似乎合论;但丙为阳火,罗为火余气,属同类,因此不合。若以变曜论,甲变曜为火,与月相孛,既不相生也不相合,因此其具体规则也不明晰。即便如此,从其解释来看,这两个神煞无疑借用了中国传统数术的思想和规则。
将十干与十曜相配,应是域外星命术进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数术相结合产生的新生事物。这一结合可以从《广成集》中的星命醮词找到些许线索,许多醮词都将星曜和神煞并列叙述,如“五鬼临于坤位,火曜躔于升宫”(《川主令公南斗醮词》)、“金火行于身宫,纲星加於驿马”(《周常侍序周天醮词》)。五鬼、纲星等神煞多为凶煞,多主“三命五行之厄”(《川主令公南斗醮词》)。醮词中多次将天文与三命并举,如“祛五行三命之灾,解宿度天文之厄”(《杨鼎校书本命醮词》)、“解天文地分之凶,去三命五行之咎”(《川主周天南斗醮词》)、“解五行三命之灾,销列宿暗虚之厄”(《衙内宗夔本命醮词》),天文部份对应星曜和宫宿,而三命五行对应的是神煞和八字算命术的内容,如天符和财位,体现出此时星命术和八字算命术同时在社会中广泛流传。
“三命”术是八字算命术的一个流派,以四柱八字为算命依据,三命即天元、地元、人元,分别为生辰的天干、地支和纳音[62]。《张果星宗》中有天元禄、地元禄、人元禄的神煞概念,但具体内容和推算方法已经不同([16],468册,页16A)。五代时的星命术和三命算命术,可能正处于相互接触和融合的阶段,在天文星曜和三命五行并列叙述的例子中,出现了神煞进入宫宿的情况,如“又今年五鬼在于妻宫,天符入于财位”(《周常侍序周天醮词》),五鬼明显不是星曜,是三命算命术中的神煞;又如“今年三命之内,土木气微;行运之中,命禄皆薄。天符临官禄之位,游年当绝命之方。大运则土曜所加,小运乃元辰所主。”(《衙内宗夔本命醮词》)土、木等星曜这里也与三命、大运等八字算命术的概念结合,不再局限于宫宿的位置。可见五代正是星命术和以神煞为组成元素之一的八字算命术相互影响、融合的时期,不仅八字算命术中的神煞、大运等概念被运用到星命术中,星命术中的星曜、宫宿等元素也渗入八字算命术,元明时期最终形成的中国本土星命术应肇始于此时,八字算命术的引入是其本土化发展的一大促进因素。
6 结语:星命术的流派和综合
综合以上对《星命溯源》作者、年代、内容和所体现出的星命术发展过程的考察,可知该书涵盖了星命术从五代至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容,其内容形成年代不一,卷一偏重于十一曜和宫的星命论述,形成时间上可能最早,应在五代至北宋之际,卷三正文部分形成时间可能相同,但注释内容稍晚,为元末明初郑希诚所作;卷四为郑希诚所作,收录的星命术应为宋尤其是南宋至元代内容,注重宿度;卷五应形成于卷四之后,为元至明代所作,形式上虽以十一曜、宫为主,但非常强调宿;卷二内容应形成于元明时期,强调宿。以上各卷都强调了神煞的运用,与星曜并重。
这些形成于不同时期的内容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不同的流派呈现出来,如前文所述宫宿五行化、宫宿之争形成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流派,这些流派的不同一方面在于形成时间的先后,更重要的是内容和观念的差异。卷二末有题记“术家有《壁玉经》《耶律经》《历象赋》《星家躔度歌》,亦太阴分金,支分派远,其实出乎此。”([11],页61)这里四书并举,称它们“支分派远”,透露出星命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流派,《耶律经》可能为耶律纯《星命总括》,非常重视宿度。《壁玉经》可能与后世流传的《壁奥经》关系密切,如此则为专论“星格”的一派(同[18])。
前文提及《张果星宗》还收录有《历象赋》一首,内容简短,论述十一曜位于黄道各宫的命断,一部分用原始的黄道十二宫名称,另一部分用各宫对应地支相应的地域分野,其推算不用五行推演原则,应为域外星命术的内容([16],468册,页41B)。而且,比起星命术后来的发展,它只论述了十一曜在宫的命断,而不涉及宿度,如此其代表的流派很大程度上应为早期域外星命术的代表,该派即张果所谓的“专用宫”一派。
《星家躔度歌》目前暂未见到同名歌赋,但《张果星宗》第十二至十五论述十一曜各篇中都有“躔度”一小节,如“太阳躔度”下有“日心:日躔心宿号天昌,白日生人福寿康,若至晚年尤享福,一生终是足衣量。”([16],469册,页10A)为专论十一曜运行至各宿度的命断,应为张果所谓“重度主”的一派,与《历象赋》一派形成对比。
因此,所谓张果的星命术至明代时已是综合星命术各流派内容的集大成之作,星命术内部各流派间的分歧和融合,一方面来自于域外不同星命术之间的差异,如对宫和度的不同重视等等,另一方面源于星命术不断与八字算命术等中国传统数术门类之间的融合,如引入神煞。而所谓的张果星命术,实际为区别于紫微术、八字等算命术类别的五星术一派,其传承始于五代的星命术士,宋金以后他们利用张果的社会名声将其术托名张果得以在社会中流传,随后由元末明初的郑希诚继承,最后传至明代的李憕。中国本土的星命术,在组成上囊括了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等星曜体系与五行、干支、神煞等基本概念,方法上既保存有域外星命术依据星曜位置关系等形成的推算原则,也融合了中国传统数术中五行、干支、神煞相关的逻辑推算原则,最后形成了一种与希腊-印度星命术既相似又不同的中国星命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