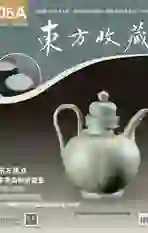飞青点彩
2019-10-21叶英挺竹大和男
叶英挺 竹大和男
最近在日本一藏家處上手了两件龙泉青瓷,一件是明代的观音佛龛,精虽精矣,却无甚突出的地方。另一件元代点彩玉壶春瓶,则令人“一见倾心”。瓶子被主人置于壁龛上,墙上挂了画,一旁还有简约的花道等小摆设,令人想起宋人的“挂画插花”传统。唐人云“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典雅)”,若说诗有诗品,那么瓷也可以有瓷“格”。如玉壶春这一造型,可奉为瓷品中之典雅一格。而这件玉壶春瓶可谓典雅格调的最好注解。
这件玉壶春瓶喇叭口,束颈,溜肩,垂腹圆鼓,圈足。整器轮廓线条流畅柔美如一水滴,端庄而不失灵秀,青釉呈色青莹淡雅,质感如冰似玉,褐斑点染自然,冲淡素雅。
褐彩装饰,最早起源于西晋晚期的越窑,元代龙泉窑继承发展了这一技法。它利用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作材料,在青釉瓷上点染烧造,烧成后即呈褐斑装饰。与青釉相衬,鲜明夺目,大大提高了纹饰效果的表现力。就传世器而言,点彩手法在元代龙泉窑中的运用比较广泛,但精品并不多见。与普通青瓷相比,点彩青瓷对于釉色的要求无疑更高,过烧或欠烧导致的偏色,以及釉面的开片都会大大削弱褐斑的美感,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其次,施彩手法也很关键,自然清新的彩斑令人遐想,而呆板造作的斑点恐有画蛇添足之嫌。以此两点而言,本品呈现的是一种罕见的“不完美之美”。本品器式比例精准,形制典雅,“美中不足”是烧制过程中温度稍高,釉色并没有达到“炉火纯青”,包括圈足露胎处的火石红,以及装饰的褐斑呈色上均偏淡,且釉面有少量稀疏开片。但整器观之,却有一种独特的冲淡之美,含蓄婉约,温文尔雅。其实,窑温高了也不一定是“败笔”,比如瓷化程度更好。如本品玉壶春瓶,相较于一般的龙泉青瓷器,釉质更为莹澈通透,如积水空明,褐斑虽不够鲜艳,却有水墨般的渲染效果与韵味,艺术感非常强。
类似点彩玉壶春瓶亦见于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瑞士远东艺术博物馆等相关珍藏。最知名的一例则是现藏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被日本指定为国宝的“元龙泉窑青瓷褐斑玉壶春瓶”, 日人呼作“飞青瓷花生”。“飞青”即指点彩,以字面解读,犹如天边飞来的一抹云霞,极富诗意。“花生”指花瓶,花养入花瓶能继续存活,故曰“花生”。“飞青瓷花生”在当时的日本是茶室、武士门第和朝臣书院等处用来装饰茶道的花瓶。这几例点彩玉壶春瓶,器式接近,体现出时代的共性。就釉色而言,是造化天成的不确定性,深浅浓淡中,是青釉呈色的千变万化。而最具个性的则是褐斑的点染手法,褐斑有大有小,形状不规则中仍能见出纵横的差异,纵者如落红,横者如飞霞。若本品,则如朦胧水墨,正所谓“恬淡为上,胜而不美”。
玉壶春瓶形制优美,用作花瓶自是风雅。不过从多例考古资料来看,元时更多是用作酒器。元代墓葬壁画及大量墓葬窖藏等出土器物的伴出关系表明,玉壶春瓶和匜(时人呼为“马盂”)、盘盏是流行于元代的一套酒器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