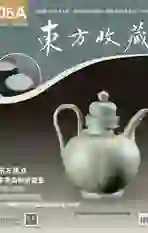苏轼与定窑
2019-10-21夏文峰
夏文峰

定窑瓷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裝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等。印花以花卉为主,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等,也有鸳鸯、龙凤、狮子等动物图案,画面严谨,讲究对称。工整素雅的白釉印花定器历来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
宋代是定窑的发展时期,产量、质量以及制作工艺较五代又有明显提高。但文献记载对宋徽宗以前时期的定窑很少论及。早期定窑饰以浮雕莲瓣纹的居多,莲瓣肥大,与五代宋初越窑风格类似;早期定窑均用匣钵装烧,不见有芒口碗,可知尚未采用覆烧工艺。中期定窑的浮雕莲瓣纹明显减少,葵瓣口相对比较多,萱草划花纹开始出现。北宋后期定窑广泛采用覆烧法,口沿多不施釉,再在芒口处镶金嵌银,成了金边、银边白瓷珍品。
定瓷在宋代是相当珍贵的。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载:“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仁宗宠遇贵妃先于六宫,其责以正礼尚如此,可谓圣矣。”宋仁宗是个非常俭朴的皇帝,有一天他跑到他的宠妃张贵妃那里,突然看见一件定州红瓷器。他就问:“你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啊?”这妃子就跟他说:“是一个叫王拱辰的大臣送的。”皇帝生气了:“我经常告诉你,不要接受大臣的馈送,你为什么不听呢?”说完以后,手持柱斧,当场把它打碎了。臣子将定瓷送给皇帝最宠爱的妃子作为礼物,可见定瓷在当时社会的地位和珍贵程度。
定瓷历来与许多帝王(如清乾隆皇帝曾作诗30余首咏定瓷)、大文豪、大学者关系密切,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气息。其与宋代大文豪苏轼的渊源亦值得探讨。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六月二十六日,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衔除知定州。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任,至翌年即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罢黜离职,苏轼在定州仅仅半年的时间。
苏轼知定州期间,曾遍巡太行沿边重镇。在曲阳县,有作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瓷窑厂。宋代定瓷,制作技艺精湛,造型精巧,装饰绚丽,瓷质莹润,有“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美誉。苏轼十分珍赏定窑瓷器,曾在《试院煎茶》一诗中夸赞“定州花瓷琢红玉”,评价很高。他知定州期间,精选定瓷作为珍贵礼物送给弟弟苏辙,并附《寄馏合刷瓶与子由》诗歌一首,认为“小甑短瓶良具足”,即瓷器光泽品相具佳,可与“稚儿娇女共燔煨”。遗憾的是,在关于苏轼的历代文献及苏轼所作文章中,却都没有其本人与定窑、定瓷相关的任何记载,而其所作文章中提到定瓷者也仅仅只有三篇,实不知为何也。
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八月,时苏轼任杭州通判。是年八月科场,苏轼监试,作《试院煎茶》诗:
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
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
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古语云:煎水不煎茶)
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
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
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
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
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该诗不仅论及了茶与水、火的精妙关系,还提到了当时非常珍贵的定瓷茶具。苏轼通过宰相文彦博用定瓷喝茶,说明在宋朝上流社会使用定瓷是一种时尚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可见,苏轼十分珍视定瓷,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并使用定瓷,这为他以后到定州任职并且亲自见识到定瓷作了铺垫。
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十月十四日,苏轼作《独酌试药玉滑盏,有怀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诗招之》:
镕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
琢削为酒杯,规摹定州瓷。
荷心虽浅狭,镜面良渺弥。
持此寿佳客,到手不容辞。
曹侯天下平,定国岂其师。
一饮至数石,温克颇似之。
风流越王孙,诗酒屡出奇。
喜我有此客,玉杯不徒施。
请君诘欧陈,问疾来何迟。
呼儿扫月榭,扶病及良时。
苏轼在该诗中再次提到了“定州瓷”,说明了当时的“药玉盏”即玻璃酒杯是摹仿定州的瓷器所作。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玻璃器不如瓷器贵重,且仿制定瓷的器型,可见定瓷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高,苏轼对定瓷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皇天不负苏东坡。终于有一天,苏轼来到定瓷产地定州任职,总算如愿以偿。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十二月二十五日,苏轼于定州任上,给弟弟苏辙寄送定瓷“馏合刷瓶”,并作诗《寄馏合刷瓶与子由》以纪念:
老人心事日摧颓,宿火通红手自焙。
小甑短瓶良具足,稚儿娇女共燔煨。
寄君东阁闲烝栗,知我空堂坐画灰。
约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枣待归来。
“馏合”为饭甑之类,蒸饭小甑。“刷瓶”待考,疑为煮饭用具。馏合、刷瓶,皆为当时定窑新产品。
苏轼与苏辙兄弟感情深厚,苏轼将当时最为珍贵的定瓷赠送给弟弟苏辙,可见苏轼对定瓷的珍视程度。以苏轼之幽心,面对情深意重的弟弟,此必是千挑万选之瓷器。他选的这一套定瓷,蒸、煮、烤皆能,可谓功能强大,更加突出对兄弟之真挚感情。以苏轼之雅致,前往定窑了解风土人情,亲自挑选精美瓷器送给弟弟,想必是可期的。
以当时北宋的文化氛围、苏轼的身份地位、文化修养和他对定瓷的珍爱程度来看,苏轼使用定瓷甚至是定制定瓷都是合情合理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件北宋定窑刻划花莲瓣纹盏,圈足内刻“彦瞻”二字。马春雨在其硕士论文《定窑铭文考释》中指出,“彦瞻指代的正是苏轼”,并进而指出,该“彦瞻”款北宋定窑瓷盏不是苏轼自己在定窑定烧的,而应是别人知道苏轼爱茶的癖好,特意送给他的。作者由此得出结论:第一,“彦瞻”款定窑白釉碗从釉色和器型上看,应为北宋产物,与苏轼时代相符;第二,苏轼饮茶且在诗中提到过定窑白盏,喜爱饮茶之人追求精美的茶具也是理所应当的;第三,苏轼博物好古,喜欢收集;第四,苏轼曾于元祐八年被贬知定州,更多了一份与定瓷的联系。因此,该“彦瞻”款北宋定窑瓷盏是苏轼之物。另外,苏轼挚友道潜(即参寥子)有诗《次韵彦瞻舟次三墩见寄》,“彦瞻”当为对苏轼的尊称,亦可证明“彦瞻”当指苏轼。
胡云法先生《北宋定窑“子瞻”铭文白瓷碟刍议》揭开了苏轼曾定制定瓷这一谜团。胡先生有幸观赏了海外藏家的2件定窑白瓷“子瞻”款小碟(图1、图2),其一高0.8、口径6、底径5.1厘米。圆口、弧形浅壁、平底无足,芒口覆烧。其二高0.8、口径6.1、底径4.4厘米。圆口、折腹浅壁、平底无足,芒口覆烧。两碟造型端正精致,釉色润白,除碟壁外形稍有差异基本相同。两碟外底“子瞻”铭文系在器物成形后,入窑烧制前所刻。字迹秀美,当出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窑工之手。两碟具备北宋后期瓷盘碟造型的基本特征。
作者从定窑铭文的演变轨迹与分期特征、苏轼的生平经历与定窑瓷器关联的探讨、定窑“子瞻”款瓷碟的年代特征和用途、定窑“子瞻”铭文落款习俗与类似铭文的讨论等四个方面展开研究,认为苏轼出任定州期间,是其和定瓷结缘的最好时机。北宋后期定窑为朝廷烧造贡瓷,作为定州经济和税收的重要支柱,肯定会引起苏轼的重视和关心。苏轼有机会关心、接触定窑,存在地域和时间上的关联。因此,把定窑“子瞻”款瓷碟的烧制时间定在苏轼定州为官时是合适的。定窑“子瞻”款碟的尺寸较小,明显不同于常见的瓷碟,应该是按主人自己的意愿而定制。经作者考证,该瓷碟应为文房用具之笔觇(笔舔),苏轼身为文学家和书画家,烧制定瓷小碟用于舔笔、试墨等,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存有需求的倾向。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定窑白瓷“子瞻”铭文为苏轼的字号,瓷碟为苏轼在定州为官期间(1093—1094)定制的器物,总体特征符合北宋晚期定窑盘、碟的基本要素,为北宋后期哲宗元祐年间的产品。苏轼定窑“子瞻”铭文碟的问世和讨论,拓宽了对苏轼文化领域研究的视野。
无独有偶,河北博物院“河北古代名窑标本展”特展上有一件“子瞻”款白釉定瓷盘残件(图3),盘底刻“子瞻”二字,与胡云法先生所见两件瓷碟款识相近,与2018年1月某拍卖公司20周年庆典拍卖会推出的一对明以前定窑“子瞻”款笔觇白瓷碟(图4)相对照,款识几乎如出一辙,很可能出自同一窑工之手。该残件现被私人收藏。据介绍,该残片出土于定州文庙附近的基建工地,文庙一带在宋代正是定州府衙所在地,苏轼所种“东坡双槐”就在今天的文庙院内。该地发现“子瞻”款定窑盘,说明其和苏轼的关联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