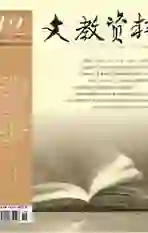论灰娃诗歌中的死亡想象
2019-10-14李宇舒
李宇舒
摘 要:本文主要阐述灰娃诗歌中的死亡想象,这些想象常常伴随着坟墓、黑夜、鬼魂与亡灵等意象出现在诗中。灰娃的诗歌是诗人心灵破碎流血后的自我倾泻、抚慰,是一种如同受伤的兽在痛呼的反应,如同灌注了激情的行走自然成了舞蹈。投入感情的话,出口便自然成了诗。
关键词:灰娃 自我回归 死亡想象
一、自我回归
灰娃作为诗人是一个另类,她从未想过要成为诗人。灰娃1927年生于陕西,十二岁进入延安青年剧院儿童艺术学园,在延安的革命大家庭中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她生性纯洁而晚熟,在延安被当作“八路军的公主”受着众人的宠爱。她在自传《我额头青枝绿叶》中回忆道:“延安是一个大家庭,而北京却是一个大社会。”[1]在北京接连不断的运动里,灰娃常常受到污蔑与批评,她未经世事的内心经不起这般压抑,充斥不解与委屈,渐渐地她患上被虐症,“文革”时期其心理疾病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灰娃说:“我很不情愿做那些事,藏在心中又不敢言说。内心与社会环境越来越抵触,加之‘文革所见所闻,就造成了我精神的反常,以致发展成精神分裂症。”[2]
患上精神分裂症的灰娃在偶然之间,竟然找到了治愈了自己的方法——诗歌。灰娃说:“人生和世事馈赠我以诗。它让我的心摆脱了现实对我的折磨,超越于平庸烦琐的日常。”[3]这正是王鲁湘在研究灰娃时所提出的“自我谈疗”。因为灰娃从未想过要成为诗人,她写出来的句子或许与其称之为诗歌,称作表现为诗歌形式的私人内心对话更恰当。它们是心灵破碎流血后的自我倾诉,是一种如同受伤的兽在痛呼的反应,如同灌注激情的行走自然成了舞蹈,投入感情的话出口便自然成了歌。灰娃说“写出的文字是我心灵的载体”[4].发乎自然流露的文字是灰娃心灵的歌声,矫正了她所处的扭曲颠倒的世界,因此使她感到如同回归精神家园般的平静,具有疗伤的效果。在写诗过程中灰娃不断回到过去的美好日子,“往事往昔种种,虽已遥远,但依然温暖地活在心上,抚慰着我的生命,散发出人情人性之美,诗意地照临着我的内心世界。……却如‘精神木马一样支撑着我”[5]。这些充满人性温暖的回忆使得灰娃能保持对世界的热爱,将纯洁心灵保鲜在久远的过去。
二、死亡想象
在诗歌中,灰娃的思绪常常飞回故乡、土地与死亡,感受生命的真实。“时常,思绪还游到阴间……这刻骨的遗憾之悲凉是莫测的、不可解的”[6]。
灰娃想象自己的葬礼,朴素又自然,树林中点着蜡烛,烛火、琴声与萨克斯声伴着清风远扬。死亡在这里不是可怖的,而是能从战阵划分与批斗的泥沼中解脱的轻松自在。“清风把这音乐扬起,琴弦悠长萨克斯呜咽/烛火摇曳青枝绿叶轻颤/朴素高贵的葬礼俄再不担心与你们/遭遇陷身那,无法捉摸猜也猜不透的战阵/我算是解脱了”[7](《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题为《墓铭》的诗是写给自己的墓志铭。灰娃柔软单纯的心被世人残忍地撕开,鲜血淋漓,她想象自己死亡之后埋入土中,再也不用睁眼被世间万事烦扰,自己的额上长出郁郁葱葱的桂树。这里所写额上的树叶与《我额头青枝绿叶……》相吻合,而且这两首诗基调极为相似,又同为灰娃的外甥女肖菲代为保管的诗稿,或许是诗人病得最严重时同时写出的。与诗人愤怒痛斥的残暴世间相比,她所想象的死亡祥和又宁静,像一片归根的落叶一般自然。“我眼睛已永远紧锁再也不为人世流露/深邃如梦浓荫婆娑/安息着我额上青青的桂树,谁给栽的,我/已然沉寂不醒/松涛凝定不动一口静穆万年的钟/想起我挂了重彩的心它/一面颤抖一面鲜血直流/如今它已停止了跳动世人再不能/看它遭严刑而有丝毫满足”[8](《墓铭》)。
在《不要玫瑰》中,灰娃以嘱咐的口吻再次想象了自己的坟墓,她的墓上不需要代表虚妄的浪漫的玫瑰,不需要生者的供奉,她已与土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长青藤与山水会为她哭泣,文豹会为她衔灯。土地下漫长的黑暗里无人打扰,她可以远离人世的受苦与熙熙攘攘,长久地沉思。“不要玫瑰不用祭品/我的墓长青藤日夜汹涌泪水,清明早上一只唤春低唱,文豹衔一盏灯来/匆匆赶来安顿歇息/我沉思在自己墓地/回望所来足迹/深一脚浅一脚……/我已告别受苦的尘环/这儿远离熙攘的人世……/黑夜里我听见山水呜咽奔流”[9](《不要玫瑰》)。灰娃称死亡是“纯洁无辜永无希求”的,人们不需在告别人世时不舍叹息,不需挂念凡间纷扰或未澄清的冤情,长眠后坟头自会开放一朵素静百合,抚慰自己的心灵。“当我们告别人间依稀长叹/可还有什么值得顾盼/为何总不肯闭合双眼/它是那样纯洁无辜永无希求/当我们长眠在荒墟墓园/坟头松枝荫蔽一丛素静百合/抚慰寂寞含冤的心愿”[10](《路》)。灰娃常常想象着鬼神与亡灵的存在,思考包含了死后存在的世界。她称湘西武陵源自然保护区“神秘诡谲,聚散幻化,瞬息莫测,果真楚国游魂故地山鬼故家”[11],在诗歌《山鬼故家》中她将此地描述为“神界鬼域迷宫的残骸”(山鬼故家),是鬼魂归来的故乡。“山鬼故家”是灰娃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的名字,可见灰娃对鬼神的意象之痴迷。她描写墓地的神秘幽寂:“那时黑夜还正揪住黎明?/夜气浓湿古坟幽寂/原野布满埋伏”[12](《穿过废墟穿过深渊》)。在《乡村墓地》中写道:“永恒不改的只有咬噬人心的寂静,亡魂游荡飘零,神秘虔诚的凭吊。如魔似迷,幽玄冷森,叫人心跳却又亲近。……這坟墩儿上,今天竞开出一朵花,孤零娇矜,火焰一样,在古老阴森的柏树丛,照眼惊心发着红光。”[13]灰娃还描写了乡间的墓地:“阴气弥漫乡间墓园,轰轰然林隙导入光的泉光的瀑,干线万点迷离飘扬,仿若一片亮亮的幻象,一座颤抖神光鬼火的灵殿。嬉笑呼唤驾着风,亡魂们惊讶了,停下脚步,似有哭声叮咛从地缝钻出……这儿黄土掩埋着整段整段的旧梦。”[14](《土地下面长眠着——》)她在描述对故乡的村子的依恋时,也写其中的幽灵:“我怎么能说清,夜幕低垂,笼罩弥漫我们的村子,那苍凉忧郁的幻影?万古不散的幽灵?悄没声息的猫精?”[15](《我怎么能说清》)她描写在墓园祭拜扫墓的场景。人们在萧条的墓园思念着亲人,仿佛在与亡者进行对话,地下的亡灵能听到亲人唱的安魂曲。“亲人们活过,爱过/却抛下我们在世路/竟天人永隔了/在那墓园,那儿已是萧索寂寞/我们还要唱起安慰死者的/安魂的歌,因为啊/因为那儿埋葬着朴素、美丽的灵魂”[16](《心上的清泉》)。灰娃还会想象历史人物的死亡,武则天曾经的辉煌宫殿也不如这皇陵的苍凉使人感慨万千,武则天的亡灵必然已经疲于世事,长眠地下。司马迁也在土中住得安闲自在,有群鸟与古树作伴。“哦,什么祭殿丽宫/有这天然祭坛苍凉磊落/叫人追思默悼/已然疲倦/长睡不醒的亡灵”[17](《武则天皇帝陵》)“他告诉我/住在这黄土岗上挺好……/南来北往群鸟/土崖上筑窝/飞绕陵墓古树/翠柏枝头山雀吟唱”[18](《过司马迁墓》)。
三、超越死亡
灰娃將死亡写得自然动人,是向往与尊敬死亡的表现,但这并不表示她轻视生命。《山鬼故家》诗集后面以大篇幅附上了王鲁湘对灰娃的作品解读,标题正是“向死而生”——这是对灰娃诗歌中的死亡想象的绝佳阐释。灰娃曾有濒死体验,当她在南京国民党原陆军医院时,因得知丈夫武昭峰在战场上牺牲而病情加重,濒临死亡,“我生来第一次有生命的孤单凄楚之感”[19]。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使灰娃对生命有了更深层的认知,感受到人生的孤独与脆弱后,站在死的角度超越生的意义。灰娃的诗歌中同样有许多对黑夜的描写,黑夜与白天相对应,正如同死亡与生存相对应,在夜中灰娃感受到如同死亡的萧瑟与寂静。黑夜同时也与死亡一般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灰娃在诗中多次提到死亡可以使她解脱,黑夜同样可以使她暂时摆脱日间繁杂。灰娃在自传中说道:“自己觉得深夜里常听见宇宙的动静,那声音从遥远的时空传来,浩浩渺渺,混混茫茫。”[20]深夜是属于灰娃自己的另一个世界,她住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中,处于自身面向自身心灵和谐统一的状态,感受着如同死亡一般的宁静。在这个世界中灰娃终于可以静下心思考,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到宇宙的声音,与宇宙平和地对话。灰娃称自己写诗的方法是:“随意地写下当下纷乱思绪的一些碎片,像采下一片片花冠,零乱而不完整。写时心绪似乎宁静了片刻。”[21]我们仿佛可以想象,在死寂的黑夜中诗句如音符一般跳跃在灰娃的手边,她自由地翱翔在内心世界的天空中,如同摘星星一般摘取它们。
灰娃想象死亡,不惧怕死亡,死亡似乎反而给她带来了生的勇气,让她继续坚强地面对生活。我们从灰娃的诗可以看出,即使她年近半百甚至更老时的心境仿佛还保持在幼时的懵懂与纯洁,灰娃在《我怎样再听一次》中写道:“如今/每时每刻我都被动地残酷地/意识到生的虚假/活着但活的不是自己的生命。”[22]可见,以死亡与黑夜的想象来逃避、超越现实,她的诗歌作为“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具有强烈的个人独特性,值得加以研究。
参考文献:
[1][2][3][4][5][6][19][20][21]灰娃,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43,130,142, 243 ,237, 255, 257,190. 190,124 ,253 ,122, 252, 187.
[7][8][9][10][11][12][13][14][15][16][17][18][22]灰娃.山鬼故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96-197 ,199,5 0-51,5 ,23 .13, 110-111 ,174, 161,177 ,20 ,62-63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