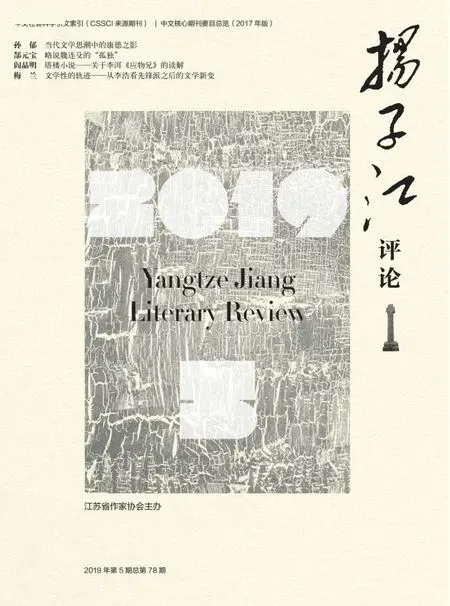诗教传统的现代叙事
——宗璞小说创作论
2019-10-10孙伟
孙 伟
从194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A·K·C》,宗璞的文学创作至今已逾70年,其持续时间之长和风格之稳定,均表明她是新文学作家中的独特存在。特别是从1985年开始,她用了三十余年时间,创作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书写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作者本人的家族史,这不仅在新文学中绝无仅有,也罕见于世界文学史。她的小说创作,追求个体的发展与家族保持和谐,与民族命运相连,尤其是其间浓浓的古典韵味,不仅体现着家学渊源,更造就了与众不同的风格。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于宗璞的小说创作,一直都以散篇作品评论为主,还没有进行过系统化的全面研究。本文将从“爱情”“家族”和“诗教”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宗璞小说创作的魅力所在。
一、爱情:个体国家的紧密联结
宗璞的小说在爱情观念方面,有着独特看法。她所表现的爱情,没有“五四”小说中离家出走式的激烈决绝,没有《青春之歌》里拯救与怜悯式的政治说教,也没有新时期小说中控诉与痛感式的苦难叙事,而是强调爱情应是“情投意合”和“志同道合”的统一,前者强调个人的文化素质和禀赋性格,后者侧重人生观和价值观,两者间的和谐关系,是宗璞爱情书写中的核心命题。她笔下的爱情,也关注个人与历史间的互动关系,并通过爱情的曲折幽微揭示时代的变迁,更注重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即以“爱”和“家”的生命感悟,去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艺术想象。
爱情中个体与他人、家族、民族的关系,始终是20世纪中国作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启蒙文学中的爱情以“自由恋爱”之名过分张扬个体自由,对他者的忽视反而造成了自我的被吞噬,杨联芬指出这类文学作品的缺点:“‘自由恋爱’,则把恋爱本身放置在两性关系的首要地位,恋爱既是前提,也是结果,它的最极端的观念,隐含着对婚姻制度的忽略甚至否定,视家族与家庭为个人自由的障碍,是个人主义的极端表达。”与此相反,革命文学则以革命正统对爱情进行压抑和收编,同样也不利于两者关系的长久发展。
宗璞小说里的爱情书写,与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都不一样,她致力于寻求个体与他者关系的和谐。个体在恋爱时与家族成员保持沟通以寻得理解和支持,青年可以从家中获得物质资助和精神依靠;与民族保持同向而行,可以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归属和升华。对此,她的写作经历了由犹豫迷茫到清晰坚定的发展过程。青年宗璞的爱情书写,充满纠结挣扎,但依然努力不让爱情充当人生的全部主宰,不能代替个体对历史的选择。这种努力在《红豆》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出身书香门第的知识女性,用爱情的缠绵迷茫来表达对历史选择的困惑。与《爱,是不能忘记的》相比,《红豆》虽然也是悲剧叙事,但它的悲剧既不是道德问题,也无关政治迫害,而只是生活态度和思想观念的分歧而已。《红豆》透过爱情叙事,更加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面前的复杂情感和内心矛盾。
中年以后,宗璞形成较为稳定的人生观,到了《三生石》时期,宗璞笔下的爱情便是明晰坚定的。它既是历史灾难中完成自我成长的精神方舟,还是反思过去的情感凭借,呈现出很强的力量感。在这里,个体的受难和民族的受难通过爱情联系在了一起。梅菩提和方知在历史劫难中相濡以沫,挺身抗暴,他们的爱情早已没有了《红豆》中的神秘和悲剧特征,而是极具人性的温暖和反思的力量。爱情是疗愈心灵硬化的良药,能使人保留住人之为人的最宝贵的东西,它以超越生死的力量,在对历史劫难进行对抗和反思时,实现了自身成长。
晚年创作的《野葫芦引》,宗璞更加注重以爱情作为切入角度,去完成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以及作者本人的家族史的三者统一。她试图以爱情沟通起小家庭和大国家,以小家庭作为物质和精神信托,以爱情作为走向社会的触角,关联起抗战救亡的家国情怀,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实现个人成长,以爱情的圆满见证救亡事业的圆满。
四卷本的《野葫芦引》,从容细致地展现了爱情在生活的点滴琐碎中渐渐酝酿、萌生、发展、变化、圆满的过程,摆脱了新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在极短的时间内迅急婚恋的情感模式。宗璞说:“没有经过战争的人可能永远想不出战争怎样‘化’进每个‘凡俗’家庭,而影响着‘凡俗’的一切一切”,“爱自己的祖国、民族,和爱自己的家乡、居所,爱自己的亲人、邻舍一样,又都是十分美好和平凡的。”她小说的男女主角在以原生家庭为依托的人际交往中,由于生活圈子的叠加参与了彼此成长。爱情双方,由于情投意合而相互接近,在参与民族救亡的事业中志同道合,最终走到一起。那些共同参与救亡事业的情侣,都“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只关注个人小天地的情感则很难获得圆满结局。峨在开始时沉溺在一己感情的幻想中,只能遭到萧子蔚的无情拒绝,而当她以在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工作参与到民族事业中来的时候,与同样热爱这一工作的家毂就走进了婚姻。嵋和庄无因,玹子和卫葑,也终得美满。反观凌雪妍和卫葑、殷大士和澹台玮、玹子和麦保罗,虽然也情投意合,但在共同参与民族救亡事业这一点上没有能够做到志同道合,只能各奔东西。这是当时处于危亡之际的中华民族对有志青年的最朴素的召唤,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个体必须献身于民族救亡,爱情才有未来。
综观宗璞小说中的爱情书写,已不再像五四启蒙文学那样,把个体爱情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以至造成青年人因“爱”而同家庭决裂。同时,也不像新时期文学那样,先是把爱情描写成意识形态悲剧,后又把爱情描写绝对自我化,进而形成以“性”代“爱”的荒诞逻辑。宗璞注重表现爱情的和谐因素,没有将个人和家庭对立起来,而是强调父辈的理性经验对青年人成长的正面引导作用。正是因为在原生家庭文化传统的熏陶下,青年人形成了参与民族历史的内心操守,父辈们也从被否定的对象,转变成儿女们精神成长的引领者。就此而言,《野葫芦引》四部曲,明显带有修复新文学盲目反家庭与反传统弊端的积极意义。
二、家族:联通内外的家国情怀
新文学在开始之初,即将家庭和家族作为打倒对象,实行伦理革命,认为家庭对子女是极大的束缚,父亲对儿女是压迫的重担,甚至将家庭视为“万恶之原”,公开宣称,“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不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娜拉出走”和“觉慧离家”成为无数青年人效仿的对象。但抗战爆发,使得作家们开始重新思考个人与家庭和家族的关系。巴金的《寒夜》和《憩园》、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都流露出个体对家的追思和依恋。
对此问题,宗璞有着自己的思考。1985年动笔的《野葫芦引》系列,显然没有受到当时火热的“反家”文化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承续五四启蒙文化而来,但对“家”的否定有过之而无不及。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苏童的《妻妾成群》、方方的《风景》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他们有的以家反思历史,有的以家表现现实生活的苦难,有的以家消解革命正统叙事,都将家置于批判的境地,似乎是万恶的家族制度带来了这一切。但即使是作为《家》的原型的巴金的家,陈思和通过研究就指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旧式大家庭,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也不是什么专制的王国”,这是较为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的,《家》是当时的“反家”文化在巴金身上的集中映显。而新时期以来的“反家”小说,也均是当时历史思潮在小说创作中的反映,并不能代表“家”在现代转型期的全部意义。宗璞在创作《野葫芦引》时,将家族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思考“家”在现代转型期的积极价值。因为中国是“伦理本位底社会”,所以家庭和家族对于个体和民族国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宗璞的小说没有多数新文学作家笔下惯常的“恨”和“反抗”,展现出另一种以“爱”与“和谐”为原则的伦理关系。战争使在此之前个体逃离家庭的时代思潮发生转变,开始回归。家不再是个体迫切出逃的伦理之网,它对内是培育教导青年的血脉承续,对外则是挺起的抗战救亡的民族脊梁。
宗璞在创作《野葫芦引》时,以家族中的伦理关系作为小说的内在肌理。她说:“大概写长篇,我觉得用家族关系来写比较方便,在一个家族里自然就有很多关系,然后在这里头就发生了一些事。”《野葫芦引》每卷之前均列主要人物表,既给出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又显示出人物在文化价值上的重要程度。以《南渡记》为例,排在第一位的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孟樾,下面的人物以其为中轴展开,吕清非的身份是“孟樾岳父”,绛初是“吕清非次女”,澹台勉是“绛初丈夫”,然后依次扩展开去,形成以孟樾为核心的同心圆组合。这和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很一致。这种人物设计与孔子作《春秋》和司马迁撰《史记》颇有相似之处。《春秋》以“春秋笔法”暗含人物褒贬,《野葫芦引》中的小说人物列表清晰地给出价值取向。《史记》依据人物的重要程度,分成世家、本纪、列传,孟樾是整部小说的价值取向,所以将其置于首位。其他人物依次排列,略持贬意的列于表末。
老太爷吕清非虽是一家之主,却不像《家》中的高老太爷那样,以礼教压迫青年,以威权棒打鸳鸯,制造着家族中的诸多不幸。与此相反,他是整个家族的核心灵魂人物,以为人为学凝聚着整个大家族,更以知识分子的操守传承着民族的文化气节。他尊重他人,威望是平素为人获得的,“老人一向待人宽厚,体恤下人,尊重莲秀”。对于子女,他不过多干涉他们的生活,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对于孙子一辈,他悉心教导,以慈爱给予家的温暖;对于本是侍妾的赵莲秀,坚持正式嫁娶。
更为重要的是,吕清非在民族大义面前的道义坚守和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为整个家族注入了代代相传的不死灵魂,这既是家族之魂,也是民族之魂。他在年轻时为了民族振兴,奔走操劳,贡献了热血和青春;在晚年时,面对日伪的威逼利诱,宁愿以死保持名节不堕,光耀千秋。吕清非为整个家族注入了高贵的知识分子品格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家族中人没有新文学中常见的激烈决绝的对立,而是互相体谅和帮助,保持着家族内部的和谐。面临国难,他们以知识分子的操守,舍生取义。正是为此,整个家族中的每个人既是努力维护家族存续的一分子,也成为民族救亡的一分子。
作为吕清非的女儿,碧初既能做到传统伦理中的夫唱妇随、琴瑟和谐,又能做到现代社会中的平等尊重、独立自强。她宁愿卖掉首饰,也不愿接受大姐接济。她抛却传统偏见,放下教授太太的身段,在路边摆摊卖食物,以贴补家用。对于父亲,她极尽孝心;对于子女,教育他们堂堂正正做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青年们的抗战事业,去已经被日军占领的明仑大学取秘密文件。正是由于碧初对家庭的精心呵护和对子女的耐心教导,才使得他们在“自由恋爱”新思潮的面前依然不会选择离家而去。
新文学中因“自由恋爱”离家出走引发的诸多问题,宗璞的小说以“家庭之爱”消解了“娜拉走后怎样”的困境。这里没有父母对子女婚姻的粗暴干涉,而是父慈子孝一片和谐景象。父母在子女的婚恋问题上普遍采取的都是关爱和支持的态度,即使有些不同意见,最终也都能以尊重子女的意愿为原则。岳蘅芬对卫葑有些意见,是因为嫌他对女儿关心不够,并没有过多干涉。对于峨,孟樾和碧初虽然内心着急,但始终还是尊重她的意愿。即使在老派家长吕清非那里,被父母包办的素初的婚姻,也没有父女冲突。当时坚守传统文化的老派人物,对儿女的婚姻也并不都采取横加干涉的态度。据宗璞回忆,梁漱溟就是这样的例子,“老人说他原打算出家,不愿结婚,很经过一番痛苦挣扎。老梁先生很盼儿子结婚,但从未训诫要求,他对这点常怀感谢”。
由于父亲出任伪职,凌雪妍不得不登报断绝父女关系,但她没有像五四反叛青年那样充满了“恨”,而是表现出父女之间情感的复杂性,对其充满了关心和不舍。李之薇由于母亲沉迷巫术,想离开家;峨由于性格原因,对家庭不怎么亲近,但她们都表现出对家的感恩之心。这里没有新文学惯常弥漫的家庭之恨,而是真实地写出了生活中的感性之爱、日常之爱和伦理之爱。宗璞小说中只有爱,没有恨,尤其没有新文学中那种决绝的、激烈的仇恨。在这里,她写出了由于代际差异、生活观念、气质性格等一系列日常原因而形成的青年离家的现象,这与将家视为万恶之源而必须打倒形成了另一种叙事。
在宗璞的小说中,爱情是切入社会历史的重要视角,但从来不是唯一和最重要的价值维度。她总是将爱情视作伦理之爱中的一维,不会像五四时的爱情那样不顾一切,而是力求将爱情与其他伦理之爱达致和谐。如她所说:“我觉得生活、生命里爱情不是最重要的,必须给它恰当的位置,感情总应该受理性约束。”在描写婚外恋的小说《心祭》里,虽然黎倩兮与程抗心有灵犀,但他们并没有完全以此为旨归,而是表现出对原有家庭的深情厚意。处于三角恋爱关系中的黎倩兮、程抗和柳明,都没有以爱之名赋予自己伤害他人的合法性,而是表现出人与人在困苦危难之际朴素珍贵的友爱之情。这些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感情,是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共通基础。李子云认为,“宗璞的主人公在这种‘抉择’中,往往是照顾别人、考虑社会、尊重自己”。唐晓丹将小说中与人为善的伦理,称为“一种道德启示的精神热力”。宗璞将三角恋爱小说中经常缺席和失声的第三方,纳入到文本叙事中,并给予平等的人格尊重和道德关怀,体现出人性中难得的善。
除了以“爱”维护着家族的存续,更为重要的是,诗书传家的知识分子将家族的命运始终与民族的命运维系在一起,将小家融于大家之中。吕清非以道殉国,其后辈承续着这种精神。孟樾既有传统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士人品格,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学识和视野,在民族危亡时不局囿于书斋,鼓励学生上前线。他不惧权贵,指斥时弊,可谓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现代典范。严亮祖在抗战时血洒疆场,在胜利后,不愿民族再起内战,以死相谏。家族的后辈嵋、严颖书和澹台玮等亲赴战场,保家卫国,澹台玮更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宗璞在描写家族时,脱离了新文学作品中以恨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模式,笔下很少对人物的嘲讽和批判,而是将个体置于密不可分的伦理关系网中,以平等和怜悯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尽量站在人物的处境给予理解之同情。这是她在新文学中的独特价值。诚如赵园指出的,“近年来家族小说(以至个人的家族历史叙事)的兴盛,像是对五四新文学的隔代回应,包含于其中的情怀却大有不同。无论由家族展开当代史叙述,还是追怀一种消失中的文化,‘家族’都不再是仅有负面意义的符号”。宗璞在其小说创作中,表现的就是现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家族中的日常伦理,在雅致的生活中,虽然不乏吕素初、荷珠对于严亮祖的依附,绛初对于赵莲秀的略显刻薄,吕香阁以利益为取舍标准的野心勃勃,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夫妇、父子、兄弟姐妹,均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平等尊重的互相善待。这是一种值得保存和承传的人与人之间温情的伦理关系,不但不会成为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障碍,还是大有裨益的生活和文化基石。
三、诗教:士人传统的文化凝聚
如果说伦理是家族文化的框架的话,那么儒家诗教则是家族文化的灵魂。宗璞所在家族,是由传统士大夫平稳过渡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功案例,是稀有的在百年命运多舛的中国现代历史中一直延续至今的书香门第。她的小说创作集中展现了诗教传统在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下发生的新变,既维系着家族成员间的和谐关系,又加入了人人平等和互相尊重的现代意识。诗教传统还通过家族塑造了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家族和民族的灵魂,特别是在民族危难之际,显示出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儒家诗教强调以礼节情,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打倒的目标,在五四知识分子看来它限制了人的个性与自由,对于现实人生缺少真实的反映和参与能力。问题是,儒家诗教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到底还有没有参与现实的能量?“学衡派”坚守此阵地多年,但缺少能反映现实的代表作品,尤其是在小说方面。宗璞的价值在于,以持续的创作,反映出儒家诗教在文学领域的生命力,既能吸收西方现代技巧以加深对人的深切表现,又可以对时代风云的变动积极参与,还能够以优雅纯正的审美趣味慰藉人的心灵。
“诗教”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毛诗序》将“诗教”作为正式理论提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宗璞自幼学习诗歌,“我从小背唐诗,第一首是白居易的《百炼镜》。小学时,每天早上要先到母亲床前背了诗词才去上学。八、九岁就读《红楼梦》”。当被问到对她青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书时,她说:“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精神和东坡词中旷大阔大的气象传达了我国文化的儒、道两家思想,使我受益。而中国诗词那不可言喻的美,熏陶了我的创作。”可以说,儒家诗教是宗璞文学观念的根柢。
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是一代哲学宗师,叔父冯景兰是著名地质学家,姑母冯沅君是五四著名作家。她正是在这样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气息的书香门第中出生成长,自然而然地,上层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也就成为她小说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书里这些莘莘学子不仅个人符码古雅脱俗,他们还都掌握着中国古典与外国古典的符码系统。”出身书香门第,使宗璞拥有绝大多数新文学作家没有的优势,在稳定和谐的家庭生活中养就了温和稳健的从容心态,在承继传统士大夫儒家诗教诚雅温婉文化的同时,还有条件深入学习西方外来文化,承前启后,融汇中西。具体到小说创作,宗璞对儒家诗教的承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品格;一是对传统文学中的“白描”进行创新。
宗璞始终保持知识分子对社会道义的主动承担意识。“还是把知识分子看作‘中华民族的脊梁’,必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在《红豆》里,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写得那么美,正是前者对于他人的道义担当才使得小说中充满了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在《三生石》中,菩提、方知、慧韵在历史的劫难中相濡以沫,以知识人的良知守护着人性中宝贵的善。在《野葫芦引》里,她更是描写了以吕清非、孟樾、嵋为代表的三代知识人前仆后继、共赴国难的壮举。吕清非早年从事革命,为中国奔走大半生,他的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在国家危难之际“剑吼西风”的铮铮铁骨,显示了极强的现实力量和强大的人格魅力。孟樾在昆明的住处名为“腊梅林”,包含着中国传统中代代相传、永不熄灭的坚韧不屈的抗争精神。碧初“教育孩子们要不断吹出新时调。新时调不是趋时,而是新的自己。无论怎样的艰难,逃难、轰炸、疾病……我们都会战胜,然后脱出一个新的自己”。嵋更是巾帼不让须眉,直接投笔从戎,在血与火的硝烟中为民族的抗战事业贡献力量。




相较新文学中的“启蒙传统”和“革命传统”,对于人伦日常,宗璞强调和谐共存而反对斗争批判;对于传统文化,强调承传而反对断裂。她的小说创作展现了中国诗教传统的强大生命力,它培养了吕清非、孟樾、嵋这样一脉相承的具有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牢固支撑起民族的精神图谱。个体在与家族保持和谐关系的情况下,共同面对文化转型期中的生死存亡,在危机中相互扶持,协同蜕变,一起成长。正是由于宗璞对“爱情”“家族”和“诗教”的认识来源于深厚的生活和文化积累,使得她在思潮多变的新时期具有极其强大的文化定力。面对强调西方现代形式的先锋文学,她能够坚守文化本位;面对倾向质疑民族传统的寻根文学,能够保持文化自信。这种文学观念对于宗璞的生命和写作都具有滋润和呵护的功能,使得她不但没有新文学作家普遍存在的中年创作危机,反而在晚年孕育出创作的高峰。这同时也显示出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当下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
【注释】
①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②宗璞:《致金梅书》,蔡仲德编纂:《宗璞文集》(第4卷),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
③孟真:《万恶之原》,《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
④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1页。
⑤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⑦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5-32页。
⑧宗璞:《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宗璞文集》(第1卷),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⑨⑮⑳施叔青:《又古典又现代——与大陆女作家宗璞对话》,《人民文学》1988年第10期。
⑩李子云:《净化人的心灵——读〈宗璞小说散文选〉》,《读书》1982年第1期。
⑪唐晓丹:《宗璞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4期。
⑫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⑬[清]孙希旦:《礼记·经解》(中),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54页。
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⑯宗璞:《答〈中学生阅读〉编辑部问》,《宗璞文集》(第4卷),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⑰刘心武:《野葫芦的梦——对〈南渡记〉〈东藏记〉的一种解读》,《粤海风》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