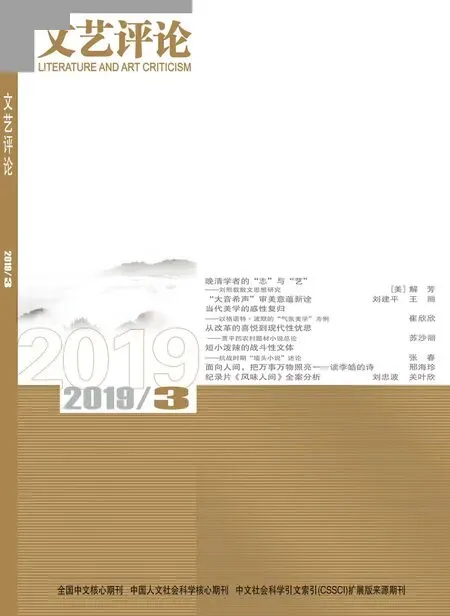山为本:中国“山文化性”的多重言说
——评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
2019-09-28○张欢
○张 欢
《山本》是贾平凹第16 部长篇小说,作品在经历问世之初的“好评如潮”后,近来又现被批评、否定的势头,扬抑之间,可见当代批评诡谲的一个侧面。笔者以为,相较热闹浩大的宣传声势,小说自身并非尽善尽美,更无法到可以与《红楼梦》《百年孤独》并论的程度,但《山本》也绝非是“一地鸡毛”的拙劣之作。贾生文章老更成,是作品给人的最深切感受。笔者试图从中国“山文化性”的角度来切入文本,就“山本”的含义究竟是“山之本”还是“山为本”进行讨论,挖掘作品在另一文化层面的价值。并在贾平凹山性书写的沿革变化中,看《山本》在作者创作历程中的地位。
一
关于“山本”二字的含义,作者于后记有明言——“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①。因此把“山本”理解成“山之本”似乎合情合理,那么“山的本来”究竟是什么呢?立足于文本,这个问题似乎无从回答,如果说这就是整本书的真意,未免与读者的直观阅读体验不相符,何况经验也告诉我们,对于作家主动暴露出来的写作意图,读者往往要保持警惕、不能盲信,更深层的意思恐怕还隐含在后面的话上:“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这是生命的初声啊。”②贾平凹在这里对秦岭流露出的,正是婴儿唤母般的感情,是对山如父如母的眷恋和依赖,因此不妨将“山之本”进一步理解为“山为本”或“山为母”,可能这样才更符合作者的深衷,“山之本”与“山为本”的问题并非是命名上的简单差异,更涉及到对于全书主旨内质的把握和理解,这就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的分析。
不管是“之本”还是“为本”,《山本》中的“山”,指的肯定是秦岭,与葛水平小说《喊山》、韩东诗歌《山民》之类侧重揭示山的落后贫瘠与对人束缚的作品不同,贾平凹不论在正文还是后记中,都丝毫不掩饰他对于秦岭的浩叹崇赞与为这座山立言的巨大冲动:
“秦岭可是北阻风沙而成就高荒,酿三山而积两原,调势气而立三都……秦岭其功齐天,改变半个中国的生态格局哩。”③
“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我就是秦岭里的人……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本书了。”④
贾平凹前后关于秦岭的描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方面是不断在确立着秦岭与中国的关系——“最中国的一座山”“无秦岭则黄土高原、关中平原、江汉平原、汉江、泾渭二河及长安、成都、汉口不存,秦岭其功齐天”;另一方面则说明“我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持续强调着秦岭与自己的血脉联系。自小与山的触肤之亲,加上秦岭自身的巍峨、连绵与神秘,很容易唤起人的亲近乃至崇拜之情,对贾平凹而言,山土不仅生养了他,更是其创作上广阔渊深的文化资源所在。这点也在后记体现出来“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一有空我仍是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笔和手的亲切感之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⑤回顾他的创作史也会发现,“进山”一直是其化解创作、人生危机的不二良方,最典型的恐怕要属“商州系列”——这些让贾平凹在经历1982年“笔耕”文学组批判后于文坛重开天地,在其创作中有着“转折点”意义的作品,正来源于他对商洛山土的行走与钻察。
就这样以秦岭为出发点向前后延伸,可梳理出的,是“中国—秦岭—贾平凹”的逻辑链条,作家暗含的意图实际在这里——顺着链条往前推,就是贾平凹自称为“中国种”的理由,根植于中国与秦岭的生命经验,是他在信息爆炸的同质化时代获得表达自信的来源,他真正沦肌浃髓的,自始至终都是这二者的乳汁血液;而把链条倒过来看,“贾平凹—秦岭—中国”的逻辑则意味着他认为自己的创作,也必然要发中国和秦岭之音——所谓“生命的初声”,我们也由此理解,为何他将写作《山本》看成了自己宿命般的任务。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作家外在的表达,还是内在的接受这两方面看,秦岭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山为本”恐怕才是小说的“味外之致”与“韵外之旨”所在。
对于“以山为本”的内涵,除了从作家的个人言说中理解,不妨放到更宏阔的视域中去开掘,因为山母题文学本就根植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山的诗文如秦岭草木,无可尽数:陶渊明“悠然望南山”(《饮酒》)的审美心境与“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的生命宣言,皆与山相连;“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李白,不仅将对山的游赏摹描作为极大的爱好,也将其视为灵魂慰抚与安放的载体——在诀别“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后,能使他“开心颜”的,只能是“须行即骑访名山”(《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也是借对泰山的铺赋,来表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志向,将强烈劲直的生命意志与山的形神贯融……可以说,整部中国文学史,都是以这种“山文化性”为突出特点,而与西方的“海文化性”相区分的。再接回上文“中国—秦岭—贾平凹”的逻辑,我们发现:以山为本,实际上就是以中国式的“山文化性”为本,如同《老人与海》之于西方海洋文明一样,《山本》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山性的一种文学言说。
二
《山本》的山性言说,首先体现在对秦岭的描写上。秦岭是涡镇所依托的自然资源,更是小说人物成长、修窟、打仗、贩茶与采药的客观环境,就如同《白鲸》《海底两万里》等西方海洋文学著作以大海为描写、抒情、象征和隐喻的载体一样,整部《山本》都是基于秦岭这个客体而展开、存在的,无山则无此小说。
当然贾平凹直接描写的秦岭的地方并不多,原因正如后记所说:“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入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⑥他采用的正是古典小说的“烟云障眼”之法——秦岭罕少地在文中直接被描写,但却“润物细无声”,从各个侧面不断地出现在读者的纸上目前:麻县长的《秦岭志》、从秦岭采摘的云雾茶、众人嘴里的传说、山里的奇花异兽等等,使这座山“不在眼前,胜在眼前”,换言之,对秦岭的描写更多是依靠对秦岭里人与物的记述来体现的。其实《山本》之前的名字就叫《秦岭志》,确然,作为一部带有中国传统“博物志”色彩的作品,满纸皆是秦岭众生,其中名物之繁复密杂,鸟兽之神怪幻奇,在当代小说中可谓罕见。怪兽有飞鼠、羚牛、斗鱼、浊猴;奇鸟有绶带、鸱鸺、雕鸮、噊鹛;草木有漏芦、锁阳、连翘、蛇菰......可谓兽禽虫木熙攘,遥接《山海经》,让人似回远古洪荒之境。但《山本》又并非传统博物志、怪物谱的当代翻版,贾平凹从始至终都将对秦岭名物的描写,紧紧地与人类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使人、物混杂交错,常常令读者恍惚。
实际上整部作品中贾平凹都有意识地在模糊着人与物的界限,这体现在物带人情与人有物性两个方面。一方面小说中的动植物常常颇具“人性”,有着类似人的行为举动,如李景明家的狗突然说人话,山猴喝醉了酒卧在龙王庙,树上的叶子听了景宗丞的话就落下,青蛙跳上麻县长的脚带着他破案等;另一方面则是人往往和动植物的长相、习性相一致。在麻县长眼中,涡镇“好多男人相貌是动物......我有时都犯迷糊,这是在人群里还是在山林里?”⑦“这人不是动物变的就是植物变的。”⑧井宗秀与陆菊人,更是多次被直接点出是老虎与金蟾“托生”,至于“蚯蚓”“花生”之类,则无名无姓,干脆以动植物名来称呼了。事实上小说形形色色的人物主要是于其“类物性”一面展开的,人关于道德、教化的社会属性一旦被褪去,便迅速地滑向了动植物性的生存层面。
对于井宗秀、杨钟、阮天保、邢瞎子这些书中人物来说,是红军还是保安队或土匪,是姓蒋还是姓冯都并不重要(他们的身份也经常相互转换),诚如杨钟所言:“什么国军呀土匪呀刀客逛山游击队呀,还不是一样?这世道就靠闹哩,看谁能闹大!”⑨最重要的便是“闹”,而这种“闹”是恰恰动植物式的,而不带有人类的特性。与《白鹿原》不同,黑娃可以在“闹大”后投归乡土礼法的子宫,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执念,却从未植于秦岭众生的基因里,他们在“闹”里贯彻的,既不是“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文人式理想,也非《水浒传》中“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民间价值观,而在于单纯地追求现世中饮食男女的快意,像山里的豺狼虎豹一般茹毛饮血、相互斗杀,是书中人物存在的唯一目的,因而一切宏大的意义、贵鄙的取向、正邪的判断,都在他们或吃玩快活或弱肉强食的动物式生存观被消解掉了。“闹”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归于它的反面——“寂”,书中的英雄、草包、混蛋、凡人最终都如尘如土,随风云而散,至死都是一派禽兽般的浑噩昏愚,与一朵花、一片叶的凋零没有任何区别。
《山本》中的人,生如禽兽般懵懂,死如草木般寂静,贾平凹作为一个深受商山洛水熏染的作家,他创作中这种“人物混同”所浸润的,是中国山土的文化养料,在后记中贾平凹记载了他观察秦岭时的顿悟:
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似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省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⑩
山下自然的河与山上感觉的河本无区别,兼之陕南山岭中本就于现代化进程之外多遗存着物我混同的原始思维,《山本》在“人”与“物”的讨论中表现出类似于庄子的“齐物”观,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篇》),作品在这里承发的,既非《诗经》的“比兴”传统,也不再是《怀念狼》《老生》中“人变成兽”的视点,而是进一步超越了“我”与“物”之分,将二者之间的界限消解,从而达到对于“天我合一”的文学观的追求,这种“天我合一”“人物混同”的玄思,来源于对秦岭的钻察体会,与“山文化性”密不可分。确然,当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山本》,难免会基于分门别类的生活认识经验,但不同的存在形态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去除人为“分类”观念的桎梏,从秦岭的层面来关照众生,人与动植物,英雄好汉与混蛋孬种,看似是类与类的分别,但其实质终究是世界的统一的存在形态,如作者自言:“随便进入秦岭走走……仍还能看到像《山海经》一样,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而不同于《山海经》的,也能看到一些人还长着似乎是兽的某一部位。这些我都写进了《山本》。”⑪
三
《山本》关于“山文化性”的言说,不仅见于对秦岭的描写,还体现在贾平凹讲述中国的方式上。其实在小说的叙述中,一直存在着两个中国的二元对立,即“政治中国”与“自然中国”的分峙。
《山本》将故事的时间地点拉回百年前的秦岭深处,以中原大战、蒋介石、冯玉祥、陕南游击队、逛山、刀客这些历史上的人物与客观发生为背景,贾平凹的写作一向以细密质实的田野调查和材料功夫为前提、基础,即便井宗秀、井宗丞兄弟这对虚构的人物,其原型也来源于民国时期陕北军阀井岳秀和同盟会早期领导人井勿幕,可以说《山本》与中国的政治、历史息息相通,实际上正是“政治中国”的一种讲述。这种讲述对政治的理解,不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元动力,也不以论述革命的必然性、正当性为任务,而是继承着《古炉》《老生》以来“告别革命”“反思政治”的主题,并在这一点上继续推进。
井宗丞的故事作为小说主线之一,集中体现着贾平凹对于革命的思考。这个人物一开场投奔革命的方式,就是以对家庭与宗亲关系的伤害作为前提——为了筹措活动经费,让人绑架自己的父亲井掌柜,以换取赎金,最后导致了父亲的猝死。井宗丞靠吃父亲的“人血馒头”来“闹红”,以血缘关系构建出来的传统人伦在这里被颠覆、解构,“革命”的行为从一开始就被烙上了道德的“原罪”。至于他后来所加入的游击队,亦鱼龙混杂,不乏像阮天保这样的恶棍流氓,也有滥杀平民的行为,并非带有儒家理想色彩的“仁义之师”,不符合传统意义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逻辑。
相较背弃亲人、投身“革命”的哥哥,井宗秀则在父亲死后从学艺的远方“归来”,接受“父债子还”的民间伦理所支配。这个人物更多地站在了家庭宗族的立场上,一方面是割据涡镇的军阀,另一方面也是地方乡绅,双重的身份角色所带有的,都是地方与乡土的色彩,这也与历史上的“榆林王”井岳秀类似。但是我们在“否定革命”之后,并不能自然地滑入认可军阀乡绅势力的逻辑。井宗秀在做大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涡镇的“土皇帝”,挂马鞭、改街道、建戏楼,对他的治下进行着随心所欲的统治,地方与百姓,只是他随意揉捏的对象,满足野心的工具,最后也因他的仇杀给涡镇带来了灭顶之灾。
由此可见,无论是井宗丞离家出走式的革命道路,还是井宗秀安土重迁式的地方割据,皆非贾平凹所认同,实际上对两者的双重批判、反思才构成了《山本》中“政治中国”的内涵。“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是贾平凹在《山本》后记里写下的句子,而“灾难”与“荒唐”才是政治中国的裸质与真意。与堂吉诃德那种带有理想主义与道德崇高感的“荒唐”不同,枭雄好汉们都以对他人的压迫、掠夺、残害来达成政治目的,由此所带来的必然是无穷无尽的斗争与杀戮,直至所有人都被仇恨所吞噬,将秦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场,所谓“灾难”是也。贾平凹所记录的政治中国,是一个礼乐簪缨之外的世界,与孔子“郁郁乎文哉”的理想社会绝缘。在阅读的直观感受上,我们感慨于作者对于生命消逝的惊人淡漠与冷峻态度,尤其是井家兄弟,夏天义、夏天智死亡中那种为传统乡土“殉道”的悲怆意义,到了《山本》这里已被黑河白河的水流溶解,如秦岭烟云般消散,贾平凹对“英雄”们的逝去不带有任何感情的色彩与意义的赋予,实际上暗含着埋葬与终结“政治中国”的情感与意图。
这种对于意识形态的消解、主观情感的悬置与“否定英雄”“告别革命”的历史观不仅从《古炉》《老生》一脉而来,在《红高粱》《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等所谓的“新历史”小说与王小波的作品中早已有所体现,但贾平凹的变化在于,他在《山本》里明晰地勾画出了一个他所倾心向往的“自然中国”,并且表达出以“自然中国”来映照、救赎“政治中国”的意味,这点在结尾处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炮火即将摧毁涡镇的时候:
陆菊人说: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部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陆菊人看着陈先生,陈先生的身后,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峦叠嶂,以尽着黛青。⑫
再凶猛的人间炮火也改变不了远山的高翠连绵,因为从孔子开始中国人就对山赋予了“仁”“静”“寿”的文化内涵,⑬山的哲学是稳重沉静,意味着给漂流湍急的社会变化所赋予的定力,“自然中国”的立场,正是用“秦岭之眼”来关照、洞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中国政治与历史,以这种深博坚恒的山性为基石。陈先生与宽展师傅是书里“自然中国”立场的代言人,在他们的盲眼与竹笛声中,人物的聚散死生不过是一个伪命题,秦岭底下无新事,人事的代谢、兴亡的交替,对亿万年屹立的山体来说太不值一提了。“世道荒唐过,飘零只有爱”,这是贾平凹在《山本》勒口所写的句子,虽然整部《山本》“到处是枪声和死人”⑭体现的是“今日我杀了你,明日你杀了我”⑮的血腥,却无慌张与恐惧之气,《山本》从“山文化性”来看政治中国,获得的是“惯看秋月春风”的定静与悠稳。“自然中国”对“政治中国”的映照与救赎,所依凭的并非是朱先生“砥柱人间是此峰”的儒家济世情怀,而是秦岭的“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是如山般饱厚的文化内质与深沉的精神力量。
四
《山本》体现的“山文化性”,也可以从作品整体风貌与创作心态的转变来看。在《山本》之前,贾平凹一向以对现实的敏锐捕捉与直击力度屹立文坛,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创作,可以说置身时代,体物入微。但到了《山本》这里,贾平凹却一反往常的入世姿态,从现实与乡土的“前线”暂退,转向历史与秦岭的深处,彻底“隐逸”了起来。所谓“隐逸”不仅仅指题材的转向,更是作家笔调、作品风格的改变,这一点可以从作品中的生活细节、风俗画面、人物心理等方面来分析探视。
饮食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山本》以前的作品中罕有涉及,即使写到,也只是匆匆带过,且意不在此,以《极花》为例:
黑亮仍是十天八天去镇上县上进货,回来给我买一兜白蒸馍,有一次竟还是买了个猪肘子,我以为这是要做一顿红烧肉或包饺子呀,黑亮爹却是把肉煮了切碎,做了臊子……叮咛吃荞面饸烙或是吃土豆炖粉条了,挖一勺放在碗里。⑯
作者在这里写到猪肘子并非有意为之,只是借此表现农民物质生活的匮乏,以反映农村的凋敝衰败,重点并不在食物本身。而到了《山本》则完全不同,以陆菊人包饺子为例,同样是写吃食,作者在这里却以3页纸、近三千字的篇幅,不厌其烦地描写了她买原料-借面-醒面-洗地衣-剁馅-揉面-擀面-包馅-下饺子的全过程,试看洗地衣的片段:
泡在水盆里的地衣全发开了,油黑油亮,一朵一朵,像开的花,陆菊人拿起一朵,细细地掰开每一个皱,把草屑捏出来,又在水里不断地涮……就想:地衣这名字谁起的……要赐衣服怎么不赐彩色的衣服,黑颜色真的好吗……黑衣黑鞋黑裹腿黑鞋子,陆菊人不经意地笑了一下,她觉得自己的胡思乱想可笑。⑰
这里不仅详写了地衣的形态与清洗的动作,还与人物的心理活动(对井宗秀不由自主的思念)结合了起来。事实上这样的生活细节、心理描写和情景展示,在《山本》中十分多见,如杨家做纸扎、陆菊人教花生“妇德”(足写了五页纸,活脱一部当代《女诫》)、井宗秀受伤后菊人的担忧、涡镇集场的风俗等。《山本》的笔调与风貌,不再与“激愤”“悲怆”“挽歌”这些字词相连,而变得悠容和缓。书中处处出现的“闲笔”,与主旨关系不大,按照以往的情形,完全会被贾平凹以一贯省练的笔法轻轻带过,在《山本》中他却空前“奢侈”地大量运用,墨浓彩重,引人好奇。
作品风貌、笔调的改变,来源于作家创作心态的更迭。按《后记》所说,贾平凹创作《山本》的初衷,起初是怀着麻县长般“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的愿望,却意外地“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倒使我改变了初衷”⑱。可见关于写作的动机,不论是记录草木动物,还是感兴趣于秦岭的历史传奇,贾平凹都改变了以往“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的创作模式,用他的自我总结来说,就是不再是“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而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⑲。作者在这里正式宣告了自己的由“入”返“出”,我们从《山本》中感受到的,不再是《土门》《秦腔》《高兴》《极花》那般强烈峻急的乡土关怀与农民式的身份意识,而是更为舒缓娴稳的笔墨,是“自其达者观之,殆不值一笑也”⑳的出世心态。
这种“出世”的超逸达观心态造就了《山本》独特的气质,在一贯绵密的针脚背后,是与紧张现实和解后的悠远高致之气,这都与“山文化性”息息相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庙堂”是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政治性场域;“市井”则是民间社会的代称,带有生活与烟火的气息;而“山林”与前两者不同,是承载出世心态与放逸精神的空间存在。从上古时期的巢父许由,到元明清时期的倪瓒、八大山人,这些著名的隐士幽人,都以山作为身体与心灵的栖身之所,所谓“性本爱丘山”,对他们来说,不仅因为山林在地理空间上足以远离政治、现实与人事,更源于山本身玄远、缥缈与悠远的文化性,与其隐逸、出世的心境相契合。无论隐于何处,追求内在精神的超逸达观,才是山文化之真谛,而这种“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的隐者视角与出世心态,也自然会让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悠闲洒脱的风貌。
没必要说贾平凹对现实的暂避与隐逸意味着写作上的倒退,“我是农民”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叹息肠内热”的仁者心态,永远是他的最重要的生命底色之一。但我们同样不能忽略贾平凹身上的出世味与隐者气,作品完全可以体现作家丰富多元的内在文化构成,正如倪瓒的画是“写胸中逸气”,体现山林简远幽淡之精神一般,贾平凹的出世心态,体现的正是旷达超逸的山文化,《山本》深沉悠远的风貌品格,实则也是这种“山文化性”落到文字表达上的呈示。
纵观贾平凹的创作,在《山本》之前的山性言说,大体可分为三种模式,首先是早年的一系列山村改革题材小说,如《山地笔记》《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等,侧重于表现改革浪潮给偏远山村所带来的物质与人心变化,山地在这里虽然还呼唤着现代文明的改造与变革,但那种世外桃源般的清新淳朴之气却扑面而来,优美、宁静与清朗的山性在此展现;其次是以《人极》《太白山记》《烟》《怀念狼》等为代表的作品,带着中国古典传奇、志怪小说的奇诡幽幻色彩,用类似于唐传奇、《太平广记》《聊斋志异》的笔法,描写了山区那些巫鬼幻化、奇闻异谈,情节常常扑朔迷离,集中地体现出了山地文化神秘、怪奇的一面;最后是以秦岭的山水草木、一城一寨为空间与载体,将风土人情、历史传奇、山情野趣填充其中,展现出丰富多元的“山文化性”,进而透视整个中国,以早期的《商州三录》为滥觞、《老生》为典型代表,所谓“商州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也就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目的。”㉑“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十多年。”㉒将中国的百年历史揉捏进秦岭深处,借山土来表达现实与历史之肌貌,寄寓作者对乡村命运的关怀与历史变迁的思索。
《山本》则脱离了早前描写山村改革的窠臼,但“山性”中清新自然的一面,却在笔调风貌中有所复现;作品又是一部秦岭之志,记录了秦岭的形貌、男女与鸟兽草木,依旧带有“山地志异”的色彩和痕迹,但重点不再集中于怪奇的展现,而是体现出“人物混同”“天我合一”的山地哲学;在借秦岭来言说、关怀中国山土历史的层面上,与《商州三录》《老生》一脉相承,但相较前者,以秦岭为代表的“自然中国”立场则更为明显和突出,诸多信手拈来的闲笔,也为前者所无,这些都构成了《山本》山性言说的沿革。可以说,《山本》是根植于山土,体现出中国“山文化性”的一部作品,花甲之年仍能以两年一部长篇的速度推新,执著地探索小说的艺术,对脚下中国的乡土山岭予以持续的关注和迭样的表达,无论效果,贾平凹有功于焉。
①②④⑤⑥⑩⑪⑭⑱⑲⑳贾平凹《〈山本〉后记》[J],《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③⑦⑧⑨⑫⑮⑰贾平凹《山本》[M],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300页,第332页,第481页,第162页,第520页,第496页,第265-266页。
⑬《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⑯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3页。
㉑贾平凹《商州初录》[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㉒贾平凹《〈老生〉后记》[J],《东吴学术》,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