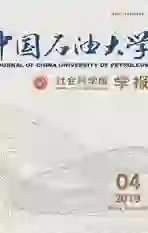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2019-09-18李雅雯
李雅雯
摘要:循吏群体形成于汉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亦师亦吏”的双重作用。循吏“亦师亦吏”的角色定位渊源有二:一是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二是“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二者均滥觞于上古三代,并在后世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在社会治理中,汉代循吏通过礼义道德教化、发展地方教育、整顿社会风俗等方式将“以教为治”的观念付诸实践,这对于稳定乡里秩序和促进蛮夷边地对汉帝国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对当代社会治理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汉代;循吏;“以教为治”;“以吏为师”;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4-0047-06
循吏形成于汉代,宣帝以后其队伍不断扩大,成为汉代官僚群体中的特殊类型。循吏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兼具“吏”与“师”的双重身份,不仅涉身于纯粹的行政事务,还要以“师”的身份从事教化工作。①
关于汉代循吏群体的产生原因、政治功能以及影响,前人已做过很多深入研究,似乎题无剩义②,但实际上,若以“以教为治”的思想渊源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为线索,探析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尚有可阐述的空间。本文即从这一视角入手对该问题进行探析,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发掘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当代价值。
一、“以教为治”的思想渊源
循吏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1]3317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借用5位春秋时代良吏的事迹归纳了心中循吏的标准。其中,孙叔敖“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1]3767,这说明司马迁把教民看作循吏的主要职责之一。归纳《汉书》《后汉书》所记载的18位汉代循吏,他们大多是郡守或县令等地方官,在治理地方时都十分重视教民。比如,“(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2]3625,“(黃)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2]3631。究其思想渊源,汉代循吏重视教化治理模式源于儒家“以教为治”的思想。
《说文解字》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段玉裁注曰:“上施故从攵,下效故从孝。故曰:教学相长也。”[3]从字面理解,“教”是一个“上行下效”的单向过程。在儒家语境中,“教”是古代中国“政教合一”传统中的一项政治实践,兼具社会性和道德性,是统治者通过传递政治要求、价值观念使下层民众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更化社会风气,从而达到政局稳定、社会和谐的一种统治手段。
“以教为治”的实践最早可追溯至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荀子·正论》云:“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4]336-337尧、舜之教侧重人伦秩序规范的形成,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5]。西周以后,“教”的政治功能逐渐凸显,周公主张“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并将教民作为实现“德治”的手段。《周礼·地官·大司徒》载:“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6]1523
儒家寓治于教、教以导政的传统肇始于孔子。孔子的夙志是“天下有道”,他认为实现天下有道的途径即是“教”。《论语·子路》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7]528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主张通过“善教”实现仁政。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8]897他认为,良好的管理不如良好的教化。教化以其温和的形式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从而收获更好的治理效果。荀子认为礼义教化具有整齐民心的功能,即“礼义教化,是齐之也”[4]275。与孔、孟不同的是,荀子强调兼综礼法,发挥礼义教化功能的同时重视刑罚的作用,即“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4]440,这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治理之道。
汉初,儒生在反思秦政之弊的基础上探求治国之道,贾谊将“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9]349看作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因此,他继承先秦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将“教”视作为政之本。《新书·大政下》云:“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9]14他的思想为文帝采纳,史载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1]433。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也逐渐受到重视。董仲舒谓:“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10]他认为社会治理依靠的不是刑罚等国家强力手段,而是要依靠润物无声的道德教化。董仲舒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证了教化在实现王道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在《天人三策》中说道: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2]2499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2]2503-2504
策论提倡发挥礼乐和教育的教化功能,主张设立国家层次的太学以及地方的庠序,并且简省刑罚,以由上及下推行教化的方式更化风俗。这与汉武帝“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2]166的政治要求不谋而合,也为循吏的教化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
循吏采纳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上层的政治要求,汉宣帝重用循吏,“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2]3624;另一方面,出于循吏作为儒生的自觉,尤其是光武之后,循吏基本上都有研习儒学的经历,所以,他们以儒家“以教为治”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社会治理当中。例如,蒲亭人陈元之母告其不孝,亭长仇览认为陈元并非恶人,只是教化未至而已,于是“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11]2480。
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
吏以治民,师以教民。“以教为治”的治理观念要求循吏在担任地方官的同时扮演“师”的角色。这种“亦师亦吏”的角色定位有其历史渊源,即三代以来形成的“以吏为师”的传统。关于“以吏为师”的渊源,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释》中有精辟论述: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12]
此段论述中,章学诚追踪了“以吏为师”传统自三代至秦的流变。在传统的研究中,秦之“以吏为师”通常被视为秦统一后运用法家学说加强思想专制的产物,强调其反传统的一面。①
然而,根据章学诚的判断,在“吏师合一”的视角观照下,秦之“以吏为师”恰恰呈现出“合于古者”的一面。
三代之际,政教合一,故君师合一。《尚书·泰誓上》言:“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孔颖达疏曰:“治民之谓君,教民之谓师。君既治之,师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师。师谓君与民作师,非谓别置师也。”[13]上古社会,“师道”和“君道”的承担者都是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的贵族阶层。按:“师”本义为民众,后引申为官长,官长所承担教诲民众的责任又赋予了“师”教人者之称的义项。“师”的语义引申功能正体现了上古社会“君师合一”的传统。[14]《周礼》中有许多以师作为官名的现象。《周礼·天官·大宰》载:“以九两系邦国之名;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6]1395关于“师”和“儒”的记载也为“以吏为师”在先秦的实践提供了具体例证。
① 余英时认为秦人“以吏为师”在思想上源于法家的传统,法家思想支配下的“以吏为师”不但“吏”与“师”合而为一,而且“师”完全从属于“吏”,秦代“以吏为师”的政策是企图用政治秩序取代文化秩序。参见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以吏为师”的传统至秦并未中断,秦早在统一前已有“以吏为师”的具体实践。《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载:
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灋(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恶俗。灋(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凡灋(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殹(也)。[15]30
研究者指出,《语书》发布的时间为秦王政(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15]29其内容是南郡守腾要求各县、道啬夫等整顿各地风俗,推行法令,实现“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可见,早在秦统一进程中,“以吏为师”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统治原则。秦始皇泰山石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1]243在秦始皇看来,“专隆教诲”甚至成为值得刻石记录以传后世的重要功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秦之“以吏为师”虽继承了三代“以吏为师”之形式,实则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如《语书》所记载,南郡守腾要求基层乡官以法令为教民的内容,认为只有法律才能达到“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的目的,这说明了秦代“以吏为师”的精神实质是建立在法家“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道,以吏为师”[16]的“法治”理念之上,而拋弃了三代“君师合一”传统中具有伦理价值的礼乐精神。
汉代延续了三代以来“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汉文帝说:“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1]419汉景帝也说:“夫吏者,民之师也。”[2]149
实际上,循吏“吏”与“师”的双重身份相辅相成,在社会治理中这两种角色相互融合、渗透,
而非余英时所说的“汉承秦制,故严格言之‘吏的本职仍然是奉行朝廷的法令。不过由于汉廷已公开接受儒学为官学,因此不得不默认地方官兼有‘师的功能而已”[17]。以颍川太守黄霸为例,史载“霸少学律令,喜为吏”[2]3628,“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2]3627,是典型的文吏。因夏侯胜非议诏书一事受到牵连,入狱三年,跟随夏侯胜研习《尚书》,渐受儒家思想浸染。黄霸复出后,将儒家“以教为治”的思想运用到颍川的治理中,“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2]3627,“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2]3629。黄霸为政宽和,“力行教化而后诛罚”[2]3631。治颍川八年“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2]3631。黄霸的政治实践表明,汉代循吏的“亦师亦吏”双重角色定位是对三代及秦的“以吏为师”传统的统合与升华:循吏上承三代“君师合一”之遗风,重拾礼乐伦理规范以化民成俗,使“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2]3631,同时又继承了秦政“以吏为师”的“法治”精神,将帝国政令作为“教”的重要内容,“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2]3627,并在民间颁行条教,承担作为帝国官僚的职责。
从三代至汉,“以吏为师”的传统一脉相承,未曾中断,但是不同时期“以吏为师”的精神内涵有所差异。三代之际的“以吏为师”指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下的“君师合一”;秦之“以吏为师”是在法家专制思想下排斥非吏之师,强调发挥律令的教化作用,以政治秩序统合文化秩序;汉代之“以吏为师”具有儒家色彩,并与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观念相契合。自孔子到孟子、荀子再到汉代的贾谊、董仲舒,儒家都企图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秩序,并且这种文化秩序是植根于民间社会的。孔子追慕政教合一的圣王时代,认为官吏不仅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管理者,更是社会思想文化的导向者和传播者,官吏作为“师”发挥礼乐、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文化秩序来统合政治秩序。
三、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实践
在“吏”与“师”的双重身份下,循吏不仅涉身于纯粹的行政事务,还要以“师”的身份从事教化工作。《周礼·地官·大司徒》云:“四曰联师儒。”郑玄注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6]1522按:“艺”当为“义”,《北堂书钞·礼仪部》引郑玄注“乡里教以道义者”,并谓“《地官》注作道艺”。[18]乡里之间传播道义是循吏作为“师”的基本责任。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7]41在孔子看来,理想的社会秩序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和礼治秩序。循吏所遵循的“道义”即是儒家的“德治”和“礼治”。
所谓“德治”就是“以德善化民”,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2]2515这要求作为教化之官的循吏为政要启发百姓的道德自觉。《礼记·曲礼上》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19]2663循吏的道德教化主要是以“礼”作为载体。如《后汉书·循吏列传》所载:
(卫)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11]2459
(秦彭)建初元年,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11]2467
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许)荆为设丧祀婚姻制度,使知礼禁。[11]2472
《史记·礼书》曰:“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1]1157社祭之礼、飨燕之礼、敬老之礼、婚丧之礼,这些依据人情、人性创设的礼仪在乡土亲缘社区中起到了维系群体秩序的作用,同时也提供了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因此,在儒家看来“礼”是整合社会的主要机制之一。费孝通说:“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过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20]“礼”来源于“乡俗”,并以教化的方式改造“乡俗”。循吏正是通过将儒家“礼”转化为与之相适应的乡俗投射到基层社会,实现了乡里社会的“礼治化”。
发展教育是循吏实现“以教为治”的重要途径之一,儒家历来重视教育,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广招门徒,兴办私学,打破了西周“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制度。孔子的平民教育的实现为“礼下庶人”提供了可能。《礼记·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19]3296发展教育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的重要途径。文翁“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2]3625,“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2]3625,“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2]3626。古代的学校教育以教民为目的。《孟子·梁惠王上》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朱熹注曰:“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21]文翁开创了汉代地方官建立地方学校的先河,培养官学弟子,为基层行政队伍输送人才,使得蜀地风俗大为改观,“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2]3626。此后重视地方教育者众多,如“(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11]2557,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11]2571,他们都是受到文翁的影响。
“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22]整顿风俗也是循吏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孟子·滕文公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8]5875居上位者的品行,会直接影响下层社会风气的形成。这首先要求循吏要正己修身。《新书·大政上》曰:“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9]341只有提高自身修养,成为民众之表率,才能担负起教化一方的责任。“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2]3063,整顿风俗要根据各地风俗以教化的方式进行疏导。《汉书·循吏传》载:“(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2]3640渤海太守龚遂躬亲劳作、劝民农桑,改变了重商贾、轻农业的社会风俗,不仅使渤海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得到提升,也使得社会秩序更加和谐稳定。
循吏整顿风俗与儒家所倡导的民族观密切相关,儒家所倡导的民族观是基于文化认同的民族观。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7]5457不用华夏衣冠,被视为夷狄化的象征。如韩愈所概括的:“孔子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3]汉初承秦立国,疆域辽阔,七国旧地已是风俗各异,“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24]。边远地区更是未染王化,“椎髻鸟语”。秦二世而亡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未曾对各地文化及风俗进行有效的整合。①
贾谊曰:“夫移风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为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2]2245这体现了汉儒整顿风俗,在天下秩序中构建华夏认同的追求,循吏任延治理九真是对这一追求的具体实践。《后汉书·循吏列传》载:
① 陈苏镇从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这一角度出发,认为秦失败的原因在于它完成了对六国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后,未能成功地实现对六国旧地特别是楚、齐、赵的文化统一。秦朝统一文化的手段是向全国推广“秦法”。由于当时文化上的战国局面依然存在,秦法与东方各地固有的传统习俗发生了冲突,其中尤以秦、楚之间的冲突最为严重。参见陈苏镇的《〈春秋〉與“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页。
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任)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11]2462
九真地处华夏边缘,属化外之地,任延通过推行华夏嫁娶礼法,整顿边境风俗,从而建立起九真对华夏的认同感,这对于稳固汉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积极作用,正如葛兆光所说:“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认同基础,变化了的国家很难建立稳定的秩序。”[25]
四、余论
汉代循吏基于“以教为治”的儒家思想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发展教育、整顿风俗的方式将儒家“礼治”和“德治”理想付诸合理且有效的实践。这种治理模式对中国古代官僚士大夫群体形成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二十四史”与《清史稿》记述的循吏共达五百余位。[26]而在正史《循吏传》外,尚能在不少士大夫身上看到循吏的影子。本文将受汉代循吏影响兼具“吏”与“师”双重身份并遵循“以教为治”治理原则的官僚类型概括为“循吏型官僚”。
当今中国,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有了充分的发展,贫富差距也大大缩小,“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27],儒家“富民”的理想正在实现,“教民”层面的精神文明建设正受到高度重视。循吏“以教为治”的治理方式可以为此提供诸多启示。
在循吏的信念中,教化作为“治道”途径,被视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循吏的治理成果也证明,以教化为途径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其弥散性和渗透性,收获了寓教于治、以教化政、以教导政的良好效果。“循吏型官僚”除了注重通过学校进行知识传播和意识形态教育外,也关注在人伦日用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下渗透儒家的社会理想和国家的政治意志。这些都是值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借鉴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循吏型官僚”是一种官方与非官方相结合的二元同构的教化模式,其教化行为一方面来源于政府要求,另一方面出于其理想的自觉。这提示当代社会要以全面提高精神文明建设为前提提高各级干部的自身修养,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有理想、有信念、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做到儒家所提倡的“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
最后,循吏“以教为治”的政治实践让我们看到了儒家以礼治为核心、以教化为途径的“治道”之合理之处,提示我们在当今社会治理中,将礼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在灵活地发挥政府教化职能的同时,鼓励民间教化组织在继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理念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性和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7.
[4] 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5]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565.
[6]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刘宝楠.论语正义[M].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8] 焦循.孟子正义[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9] 贾谊.新书校注[M].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319.
[1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长青,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232.
[1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383.
[14] 阎步克.士·事·师论——社会分化与中国古代知识群体的形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19-32.
[15] 陈伟.秦简牍合集(一)[M].释文注释修订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16] 王先谦.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452.
[17]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55.
[18] 虞世南.北堂书钞[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345.
[19]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0]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53.
[2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55.
[22] 应劭.风俗通义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8.
[23] 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刘真伦,岳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3.
[24]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492.
[25] 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J].思想战线,2017(6):1-8.
[26] 彭新武.论循吏與时代精神[J].政治学研究,2015(5):46-54.
[2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
责任编辑:赵 玲
Abstract:The upright official, which started to appear in the Han Dynasty, played the roles as teacher and bureaucrat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re are two origins: one is the tradition of "official as teacher" and another is the concept of "rule by education" in Confucianism. Both of them startedin the ancient times in China and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in later generations.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 upright official in Han Dynasty put the concept of "rule by education" into practice through moral education, setting up schools, and changing social customs, etc.,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ord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nation identity to Han dynasty. Upright officials social governance in Han Dynasty was inherited by the later bureaucrats, and i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Han Dynasty; upright official; "rule by education"; "official as teacher"; social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