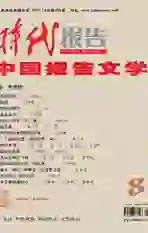浏阳会馆: 城南明明 千里恻怆
2019-09-11彭晓玲
真是很巧,不管是谭嗣同的出生地孏眠胡同,还是后来谭继洵购置的库堆胡同房屋,后辟为浏阳会馆,都在京城宣武门外。在宣武门外,在宣南,谭嗣同曾度过一段美好而又刻骨铭心的童年时光。
初遇浏阳会馆
“宣南地区文化历史积淀非常深厚,全国数一数二。”清史学家戴逸曾这样称赞。如今,大多数会馆已经湮没无闻,那么曾是浏阳会馆的谭嗣同故居又如何?
那是2010年秋天,北京的秋天,就有些萧杀之气了。其时我在北京学习,与友人念叨了几次,想去菜市口看看,去谭嗣同故居看看。那是个阴雨的天气,友人特地送我去浏阳会馆。下得车来,猛然发现我就站在谭嗣同故居文物保护碑前,再过去便是一座陈旧的青砖平房,大门口在中间,却只有光光的门框,看来已成过道了。而屋前有一棵槐树,倒是长势旺盛。
我愕然了,我原以为,谭嗣同北京故居,既为昔日的浏阳会馆,至少大门口会有些气势,却是一副平民模样。原以为,浏阳会馆旁边还有成群的四合院,还有悠长清爽的胡同,竟然面对着新修的菜市口大街,且车流如织,高楼萦绕。凛冽的风呼呼而来,我竟有些站立不稳,寒意自脚底直往上窜,莫名地慌乱起来。
我犹豫不决,甚至萌生了退意。我清楚地知道,浏阳会馆虽然不是中规中矩的四合院,但它依然拥有前后三进房屋,是个大院落。但到底什么模样了?是不是真如媒体上所说,长达几十年来,谭嗣同故居已面目模糊,只有混搭的房屋、狭窄阴暗的过道、凌乱不堪的杂物,和挤住在一起的百多个男女老少居民?
但既然来了,不进去看看,真还有些不甘心。我独自纠结了一番,冷风萦绕着我,竟然有些辛苦。于是,我决意进去看看,不管将面对如何局面。
我直直地朝门口走出,门洞边上撂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及一些面目模糊的杂物。原以为,进去便是无比杂乱的一个四合院,但我的视线被墙壁挡了回来。眼里除了冷冷的墙壁,什么也没有,好在左边有一线狭窄的巷道,拯救了我。我只得顺着巷道往左,走了一会,两边都排了些年代不长的低矮砖木平房,除了参差不齐的墙壁,就是参差不齐的门或窗户。门窗上多半蒙着褪色的画纸,或脏兮兮的布帘。
我真是惊叹,过去的岁月里,此地的居民,各自施展各自的招数,不时在院子里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时地你搭一间我搭一间,院子里除了留下这条巷道是公共的,其余的都成了私人空间。我估摸左边那排房子,是昔日的第一进房屋,曾有谭嗣同的会客之处,大气而端庄的“怀旧雨轩”,现在却隔成一间间的小平房。一家家房门紧闭,色泽斑驳。
随后,往前直直地走过一条狭窄的过道,两边依然是搭建的低矮不一的平房,毕竟宽了些,略微可以喘气了。走道很快走到尽头,得向右折。站在交叉口,我抬头一瞧,眼前这排房屋倒有些气势,依然可以看出昔日的庄严,此处应是当年会馆的第二进屋子,也是这里的主屋。
想当年嗣同就住在这排屋子的西端,他的书房“寥天一阁”和住房“莽苍苍斋”,大概就在这里了。当年的“莽苍苍斋”,如今早换过几次主人了。当年房门上,谭嗣同曾自书对联:“家无儋石;气雄万夫”。康有为认为太霸气了,谭嗣同便改为“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而屋子里原本挂着谭嗣同的照片,照片上他一副宽额阔鼻、眉心微蹙、留着长辫子的英俊模样。这排屋子也挤成一团,对联早已不见,两侧的柱子和房顶的木椽破落斑驳,在白石灰和混凝土涂抹的墙壁裂痕处,能隐约看到青灰的砖块。
再四周瞧了瞧,院子里几棵古槐还在,但已被后来搭建的矮屋包围,一副孤独忧郁的模样。只有老屋的青砖黑瓦,还有那些雕花的窗棂,在诉说逝去的历史。
站在周围狭仄杂乱的过道中,怎么也无法窥清全貌,也實在无法想象当年谭嗣同当年在这里生活的景象。也许是上班时间吧,除偶尔从某间房屋透出电视机的声音,或突然而起的说话声,竟然连人的影子没看到。
渐渐地,我恍然起来,不知身在何处。这么一个杂乱而肮脏的小院,竟是昔日的谭嗣同故居,令我除了无语,还有无奈。我的心绪低落,匆匆地逃离了出来。
再次站在大门口,却门洞冷冷地瞧着我。我突然发现,大院一侧有天桥通向路菜市口大街的另一面。从高处看故局大院又如何呢?我来到天桥之上,顾不上去大街奔向如何,只管去眺望故居大院。院子里那些后来搭建的房子屋顶不高,让那几棵槐树遮住了阴影。于是,大院的整体格局大致出来了,那些漆黑的屋顶,演绎着昔日大院的风采。我长吁了一口气。
就在刚才,我在大门口遇见了一位壮实的中年男子,我问他,院子里怎么搭建了那么多房子?他原本不想理我,但还是不耐烦地说:这旧居占地800多平方米,只有3个院子,却住着26户人家——就这个数字还经常变动,总是有人搬走,又有人住进来。原先的一间房子被隔成两间,仍不够住,当然就有人想方设法搭建房子。房子和房子挤在一起,高低不一,当然就彻底破坏了原有的布局。你看看,现在许多地方都得侧着身子才能过去,有时候一不小心,还会闯进了人家的厨房呢。说是要拆迁,怎么到现在就不拆迁了?
说完,他还瞪了我一眼。以为我是街道派过来的工作人员么?我吓了一跳,也不敢多停留,匆匆朝前面的天桥方向走去。当我终于站在天桥之上,再次眺望着昔日的浏阳会馆,年代久远的屋顶上,一堆堆的野草正肆无忌惮地生长。不能不承认,于浏阳会馆而言,浪漫和优雅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嗣同的南下洼
同治四年(1865年3月10日),谭嗣同出生在宣武门外孏眠胡同,因在族中排行第七,他被人称为“七公子”。那时,他的父亲谭继洵正在户部任职,家境日渐殷实。
至同治六年九月二十日(1867年10月17日),就在谭嗣同2岁之时,谭继洵买下了时宣武门外库堆胡同房屋一所为府邸,为其座师刘崐故宅。于是,一大家人就搬于了此宅。虽然后来,谭继洵又将此宅买给了浏阳宾兴会,成了浏阳会馆,但他家依然住在这里。后来,谭继洵因京官外放,带着全家前往任所,这里依然是浏阳会馆,谭嗣同来往京城就常常住在这里。
其时,浏阳会馆坐落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北半截胡同,是一所坐西朝东的宅院,它由前后三个相连的跨院,附带一个小跨院组成。其前院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院中有两棵长得十分茂盛的老槐树,树冠覆盖小院上空,春天槐树新绿,花开之际,香气四溢。一进浏阳会馆的月亮形大门,就可以看见五间整齐的西房,这是会馆的正房,为谭家主人所住。靠西三间,就是谭嗣同后来所住的莽苍苍斋,两棵老槐树就住于正房门前的两旁。会馆的后院,辟有后门,可通南半截胡同,后院中有一棵枣树,每至深秋,树上就挂满了通红的枣子,给小院增添了无限风情。
他对手足之情十分依赖,时常赖着两位兄长带他在附近一同来回地玩耍。浏阳会馆地处宣武城南,接近南城墙,四周地旷人稀,那条巷子里只有二三栋房屋,精致清爽的模样。屋后就是大片大片荒野,人称南下洼,这里积水成泽,芦苇丛生,鸟兽出没。于是,四周的旷野,便成了他们的乐园,他们欢快地在附近的胡同巷里奔跑,在河边戏水,在陶然亭中玩耍,在沼泽树林间探险,玩得不亦乐乎。
但伯兄嗣贻大他13岁,嗣同小时,他已长大成人了,和两位弟弟在一起玩的时候不多。他给嗣同留下一个喜欢独来独往的印象:伯兄很少外出,外出就健步如飞,只管往前走,他跟在后面怎么也追不上,甚是失意。于是,他转而找他的仲兄谭嗣襄,这个比他大9岁的哥哥,成了他儿时的玩伴,亦是他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亲人。
仲兄嗣襄小时很调皮贪玩,喜欢攀登到屋脊上,大胆地在屋脊上走来走去。他又擅长骑马,但见他跃上马背,挥鞭绝尘而去,直到马跑不动了才作罢。真是个上房揭瓦、上马挥鞭的主。父亲鞭打教训他,他却嬉皮笑脸,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去,依然故我。但他聪明颖悟,书读得好,有人说他孺子不可教,但懂得他的人则认为他志向高远才气出众,为人豁达不拘细节。
嗣同最喜欢和仲兄在一起,嗣襄通达脱俗,不拘小节,喜欢冒险,带着他轻捷走险地,到水里游泳玩耍,爬山涉水,没有不敢去探索的地方,享受着童年的快乐。一个雨后初霁的夏天,在浏阳会馆的门口,或许是因为有事而去,或许是为了捉弄年幼的弟弟,玩到一半,嗣襄哥哥竟不见了踪影。猛地不见哥哥的身影,五六岁的嗣同非常孤独害怕,情不可已,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嗷嗷大哭起来。
在离开北京之前的十二年里,他与嗣襄一同读书、学习、玩耍,他曾极富诗意地描述这段儿时与仲兄一起伴读的经历:“回忆当初烟雨在帘,入夜蛙声鸣叫,或落叶簌簌而响,庙里的钟声响彻云天,灯下共读,却想入非非,神游八方。”
会馆附近南下洼大片旷野,原本是清代八旗校练场,已接近南城墙。陶然亭、龙爪槐、龙泉寺等都在这一带。嗣同兄弟读书之暇,就经常到南下洼去游玩。而陶然亭,位于元代古刹慈悲庵之内,历来是文人墨客雅集之所。嗣同时常前往慈悲庵游玩,久而久之就与这里方丈熟识了。佛寺钟磬间,他将僧院里前前后后的小路走了个遍后,最喜欢呆的地方还是禅房后面的僧人墓地。那里树林茂密,黄昏时乌鸦喧哗叫嚷,更加觉得四下里一片宁静。野草长势旺盛,比人还高,野鸡和兔子在草丛中跳跃飞窜”。他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竟然喜欢独自呆在人迹罕至地方,品味着与他年纪不相仿的哲思和寂寞。
站在暮色初降的陶然亭前,极目远望,可以看见远处雄伟起伏的西山,不远处蜿蜒伸展的城墙,欣赏着迷人的景色:“西山晚睛,翠色照地,雉堞隐然高下,不绝如带,又如去雁横列,霏微天末。”
其时,南下洼,荒冢遍地,人迹罕至,其荒凉萧索的景象,不免使人有孤独哀愁之感。城南穷人本多,叠瘗乱葬、狸猃穿冢,骷髅横路都是常事。于是平野荒凉的景色,对嗣同来说,往往是别有一番风味,既兴奋又迷惘。春雨绵绵、蛙鸣不已、海棠花开的时节,有一天忽然哭声盈野,纸灰时时飞入他家的庭院中,他便知道,又是一个清明节到了。这年清明,他坐在自家书室里,私塾先生正好讲到宋代诗人高翥的《清明日對酒》,当谭嗣同读到“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的诗句之时,忽然悲伤哽咽不能成语,以至不能自已。老师愕然,不解其故,问及他为何而流泪,他却说不上缘由。
谭嗣同是天生的多愁易感,幼时严重怕鬼。宣南到处植有白杨树,某天晚上,嗣同正在夜读,听白杨树在风中咆哮,仿佛鬼号。小嗣同大为恐惧,吓得哭着跑到兄长跟前,两位兄长一起好言好语地安慰他哄他,方才止住悲声。可是第二天白天,他又迫不及待地去坟地里探索新路,不再知道害怕了。
而在十五年后,光绪十五年(1889)春,他带着侄了传简一道来到京城,拟参加此次顺天府恩科,就住在浏阳会馆,再次重回宣南故地。他又在晚上听到这酷似鬼叫的白杨风声,他竟披衣而出,与白杨对语:“曰鬼来前,予识汝声。二十之年,汝唱予听,予于汝旧,汝弗予撄。”鬼啊鬼啊,二十年前你唱我听,如今我还记得你,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
这一次,谭嗣同还带了传简一同重游故地,他找到了幼年玩耍的林泉沼泽、瑶台甘井,把少年时和两位兄长的游历一一告诉他,还有当年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兴奋与悲哀。传简却很不懂得他的意思,反应迟纯,不为所触动。令谭嗣同颇为怅恨,他想这个世界上,除了二哥之外,大概没有人能理解自己对于城南的怀念了,也唯有独自黯然神伤。
就在此时,五月五日(6月3日),谭嗣襄卒于台南府安平县蓬壶书院的噩耗传来,如万箭穿心,谭嗣同痛彻心扉。他携侄子传简星夜南奔,打算前赴台湾迎回仲兄嗣襄灵柩。取道南下洼时,他目睹昔日景物,误以为往昔而更生伤痛。
自此,仲兄嗣襄逝去的伤痛,总是击打着他,他无法忘怀这位给予最多温暖和关爱的亲人。在谭嗣同眼里,仲兄嗣襄个子挺拔,如玉树临立,光彩照人,目光炯炯有神,聪明过人。年幼见人在下围棋,试下数子,就赢了对方。每当好朋友一块聚谈,嗣襄话锋最健,生动而又风趣,谁都不是他的对手。遇到问题,他喜欢苦苦地思索,探索精微奥妙,无微不入。如此说来,谭嗣襄虽然没有画像传世,但其神韵与嗣同颇为相似。
但他死前最后一段日子住在浏阳会馆,为国事而忙碌奔波,死后一段日子也停灵于浏阳会馆后院。却不知其最终的轻死轻生,与其年少之时多历生死是否有所关联。八岁的谭嗣同在书斋内读着《清明》忽而哽咽不已,而三十三岁的谭嗣同在书斋外后院静静沉眠。一墙之隔,就在纸灰飘转间,时间的罅隙终于缓缓接壤了,却令人伤痛不已。
谁信京华尘里客,独来绝塞看明月。至此,宣武城南那个怅怅看着纸灰落泪的童子,度过边塞纵辔狂奔的岁月,而终能回到京城,坦然名世了。
再访浏阳会馆
2017年5月28日,一大早,阳光倾泄而来,天气热起来了。我拖着行李,再次来到了浏阳会馆。菜市口大街甚为宽阔,车流如织,差点走过去了,是浏阳会馆门口那棵槐树提醒了我。看着低矮的大门,还有门边靠墙放着的破沙发。还没有进去,我就能想象到院子依然故我地杂乱。
我是如此矛盾,我多么想缓缓地在院子里走走,去找寻昔日英雄的精神气韵。但想想混乱的院子狭窄的过道,又犹豫了。我不由再次张望大门口,猛然发现大门口右侧墙上,小窗户玻璃上贴了红底白字的广告语:香河肉饼。上次都没有这个广告,看来这里新开了家小吃店。可香河肉饼,之前没听说过,产自哪里呢?门口站着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穿着桔色的T恤,他对我的问话置之不理。我只得无趣地自顾自朝大门洞走去。
院子里静悄悄的。一走进院子里狭窄的通道,便传来小狗的叫声,一个蓬着头发的中年女子牵着一只小白狗,正朝外面走,小狗叫个不停。我继续朝前走,我想接着上次的路径朝前走,便从二进前小巷往右横过去,再穿过屋侧小巷道,来到后面,又是小巷道。见一位瘦个子老大爷坐在路边,举着一张报纸在看。我忙停了下来,试着与他打招呼,没想到他放下报纸,招呼我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坐下。我心里一动,何不与他聊聊?没想到,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大爷非常知道谭嗣同,一说就是一大串:
我看了谭嗣同的简历,他母亲带着三兄弟在这里读书,这是浏阳会馆。会馆,你懂什么意思么?北京会馆多得不得了,成千上万,那时在北京盖房子随便。地方上有旱灾水灾及进京赶考,都有地方住。这房子是会馆,别人家早盖好的,是他父亲买的。谭嗣同与光绪皇帝关系不错。他们怎么好的?咱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接触人多,他对光绪说外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外国先进,中国太守旧。光绪与慈禧太后,慈禧是光绪的姨,不是他亲妈。慈禧太后知道谭嗣同说外国好,吹嘘外国好,就将他斩头了,那个时候杀个人不算什么!
你等会出院子,往北左拐走200米了不得,过去是丁字街,有个菜市口杀人场,多少朝代都在那里杀人。十年前,没有门外那个大街,后来将四个小胡同拆迁了,丁字街也没了,才修了菜市口大街。
你说我今年多大了?我今年89岁了,1926年生。到这里只住了十年,当初老伴在伊利食品厂,给她分了一间房子,二进右边一间房(西房)。之前有人家人口多,见院子里有空地,就盖间房,没人管。之前我住在广安门大街,那里拆迁给我四环二居室,我的户口还在北边。我与大儿子合不来,大儿子也有一居室。孙女35岁了,也有一居室。都是搬迁给的。我们刚过来的时候,住不下,见房子后面有一块空地,就盖上了。盖了间小卧室,还盖了间小厨房。但自己盖的与政府没关系,政府管不着。我有三个孩子,二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女儿64岁了,大儿子60岁,小儿子48岁了。
这个院子住了多少人?搞不清楚。原来的正经房,是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挺大。后院是后盖的,是解放后盖的。白天上班去了,人不多,周末就人多了。也有些房子,没人住了,主人过段时间来打扫打扫卫生,房产局每月收20多元租金一间房子。现在20多元不当回事,如果拿出200万,这里的房子就写成你的名字,你就可以住。可这里上厕所不方便,出门往右拐,住南走,老房子都这样,厕所不在院里,都是公厕。
我哥哥人口多,没地方住,房管局指定在这里住,在这里也分一间房了。我的妹妹根本不住这院里,见我在这里盖了间房,就在我隔壁盖了一间房,给快结婚的女儿住了。房子盖好了,女儿死了,她自己也死了。她儿子将房子租出去了,每月有1000元钱,街道上的人找了他两回,都没找上。
正聊得热闹时,他儿子端着一碟子煎饼过来了,搁在他身边的高凳子上,也不做声,转身又走了。大爷笑笑说,这就是最小的儿子,他媳妇上班去了,他就每天照顾我与老伴。我老伴都80了,这个时候到外面捡破烂去了,等会就会回来。
老大爷虽然瘦弱,却说话直爽,真想再和他聊聊,但怕打扰他吃饭,只好告辞。谢过他之后,沿着弯弯的小道,继续往前走,往右转,没走几步,两只小宠物狗直冲我们而来,使劲地叫着。右边是一间小厨房,一位老妇人在忙着做午饭,左边房间里走出来一位戴眼镜,穿着白色背心杏色短裤的汉子,有些胖。他招呼着狗,不要乱叫。
我忙上前自我介绍:“大哥,我们来自浏阳,来自谭嗣同的老家,来看看他故居的情况。”他人很热情,就站在过道上与我们聊了起来。他说:“我姓田,现在北京出台了一项政策,比如谭嗣同故居,是文物改造,倘是浏阳地区出钱,将院子里的人安置了,院子就可以给浏阳!”
我与同伴对此既高兴,又惊讶:“这块地,浏阳出钱,就给浏阳!但拆迁怎么办呢?院子大大小小堆积起来的房子,实在是个大难题。”老田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文物改造政策!要是别人出钱,倒不干了。只能你们浏阳人出钱买下,才行得通!当然没有几个亿怕是不行!”
“啊,几个亿,说来轻松,浏阳哪有那么多钱呀?可明明这些房屋还是公产,安置起来也那么难吗?”我真是不敢想。
老田看来也是个爱说的主,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告诉你们吧,上次量房量到附近几个院子,有六七十多户。至于北半截胡同,加上后院,南院,怕有三十多户吧。原来后进有后门,后门也有房子。分配的是公房,各家私自盖的,就是私房。我家只分了一小间,也挺困难的,就在前面盖了间小厨房。侧面原本是我家的范围,应该我盖,却让人盖了间住房。人家比我早来了,抢先早盖好了,就成人家的了。
接下来,老田又说到了拆迁的事:这点钱,搁在个人身上算钱,搁在政府上根本算不着钱,一说就是投资多少多少!
我说:“买地的钱浏阳有,可拆迁的钱只怕难。
他急了,插嘴道:“等于是一舉两得的事,把院子这帮人安置了,你们浏阳得了这块地。等于建招待所也好,干什么也好,等于也有用呀,在别处买地不是也一样么?”
我赶紧说:“盖招待所肯定不会盖!”
他不以为然:“这个院,过去的会馆,不也是招待所似的么?也可以是驻京办事处,或者博物馆,都可以!”
我也觉得很好,忙附和道:“哦,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信息,回去可以找有关部门汇报一下,搞个博物馆真的很好呀!”
他又说:“你们浏阳地区,多少年前,有十好几年前,小二十年前吧,你们管文物的也上这儿来过,我那时就向他们提出来了,你们要投资也是一举两得!你们得了这块地,也给老百姓安置了!现在北京市捉摸过味了,提出谁投资算谁的,比如绍兴会馆,绍兴你要是投资,就归你绍兴使用了!
我只得说:“浏阳也是财力不够,不然真可以买下来!”
他依然不罢休:“弄个驻京办事处,弄什么也好,对浏阳来说,可以提升浏阳的名气!”
我不想再谈这个话题,就赞扬他很头脑,多年前就想到了这个主意。见他有些小得意,我赶紧转换话题,问道:现在院子里一片安静,大家都去上班了么?同伴则插着问道:这里住得最久的是哪一户?他倒是很自然地答道:“现在来说,应该就是我住得最长的啦!我今年六十多了,退休了,我的孩子在外面租房子住!出门往南走,那里正拆着!和这个院子差不多!”我问:“那棵槐树,是不是以前的?”他想了想说:“这说不好,杨槐长得快!可能只有三四十年的样了,要是国槐就有可能是以前的!”
我接着问:“您挺懂历史的,能和我讲讲这个院子的历史么?”他又滔滔地说了起来,但只说戊戌变法的历史,真拿他没办法,只得打断他:“您在院子住了三十年,您对谭嗣同如何看?”他的话头又来了:“他是改革派,但改革要分开来看,有的改革往好的改,有的改革往坏的改!从上往下改革也是好的!”我笑了,不由问他:“谭嗣同要是改革成功会怎么样?”他肯定地说:“我觉得中国到现在会相当富的,那就不是皇上说了算,可能会像英国一样推行君主立宪制!你想想,从1898年开始,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中国已经很富裕了,还会有日本打中国的事么?不可能的事!從历史上看,日本老想打中国,一直打不进来!维新变法成功了,日本绝对打不进来。”
我又问:“您是地道的北京人么?您觉得谭嗣同这个人怎么样?”他很坦然地说:“我老家是河北石家庄,父亲过来了,就将子女带过来了!我就一直在服装公司工作!我觉得谭嗣同他这个人还行,他能像康有为一样地走,但他没走,他想变法流血从他开始。”
这田大哥也太会说了,这时小狗又叫了,快十一点多了,我们就趁机告辞走了。往回来,快到大门口时,意外地发现之前会馆门房处,竟开了扇门。忙敲敲门,屋里有男声应答,我便走了进去,一位高个子男人从另一间屋里迎了出来。屋里光线暗淡,过了好一会,我才略略看清屋里的陈设,倒是简洁大方。原来他是刘家女婿,我心里暗喜,好不容易逮到了刘家的人,说什么也要多问。刘家女婿倒是性情好,言语从容而得体,一一回答着我的疑惑:
我是刘家女婿,家人都上班了。老太太刘万华得了肺癌,前两三年过世,老爷子刘正源于1995年去世。刘老太太有一个儿子三个闺女,有一个孙子。这栋房子是前栋,刘家分有两间房子。现在只有老二儿子住在这里,他在一家汽车交通公司,负责加气加油,他今天上班了!我是刘家大女婿,我退休了,回来住住。隔得太远了,刘家在1980年代之后没有回过浏阳,因为都不知老家在浏阳哪里。
刘家原本还有谭嗣同照片呢。老太太常常说起,谭嗣同梳着长辫子,很英俊。可就在1969年夏天,北京下大雹子,把刘家的房子全砸烂了,家里的照片都被吹到院子里,搅到了烂泥团里。那时,保护吃饭睡觉的家伙要紧,哪里还管得上什么照片。刘家祖上的照片,和谭嗣同的照片,都在那时毁了丢了。
老太太于1956年嫁到这里刘家,那时整个北半截胡同四周的建筑古朴陈旧,院子里还很安静很整齐,没有住几户人家,而前面院子里还有两棵高大的槐树。到七十年代,这个院子还保持之前的模样,到1980年左右就开始乱盖房子了。也是家里的孩子多了,住不下了,只好乱盖。自1982年他第一次来,当时后院盖得差不多了,前院也乱盖了。
这个院子,人一天天变多,房子一天天变密。一开始来的人,多半是通过单位分到房子,至1991年,“谭嗣同故居”的牌子被刻在了院门外的墙上。没多久,最后一拨常住人口搬进来。当时,分配房子的政策还没有取消。后来,有些人搬走了,房子租给了外地人。
现在这里大多数住户都盼着早日拆迁,希望用拆迁获得的补偿购买新房子。1999年,为了修建现在的菜市口大街,院子里的人家都已经与建筑单位签了合同。不过,因这里是文物单位,不能拆迁,也就没有拆迁。
谭嗣同是向封建王朝“开枪”的勇士,但现在这里破成什么样子了,都乱成一塌糊涂。今后可能还是要拆,根本不能弄回原样了,可能就是将来竖牌了事。
刘家女婿竟然知道这么多,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终于知道了浏阳会馆这么多年的状态。待我在故居大杂院里转过几圈后,依然杂乱,依然狭窄,且几乎家家房门紧闭。
便来到隔壁香河肉饼店。这里也有一个门洞,也有一家小院子,与故居大杂院连在一起。之前是不是属于故居的房子?倘按之前的规格来看了,可能属于同一家院子。就在门洞靠左侧一间小房子,就是肉饼店。中间摆了一张长条桌,靠内墙还摆了两张小长桌,一律红艳艳的塑料方凳。进门靠墙,则依次排着大冰柜、烤饼的炉子、方形工作台,还有一列三层高的铁架子,其上搁了些什么大碗小碗筷子之类,什么面粉、香菇、蔬菜、粉丝之类。桔红衣老板现在已经在忙碌,戴上了白帽子围上了白围裙,而屋子里还有一个中年嫂子在忙碌,留着短头发,穿件棕色短袖衣。见我们来,她笑笑地迎了上来。
我走进屋内,与同伴每人点了一个沙锅面条,就在坐那里等。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便询问桔红衣老板关于故居的情况。他背对着我们在干活,但依然感觉到他很不耐烦的神情。他终于不忍耐地说了起来:“1898年的事现在能记得清吗?都不记得!1898年的事现在知道吗?谁都不知道!离现在多少年了?还问什么?吃饭吃饭,喝水喝水,慢慢地,别管那么多。什么故居?就只一个牌子,啥都没有!”
我倒是沉得住气,同伴却急了,说:“我们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想了解一下到故居参观的人多不多?”老板的语气依然生硬:“你们进去看到什么了?和里面的人聊了什么?他们说的,你们没看见?了解的都是假的,眼见是现实;别人说的是假的,眼见为实。”
我接着说:“上次这里没你这家小店!”他反问:“你上次啥时来的?”我说:“前年!你这个店是前年开的么?”他倒是很痛快地承认了:“现在变化多大,一年一个变化。100多年有啥?就只有一个牌子。你们看这里保留了的都不齐整,何况是没保留的?我是西安人,我家在西安东北的渭南平原,我们村子里的古迹都比这个好多了。北京还有很多这样的院子,条件太差了,不是一般差,差得不得了,乱得一塌糊涂。而我们老家那里保护得很好,虽有人住,住归住,东西不能动人家的。这里光只有一个牌子,啥都没有。”
这时面条端上来了,我趁机再加上一份香河肉饼。他依然气不顺的模样,当我提起故居院子乱搭乱建时,他又来气了,气愤愤地说:“乱建还不说,有些人把住着的房子都卖掉了!”我一听傻了,卖了?把公家的房子卖掉了?他说:“有的就是卖了!好多都成了私人的!哪有公家的房子?”我不由赶紧表扬他有正义感,他倒是笑了,却又无奈地说:“姐妹,哪儿都一样,都一样!这里保护得太差了,啥得没有,最起码连一棵树都没保留!一棵树都没保留!你要看,看啥呢?没啥看,没有!里面啥都没有!发展也不能把人家东西拆了,要保留的一直要保留,破了要维修,坏了也给人家修,不能给人家破坏了,弄得啥都没有。”我也颇有同感,感慨地说:“真是乱搭乱建,有地就加一间,有地就加一间。”他说,他作为西安人,对此不能理解。人家是古董,就要把它当古董,不要破坏。这个故居是古董,可都拆得差不多了。我赶紧说,主体建筑没拆,只是密密麻麻搭建了好多房子。
交谈如此压抑,我在小店再也呆不下去了,就走到菜市口大街上。看看街对面高耸入云的中国移动大厦,再看看身后破旧的故居,一个是时髦神气的现代巨人,一个是病病歪歪的垂危老人。突然产生联想:如果没有谭嗣同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没有一批批为改变中国命运的烈士流血献身,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成功吗,会有再后来的中国人民共和园和当代的伟大改革吗?倘忘记了这些先烈,就是中国人的羞耻。
来日又如何
但至2010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北京市宣武区行政区划,将其原有地域划入西城区范围。至此,宣武区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终于,2016年底,在《北京晚报》的头版头条看到了这样一条报道:“最大规模文保腾退启动:西城区发布文保计划,浏阳会馆、谭鑫培故居等14处文物明年腾退。”我心里满是慰藉,忙与好友们分享这一喜讯。我清楚地知道,这是谭嗣同后裔谭志宏先生多年努力多方奔走的结果。当我打电话询问他时,他在那头沉吟了一会,才缓缓地说道:有今天这样的结果,既在我意料之中,又在我意料之外,但实在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哪天我们找时间好好聊聊吧!
为了谭嗣同的话题,虽然我们不时见面,便始终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交流。当我们坐在一起好好聊时,已是两年后一个火热的仲夏之夜。在株洲他家三樓那间宽阔却又闷热的书房,围绕浏阳会馆的前世今生,不知不觉就聊了二个多小时。话题却从他的父亲谭恒辉开始。当年谭嗣同伯兄谭嗣贻故去时,其子谭传赞还很小,谭继洵很喜欢他,一直将他带在身边。毕竟是书香门第,谭传赞书读得好,写得一手好文章。谭恒辉是谭传赞的大儿子,生于1908年,于1926年考到了北京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五年间,他不时来往浏阳会馆,他非常景仰嗣同公的节气和精神。
大学毕业后,谭恒辉至天津市政府城市公共事业管理局工作。就在这一年,与毕业于北京朝阳女子大学的王蓉一见钟情,与这位山东济南姑娘结婚了。1937年日本鬼子来了,他就带着妻儿回了浏阳。至1944年抗战时,蒋介石推出“十万青年十万军”计划,谭恒辉满怀激情地从军了,在岳麓师管区担任司法处长。后来,谭恒辉又至廖耀湘新六军六十六师任司法处长。辽沈战役时,部队被解放军围了两个多月,廖耀湘下令突围。谭恒辉是文职官员,不会骑马,从马上掉了下来,被俘虏了。解放军对待俘虏政策很优惠,在内蒙古集训半年后,谭恒辉本来想留下,但解放军政委见他是名门之后,就劝他回浏阳。于是,谭恒辉先回北京接妻儿,一同再次回浏阳,在浏阳崇兴小学当校长。
谭嗣同兼祧子谭传炜,他的杨氏夫人,人称三娭毑。三娭毑的儿子谭训聪在浏阳解放前夕跑到台湾去了,家里的钱也让他带走了。她是小脚,又七八十岁了,没走。三娭毑有很多田,1950年减租退息时,三娭毑只得将家里值钱的首饰拿到长沙当了,换钱退给佃户。还不够,佃户仍来找麻烦,三娭毑无奈之余,就上吊死了。那些佃户就转过来找谭恒辉,说钱还没还够!谭恒辉也很无奈,只得回复他们说:“她死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又不是我欠了你们的!”就因这句话,谭恒辉就成了“破坏减租退息运动”的人。后来,他又给在学习班的弟弟谭虎当保人,可当时广州军区港澳工作组安排,让谭虎以难民的身份先到香港,再潜入台湾做卧底。但这是绝密信息,谁都不知道。当浏阳公安局找谭恒辉要人时,他也交不出人。于是,新账老账一起清算,谭恒辉就被抓起来了,于1951年被判了10年徒刑,送到东北嫩江劳改。
家里的顶梁柱走了,孤儿寡母如何生存?王蓉想死的心都有了,但她是一位坚强的女子,就靠她在时县政府当会计的工资,养着一大家子人。至1954年浏阳城涨大水,王蓉又失业了,只得带着年幼的几个孩子到长沙谋生。因是谭嗣同后裔被安排到株洲铁路机电学校教书,虽日子艰难,但从此在株洲有了安定的家。
1958年9月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隆重举办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王蓉作为谭嗣同后裔接到北京的与会邀请。当孩子们送她去车站时,8岁的谭志宏吵着闹着要和她一起去。王蓉心软了,就带着他一起去了。这次活动意义深远,让谭志宏小小年纪,就知道到嗣同公竟然是个伟大的维新变法人物,他是烈士的后裔。
而真正促使他为弘扬谭嗣同精神,而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懈地努力,当在1982年10月。那年10月21日,他含辛茹苦一辈子的母亲王蓉去世了,悲痛之余,谭恒辉及谭家子女都特别想将她葬回老家浏阳。于是,第二天谭恒辉就带着谭志宏来到嗣同墓地所在地,找到当地生产队负责人商量。当地生产队一口答应下来,而且不取分文,令父子俩很感动。随后,谭恒辉父子来到了嗣同公墓地,沿着一条泥土路,来到墓地,但见铺天盖地的茅草展现在眼前,哪里有坟墓的踪影?谭氏父子大为惊愕,走进重重草丛深处,方才找到衰败的坟堆。细细查看,当初坟堆由三合土和着糯米筑成,其上还嵌着颗颗精致的鹅卵石,虽被青苔遮盖得严严实实,倒还完整无损。谭氏父子不由长吁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才渐渐平静。再认真查过,三块墓碑也还在,只是周边的青石板墓围大都掉了下来,东倒西歪地躺倒在坟堆旁边,墓前的石马石虎乱了阵脚,华表干脆大都埋在了泥土之中。十月的阳光很温暖,行走在墓地里的茅草丛中,父子俩的心里却直冒寒气,烈士为国捐躯,却已被世人所忘记,乃至墓地极其潦倒。甚至其夫人李闰的墓,父子俩在山上辗转了许久,一时都未能找到。两天后,谭志宏兄弟姐妹们将母亲及之前故去他们大哥的谭彪都安葬在昔日的谭家土地上,离嗣同公及夫人李闰的墓地很近,倘亲人地下有知,他们也就欣慰了。
重新回到株洲,念及嗣同墓地的无人料理无人保护的情形,谭恒新、谭志宏父子就赶紧书写一份情况反映送至了湖南省委统战部、湖南省政协。当即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和关注,由此得知谭氏后人去向。不久,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亲自接见了谭恒辉、谭志宏父子,至当年年底就安排谭志宏为特邀界别政协委员。也因此,从1983年起,一直至1998年,谭志宏连续担任了三届省政协委员。
对此,谭志宏心怀感激,1983年就向省政协提交了三份提案:关于在1983年举办谭嗣同殉难85周年;关于请求修复谭嗣同墓地;关于腾退谭烈士专祠,并重新布展。令谭氏父子大为鼓舞的是,三项提案一一落实:当年9月在浏阳县城举行了谭嗣同殉难85周年活动;当年拨付3万元修复墓地;当年浏阳成功腾退谭烈士祠,并重新布展,对外开放。
谭志宏大受鼓舞,他的视野越来越广,他的事业越来越向前发展,他的履职积极性充分得到了调动,且成效明显:1988年9月,在浏阳举办谭嗣同殉难90周年活动;1998年谭嗣同殉难100周年之际,腾退并修复了谭嗣同故居,举办了隆重的系列纪念活动;2008年9月,在浏阳举办谭嗣同殉难110周年活动;2013年10月,谭嗣同爱国基金会顺利成立……
一系列活动的举办,谭嗣同为改革而献身的精神,日渐深入人心。而在谭志宏看来,他已由之前仅仅对谭嗣同纪念的一种狭隘理解成长起来,谭嗣同不仅仅是谭家的,更是整个中民族,甚至是世界的谭嗣同,谭嗣同精神是值得我们民族永远推崇的精神。
而当谭志宏第一次走进北京浏阳会馆时,他也和我一样,被其中的杂乱无序而悲哀而气愤,我的悲哀只是悲哀,而他却将悲哀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当他认为浏阳故居、墓地及谭烈士祠都修复建设好了,他的视线转到了北京浏阳会馆。他是一个坚定的行动派,总是毅然决然地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情。记不清多少次赴北京找相关部门相关专家,也记不清他为此流了多少汗着了多少急,更记不清他为之受了多少委屈用了多少钱,终于到2015年谭嗣同诞辰150周年之际,他认为条件成熟了,他行动起来了。这一年他湖南北京来回奔波,促成北京西城区、浏阳市都举办了大型纪念活动。且就在这一年年初,由民革湖南省委主委刘晓先生牵头,联名6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腾退浏阳会馆的提案;与此同时,由北京市港澳委员庞鸿先生牵头,联名22位北京市政协委员向北京市政协大会提交腾退浏阳会馆的提案。兩份提案,当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至2016年终于迎来了振奋人心的结果,西城区向全社会作出公共承诺,包括浏阳会馆、谭鑫培故居等14处文物2017年腾退。
那一刻,谭志宏这个坚强的汉子,竟然禁不住热泪盈眶:三十五年一晃而过,一个人一辈子又有多少三十五年呢?他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在弘扬嗣同精神的路上跋涉,到如今已然华发早生,两鬓斑白!
2017年腾退工作如期启动,但当初由重重利益搭建成了混乱的院落,要去清理去腾退那些纠结在一起的利益又何其艰难?2018年清明前夕,我正好在北京。就在清明前一天,北京寒风凛冽,竟然还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小雪。清明那天下午我飞机回长沙,但在上午我还是匆匆赶至浏阳会馆,一为祭拜一为牵挂腾退之事。当我走进院子,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可院子似乎空阔了,又似乎沉静了,院子又不是那个院子了。一路走过那些弯曲的过道,但见墙壁上贴有一张张小纸条鼓励、劝导拆迁的标语,而那些大大小小门上窗户上,斜斜地贴着长长的白白的封条。但依然还有顽强的守望者,在作最后的博弈,我之前聊过天的老太爷、田家,甚至刘家,都还在坚守。这次我没有再找他们聊天,各人有各人活着的理由,我不想窥见生活最残酷的一面。其时,风很寒,我则心冷如铁。
而那天深夜,当我挥手告别谭志宏先生时,他真切地安慰我,腾退工作艰难,浏阳会馆32家住户,只剩下十二三户了,快了!
其时,我不知他是安慰我,还是鼓励他自己?
又一年快过去了,已是2019年5月底,志宏先生赴京出差,他特地去了一趟浏阳会馆,院子依然故我,已寂寥了许多,却依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家在坚守。其时,他拔通了我的电话,告诉我腾退工作依然艰难,而院子里那两棵槐树已是绿叶苍苍,然后就叹了口气,挂了。
作者简介:
彭晓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浏阳市文联副主席。曾出版散文集《红石头的舞蹈》《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苍茫潇湘》《寻访谭嗣同》,散文特写集《民歌婉转润浏阳》,长篇纪实《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