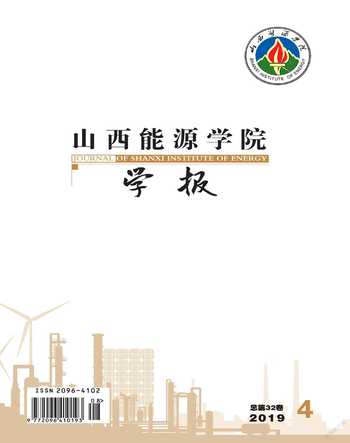管窥从小说到电影文本样态的嬗变
2019-09-10李琳
李琳
【摘 要】 自电影诞生之日起,文学与电影始终都有着“暧昧”的关系。小说与被称之为“第七种艺术”的电影相互促进,小说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文学养料,电影的发展推进了小说的传播。本文以《推拿》为个案,在把握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的内在关联与互动性的同时,去管窥电影文本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的诸多嬗变,进而从多元的角度去体会《推拿》的意蕴与人文关怀。从宏观上看,小说与电影具有不同的理性建构,电影版本的《推拿》对于故事的结局做了增补,对叙述着力点作了更加突出化的处理。从微观上看,从单一文字的叙事到多元言语介质的视听表达,电影发挥了它叙述功能的独特优势。
【关键词】 《推拿》;小说;电影;结局;叙述;多元
【中图分类号】 I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19)04-0083-0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2008年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出版后,引起了大众的极大关注,并于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诸多奖项。改编的同名电影于2014年2月11日在柏林电影节首映,该片由“第六代导演”领军人娄烨执导。这部影片先后斩获第63届柏林电影节最佳艺术成就银熊奖、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第9届亚洲电影最佳电影奖等诸多奖项。《推拿》从小说到电影的成功转换,离不开导演对原著精神的直接继承与对电影这种年轻艺术内核的熟稔把握。与小说相比,在宏观上,电影对于故事结局作了一定程度的增补,叙述的重点有了更鲜明的突出。在微观上,借助多元的言语介质对小说文本进行了比较成熟的二度加工。
一、对结局的增补
小说一般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告诉读者道理,哲理蕴含在具体的文字与细节的描述之中。电影则往往通过影像的组接形成触媒去激发观影者的想象与体悟。小说往往对结局交代得不是特别明晰,留给读者自己在文字与细节中去想象与构建。电影作为一种直观的视听艺术,则往往把加工好的结局呈现给观众,让观众直接收获一个完整的故事。《推拿》从小说到电影文本样态的嬗变首先表现在对于结局的不同设置上。
毕飞宇说:“我的小说是没有真正的结局的。”在《推拿》这部小说中他仍然保持着自己一贯的写作风格,直到小说末尾,也没有交代各自的归处。毕飞宇说:“《推拿》是部写实的作品,但是对写实的作品不能太刻意。如果我的大纲太过周密,它不像是真的,而像是编的。留下空间,让读者通过自己的观察,通过自己的思考与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去寻找故事的答案。”
小说以《夜宴》这个章节收煞,沙复明在厕所吐血进了医院,还要再观察七十二小时,至于沙老板的病情何时能好转,好转之后大家是不是能在沙宗琪正常上班,小说也留下了空白。王大夫为自己的老朋友兼老板生了重病却丝毫未察觉而愧疚,并对生命的无常充满了恐惧与哀嘆。
王大夫语无伦次了:“结婚。结婚。结婚。”他带着哭腔哀求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像样的婚礼。”王大夫怀里的女人不是小孔,是金嫣。金嫣当然是知道的,却怎么也不情愿离开王大夫的胸膛。金嫣也哭了,说:“泰来,大伙儿可都听见了,——你说话要算数。”
王大夫很显然是在悲伤与无助之下,误把金嫣当成了小孔,沙复明的病重让他感慨万千,他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会说话的洞”。盲人因为自己身体的残缺往往形成自负或者自闭的心理。他们彼此之间朝夕相处,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本来与主流社会的对峙已经让他们忍受了黑暗中太多的孤独,但是盲人之间却没有互相取暖,只是自负或者自卑地把自己的心灵紧闭。他们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才这样做的,或者是为了维护敏感的自尊,或者是自闭这样的状态让他们更有安全感。沙老板的病重让大家明白,他们应该抱团,最起码应该有个真正关心自己的人。他们渴望爱与被爱,渴望温暖,爱情和婚姻是他们走出孤岛的有效路径。王大夫想跟小孔结婚,金嫣想跟泰来结婚,至于他们是否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小说并没有交代。还有小马和小蛮究竟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也没有给出说明,都红走后也杳无音讯。小说对人物的最终归处进行了留白处理,留白艺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讲求“此处无物胜有物”,以空白来烘托画的整体意境。故事运用留白手法,人物命运的结局没有交代就中止了,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增加了小说的悲剧气质。
因为小说以文字为传播媒介,是一种时间文本样态,它具有内敛和意蕴丰富的特点。对于结局,作者不希望代替读者下结论去给出一个清楚的交代。真正有价值的小说是不会给出清晰的结局的,作者把最终的裁判权交给了读者。
电影是通过声音、画面、光线等多种元素表达的一种空间式的文本样态。它将文本进行更深层次的处理,观众在这时处于一种更加被动的境遇,他们需要上帝告诉他们这个“梦”的结局,或者大团圆,或者悲剧,这样他们的心里才有一个着落,他们才算做了一个完整的梦。由此,让观众收获一个完整的故事再收场是一个导演应有的责任。在《推拿》这部影片中,娄烨对故事的结局却做了相应的补充。影片最后,沙宗琪被转卖;金嫣和泰来回了老家;婷婷和一个聊天室的网友结婚;张一光重返了适合自己的位置—贾汪煤矿;张宗琪当了盲人剧团的团长;沙复明终于放下心中对“美”的执念,在舞场中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小孔和王大夫重返深圳打工;小马和小蛮在一个破旧的院子里开了一家“小马推拿”店,过着安静的生活。他们都不提在“沙宗琪”的那段日子。
该部影片前半部分色调是比较压抑的,其中出现两场血腥场面,一是小马在车祸后失去母亲与眼睛后的自杀场面。二是王大夫为了赶走债主在自己胸口划刀流血的场面。另外,整部影片出现了诸如“小马被殴打”“都红手指受伤”“沙复明病重吐血”等具有悲情风格的画面。所以,为了缓解观众的压抑感,导演有必要给观众一个相对温和的结局与交代,让大家在沉闷与冲突之后能够看到希望。这样的安排符合了电影文本的表达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观众的观影心里。相对完美的结局与交代给电影打上了一层温情的光泽,让我们在悲凉的生命底色中看到了温暖。
二、叙述着力点更加突出
文学与电影都离不开叙述,文学主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在影射哲理,叙述只是一种言语技巧与辅助工具。电影的终极文本在观众的意念之中,电影不单单是在叙述,也是在利用电影这种表达形态去触动观众的认知点,让观众认清“他人的自我”。电影通过“叙述性的自我”和“讲故事式的自我”充当着文本意义上的“他人”,使得观众得到自我实现。电影的叙述尽管会以文学文本的故事情节为基础,但并不仅仅依赖于故事情节。它并不注重文本的完整性,有时会有意识地通过消弭宏叙或增加故事情节的方式进行处理。电影的关键任务是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空间构造的样态去触发观众的意念,它不可能像小说一样面面俱到,而是要把叙述重点突出表现出来。
影片《推拿》在小说基础上进行转换时,叙述的着力点更加突出,首先把叙述着力点放在故事主人公上。在小说中,毕飞宇在每一章引入一个关键人物,章节的名字除最后一章为《夜宴》外,其他章节均以该章主人翁的名字命名。每章相对独立,像是人物志,整部小说对众多的“中心人物”着墨均匀,对人物平均用力,人物不分主次,平面铺开。小说运用了散文化的叙述方式,不制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往往在平淡之中娓娓道来。将故事的主要人物都集中在“沙宗琪”这一固定的空间,将看似没有因果关系的人物故事进行了串联,让他们见证沙宗琪的兴衰历程。在这样一个空间中,毕飞宇抽丝剥茧地将人物的网络关系呈现给读者,并细致描摹个体独特的经历与故事,多条线索同时并发。电影增加了主人公意识,电影在改编时,为了增加戏剧张力,有必要采用以主人公为中心的呈现方式,这样更能捕获观影者的心。电影如果完全遵循小说的手法,会造成主角过多,情节紊乱的现象。娄烨将主人公设置为“小马”,以小马为线,将故事的诸多人物串联起来,主人公的设置使情节线索变得更加明朗。以小马的受伤说起,以呈现小马与小蛮的幸福生活画面结束。小马在车祸中伤了眼睛,医治无效,他在绝望中用打破的碗的碎片割自己的脖子。他在死里逃生之后,终于接受了看不见光明的事实,又重新有了生存下来的信心。后来进入了推拿中心,混入了沙宗琪的人群之中,于是把主人公融入了其他人物之中。娄烨在改编时曾说:“虽然在改编过程中也有妥协,但最后还是尽量找一个群戏的感觉。”为了合谋原著对不同人物故事进行群像展览的意图,影片也让小马汇入了集体之中,让电影在有了主人公之后,依然有种群戏之感。
其次,影片的叙述着力点还突出表现在“主流”与“非主流”的对峙上。盲人认为眼睛能看得见的人构成的群体是主流社会。对于五官健全,智力健全的人而言,身体残缺的人构成的群体就是非主流社会,盲人是非主流社会的一个分支。影片表达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人群构成的主流社会与非主流社会的隔膜与对峙。因为老板沙复明是盲人,接待员就可以在老板面前光明正大地坐着沙发休息。“上班时间不允许坐沙发”这在沙宗琪是有明文规定的。当着老板面坐沙发的行为是明眼人对规则的無视,她以自己身体上的优越去获取一种身份与权利僭越之后的暂时快感。沙宗琪的“羊肉事件”也充分说明“明眼人”有时是不讲尊严与良知的,他们会以自己的身体优势对非主流社会进行无情的讥讽。王大夫的弟弟,作为一个“明眼人”,却不能自食其力。他在自己结婚时,还恬不知耻地开口向他的盲人哥哥要钱。他竟然发出“我要是个瞎子,就能够自食其力了”的牢骚,这是健全人对盲人群体宣布的对峙,也是对自己眼睛发出的挑战。在面对蛮横无理的讨债人时,王大夫很是无奈。一方面他把金钱看得很重,因为只有钱才能证明他的尊严,另一方面他要保护自己的家人,要摆平这个不懂事的弟弟捅出来的娄子是他作为长子的责任。他最后就只能以身体的自残向讨债人发出无声的反抗,达到了屈辱的胜利。讨债人只是不想与一个“瞎子”在这玩命才结束了追债。小马也对主流社会发出过挑战,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保护自己的女人。当他知道小蛮在接待其他“客人”之后,他向健全的“客人”主动发起了进攻。盲人对健全人的态度,就是健全人面对鬼神的态度,对待鬼神只能敬而远之。这两个社会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影片中加大了二者的对峙力度。影片是站在平视的角度对盲人的生活进行描摹的,但关注视角很明显向非主流社会进行了倾斜,表现之一在于对主流社会人物进行缺席设置,其中有很多画面直接忽视了“明眼人”的存在。如顾客在沙宗琪接受推拿,在跟推拿师进行聊天的时候,正常的拍摄应该是镜头随着说话人来回切换,但娄烨导演直接没有给“明眼人”入镜的机会。王大夫自残的时候,明眼人也全部缺席,王大夫自残时父母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只听到劝止的呼喊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其实是一种在场的缺席。通过限知视角的观察方式,将平等叙述的姿态发挥到极致,淡化盲人群体的特殊性,以这样的方式增加主流社会与非主流社会的对峙。
三、言语介质更加多元
小说是借助文字这一语言介质进行言语建构与意义表达的,从历时和共时层面它都需要遵循形、音、意的构建规则与语法模式。弗洛伊德所说:“我们所控制的、痛恨的、视为恶魔的乃是我们最害怕的东西。因为惧怕就压制,而被我们压制的东西便不断地回到我们的梦里,回到我们的补偿性的行为里。直到有一天,我们不再躲避它,而与它交朋友,将它作为我们不可或缺的部分接纳下来为止。”这是观众去看电影的目的,也是电影称之为“白日梦”的原由。电影为了更加真实地营造那样一个“梦”的场景,需要动用视听方面的诸多言语介质,如音乐、色彩、图形、文字、音响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电影是多种语言的综合与糅合,它把文字改编成了主观个性化的镜头。《推拿》从小说到电影文本样态的嬗变也表现在影片中运用了更加多元的言语介质去缔造人物。
小说《推拿》中出现了很多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文字,毕飞宇用生动的语言向我们展览了沙宗琪的人物群像,诉说了那个特殊群体中每个人的不同悲剧。小说在塑造小马这一人物时,就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他的内心,通过文字对内心的细致描摹在影片中是无法直接表达的,必须通过其他言语介质进行转换。在电影中小马大多是沉默的,为了表达他的内心世界,除了用他玩玩具车时的声音去表达,影片还赋予了他更多的嗅声。嫂子来男寝室串门时,他的嗅声萦绕在屋子里,那是一种青春悸动的欲望。
短短两个小时之内,要诉说的故事情节过多,人物庞杂,这也给影片的生成造成了困难。在该部影片中,导演对声音有着很敏感的神经,往往从个体周围的微弱的声音出发,去捕获更多的信息。有基于文本的人物对话的声音,有叙述环境的大自然的声音,还有为了营造氛围的配乐、零度的旁白等。
雨声在小说中不是话语构建的元素,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下雨的声音。在湿润与黑暗的南京体会下雨的滴答声,似乎是老天在哭泣。当小马去洗头房找小蛮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雨,这似乎在预示着有危机出现,告诉我们要在湿润的城市上演一部“黑暗”的电影。影片中还有很多嘈杂的市井之聲,来衬托着这个都市的喧哗与浮躁。
影片中出现了小提琴的伴奏,琴声在黑暗中变得更加幽深了。淡淡忧伤的小提琴伴奏的出现,伴随着隐秘的情感表达,营造了一种淡淡的哀婉的氛围,也映衬出娄烨电影独有的气质。这些虚幻的音乐出现在虚焦的画面出现之时,丰富了人物的感情与特定事件的意蕴,也让观众在视觉的黑暗中去探寻听觉上的光明,这些光明让观众更能真切感知到黑暗。
影片在开头就出现了一个普通话不是特别标准的低沉的女声在播报演员表,此声音一直贯穿了这部影片。当没有人物对话时,女声解读便会介入。小说作为历时性文本讲述了很多故事的来龙去脉,由于电影表达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带着“时间脚镣”跳舞的电影要想展示这么庞杂的内容不得不采用旁白解说的方式,以期对故事背景进行交代。这部小说人物众多,关系庞杂,电影通过增删之后,情节明显不够紧凑,这个时候就需要旁白将故事串联起来。另外旁白是利用一种零度情感的口吻,这贴合了小说要站在平视的角度去关注这个鲜有群体的初衷,也是一种用冷静客观去代替怜悯与同情的方式。
影片的摄影师曾剑在《推拿》中运用了“盲视觉”,这是他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把这种新颖的电影表现手法称之为“黑暗”影像。通过手持摄影机与虚聚焦的方式构建粗粝的画面,让观众真实体会小说文本中塑造的“黑暗世界”。在观影中将观众的视力优越降到最低,让人们真切感受到盲人世界的黑暗。为了达到这种视觉效果是很不容易的,摄影师要通过白天正常拍摄,夜晚进行移轴补光以及特殊镜头补光摄影进行处理。另外,通过虚焦呈现的画面与特写镜头的自由切换,黑夜与白昼的明暗交替,主客观视点的迅速转换,手持肩抗摄影机的晃动与眩晕,长短镜头的自由切换等诸多摄影技术处理,形象化地呈现盲人眼中看不见的图景,从而产生了“盲视觉”效果。通过表现这种看得见的黑暗,打造一种盲人世界的感知模式。如小马被殴打,因祸得福那个场景就很典型。这段用了长镜头,这也是娄烨所擅长的手持式拍摄。镜头摇摇晃晃,失焦与晃动之中模拟了盲人的视角。此外,将主客观视角交叉剪切,运用了断裂、晃动、眩晕等表现手法将小马那种痛苦、模糊、眩晕、意外的喜悦状态表达出来。小马晕倒在地时,这时的镜头表现的即是小马的眼睛看到模糊与晃动的世界。“盲视觉”的技术把画面处理成单调的灰暗,当小马站起来,睁大了眼睛,站起来了,这时候的镜头才转为正常视角。通过“看见”去表现“看不见”,让《推拿》成为一部“看不见”的电影。以电影的“不在”呈现文学的“在”,并以电影文本的“在”去触动观众自我意识的“不在”。
从单一的文字叙述到多元的言语介质的视听表达和高级的摄影技术处理,电影把小说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毕飞宇曾这样评价娄烨的改编:“主要的一点,就是你在看一场戏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电影跟我的小说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充分肯定了娄烨在改编时保持了电影的真正独立性。
小说到电影的转换,无不考验着改编者的艺术修养与专业技能。这既要求改编者对文学经典要抱有崇敬之心,又要求现代叙述者(电影)与传统叙述者(小说)进行及时沟通,去二度创造小说给人带来的那种人格魅力与人格力量,从而在小说的基础上进行超越与创新,这两种文本样态都是在对自身文体特质熟稔掌握的基础之上展开的。与小说相比,电影《推拿》在宏观建构上对结局做了增补,叙述的重点得到了更鲜明的突出。在微观上,借助多元的言语介质对小说文本进行了比较成熟的二度加工。
作为观众,如果只是被残存于电影当中的文学故事与情结所吸引,并“游离”于观众自主意识叙述的流动之外,电影就会从外部强制干扰。以镜头的机位变动和画面影像的断裂式组接,迫使观影者离开电影本身,回归到自我的“踪迹”里去。这是电影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区别,也是观众不能依据文学理解的惯性思维模式去理解电影的重要原因,同时是专业的电影观众与习惯于传统文学接受的观众对同一影片得到迥异体会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摆脱文学的被动灌输式的接受方式,是不能启发自我意识进入电影的艺术之中的。影片《推拿》是一部很难被传统的文学读者所接受的影片,这也是《推拿》虽在电影节上获奖,但票房并不高的原因。但是对于一部影片价值的界定,票房显然并不是唯一的尺码。
【参考文献】
[1]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M].高俊千,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53.
[2]毕飞宇.推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08-319.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4.
[4]李效文.脱胎文学的电影本体彰显及个性化表达—从娄烨的《推拿》说开去[J].电影评介,2015(22):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