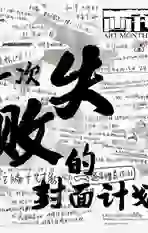梳理不是终结:蓝庆伟访谈
2019-09-10孟尧蓝庆伟
孟尧 蓝庆伟

孟尧:“新艺术史:2000-2018·中国当代艺术”展由你和李国华、宋振熙三人团队联合策划。从确定本次展览议题到该展览最终呈现在银川当代美术馆,三位策展人是怎样协作分工的?
蓝庆伟:展览的筹备是从2018年9月开始的,策展人由我与李国华、宋振熙共同担任。我们都非常重视此次展览,为了保持信息同步,减少疏漏,没有预先进行分工。但随着展览的推进,每个人的负责板块都各有侧重。比如从前期开始,李国华就是与银川当代美术馆建立工作秩序的主要对接人;在最后的现场布展阶段,宋振熙则是主力;在展览开幕当天的学术论坛上,我担任论坛的学术主持工作。也许在这方面不太有经验的人会觉得分拆工作、权责明确更重要,认为理想化的状态是1+1+1>3。但实际上,在“新艺术史”的展览中达不到这样理想的预期。在展览筹备的各个环节我们都有过激烈的争论,相当于我们每个人都把同样的过程经历了一遍,用做三个独立展览的精力合作了这一个展览。这个过程当然不甚愉快,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争论意味着辩证选择,也体现了相互监督,能让我们在磨合中发挥各自的特长,也加强自身的思考。我和李国华、宋振熙是同时代、同年龄层的策展人,并且在十几年来的实践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策展特点,合作策展恰恰能各展所长,取长补短。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次相互学习的好机会。
孟尧:在《“新艺术史”展览的争议与提示》一文中,你写道:“对刚刚发生的‘昨天’进行历史性的总结,充满了危险性:一是尘埃还未落定,二是陷于人情世故的纠葛,三是客观准确性无法保证。”如果以这段话来观照此次46人的参展艺术家规模,你们选择艺术家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你们如何来应对这种危险?
蓝庆伟:虽然所有总结性的展览不会都被冠以历史的名义,但关于当代艺术的梳理从未停止过,比如“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中国影像二十年”、“八五美术二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中国当代雕塑四十年”等。关于历史的描述,现在呈现出来的表达有不同的角度和方向,有的轻描淡写,有的无比重视。现在的主要观点有两种:其一认为历史是一项不断接近真实但永远无法还原真实的工作;其二认为历史是一场对过去的审判,或者是关于过往的云烟。“新艺术史:2000-2018·中国当代艺术”展也是梳理总结式的展览,望文生义,是关于历史的选择,其中对参展艺术家的选择又成为传递展览策展意图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最受关注。2018年是中国当代艺术40年的时间节点,吕澎老师在去年策划了“40×40:中国当代艺术40年”展览,他同时也是“新艺术史”展览的学术顾问。基于这一背景,“新艺术史”展览在艺术家的选择上首先排除了“40×40”展览中的艺术家不是说这些重要的艺术家不符合“新艺术史”展览的选择标准——我们将这样的回避视为一种致敬。在参展艺术家的选择方面,2000年以来在当代艺术各个领域做出突破性和引领性贡献是入选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艺术家的年龄和擅长领域来划分。

孟尧:本次展览划分为四个板块,分别是“抖动的幻觉——娱乐/消费”、“普罗米修斯的回归——技术/伦理/科技”、“循环播放——全球化政治身份”、“会呼吸的遗产——后传统/历史性”。具体到展览空间,艺术作品又被分类到序厅、以“风中碰撞”为主题的1号展厅、以“无人色调”为主题的5号展厅、以“行动算法”为主题的6号展厅来呈现。从策展理念和空间展示的关系来看,你们希望在这些板块和主题之间构建什么样的视觉逻辑?
蓝庆伟:“新艺术史”展览的呈现中隐藏着两条线索:一是关于2000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梳理,二是展览本身的视觉呈现。我们面临着历史的梳理、表達与展览呈现之间的矛盾,对艺术史的梳理是通过书写和论坛两种方式完成的,成果分别是出版物《21世纪中国艺术简史:2000-2018》和“21世纪中国当代艺术(2000-2018)”学术论坛。而在布展思路上,我们没有直接把梳理成果拿到展览现场,而是通过纯视觉的方式,最大化呈现46位艺术家的作品。
在展览的板块分割上,我们采取了近似风格学的分类方式为当代艺术的各种样式做了主题分类,希望能呈现当代艺术的活力,同时考虑到参观者的观看习惯,希望参观者能够在参观过程中感受到当代艺术的魅力。
孟尧:现场看完展览,我有两点直观感受:第一,展览上呈现的作品类型比较丰富,涉及了现今各类艺术创作手段,具有一定的艺术广度;第二,以展览设定的2000-2018年的艺术与历史语境来看,作品和作者之间的价值关联不够强,在展厅缺少更深度的文献梳理和视觉引导。
蓝庆伟:你的感受是对的,现场的文献梳理和视觉引导做得还不够。
我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就提到了文献梳理和作品呈现上的冲突。最早讨论展览定位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在梳理过往的同时,让这个展览引领未来,成为这个时代里程碑式的大展,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以艺术家的作品呈现为主,视觉先行,其他方面就有所牺牲。而在某一门类的作品中我们尽可能地做到了包含2000年以来的主要的艺术语言变化,如行为艺术,我们选择了何云昌、周斌、刘成瑞(刮子)三位艺术家,从中能观察到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对语言运用方式的改变,并以此为线索,推导出行为艺术在2000年后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
在呈现展览的认知上,我们将出版物、学术论坛、展览现场视为展览的共同体,它们都是展览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孟尧:你将这次展览视为一次“以年代学为基本线索的总结性展览”,并更看重它的学术研究价值。在接受《绝对艺术》采访的时候,你还说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被悬置在空中没有落地——缺少学术研究的问题”。如果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来谈,你觉得这个展览触碰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它是否解决或者提出了哪些值得继续探讨的价值命题?
蓝庆伟:虽然当代艺术的发展前景在很多人看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熟悉艺术高校状况的人会清楚地看到当代艺术在其中的教学、研究工作已经拥有了长久发展的基础和可能。当代艺术既是教学的内容,又是研究的对象,文献库里有越来越多的博士论文在展开对当代艺术的研究,学科化建设已经是当代艺术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新艺术史”展览也不例外,展览才呈现出来没多久,已经成为高校学生论文的研究对象。
“以年代学为基本线索的总结性展览”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方法,但在当代艺术领域,“史”却沦落为学界嗤之以鼻甚至是排斥的对象。如果说历史是对时间的梳理,那么方法与理论则是梳理中的重要学术问题。梳理不是终结,而是研究的开始。“新艺术史”展览也是如此,我们仅仅做到了其中一种文本形式的梳理性工作,还没来得及对其背后涉及的全球化、后殖民、艺术批评、艺术生态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这些都是当代艺术与当代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孟尧:《21世纪中国艺术简史》在展览开幕同日新书发布,三位策展人也都参与了该书的写作。你们写作这本书的初始想法是什么?它和本次展览的策划和研究,是否有直接的关系?
蓝庆伟:写这本书的想法是想提出我们这一代策展人在观看21世纪初艺术变化时的思考,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老一辈的批评家们是有所区别的。首先是在当代艺术发展的分期上,我们更愿意将中国当代艺术40年分为“当代艺术语境”的前20年和“全球化语境”的后20年。中国当代艺术有40年的发展了,但其发展路程不是线性连续的,而是复杂和迂回的。其次,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变化非常明显,艺术生态的改变也在不断提醒我们中国当代艺术的特殊处境。再次,聚焦新一辈艺术家的成长与发展,也是我们这一代策展人都在极力关注的,虽然对我们来说可能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扰,但随之而来的反思必不可少。如果要找寻出版物《21世纪中国艺术简史:2000-2018》与展览“新艺术史:2000-2018·中国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那么用“互文性”一词再合适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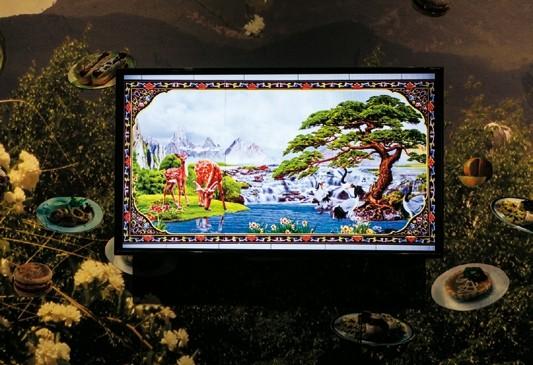
孟尧:这本书中,你写作的部分是“世纪之交的语境变化:2000-2005”,其中谈到了当代艺术的生态建构问题。以今天的艺术现场来看,当代艺术的生态建构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蓝庆伟:列举和对比是我们在做判断时常常使用的方法。在“世纪之交的语境变化”这一部分的写作中,我发现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阶段和90年代的驳杂阶段之后,走向了2000年以后的生态构建阶段。在艺术生态的构建阶段,与艺术相关的艺术区、画廊、博览会、拍卖行、艺术刊物等层出不穷,艺术生态在助推艺术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艺术家和艺术家的创作。当然这一阶段还只是艺术生态的初级阶段,是中国加入WTO进入全球化的“红利”。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虽然看似与艺术生态没有直接关系,但熟悉历史的人都清楚“讲话”在艺术上尤其在艺术创作、艺术展览上必然会产生的影响。这也是艺术生态变化中的语境变化。
在艺术生态自身的建构中,随着艺术市场的波动,经历了艺术生态粗放发展的过程,艺术生态的各个组成都将向更加专业化的发向发展。
孟尧:与你之前参与策划的安仁双年展相比,此次“新艺术史”展览同为大型的艺术群展。你觉得策划这种群展,最大的价值和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
蓝庆伟:“新艺术史”展览与安仁双年展相比,规模略小。首届安仁双年展的主題是“今日之往昔”,是在全球概念下对中国艺术现状的综合呈现,从语境到形式都更有包容性。“新艺术史”是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次主观呈现,论题明确且集中。两个展览虽然有很大差异,但对我个人而言都有着巨大的收获。
策划这类群展,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观看视角的变化与整体的把控。最困难的仍然是如何最好地呈现展览主题。

孟尧:策展、批评、美术馆研究,是你这几年做得最多的工作。在这些工作模式中切换,最值得分享的经验是什么?
蓝庆伟:的确,策展、批评、美术馆研究是近几年我的工作重点,在这些工作中,我都希望能够做到专业、学术和有深度地研究。切换过程中最值得分享的是让自己始终保持在观察者的角度——在当代艺术的研究过程中,参与感、现场感曾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在今天,积极、客观地观察则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