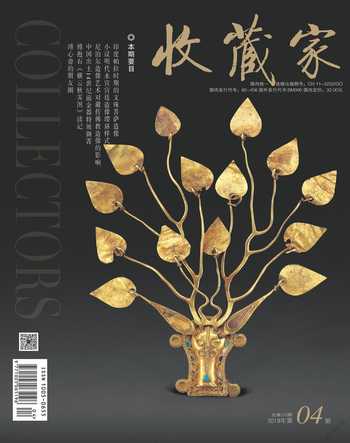宋本长短经鉴赏
2019-09-10刘明
刘明


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长短经》,其行款版式为11行18至21字不等,小字双行27至33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版心中镌“长”和卷次及叶次。卷端题“长短经卷第一”。卷首有赵蕤《儒门经济长短经序》,署“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草莽臣赵蕤撰”。全书凡九卷六十四篇,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该书“原出于纵横家,主于因时制变,综覈事功,不免为杂霸之学”。此书“辨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四库全书总目>)。而称以“经”者,盖所述皆经国济世之道,可比附儒家经典。全书征引较博,引四部书达百余种, “多能补正各书今日通行本之讹脱,部分已散佚书的残篇断章,亦赖此书得以保存下来”(参见周斌《整理和利用(长短经)必须考源》,载《(长短经)校证与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下引者均出自此书)。且该宋本为存世《长短经》的最早版本,后世诸本均以之为祖本,故极具文献及版本价值。
此书撰者赵蕤,生平事迹不详,仅孙光宪《北梦琐言》称: “赵蕤者,梓州盐亭县(序署‘郪县’)人也。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节操,不受交辟。”按光宪为蜀人,且生活在五代北宋初,所言应为可信。此后的《新唐书·艺文志》小注称: “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唐苏頲《荐西蜀人才疏》(《升庵诗话》卷二引)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李白亦撰有《寄赵征君蕤诗>。基本推定赵蕤乃蜀人,主要生活在唐开元间(周斌考证约生于武则天垂拱四年,而卒于肃宗至德二载,享年七十岁。参见所撰《赵蕤生平杂考》),与诗仙李白有交往,两人似属亦师亦友的关系。明胡应麟认为是“中唐前后人”(《少室山房笔丛》)。清吴任臣则称赵蕤乃五代前蜀人, 《长短经》撰于北宋太祖乾德年间(顾广圻《思适斋书跋》称“吴任臣以为前蜀乾德时恐非”),疑据《北梦琐言>而误以为与光宪属同时之人。
该书之编,赵蕤序称: “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纶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知赵蕤名所编日“长短经”,《北梦琐言>亦称:“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郡斋读书志》著录也是作“长短经”。而《新唐志》《遂初堂书目>和《宋史·艺文志》著录均作“长短要术”。《四库全书总目》称:“盖一书二名也。”周中孚则称:“‘长短经’乃此书本名……其作‘长短要术’者,当因‘叙以长短术’语而妄增一‘要’字以为书名也。”(参见《郑堂读书记>)此宋本中卷三、四和九则末题“长短文经”,加之序所署的“儒门经济长短经”,可谓一书凡四称。成书的时间, 《四库全书总目》称: “是书谈王伯经权之要,成于开元四年(716)。”依据是卷六《三国权>称: “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590)灭陈,至今开元丙辰岁凡一百二十六年。”恐怕也只是大致的推断,从不避唐玄宗之后帝讳而言可基本确定为开元间成书(参见周斌《(长短经>的行文特点》中的考证)。
赵蕤序称《长短经》编为十卷六十三篇,而该宋本则为九卷六十四篇, 《四库全书总目》称“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又或称: “多一卷却少一篇,疑此书文字流传至今已有衍夺。”(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或称传写有讹,“六十三篇”中的“三”乃“五”之讹(参见周斌《(长短经)的流传和版本》)。在该宋本之前,均记载或著录作十卷本,如《北梦琐言》和《新唐志》,印证《长短经》本为十卷,不存在讹误。至《郡斋读书志>(衢州本)著录仍作十卷本,而有关是书的叙录却称: “第十卷载阴谋家,本阙,今存者六十四篇。”与此宋本相合,疑即著录之本。袁州本《郡斋读书志》则称: “凡六十三篇,第十、九载兵权、阴谋云。”则此著录本又与赵序所言相合,其中轩轾不能明。又《崇文总目》著录有《长短经天文篇》一卷,小注“阙”,则北宋中期该《天文篇》-卷即亡佚不传。此与赵序所称的“十卷六十三篇”是何关系,也难于究诘(朱锡鬯称“此《天文篇》疑即其中之一”,参见钱东垣等辑释本《崇文总目》)。总而言之,本属《长短经》的《天文篇》和“阴谋(家)”篇亡佚,其中缘故,朱彝尊《长短经跋》称: “其第十卷相传载阴谋捭阖之说,故秘不以示人。”
按现存宋本篇卷之目,卷一計八篇总题以“文上”,卷二计四篇,未题总题,卷三计四篇总题以“文下”,则卷二应总题为“文中”。卷四至六各一篇,卷四、五分别总题以“霸纪上” “霸纪中”,卷六不题,应为“霸纪下”。卷七两篇总题以“权议”,卷八计十九篇总题以“杂说”。卷九计二十四篇总题以“兵权”,此与袁本《郡斋读书志》所言相合。值得注意的是,卷九的二十篇排序自“一”起,与卷八中排列“四十”的《定名》篇不相衔接。且“兵权”总题下有小序称:“……自古兵书,殆将千计。若不知合变,虽多亦奚以为。故日少则得,多则惑,所以举体要而作《兵权>云。”其他总题下均不载此类性质的小序,推测宋本已非原本之貌,内容有残缺,篇目亦经重新编排。
此部宋本的确并非原本之貌,比如存在脱文,可能是在流传中佚脱(原本当非如此)。如卷二《理乱》“何谓九风”,下文仅述及八风,据《申鉴·政体》知脱去“君好让,臣好逸,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国之风也”一句。又卷九《还师>“中州善国以富其心”句意难解,据《三略·中略》知此句当作“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据自周斌《整理和利用(长短经)必须考源>),如此句意甚明。但自身存在的文本及实物特征表明它出自唐代的传本,文本特征主要是保留了回改未净的唐代讳字,如卷-《论士》“天下无灾害,虽有贤德,无所施材”句,引自《文子·精诚>, “天下”作“世”,为避李世民讳而改。卷五《七雄略>注文引贾谊语称“欲天下之理安”句, 《汉书·贾谊传>“理安”作“治安”,避李治讳而改。又卷七《惧诫>注文有“一泉无二蛟”之语,引自《文子·上德>, “泉”作“渊”,避李渊讳而改(据自周斌《(长短经)的行文特点》)。实物特征表现在赵序与正文卷一相连不另起叶,各卷前列有本卷所载篇目,这都属于写本的特征,即“盖沿袭唐卷子本古式,应视为从写本到雕版印刷本、由卷子本演变至册装本过渡时期所产生之现象”(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这表明此部宋本的底本是源出唐本的一帙写本,而此部宋本当即《长短经》最早的一部雕印本,属从写本过渡到刻本的产物,对于考察早期雕版印本的写本特征遗留及物质形态均颇具标本意义。另外尽管存在难以避免的讹脱现象,但所引文献皆出自“唐代或更早之写本,颇敷考证校勘古籍之用”(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是除《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群书治要》等之外的又一种辑录上古及中古文献的渊薮。
有关此部宋本的刻年却存在争议, 《四库全书总目>称“犹南宋旧刻”,又或以为即绍兴时所刻,或以为属北宋刻,《中华再造善本>影印该本定为“南宋初年杭州净戒院刻本”。检书中“玄”“舷”“朗”“敬”“镜”“弘”“泓”“匡”“恇”‘恒”诸字阙笔,而“让”“顼”“桓”“鈎”“沟”“遘”“措”“慎”诸字不阙,避讳至宋真宗赵恒止。又该本卷一、八和九之末各镌刻“杭州净戒院新印”一条,称“杭州”而尚未称“临安”。按《[乾道]临安志》卷二“历代沿革>称“是年(即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 杭州为临安府”。既题“杭州”则应刻在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之前。至于“净戒院”,《[咸淳]临安志》,称:“(净戒院)在太一宫道院之北,龙德二年(922)钱氏建,旧名‘青莲’,大中祥符九年(1016)改赐今额。绍兴二十年(1150)建祚德庙,乃以春秋二仲祠祭属焉。”则北宋真宗时已有净戒院。或由此三端而作为定该本“当刻于北宋”的依据(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就不避南宋帝讳而言,冀淑英称: “从传世宋刻本来看,南宋初年避讳制度不严,南宋中期以来才逐渐严格”, “鄙意以为如认定《长短经》刻于北宋真宗时似太早了,当然这也没有明证。”(参见《冀淑英就(长短经)覆陈先行的信>,载《冀淑英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故此本仍有可能刻于南宋初的建炎元年至三年。可资佐证的版本实例,如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五臣注本《文选>,卷三十未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一行,亦题“杭州”。赵万里称:“此书虽未必为北宋本,定为南宋初年刻,当无大误。”(参见《中国版刻图录》)南京图书馆藏宋本《唐书>,宋讳缺笔至“贞”字,乃据北宋嘉祜监本翻版,仍定为南宋初年建本风格(参见《中国版刻图录》)。该宋本亦当如是观。
至于“新印”的含义,或称: “乃重印之谓,非新刻、重刻之义。即或此本重印晚至建炎三年,其刊刻似也当在北宋。”(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冀淑英则认为: “新印即是新刻之意。”(参见《冀淑英就(长短经)覆陈先行的信》)该说法是正确的,宋代存在刻书不题“刊”而题以“印”的习惯,如钟家本五臣注《文选>(刻书题记称“印行”)、陈宅书籍铺本(刻书题记称“书籍铺印”)等,故“净戒院新印”即由净戒院新刻之意。或又据该本字体偏长而不同于南宋浙本“字形略方”的特证,作为当刻在北宋时的佐证。除上述佐证外,此书在版式上的显著特色是书口未刻鱼尾,冀淑英称“此一版心现象确属少见,此例不多,可待研究比对”(参见《冀淑英就(长短经)覆陈先行的信>)。此种书口版式与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北宋本《姓解》、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通典》以及公布的山西应县木塔所出辽刻《蒙求》和河北唐山丰润区文管所所藏辽刻《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相同。笔者曾提出“书口是否刻有鱼尾是鉴定北宋刻本或其翻刻本的一个重要依据”(参见拙文《略论北宋刻本的书口特征及其鉴定》,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3期)。以之视《长短经》,可能刻在北宋,也有可能是南宋初年的新刻翻版本。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尔雅>,即书口不刻鱼尾,实即南宋初年国子监刻本。据其八行十六字的行款,知据北宋监本翻刻。故此宋本亦存翻刻的可能性,如此则“新印”即重新翻刻印行之意。概言之, 《长短经>还是以定为南宋初年刻本最属稳妥,而净戒院属刻书的主持者。
南宋初刊刻的此部《长短经》,见于《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著录,元明两朝流传罕见,即《四库全书总目>所称的“今久无刊本”。检书末副叶有沈新民跋一则,末署“洪武丁巳(1377)秋八月丁巳沈新民识”,云: “按马端临《文献经籍考》据唐晁氏云唐赵蕤撰《长短经》十卷,又据《北梦琐言>云蕤梓州盐亭人,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不应辟召。论王伯机权正变之术,其第十卷载阴谋家,本缺,今存者六十四篇,然不害其为全书也。”馆臣认为: “此跋全勤用晁公武之言,疑书贾伪托。”冀淑英则称此属“臆度之词”(参见《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影印说明>,载《冀淑英文集>),“从字体风格看,应属可信。四库馆臣认为系书贾伪托,或聊备一说”(参见《冀淑英就(长短经)覆陈先行的信》)。此跋应属作伪,理由是洪武丁巳年的八月为“庚戌”而非“丁巳”。至清初王士慎《居易录>称: “此书流传绝少,徐健庵过任城得之市中者,宋刻也。”书中正钤“徐乾学印”“健庵收藏图书”“传是楼”和“黄金满篱不如一金”四印,知即王士慎所言的宋本。检《传是楼宋元版书目》未著录此书,疑为书目编成后所得而未入目。经徐乾学之手又归史贻直,所钤“史铁厓珍藏书画”“古銕生”“友林书屋”及“子子孙孙清白吏”当即其藏印。据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史贻直(1682 - 1763)字做弦,号铁崖。經史氏之手又归励守谦,字自牧,一字子牧,号双清老人,直隶静海(今属天津)人,生卒年不详。乾隆九年(1744)举人,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入四库馆充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官至司经局洗马。励氏四世翰林,富藏书。这是此本进入四库馆充当纂修底本之前的递藏脉络。
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励守谦任四库馆编修,故进呈是本,录副后又返归励氏收藏。书衣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七月,翰林院编修励守谦送到家藏《长短经> -部计书八本”戳记,又钤盖满汉文“翰林院印”一印,知即为四库进呈纂修底本。卷首副叶有乾隆御题,末署“乾隆甲午(1774)春御笔”,钤“乾隆御览之宝”一印和“乾”“隆”连珠印。其中有两句是“宋刊奔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日短长”, “卷原称十今失一,总目翻看余一篇”。 “教忠堂”为励守谦堂名。据乾隆三十九年谕称: “其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几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又称:“又进书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励守谦家进呈达一百余种,故该本得乾隆御题。录副本即四库底抄本,归王懿荣所得(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而宋刻原本则从励氏手中流出转转归常熟翁同龢所藏。最早透露此线索者即为王懿荣,他说:“常熟翁氏有宋刻本,不知所佚之一卷(即卷十)存否?”(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所钤“虞山翁同龢印”“均斋秘笈”即为其藏印。书末副叶除沈跋外,并记“戊午夏五月重装”,“戊午”疑为咸丰八年(1858),待考。又记“光绪甘六年(1900)四月廿四日钱唐汪鸣銮、武进费念慈同观。是月携宋本《周官》郑注、 《吴郡图经续记》《参寥子集》开几快览,念慈题记”。此时翁同龢已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闲居常熟家中,故观此本当即在翁同龢宅中。翁同龢卒后藏书归翁之廉,因翁之廉无子嗣而过继翁之熹之子翁万戈,故又归翁万戈所藏,所钤“翁万戈藏”即为其印。20世纪40年代,翁万戈将包括此宋本《长短经》在内的翁家所藏精华携至美国,至2000年方由上海图书馆购归。
在《长短经》购归之前,即由文物出版社在1996年将此本作为《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的一种影印出版。冀淑英撰写该本影印说明,称: “此书自清以来多为抄本流传,清季后期始刻入丛书中,今传本卷末多有沈新民跋,可知皆出自此本。”属海内外孤本,版本价值自然不容小觑。2008年,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为00753),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保护,也成就海外善本珍籍回归的标志性“个例”。期待更多地流散海外的珍籍回到祖国的怀抱,不再是“文在它乡,史在异邦”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