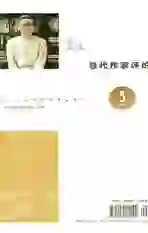在“永恒”的注视之下
2019-09-10王士强
在当代诗歌的场域中,梅尔堪称独异,她不属于某一流派、群体,也较少在诗界“活动”,但却声名远播,自带光环,自成风景。她的诗歌写作看不出明显的谱系传承,却显然有著对于中西文化、中外诗歌的深度浸淫与理解,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追求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她的作品数量或许并不算多,但是辨识度很高,所以很多时候诗歌界不见她的踪影却流传着她的诗歌传说,她是以缺席而在场、以隐匿而呈现的那种诗人。她的写作难于被归类、定义,她是女性诗人,写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女性诗歌或女性主义诗歌;她信仰基督教,写了很多宗教题材的诗歌,却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诗歌大为不同;她写了很多自然题材的诗歌,但很显然她的诗也并不属于狭义的“自然诗歌”范畴,而是与当下、与时代、与社会有着密切关联的。梅尔的诗视野开阔、格局很大,有着对于神性的仰望、对于自然的敬畏,她的诗贯穿着一个“时间”主题,这个“时间”是超越性的、永恒的,是终极性与宿命性的,这一主题也正是其诗歌高标独异、卓尔不群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永恒”的维度在梅尔诗歌中并不是单向度的存在,她的诗同时是有人间性、在场性、现实性的,“永恒”很多时候是在后台、作为景深而存在的。但毋庸讳言,永恒性、超越性的维度是梅尔诗歌极其重要的方面,在她的精神世界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梅尔的内心是有精神归属和价值根基的,她有定力,不疾不徐,坦率自然、豁达从容,这绝非简单地、表面化地做做样子就可以的,而一定是由于内在的精神结构与气质禀赋。对梅尔而言,她是信仰“神”的,“神”即是她的依靠。不过对作为诗人的梅尔来说,“神”又有其特殊性或者个体性,“神”既是宗教意义的,同时也是超出宗教的,包括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它们都给了梅尔以信心和力量,形成了属于梅尔的气质与格调。她的内心有着对于神性的坚守、对于高处的仰望,“永恒”是梅尔的尺度,是她精神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存在,如果不能超出其时空具体性,而具有朝向永恒的维度,不能在永恒的量尺上刻下印痕,其意义是打了折扣、需要重估的。神性、高处、历史、世相、自然、文明,皆是“永恒”的体现形式,未经“永恒”的注视,一切的存在其价值都是可疑的。
梅尔写有不少宗教题材的诗,有一些直接有基督教中的“本事”,她的书写融入了自身的情感、意志、信念,构成了“我”与宗教本事之间的对话、交流,以及相互的靠近。正是由于这种个人主体的投入和移情,她的作品具有了感动人心、极为动人的力量。比如《回到你的殿中》所写显然是有关耶稣降生及其经历的若干“本事”:“我一转眼就看到你躺在马槽中/戴着天使的光环/有福的草料衬托着你/那惊世的光辉,穿过/玛利亚的唇,回到上帝的圣袍边/我带着满身的伤痛回到你的殿里/十字架还在各各他山上//我流着泪,唱着你的歌/看着你的脚踝。手腕汩汩流血/请让我跪在你的面前/用我那吐露过真情、善意和谎言的嘴/亲吻你脚下的泥土//让我回到十字架上/取代那些冰冷的钉子/让我回到死海里/用盐擦拭应该瞎去的眼睛/回到你的天上去吧/我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分明看到你的身影在海边行走/我离去的时候,丢了魂魄”,与其说这首诗写的是基督教的本事,不如说写的是“我”与基督教本事之间的互动,其重心在“我”自己。诗中所写的忏悔、虔敬、皈顺、自责、自律,在梅尔诗中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是她的精神结构中一些基本特质。《约伯》中所写同样有关“我”的奉献与牺牲:“我会提前到达伯利恒/成为马槽里一根柔软的稻草/或者,错后三十年/我会提前到达耶路撒冷/摘掉你荆棘冠冕上所有的刺藜/成为另一个背负你十字架的西门/或者另一个玛利亚/准备好沉香、没药/膏你那风尘仆仆的双脚”,无论是书写对象还是书写主体,都有着一种受苦、受难、牺牲的精神特质,非常感人。梅尔的诗包含着一种深沉的忏悔、赎罪精神,正如她的《最后的审判》中所写:“没有人可以逃过最后的审判”,她的诗正是面对终极、面对永恒、面对神灵、面对审判所进行的言说,正如评论家张清华在诗集的序言中所说:“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比喻,无法断言她的角色相当于《圣经》中的哪一个人物,只是觉得她如同一个信徒,一个精神史的考古专家,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使者,又或是一个但丁式的游历者,有时她甚至还不知不觉地扮演着圣母或任何一个可能的角色……以此来评说人间的罪与罚,人性的善与恶,以及命运与神示,信仰与背反的一切母题。”这样的特征与趋向,在《大卫与拔示巴》《大卫的辩解》《耶稣山》《月亮神庙》《羊的门》等诗中均体现得非常明显,极具内涵与丰富性。
与“神”和宗教类似,对人类文明的成果、文明的遗迹等的观照均体现着对永恒的瞩望。这一类的诗在她的整体创作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她游历了世界许多地方,特别对古文化的遗迹等非常着迷,有着浓厚的兴趣。《苍凉的相遇——马丘比丘》所写是秘鲁的马丘比丘遗址。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马丘比丘显然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包含了非常多的理解、阐释的角度。梅尔于此可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写到了侵略、杀戮、苦难、狂欢、朝圣、救赎、火焰、废墟、伤痛、遗忘……,它是对文明史的观照,也是对生存史、心灵史的描摹。死与生以一种奇异的方式于此共存:“缄默的石头铁一样沉重/那曾经抡起的榔头/敲击着库斯科的虚空/黄金是不死的/但换不来你的活/国王战战兢兢地坐在油画里/面对欧洲的头盔和邪恶的马”。这样的相遇只能是“苍凉”的,“你不能决定时间/时间成全了一切/又毁掉了所有”,“时间”在这里既有“百炼钢”之硬,又有“绕指柔”之软,确乎让人感慨万千。面对被毁弃的教堂、神庙:
把一座教堂毁掉,哦不,一座神庙
可以毁掉整个高原,心的高地
毁掉石头砸出的火,毁掉
稀薄的空气
不朽的八度传奇
石头内部,阴阳榫卯
经历着一场时间毁不掉的地老天荒
沧海桑田、地老天荒,变与不变中包含着宁静与忧伤。这样的存在本身便成了“伤口”,“是的,打开印加帝国的伤口/打开秘鲁的伤口南美的伤口/世界的伤口!//打开头颅里没有记载的杀戮/打开沙漠里尘土飞扬的哭泣/打开,一颗血淋淋的心/打开,夜里石头的伤痛!”这巨量的伤痛,让人不得不凝重起来,这是一次洗礼、一次致敬,也是一次提升。
梅尔诗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对自然性的关切和讴歌。自然是长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或者说是不以人的尺度而存在的,其中包含着更为恒久的定律、准则,所谓“天不变,道亦不變”。梅尔对自然的书写,正是其对于“不变”、对于“永恒”之关切、凝视的结果。“自然”包含了梅尔超越此时此地,在一个更大的背景、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观照人生、观照世界的企图,有着颇为丰富、复杂的内涵。
当“自然”的时间刻度足够长,时间本身便成为传奇,而具有了神性。比如距今已有七亿年的双河溶洞,这里面包含着地质、物种的发展演变、生生死死,“海水再一次漫上来/带着涌动的全部欲望/从舌尖到心灵深处/那些生物无法逃脱/大地,请你收留它们英雄的尸体/昆虫,鱼类,甚至/包括熊猫和犀牛/七亿年后,人们会找到它们的化石/并奉若神明/忘记我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和秒针一样尖锐的快乐”(《双河溶洞》)。由此,不只个人是微渺不足道的,甚至人类的历史和存在也是极为短暂甚至可以忽略的,从这样的比照出发,人的生存、人的价值都是值得重新思考和审视的。七亿年而仍然活着,“我的内部也开始秘密勾连/传达七亿年前的烽火/我一直活着/像一则传奇”,当然,这其中的变化不可谓不巨大,比如石头里长石头、石头也开花:“石头被遗忘/石头里长出了另一种石头/石头以另一种形式抛弃了自己/石头,盛开成自己晶莹的花朵”,不能不让人感到震动。这样的相遇,同样是“苍凉”的,是包含了内在性和心灵性的,“当繁华落尽/所有的灯光都暗下来/我的心落满了尘埃”。诗中写到了其中不同的生存样态,更有着“我”与之的关联、互动,归根结底,两者之间是心息相通、精神同构的:
鹰尝试飞进我的内心
它俯冲的速度过于猛烈
我在有限的阳光里存满了水
茂密的树木是昆虫的天涯
经年不休的瀑布
是我呼啸的声音
我的可以倾诉的所有
圆柱形的身上布满了伤口
那是我的血脉
经由他们,我与生生不息的你们
相通
鹰沿着垂直的峭壁飞向天空
留给我一颗困境中可以翱翔的心
在这里,自然的人格化与自我的对象化是同时发生的,“鹰”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界的生物,同时也是“我”的某种外化,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一颗困境中可以翱翔的心”。这样的一颗心,对于人、人类而言显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是人之为人的极为重要的品质,与人的生存意志庶几近之,而实际上它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生物,以及对于“自然”本身,也是一样的,困境中翱翔的心揭示了生存本身,以及万千事物内部客观、冰冷而又极富诗意的本质。
“十二背后”对于梅尔具有多重的意义,它既是一个原始的、尚待认知与开发的自然奇迹,也是一个融人了情感、智慧与汗水、与个人的生活世界有着密切关联的所在。“十二”组成“王”字,“十二背后”也具有帝王般的威仪、神秘、庄严。“王,支起你兽皮制成的袍/收复一个又一个洞口/在山顶,俯视峰峦/你的盔甲,星星一样燃烧”,七亿年的时间,已发生太多故事、事故,累积成独特、既“新”且“旧”的今日,“七亿年,你做媒/让天地融合/七亿年,你吞掉的/一个又一个采药的老人/已经结成奇异的山果/你的诺言,绽放成晶花/在洞内熠熠闪光”。“七亿年”的时间厚度,使得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一切都重要了起来,或者,一切都不重要了起来。“种子在冰封的谷底/太阳山,月亮湖/它们借助我潋滟的波光/呼唤过你/王,成就的背后/是七亿年/一宿一宿的沉默”,这便是时间的力量,也是沉默的力量。正如她自己在诗集的“后记”中所说:“我就像那里的鸟儿学会了用翅膀歌唱,在石头里获得了沉默的力量。在一百年才生长0.6毫米的亿年地下宫殿,我用一次又一次的膜拜换来了尘土般的坦然……”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洗礼和成长,“我”由此而成为一个新的、更具内在性和丰富性的“我”。“我”也在此过程中成为与“王”相映照的另一个存在,“当然,我更多的时候像个天使/怀揣着婴儿,乘着精灵的马车/把美好的生活涂抹得光怪陆离//不,更多的时候我像个巫婆/把明明一帆风顺的生活描述得/荆棘丛生,陷阱密布”——
我交替着左右,重叠着前后
怕不能与深奥的你重逢
王,你的领口绣满了我的密码
北纬三十度,我在原始的路口
带着洞林山水
朝拜你脚下的尘土
与对神的朝拜和敬畏一样,自然在这里同样有了超自然的、神性的特质。这种“朝拜”,昭示着其精神世界的丰富、宽阔、有根,呈现出了一个极富诗意、诗性的世界。
梅尔的诗一般不直接抒情、叙事,似乎距离生活的“现实”有一定距离,她不直接处理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或问题,但这并不代表她排斥或拒绝生活的世俗性或者现世生活的合法性。实际上,她虽然有着显然的对于神性、对于永恒的追求,但这些恰恰是以对在世生活、对人生之现实性与世俗性的尊重为前提的。本质上,她是热爱生活,有着博爱精神的人,现实世界绝不是她要反对的对象,只不过,现实世界确需在“永恒”的注视之下才能够呈现、凸显出它的意义。
《故乡》一诗是梅尔诗歌中不多的与她的生活和经历有着密切关联、“及物性”较强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她的成长经历和对故乡的复杂感情。“故乡的草原开满花/故乡的伤痛盐花花/故乡,是一支流泪的歌/故乡,是石头上被绑架的疙瘩//让我再次远走高飞吧/飞到看不见你的地方”,她对故乡既是饱含深情的,又是决意要离之而去、远走高飞的。她与故乡之间有着复杂的纠缠:“我欠过你什么,比如年轻时的远离/不是背叛,我挣脱你的时候是含泪的/你也欠我一些,清澈的月光/恍惚的疼痛”。但无论如何,最终,故乡仍然是重要的、挥之不去的,是“一个精神的核/从生到死,回到原点/童年触手可及/今天远在天边”,其中所写是非常真诚、动人的。梅尔很少对具象的生活进行描摹,但也并不是没有,她更注重的是在生活的表象之后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从《淮安小馄饨》中约略可以看出她童年生活的一些场景:“小时候羞涩的口袋/不能阻挡鼻子的偷袭/仅仅是闻到你的香味/我的口水也能淹过门口的小河”,真切而生动,又有丰富的历史、生活内蕴。再如《除夕》中写小时候过年:“那时,不知父母的艰辛/藏在沉默的扁担里/除夕就是喜庆的礼花/每一年/都有所不同”,也是写出了生活背后隐而不显的因素,颇具艺术的张力。
梅尔有一颗柔软的心,这与她对现世的热爱、对神性的守护一定意义上也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珍爱生命》是她听闻一个孩子自杀未遂所写:“你只是遇到了一堵墙/那不是世界的尽头/如果你能夠在墙上画一扇窗/我保证/一定会有阳光照进来”,她继而写道:“孩子我站在雨中想告诉你/墙的背后就是明天/想不开的时候/一定要绕过去看看/有一朵花一直在等你”,这里面可以清晰地看出她对于生命的态度,这样的诗里体现着她“爱人”、“博爱”的“仁者”或“圣母”的特征。在另外的一些诗中,同样可以见出她身上爱他人、爱弱者而不惜与世界为敌的特质,比如在《站在丹麦的门口》中所写:“用海把过去隔开/海盗举着长矛/迎接一枚贝壳漂洋过海//布拉格、奥匈帝国、日耳曼/城堡、战争、血液和无耻的瓜分/都留在大陆的背后吧/站在丹麦的门口,期待一位公主/出现在阳光的边缘”,这样一位“公主”的形象楚楚动人,具有一种柔弱而又强大的力量。《安徒生》中的书写与之类似,“你孑身一人,举着灯塔/火柴里的温暖,闪耀忧伤的光芒/海,你就在耳边//海的女儿,珍珠般疼痛/如今她端坐海边,守护着/一个神话”,其中所写既是“童话”又是“神话”,有着永恒的、动人的力量。而在《布拉格》中,则写到了“我”与卡夫卡之间“千古的爱情”:“无论K如何伪装,土地测量员/总能在阁楼上找到种子/找到桌子下的甲壳虫,找到/刺眼的阳光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找到卡夫卡和我,千古的爱情/布拉格,那一刻开始燃烧/红色的灰烬落在屋顶/每家每户/都在深情地歌唱”,这是一种对文学巨匠、对另一个灵魂的致敬,同时更是个人心境与追求的坦陈,显示着梅尔精神气质中的某些内在结构与写作对象之间的对应、契合。
梅尔的诗正是在“永恒”的注视之下,面对“永恒”所进行的言说。无论是“神”、神性,以及自然、自然性,抑或是人性、人情,都有着超越性的维度,显出高炯、纯粹、超拔的特质。她的诗是天空之诗、飞翔之诗,同时又是立足于自然和现实人生之上的,她有一颗博大的心,有着宏阔的世界性、宇宙性关切与想象,又有一颗多情善感、善解人意的心,体贴入微,无微不至,爱着世间的一切。通过诗歌,梅尔完成了对世界的发现和塑形,完成了对事物、对他人的观照和理解,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与成全。人生固然不乏疼痛、苍凉、忧伤、绝望,但它仍然是美好的,是值得信任与坚持的,有诗为证!
【作者简介】王士强,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