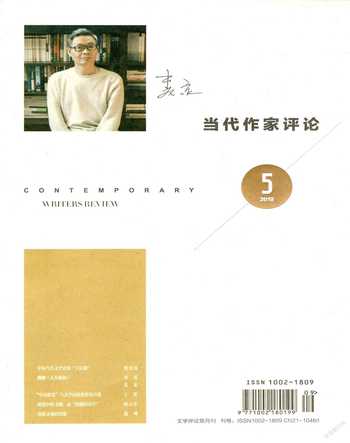论“寻找小说”
2019-09-10张伯存
张伯存
加拿大著名文艺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认为,各种各类文学作品表现了人类集体的共通的文学想象,有着数量不多且不断重复的模式或程式,构成人类整体文学经验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在文学作品中总是反复出现的,以各种变形、衍生的形式改头换面地延续着,这就是原型。一些所谓主要原型浓缩了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经验、情感和梦想。笔者以为,“寻找”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型。文学是人学,书写人的种种追寻思想与行为的文学作品演绎着一个重要的文学原型。“寻找”作为一个文学原型具有非同寻常和感人至深的力量,其间蕴涵着对现实羁绊的跨越,对精神家园的渴盼,对超越庸常、追求自由的向往,对远大理想的求索。
“寻找小说”有着独特的叙述结构,主要包括:寻找主体、寻找动机、寻找目标、寻找过程、寻找结局。寻找的目标可以是人、物、信仰、精神,甚至不知道明确的目标是什么。寻找主体一般是一个“常数”,形象性格具有稳定不变的特性,即“静态性”;还有一种情形,寻找主体是个“变数”,是个“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的形象性格随着情节展开而发展变化,参与了情节构建,具有情节意义。在中外民间传说故事中,寻找主体一般是正直善良的男性青年,为了除暴安良造福百姓,去寻找神奇的人物或宝藏,在好人或野兽的帮助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成功实现了目标,这是主要的叙述结构和情节模式。其后,根据这一定型的程式化的形式,延续、发展、衍生、变异出许多文学作品,最大的变化在寻找过程环节,情节线索的复杂多变、叙事链条的多重组合产生了不少各具特色的优秀作品。从叙事学角度讲,它有强大的叙事自我增殖能力,能够组织到各种叙述性的关系中。笔者以为,“寻找小说”有着独立的文体形式,在文类范畴意义上,寻找小说与流浪汉小说、成长小说、冒险小说、教化小说、青春小说等一样,能够构成一个独立自洽的文类范畴。
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几部以寻找为主题的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促使笔者从文学主题学角度对近40年来当代文学中“寻找小说”的关注与思考,它们是孙惠芬的《寻找张展》、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张炜的《寻找鱼王》、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以及秦岭的短篇小说《寻找》等。
《寻找张展》是一部关于教育、成长、家庭、代际冲突的小说,这是当代中国人高度关注的领域,这些问题甚至成为社会转型期中产阶级焦虑症的病源。它是密切关注当下现实的力作,小说叙述上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叙述人“我”是当地一名作家,在她寻找张展的过程中,寻访了各色人等,在一些人眼里,张展是个怪人,叛逆者,有个性,没道德感,是无耻的浑蛋;在另一些人看来,他体贴温情,通情达理,有爱心,他是个模糊的、复杂的矛盾复合体。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张展的人生真相以及与世界的深刻的无尽关系逐渐清晰起来:缺乏爱的不幸童年,父亲空难,家庭变故,成为一名志愿者,人生的追问和思考者,他向“我”展现了一个敏感的悲剧形象。“我”在寻找他的过程中自身产生了显著变化,寻找张展的过程深刻影响了“我”的生活、思想,“我”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我”被“激活”了,“我”开始反思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反思人性的两面性,感慨人生的混沌与神秘,“我”寻找到一个全新的自我。这部小说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情感表现和对复杂人际关系的洞察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叙事之网,在每个节点上发散开去,无限延伸,覆盖无限关系,显示了它的厚重与深刻。
《心灵外史》是心灵之书,信仰之书,写心灵之殇,述信仰之苦。叙述人“我”苦苦寻找保姆大姨妈,大姨妈持续不断地寻找信仰,在这种双重的寻找中,表现了“我”和大姨妈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感情,揭示了一个个荒唐离奇的隐秘世界:气功、传销、传教等,暴露了广大农村满目疮痍的衰败。大姨妈虽然没有文化,平头百姓一个,但她不愿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不愿苟且偷生,她要安顿好她的心灵,她要寻求精神信仰和心灵寄托,这是她人生的最大目标和活着的理由,就此而言,她比无数人都活得高贵,有尊严,有价值。但是,由于她自身不能生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她只能寻求外界的信仰支撑,结果一次次上当、受骗,深陷精神痛苦之中,最后精神崩溃,自我了断。这部小说直指社会中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信仰缺失、心灵荒芜的重大问题,关注国人信仰危机和底层生存危机。“当一部虚构作品为突出某个主题而写或从主题角度对它进行解释时,它就变成喻世故事或阐释性的寓言了。”在此意义上,《心灵外史》是一部讽喻性寓言,是当代版的《今古奇观》《喻世恒言》,是一部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振聋发聩之作。《心灵外史》着力于社会现实表现,由外入内,是为“外史”,它可看作是对张承志名作的致敬之作。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刘震云长篇小说新作,语言一如既往幽默诙谐,在高度写实中一种荒唐荒诞的意蕴生发出来。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农民牛小丽寻找骗婚的宋彩霞,先是被同行的朱菊花骗,后又陷入迷魂阵一般的所在,最后被骗卖身。小说里的主要人物相互之間素不相识,却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因为一种神秘的因缘发生了关联,人生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沦为阶下囚。这是一部人间喜剧,一部社会风俗录,故事情节曲折起伏,一波三折,在拍案惊奇中见出世道人心和人性丑恶。小说中的现实充满陷阱、凶险,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正面人物,人人都充满机心、算计、狡猾、奸诈、心理阴暗,主要人物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困境中,越陷越深,做着徒劳的挣扎,最后还是以幻灭、失败收场。
刘震云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其最重要的作品。小说上部《出延津记》,主人公名叫吴摩西,显然这是对《圣经·旧约》中的第二部《出埃及记》的戏仿。吴摩西是一个孤苦无告的农民,上路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感情深厚的养女却走失了,他转而又寻找养女;小说下部《回延津记》中,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是主人公,他走回祖籍延津,同样是为了寻找私奔的老婆,百年轮回,回到起点,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上演着同样的剧目,可谓意味深长。这是故事层面的寻找,而精神层面的寻找是寻找知音寻觅知己,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难耐心灵的寂寞,情感的荒芜,都在寻找一个投缘之人,一个说一句话“顶一万句”的贴心之人。这部小说以特有的中国乡土情境和独特的叙述语言表现了人精神层面的孤独,证明了表现孤独和苦闷不光是现代主义小说和先锋派的专利,中国故事中国讲法同样能对人的精神世界洞幽烛微,绘声绘色。刘震云的另一部长篇《我叫刘跃进》也是一部寻找模式的小说。
张炜的《寻找鱼王》虽然阅读对象以小读者为主,但在质地纯净的外表下蕴涵着深奥的哲理。小说主人公“我”是个梦想捉到大鱼的孩子,立志成为“鱼王”,冒险出门寻找“鱼王”,由追求“术”(手艺)而悟出“道”(做人道理)的故事。最终,“我”放弃了成为征服鱼的王者,而成了与鱼为善的护鱼人。鱼王的另一层含义是小说最后令“我”惊诧莫名、敬畏不已地看到的传说中的大鱼,犹如《庄子·逍遥游》中的那条鱼:“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小说后半部出现了叙事反转,由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向和谐相处的共生关系。“寻找鱼王”其实就是寻找一种健康完美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和生命存在方式,这是作家张炜始终关注的精神命题。一个男孩的成长史和一个古老渔村、社会、人类命运、大自然勾连起来,表達出作者深广的忧思和高远的哲理,那是令人神往的返璞归真、混沌圆融的世界。作者举重若轻,小说生发出道家文化的睿智、澄明。
秦岭的《寻找》是一篇土得掉渣的小说,用天水方言叙述,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小说主题是沉重的,但形式方面深得轻盈、飘逸、简约的神韵,小说叙述“我”父亲为了证明自己是拥护革命者而非反革命分子,在光秃秃的山上刨地寻找一个据他说装有红军血衣的坛子的故事,他用几十年时间使荒山变成郁郁葱葱的柏树林,后成为烈士陵园,以此洗刷了自己一生的冤屈。小说叙述的从容,“扣子”设计的巧妙,均表明作者小说艺术的成熟。
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寻找”是80年代的时代主题,崔健的《一无所有》《花房姑娘》等唱出了时代之声,表达了寻找的热切、焦灼和决绝,呼应了改革开放初期大众的社会心理。他在《花房姑娘》中唱道:“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噢……姑娘!/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崔健的一鸣惊人,一骑绝尘,使他成为80年代的跋涉在路上的文化英雄。
剧作家沙叶新的话剧《寻找男子汉》1986年在上海上演,发出了80年代女性的呼声,引起较大轰动。而张辛欣1981年发表的小说《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是一部较早的“寻找男子汉”的小说。张承志、张贤亮、蒋子龙、张炜、邓刚等小说家创作了一批“硬汉”小说。张承志或许最具有代表性,他的小说《北方的河》中,主人公是一个富有理想主义激情和民族担当意识的主体自我,他在畅游黄河中泅渡了政治认同的危机,完成了自我蜕变和精神洗礼。有人指出:“80年代,中国社会也将阳刚之气奉为上品。硬汉、男子汉,这些带着精神的名词,进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80年代文学中的寻找男子汉,确实是和整个80年代的浪漫气质和改革开放的精神氛围密切相关,相互促发。当时,发行量颇大的《中国青年》1985年第2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到哪儿去寻找高仓健》,引起读者热烈讨论,男性气概从两性关系、情感婚姻问题上升到国家民族富强进步问题,这是典型的80年代宏大叙事,从男性主体泅渡到民族国家主体过程中,女性主体被有意无意地抑制、遮蔽了,但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女性主义的觉醒和女性文学的兴盛是90年代的话题。
韩少功1985年发表的《归去来》是一篇匠心独运的具有一定魔幻色彩的短篇小说,主人公“我”稀里糊涂来到一个偏僻的似曾相识的村寨,山民们把“我”当成了曾在这里插队的知青“马眼镜”,“我”一开始是否认的,在他们的提醒下,往事故人一一重现,“我”相信了确实在这里生活过,还干了件杀凶除恶大快人心的事。最后,“整个村寨,整个莫名其妙的我,使我感到窒息”。“我”为什么回来?“我”想寻找什么?“我”到底是谁?“我”还是原来的“我”吗?“我”还是现在的“我”吗?“我”迷失了自我,“我”在自我意识上逐渐认同过去的“我”时,颠覆了“我”现实中的身份,“我”被从过去“唤醒”,“我”又怀疑起“我”现实中的身份,又颠覆一次。在身份质疑和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我”“在对无声的历史问话”,在思考“来到世界干什么”等宏大问题。“我”似乎是为了寻找一段人生旧梦,才不由自主地走回那个山寨,却迷失了自我。在寻找主体的迷失方面,这篇小说和余华的《鲜血梅花》相似,但是,后者中的主人公是懵懵懂懂随波逐流的,没有自主意识和思考能力,而《归去来》中的“我”却有现代知识人突出的理性意识。这篇具有浓郁哲理色彩的小说,其感性和理性结合得恰到好处,避免了理念化的弊端。
刘索拉发表于1986年的中篇小说《寻找歌王》里,艺术家B厌倦了庸俗的市民哲学和拜金主义的现代都市,厌倦了现代作曲技法和严肃音乐程式,到民间寻找歌王,寻找最纯净的“天籁99——歌王和歌精们原始的山林野唱,寻找最本真的音乐。而歌王是神秘的神一般的存在,象征着追寻的艰难,“把艺术引向纯真”的目标的渺茫和理想的难以实现。现在看来,这部小说具有某种预言性。《寻找歌王》主旨在寻找艺术之“根”,但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将它划入实验小说先锋小说,没人将它看作寻根小说。
在当代小说家中,余华的寻找意识是较为强烈的,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似乎预示了他写作的某种基调、模式和走向。他1989年春发表的短篇小说《鲜血梅花》,主人公阮海阔出门远行的初衷是寻找杀父仇人复仇,在持续不断地寻找和一次次阴差阳错的迷失中,他迷失了上路的目的和寻找的目标,他似乎是丧父状态下长不大的孩子,陷入了人生迷失方向的漫无目的的漫游中,迷惘又彷徨,找不到人生迷宫的出口,他犹如一枚落叶或飘忽的影子。小说通篇弥漫着荒诞感、无力感和虚无感,是一种作者所谓“虚伪的现实”的表征。这篇小说其实是披着中国武侠小说、新武侠小说外衣的后现代文本,形式貌似传统,表现的却是后现代主题,旧瓶装新酒。它提升了寻找小说的哲理性。
余华的《第七天》是寻找小说的力作,它的情节线索和叙事动力就是不停歇地寻找,各色人等都在寻找之中,叙事主线是主人公杨飞寻找身患绝症且失踪的养父杨金彪,他始终奔波、行走在寻找的路上。他的身份是一个游魂,他自由地穿行在阴阳两界之间,他一路上邂逅不少的游魂、亡灵,他们也在寻找亲人,追寻过往在阳界生活的日子。小说在叙事策略上以阴界的魂魄返观阳界社会人生,以独特视角观照现实中荒谬的生存本相,亡灵们都遭受了各种冤屈和不公,见证了荒诞现实,还原了世间真相。小说多角度展现了急遽转型和发展的当代中国现实中一些不义不公的阴暗的角落。而在阴间地府,一片和谐景象,亡魂们善良、淳朴、平等、和美,是一个闪耀着至善至美的人性理想的世界,俨然是桃花源或乌托邦,这是对公理和正义缺席的阳间的反讽。小说具有高超的叙事艺术和简约的语言之美。
阎连科是一位具有苦难意识、忧患意识的小说家,他也同样具有强烈的寻找意识,他笔下的耙耧山脉的父老乡亲为了寻找幸福美好的生活祖祖辈辈努力耕耘着、挣扎着、寻觅着。《寻找土地》是一部令人感伤、痛惜的小说。孤儿军人佚祥帮军营附近一位寡妇修房,他为救寡妇而不幸被砸死,因为不是因公而死,不能评为烈士,连长把他的骨灰送回家乡,却找不到安葬之地。他的家乡人富裕了,但自私狭隘,不愿意接纳,最终马家峪人慷慨仗义安葬了他。小说同样以亡灵的视角观照生者和社会,死者的灵魂在尘世辗转之后,最终得以安顿。曾经民风淳朴的刘家涧变成了富足的“刘街”,充满了铜臭气息,礼崩乐坏,而马家峪的民风却依然淳朴、仁厚、重義轻利,如世外桃源。人与土地的关系是阎连科小说的主题之一。阎连科在这部小说中寻找到了他理想中的安顿灵魂的土地。中篇小说《朝着东南走》中,“父亲”是个独特的农民,与乡亲们不同,他不重名利,人生目标是“太平快活”,高人指点东南方向有他的太平快活地,他便朝着东南方向走去。在寻找的道路上,他有过滞留,结婚生子,但寻找的火焰从未熄灭,再度燃起后,他抛弃妻儿,重新又踏上寻找的旅途。他终于没有找到那个东南方的“太平快活”之地,或者说,这样的所在永远在前方,永远在寻找的旅途中。这部小说的象征意义是非常突出的,“父亲”是一个符号化的象征性人物,在他身上充满了脱离现状,挣脱现实的羁绊,寻找美好生活的强烈冲动和欲望,同时他也在寻求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尽管他自己不一定意识到。而这种精神力量和强大意志正是人类文明延续和发展的不竭动力。他是一位超人,一位平民英雄,他就像远古神话中的神。
河南作家墨白的《寻找乐园》,写的是一个叫王新社的青年农民,不安于农村的贫穷、落后,怀揣着寻找乐园的梦想,来到城市投奔堂哥,干装卸工,为了利益之争,以地域为帮派的装卸工之间经常发生残酷的械斗,以堂哥为首的帮派最终在械斗中取胜,却陷人工头圈套,丢了生计。后来,堂哥因在路边揽活被车撞死,王新社等开始了漂泊不定的生活。这部小说虽然题目叫《寻找乐园》,却精于写实,写出了残酷的生存本相,题目和生存困境之间构成反讽,与《朝着东南走》相比,这部小说略显滞重,不够轻盈,象征意味不强。
王小波的长篇小说《寻找无双》是一部以追寻真理、求索智慧为主题的小说。与其说无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不如说她是真理、智慧、科学的代言人或符号。《寻找无双》其实是在论证以下两个命题:“无双实有其人吗?”“无双是其本人吗?”,对它们的反复质询、不竭叩问成为小说的叙事动力,这不仅仅是身份确认,而是喻示了求知道路、寻找智慧之旅的复杂性、艰巨性,要经受政治、道德、经济的多重磨难,这是对求真意志的考验。可怕的是,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寻找主体一度自我迷失,怀疑自我的存在,他的处境和寻找过程充满了荒诞感。在他又一次踏上寻找之旅时,小说戛然而止,叙述者悲观地暗示无双是寻找不到的。这是一部思考寻找本体的小说,寻找的过程在希望和幻灭、期待和绝望之间循环往复,寻找对象身份不明,明灭难辨,由“有”趋向于“无”,寓意着科学和智慧可悲的命运,寻找真理的艰辛困苦。在当代寻找小说中,《寻找无双》无疑是哲理意蕴最浓的,小说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中具有寻找原型的文学作品也不在少数,如《山海经》中有夸父逐日的神话传说。《诗经》名篇《蒹葭》中,抒情主人公对朝思暮想的“伊人”的寻找。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写尽了吕纬甫寻找出路而不得的苦闷和彷徨,而《野草》中的“过客”至死都会执著在寻找之路上。汪曾祺写于1944年的小说《复仇》运用意识流等现代派手法叙述了主人公寻找杀父仇人的故事。
寻找母题在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是西方文学创作的重要传统,它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中,《奥德赛》成为欧洲寻找母题的文学起点。而最著名的就是中世纪文学寻找圣杯的题材,尤其是骑士文学,时至今日,寻找圣杯的故事仍在欧美影视中花样翻新持续演绎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的短篇小说《寻找格林先生》是一篇寓意深远的佳构。小说主人公格里布锲而不舍地寻找一位不知存在与否的格林先生,揭示出世界的荒诞和人类生存的困境。格里布不言放弃的寻找体现了负责担当的人生态度和执著信念,他寻找的对象格林先生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上升为一个抽象符号,表征信念、理想、使命的符号。从原型批评视角看,小说隐喻了受难与救赎、爱与希望的宗教母题,主人公格里布一定意义上可看作基督的象征。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寓言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牧羊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追寻梦中的金字塔,踏上寻梦的旅途,经历了诸多冒险和奇人奇事,找到了爱情,最终实现了他的“天命”,理解了什么是“爱”。这部小说是无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的现代版,浓缩了人类的寻找原型和集体无意识,深深地击中了各种族各地域人们隐秘的情感G点。
“寻找小说”的篇目可以继续开列下去,它是敞开的,无尽的,这里提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寻梦、寻根、寻真、寻我、寻找信仰、寻找精神家园……各种目的和目标的寻找是人类不竭的精神冲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宿命,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寻找的历史。表现人类命运和情感的文学相当一部分就是寻找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是人类精神跋涉的路标和情感慰藉的栖息地。“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为我们开拓了视野,使我们不是瞥见诗人个人何等伟大,而是发现不涉及个人的更伟大的景象,这类景象反映了精神自由的一次决定性行动,反映了人类再创造的巨大力量。”“寻找小说”如是,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如是,永远在寻找中,永远在路上。寻找是人类改变命运、超越自身和再创造的永恒动力和巨大精神力量,寻找是一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