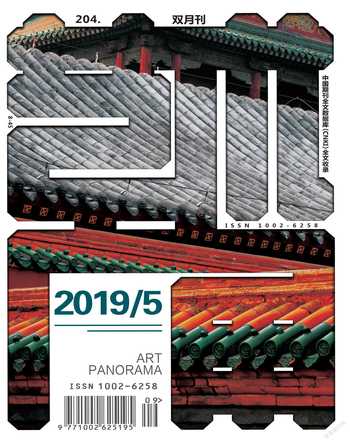《一纸情深》的结构艺术
2019-09-10王向峰
王向峰
刘文艳的散文集《一纸情深》所收录的24篇作品,都是她最近几年写作的散文作品,题材内容直关当下的现实生活,饱含深厚的家国情怀,在艺术手法上也特别讲究,读后每篇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本文专以几篇作品为例,看其在艺术结构运用上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框形结构”。这种结构是把对于以往的生活事态的表现装在眼前镜框里,情节开篇叙述的是此时此地此事,也就是开篇的情景是读者所见的当下,但内容的情节中心虽然与此当下相关,却是早已过去的事情。这种情节结构法在中短篇小说和电影中经常用,像德国小说家斯托姆的《茵梦湖》、法国小说家莫洛亚的《星期三的紫罗兰》,都是享誉世界的框形结构的经典作品。鲁迅的《祝福》写祥林嫂在除夜之前死去,“我”知道了这个事之后,回忆起初在鲁家的种种情形,立意并不是写她的死,而是写她此前一生的不幸,所以除夕之前“我”与她见面以及关于死后有无魂灵的问答,仅是镶嵌于她过往种种的一个镜框。这种框形结构的写法,能把对已往的回溯变成当前的,并能赋予回忆的情感增值。文艳的《红枣连心》从第二节开始用的就是这种“框形结构”。她追述上小学时看电影芭蕾舞剧《白毛女》,那里有民众欢迎八路军到来,献大红枣的歌唱:“大红枣儿甜又香,献给咱亲人尝一尝。”这一情节片断成为她这一篇散文结构之框,展开了安放在文中的诸多红枣情节,如她之前去姥姥家,在姥爷种的枣树上摘红枣,并把枣树苗移回自家栽种;姥爷参加抗日活动,被日寇抓去拷打、砍伤,以致逃亡外地,解放后才返回故乡,重新在菜园栽种枣树;从姥家移来枣树苗,几年后结枣返送姥家分享;解放军拉练住在自家,送枣给解放军,他们不得已收下后走时又给留下钱的事;当妈妈管理枣树后,不忘每年给儿女送枣分享,妈妈去世后嫂子管理枣树,秋枣红了依然不忘在城里的小姑;今天老家园里枣树又面临工业用地拆迁的命运,等等。散文中全篇是枣,全篇是情,它记录着时代变化,维系着几代亲情。《红枣连心》行文如果不是用当下的时间之框装进从前的枣树,就不会有现在的感人效果。
其次是“游走结构”。这种结构方式主要是由生活题材的时间运行性质决定的,也常为小说与电影所采用。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美国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都是以人物在游走中发生叠加事件为情节,以时间过程为情节贯穿线。这种结构在小说中最好用,因为可以随时造事,奇遇层出,让读者随之被吸引。如果是非虚构的散文,用此法结构则比较困难,因为作者游走倒可以无阻,但所遇是否能成为入文表现的题材内容就不好说了。游记散文可以写经历的山山水水,但一篇中只写关联的山水并不是“游走结构”,而只有在一篇中有篇中作者主体或人物自身的游走的游走才算“游走结构”。《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取经历的八十一难是“游走结构”。《大唐西域记》里玄奘的经历是“游走结构”。在《一纸情深》中的《闪光的青春》一文,由于是采风团七天行走于从丹东中朝友谊桥到葫芦岛的止锚湾三千多公里的海防线上,到几个边防检查站、边防支队、边防派出所和警务室,去访问那些为国守海防的武警官兵,写作受时间、行程与主题内容的限制,可以说是走马观花,走一个地方写一个地方,纪实性、采访性与连串性,写出来呈现原生态,就是贯穿在辽宁海防线上一代年轻卫士们的“闪光的青春”。我們在文中看到一连串的感人事迹,其中有一位海警叫徐贺,他一个人在乌蟒岛上值守,岛上所有的事情都要管。边防武警中有许多感人故事被写入了《闪光的青春》。
第三是“宅院结构”。这种结构在英国称之为“哥特式结构”,主要结构特点是情节多半集中于一个城堡的王宫或贵族府第,描写的是中世纪生活。英国18世纪后期的司各特以此类小说著名,代表作《艾凡赫》早在五四前就被译成了中文。这情节集中于哥特式城堡之中的表现,与“游走结构”的情节随人物游走的不断变化迥异,所以是小说与戏剧常用的结构模式。中国的《红楼梦》在结构上以荣宁二府为情节不变的演化地,写尽了封建大家庭没落败亡和众多青年男女的人生悲剧。这种结构用之于散文,便是以家庭为情节中心,所有的人都在宅院中登场、做事、说话,有点像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恋爱、斗智、决斗,等等,始终都在一个不变的舞台空间里表演。要论《一纸情深》中的文章,《钟点工》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篇不长的散文,所写的牛丽其人,非常善良、懂事,我读了之后立刻与福楼拜的《一颗纯朴的心》联系在一起,联篇思之,感到人格的高尚不在于身份,而在于心灵和行为,为此我特别想看到文艳对于牛丽的后续描写。
第四是“联想结构”。散文文体其名以“散”冠之,是说它不必像小说那样有完整的情节,也不用以韵律和激情去张扬主体的心志,更不用像戏剧那样设计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以及情节的突转与高潮等。但是运用联想心理机能,对时间的过去与现在、空间的此地与彼地、人物关系上的你我他,在事实上的联类结想,使本来并非一体的各类材料,在形象思维中以情化物,构结成整一的题材。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之“散”是题材表现方式的自由性,绝对不是不受主题立意限制的所谓“形散神不散”。因为,如果真的是“形散”了,依形而所载之神与依形而所传之神,岂不是如无皮可附之毛了吗?因此,散文也必须是形神统一的文学体类。在《一纸情深》中有一篇《大美无色》,是写作者在浙江雁荡山时,参观灵岩和大龙湫,见有一景点为“抱儿峰”,作者到此如果就是见景说景,不论怎样状写其形态之切,如本文中所直写的也就是“儿体微蜷,紧贴母怀,少妇将儿紧揽怀中”。写这样的象征石,没有想象性地体物赋情,就不成文章。在此,文艳运用想象移情而迁想妙得,她从冰冷的石像身上看到了自己已经逝去了的母亲,又一次重温了母亲怀抱的温暖。另外,在此文中如有天助,遇到自己早就熟悉的画家王元石,他说他在此处画千佛岩的佛,实际是带着对母亲的感恩之情在画母亲,并讲了他母亲方才来电话是告诉他今天是他生日,等等,对于著文来说,这又是凸显文章主题的直接材料,用思联结即可成文。
《一纸情深》是一本很有生活温度和艺术表现力的散文集。联系文艳以前的许多作品,可以看出她的创作是不断发展上进的,未来也大可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 刘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