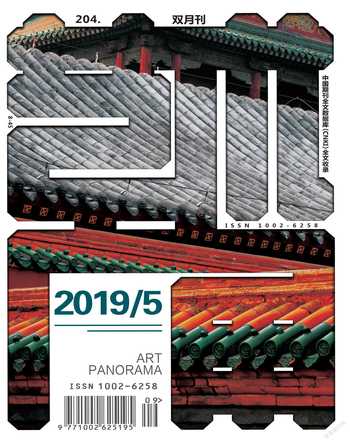跨界与融合:从电影音乐到音乐IP的电影转换
2019-09-10张璐
张璐
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音乐就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在七艺中音乐是唯一的艺术类别。电影作为综合性艺术,从内在结构来看与音乐这门听觉艺术,总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音乐是电影的组成部分,电影是音乐的影像表述;音乐是电影的听觉表达,电影是音乐的时空形态……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电影与音乐,在功能、审美趣味、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正在发生深度的跨界与融合。
一、跨界:电影中音乐的功能
苏珊·朗格曾说:“音乐可以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细节和真实性来表现情感的特征。”可见,音乐的艺术特性具有表现情感的价值。在电影中,音乐的情感特征更是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旋律、节奏、调式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往往能够帮助推进剧情,促进故事的发展。电影中的音乐虽然更像母体中的孩子,依附电影成长,但也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它的这种功能性特征,从侧面表征了电影与音乐之间融合与跨界的可能性。
1.基础性功能
电影主题音乐、背景音乐、场景音乐、连接性音乐等音乐元素,在电影中无处不在,它们不仅与电影捆绑在一起,更是始终为电影服务,比如为电影烘托气氛、助燃情绪、推动情节等,它可以是某个角色的听觉代言,也可以是情节发展重要转折的符号,它可以是贯穿整部影视作品的流动的艺术,亦或是故事情节、戏剧冲突发展变化的发酵剂……总之,在基础功能方面,电影音乐作为电影的子单元,总是量体裁衣。
2.叙事性功能
若说量体裁衣是基础性功能的话,那么电影中音乐的叙事性表达,更像是电影对音乐的内在消化与提升过程。将音乐的情感性特征进行有效的转换,通过人物、故事、情节、戏剧冲突等故事要素,通过镜头、色彩、画面、基调等外在的形式手段,突出和生发音乐在电影中的叙事性,对音乐而言,这是高于基础性功能的叙事性表达。在美国当代哲学家彼得·基维看来:“因为音乐叙述能力的匮乏,根本不具有传达真正的道德或哲学意义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需要某种复杂而具有细节的情节结构,而这是音乐无法提供的。”[1]显然,他的观点主要是针对纯音乐类型,更多地强调它的形式意义。正是由于音乐自身叙事性的匮乏,才需要借助电影中其他元素來展示它的叙事性。
电影音乐是隐藏在电影艺术里的另一条艺术平行线,它似有还无、若隐若现,总是在戏剧发展中,以音响组织结构的听觉特性展开自我表述。影片《卧虎藏龙》(2000)中经典的大提琴演奏,缓慢下滑的弦乐揉弦音响,始终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纠结的爱情与江湖情怀;影片《金陵十三钗》(2011)里的民间小调《秦淮景》,不仅突显了故事发生地的叙事背景,更是表达了主人公对故土的万般牵挂。这样的叙事效果,既来自于电影文本自身,也是电影音乐的叙事性表达与之协作的结果。
3.市场化功能
在今天的文化产业市场中,电影音乐被发酵出不可估量的巨大市场能量。中国已经成为电影大国,近十余年电影票房大幅度增长,产业链条越做越大。在这样一个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环境中,电影音乐不仅是一种内容生产,同时,它也成为电影产业链条中宣发和营销的重要环节。从宣传角度看,它逐渐成为宣发单品而直接面向受众。2014年,由韩寒执导的影片《后会无期》取得不俗的票房,这部影片的主题曲是由朴树演唱的歌曲《平凡之路》,传唱度较高,甚至出现了未映先火的现象。主题音乐的提前造势,不仅为电影推向市场助力,也打通了影视与音乐之间粉丝的界限,推动了影视文化产业链条的发展,也是不同艺术门类跨界的市场化体现。站在市场营销角度,打通影视、戏剧与音乐之间的粉丝群界限,使它们互相借力借势,能为音乐与电影更深度的跨界与融合打好受众基础。在营销时代,从个体主观的感受体验到粉丝经济的运作,离不开最大程度地满足用户体验。
二、融合:音乐IP转化为电影的密码
海顿的《第83号交响曲》曾被赋予这样的哲学主题:“在人生中冲突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不是教条主义和压制,而是宽容。”[2]显然,音乐不仅仅是旋律、节奏、调式、结构的机械组合,它所包含的哲学意义与审美情趣,也都不是单纯从音响组织结构中便可一目了然的。也正因此,当电影音乐被赋予更高的期许时,它就不仅仅是与电影互相借鉴的问题,而是在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寻求与电影的深度融合与转换。从电影与音乐的跨界,到音乐IP转化为大电影,其中蕴藏着玄机与密码。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这超过了欧洲人口的总数。这样的网络空间,给音乐IP的转换带来了更多更大的可能性。
1.类型性
从较早的《同桌的你》(2014)、《栀子花开》(2015)开始,由歌曲衍生的大电影作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银幕上。此后,又出现《睡在我上铺的兄弟》(2016)、《后来的我们》(2018)、《一生有你》(2018)、《为你写诗》(2018)等一系列由流行歌曲改编的电影,虽然这类影片数量并不多,但作为听觉艺术与视听艺术深度转换的结果,它们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和作品。探究其转换密码,首先要从哪些音乐具备转换要素谈起。
(1)经典歌曲IP的价值。不是所有歌曲都可以成为电影IP。《同桌的你》是上个世纪90年代耳熟能详的校园民谣代表作。歌词的内容并不复杂,它代表了一代人曾经历的青春年华。歌曲旋律的清新明快、节奏的匀速对称,以及歌词内容的含蓄与隐喻,都将音乐的情感表达突显到了极致。因此,在当时它就已经火遍大江南北,传唱度极高,在歌迷和观众中得到广泛的喜爱与认可,只有这样的歌曲才有可能成为IP。
另一方面,音乐IP的转换,是将旋律、节奏、歌词内容进一步完善,是在主题延伸方面进行的提升式再创作。2018年上映的电影《后来的我们》,正是歌手刘若英对自己20年前演唱的歌曲《后来》(1999)的再解读。影片上映前,制片方组织了万人歌迷合唱歌曲《后来》,来自80后群体朴素、直白的深情咏唱,唱出了这20年间他们从青年走向中年的人生体验。在观影时,观众时刻期待《后来》响起的那一刻,但导演只是用男女主角的对话“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将影片推向高潮。诚然,这是对之前歌曲《后来》的再创作、再解读。这种不流于形式上的复述、从歌曲本身开拓性地深化戏剧情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向性,显然是一种更高级的艺术转换。
(2)歌名或歌词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或是留白较多,能够给创作者更多想象空间的音乐IP也颇受欢迎。上世纪90年代末张学友经典歌曲《她来听我的演唱会》具有典型的叙事性特点。它生动描述了女主角从18岁到40岁的人生经历,展示了她一路走来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种种成长与蜕变,这已经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架构,具有转换成电影人物和故事的空间。此外,如刘若英的《后来》、苏打绿的《小情歌》(2006)等歌曲,虽然歌词内容较为笼统,可想象空间大,再比如梁静茹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勇气》(2000),也被改编成“勇敢追爱”的故事。
不得不说,音乐IP向电影的转换,不仅给经典音乐作品带来新的生命,而且也使音乐作品获得了商业价值、口碑、影响。对于创作者而言,他们对自己的音乐作品充满情感,能够将相对单一的听觉艺术作品转换为视听结合的影视作品,这貌似是可遇不可求的缘分与机遇,但整个市场的发展往往会超出预期,随着这股IP改编热潮的涌现,这将变成愈发受到关注的现象级事件,当然,这也是资本在背后操控的结果。
2.受眾心理
流行音乐由于其通俗易懂的显著特征,总会给观众较强的代入感。得知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被改编成电影,观众往往对此充满期待。观众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对于歌曲的感情代入到电影中,但这就更需要较好地把握作品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似乎是青春、爱情、校园主题歌曲更容易被转换。虽然明知制作方是在“卖情怀”,走怀旧的路子,但受众依旧会心甘情愿地买单,他们看的不只是电影,而是自己这代人的青春记忆与年少情怀。“愿你出走半生,归来时仍是少年”,这大概就是人到中年后最容易被勾起来的情感,而这恰恰也是近年诸多音乐IP电影的主打路线。喜闻乐见不仅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对艺术作品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它也代表这个时代大众美学的标准,因此,接地气的作品往往最容易引起受众共鸣。
3.产业需求
众拍时代下,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创作者,却鲜有人能真正做好电影。“卖情怀”绝非长久之计。想要赢得观众,就要注重专业性,将歌曲的意境、审美传达给受众,尽可能满足观众的想象与期待,将“卖情怀”变为“卖故事”。2015年的《栀子花开》票房3.79亿;2014年的《同桌的你》票房4.56亿;刘若英的电影《后来的我们》成为2018年爆款,刘若英在影片电影发布会上的一曲《后来》调动了所有观众的情绪,吸睛无数,影片最终获得了13.62亿的高票房。这些可观的行业数字,见证了音乐IP转换的成功,资本、音乐IP、情怀、小鲜肉等虽然都是其中的要素,但更重要的是,始终坚持内容为王,写好的剧本,讲好的故事。由于网络小说、电影电视剧的IP可开发内容越来越少,它们的版权购买价格也水涨船高;而歌曲改编的空间则越来越大,它将会成为IP电影开发的新金矿。市场需求、商业运作、受众期待及审美需求等方面的不断变化,都将为未来音乐IP转换成电影的市场发展创造无限的可能。
注释:
[1][2]〔美〕彼得·基维:《音乐哲学导论:一家之言》,刘洪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148页。
(责任编辑 牛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