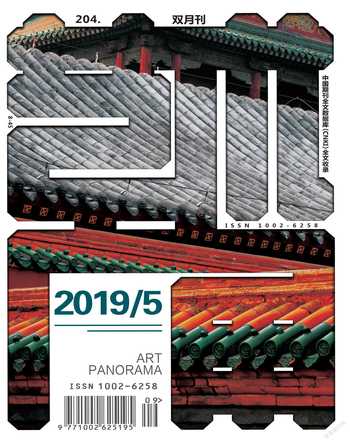人间究竟有真情
2019-09-10彭定安
彭定安
人间究竟有真情;“真情是散文的生命”。这样两个理念,前者是我在读刘文艳的散文集《一纸情深》的过程中产生的;后者则是刘文艳在《一纸情深》的后记中阐发的创作理念。它们促使我以此立题,试论刘文艳的情感散文,并进一步探讨散文的情感元素及其在《一纸情深》中的具体体现。
在陆续阅读《一纸情深》的过程中,不断产生一种情感的激荡和温馨的感受,那就是开篇所写的“人间究竟有真情”。这种情感的激荡和温馨的感受,来自两个方面:私人的和社会的。就前者来说,我的“私人审美感应”是:平生坎坷、风雨载途、颠沛流离数十年,人情社会中,白眼冷脸,自然是一种常态。这种生活状况中,所缺的正是人间温情和人间真情。社会生活且不必说了,在家庭中,即使是患难夫妻、困苦父子,同甘共苦、艰苦相携、彼此扶持,也往往由于生活的拮据和困窘,缺少那种安稳美好的情感、温馨的体验。因此之故,在感受《一纸情深》散文中的处处真情之际,不能不油然而生感叹和欣羡:她是多么幸福啊!人间究竟有真情!对于缺乏这种美好情感感受的人来说,读《一纸情深》,感受人间温馨与真情,虽是“他人酒杯”,却也能够“浇自己的块垒”!这种阅读效应,正是《一纸情深》的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应。因此,我的“私人阅读感受”,也就不完全是“属于私人的”,而是反映了部分的“社会反映”的。
说到“社会的”,还可以扩大,那就是生活中亲情疏离、家庭破碎、情感缺乏、精神紧张、情绪浮躁,以及金钱至上、尔虞我诈等等现象,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负面效应,是人们侧目并努力加以消除的。而这种情况的“感性世界”以至“理性世界”的积极寻觅与追求,正是出于对温馨亲情和人间真情的渴望。因此,《一纸情深》既反衬了社会消极现象,又提倡和激发了温馨和真情的萌生。
这就为刘文艳的“真情是散文的生命”的命题作出了实证。
我一直欣赏并常常引述美国古斯塔夫·缪勒在《文学的哲学》中表述的艺术观念:“艺术不应被看做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哲学而艺术。”事实上,无论哪个作者,在写作时,都是被一种哲学观念潜在地激起创作欲望的,内心是有“哲思”要表达的,不同的只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或者自觉程度有高低深浅的差别。刘文艳写《一纸情深》,自然是情感驱动和“情感创作激起”状态,但是,在她的内心,她的创作意识和创作心理中,却有一种“哲思”起到了潜在的、隐形的驱动力作用。《一纸情深》中所有的散文,几乎篇篇“诉情”,是所谓“情感篇”,不过她未曾作理性的表述。只有在《奶奶的幸福》中,她“偶然地”,也好像是“按捺不住”地抒写道:“亲情爱情友情乡情都是幸福之源。”“为他人做出奉献的欣慰,对他人进行帮助后的快慰,都是幸福的重要内容。”这不就是一种“哲思”吗?正是这种生活理念、幸福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正是这种隐在的“哲思”,为她的情感散文奠定了成功的艺术基础、潜在的思想性深度和社会性启迪。如果只有真情、只有情的倾诉,文章就单薄了,就浮泛而轻飘了,就缺乏感人的深度了。
这里涉及一个“情感”和“哲思”,“感性”和“理性”的悖论问题。哲学、心理学以至社会学,都把两者作为“两极”的“矛盾双方”来并列。这在学理上是需要的;但是,它们在实践上,在发展的向度上,都会彼此转换,表现出否定之否定的结果。这就是说,在情感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凝聚、提炼、升华而至“理性化”了;而“理性”在发展到极致时,转化为一种情感,也就会“情感化”了。瞿秋白在走向刑场时,高歌一曲他亲手翻译配词的《国际歌》,从容面对死亡,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感表现啊,这种视死如归的感情,正是因为上升到献身革命、献身共产主义理想的“理性”的高度到达极致的结果;也是理性的情感化。尼采是杰出而独具特色的哲学家,他的哲思发展到极致,付之于文字,也就诗化了,即情感化了。一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诗化—情感化的哲思录。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白的“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等等,都是感性的、情感的、诗的内在感情的外化;但由于感情的极致的发展和高度的提炼,便理性化、哲学化了,诗句转化为理性的高度而优美的吟诵,成为爱国、求索、追求真理、文章千古而帝业虚空、事业文章顺畅、以至以身殉国、血溅汗青……这些理性的、哲学的、道德的、心灵与境界的“诗性表达”,而成为古今传颂并化育为中国人崇高心灵的基因。以此理,解读和诠释刘文艳的《一纸情深》,她的创作实践体现了这一艺术规律;其理端在,是在学理上完全把握并有意识地运用。这就是前面所说,她在《奶奶的幸福》一文中表达的“哲思”,即她对真情、幸福以至人生的理性解读,在每篇散文中情感化地表达。我以为,这正是她的成功之处:诉之以“情”,而归之以“理”。所以,在她的散文中,屡屡读到娓娓地、絮絮地、缕缕地、细节化地述说亲人、友朋以及海防战士、防毒警察和钟点工等人,那种细致的陈述、场景的铺垫、细节的描绘,并沒令人觉得絮叨、啰嗦、繁琐或多余、累赘,而能够饶有兴味地读下去,甚至内心感奋、体验温馨地欣赏,就因为哲思被情感化以至于生活化了。“哲思”在这些细细的“情感叙述”中,是衬底、内蕴和“潜在叙述”。在这里,她获得了“哲思”:“真情是散文的生命”这一“理性”的情感表达。我觉得,这也就是古斯塔夫·缪勒所说的“不断变化的文学风格就是艺术及其他一切文学活动里潜在的哲学变化的结果。”而我的解读,则属于他在《哲学的美学观》中所说的“艺术被置于哲学中来观照”了。
《一纸情深》中抒写种种情感、种种真情,包括“亲情爱情友情乡情”,还有她未曾提及的“自然情”,都一一写到了,但最主要也是最感人至深的是母爱,这本来是人间真情中最主要者。不过母爱的表现却有种种社会形态和个体显现。刘文艳的母爱不一般,因为她的母亲不一般。这位无文化的乡村妇女,达到了高度的道德水平和思想境界。她大度、豁达、懂大体、识大局,把一生心血与大爱,献给了家庭、子女,但又不狭隘;她广施爱心、不偏狭更不吝啬,尤其是能够体贴人,宁可委曲,不亏他人。这是一位典型的、富于中国美好传统品质的贤妻良母。作者实际上是描绘了一位中国母亲的高大形象,从生活中个体臻于艺术典型的高度。作者不止在一篇文章中抒写母亲、倾诉母爱,而且还在多篇散文中顺涉母亲和母爱,读来很动人。并且,她抒写了两个时代、两种一致而又不同的母爱:她母亲对自己的爱、她作为母亲对于自己女儿的母爱。这里还涉及虽然一致但却不同的对于母爱的理解。在物质生活不算富裕、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全家居于乡村的境况下,当母爱表现为物质的施与,往往具有重要的位置,物质是情感、母爱表现的载体。而她的女儿却对这种物质的爱的表现很不看重。她对物质以及物质的获得与享受,具有一种高文化心理和道德水平下的认识、理解和批判。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整个社会物质水平提高时,具有文化修为的年青一代对于母爱的更高层次的理解。这方面,作者虽然着笔不多,但写得具体、到位,使读者看到、理解一种新的时代、新的青年的观念。这一点,颇有教育意义和认知价值。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说的,“哲思”的潜在形态和功能。
《一纸情深》以母亲和母爱为核心,抒写了广泛的亲情和友情、乡情。这本散文集中,写得最多、最丰富、最美好的是母亲和母爱,但这不是普通的天性式的母爱,与一般的民间、乡村的普通妇女不同,这位母亲和她所施与的母爱,既是外在种种细枝末节的表现,又是深沉蕴藉而有思想的施与;既是私人、家庭内的母爱,又是广施博予、泽及一家大小、各色人等的母性的爱。她心中充溢着爱、善与给予。故此,我称其为《一纸情深》的情感诉说的核心。但不止于母爱,她还写外公、奶奶、父亲、嫂子,写战士、钟点工,还写自然,红枣、绿柳、山花。即使是在抒写这些时,也会顺带地写到母亲和母爱。写孤胆英雄,“当他说到母亲时”,“泪水就在眼圈里打转,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哽咽。”写在雁荡山偶遇画家朋友在此写生,也会涉及母亲、母爱:他画抱儿峰,思念80多岁老母,“眼里噙满泪花”。
《一纸情深》写这些“情感篇”,但不是一般地写,而是有故事、有情节,特别是有细节的呈现;此外,还有场景和风光。而在抒写时,都含着温情,蕴含回忆、系念、谢忱和赞颂。其中,包蕴着作者的议叙、评论、赞扬,包含价值判断与意义阐发。她既写了事,更表现了人。除了母亲的形象很突出,其他形象也都留下可供回味和记忆的刻痕。奶奶的“古典”朴素的美和美的心灵、外公的尊严,特别是面对日寇的坚强不屈、刚毅,以及对乡亲们的忠贞;父亲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以及对亲人们的爱;女儿的思想与价值观的现代元素和对母亲真挚的爱,等等,都蕴含深深的情、诚挚的意、真心的赞。写青少年时期的两位同学,在人生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一个始终未能摆脱蛰居乡里务农的生活状况,一个则蒸蒸日上,成为领导干部。但彼此仍然珍惜往日的纯真感情,“发达”的不嫌弃老友发小,屡次帮助她;“居乡”的也不“自惭形秽”,以最朴实的“礼物”赠送回报。而这礼物则被视为“最珍贵的礼品”留存着。
这使我想起接受美学学说中关于“意义”的阐述。文学文本只提供了“原意”,而读者则根据自身的修养和生活经历,创获“意义”。我从《一纸情深》中领会到种种“意义”。释义学关于“意义”是这样说的:“意义,体现了人与社会、自然、他人、自己的种种复杂交错的文化关系、历史关系、心理关系和实践关系。”刘文艳的散文,正是体现了这样“种种复杂交错”的关系。父老乡亲、发小旧友、素昧平生的访问对象、扶贫资助的农户以至自然——美丽幽静的山村、红枣树、绿杨柳、山花等等。而她在表述这些关系时,既充满了感情,又阐发着感情;同时也表达了她自身内在的情感诉求和思索,而且进一步理解和阐释了其中的“意义”。我从这些陈述、记叙、描绘中,感受到她的思绪和情感、她的怀念和记忆,她表现了现代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既享受又惶惑的情感和心态:怀念故土家园,怀念自然和其中的花草树木,冀望留得住乡愁,重拾真挚朴素的亲情、友情、乡情。这正是“现代人在寻找‘丢失的草帽’”,“走向回家的路”的表现。我在阅读中,体察、感念、接受这一切时,从中体会到刘文艳情感散文的哲学意蕴。她对“种种复杂交错”关系的体察和抒写,正是实践着“为哲学而艺术”的文学创作的使命和意愿。
海德格尔有言,“语言有自我陈述的能力”,不仅我在说“话”,同时,“话”也在说我。我们在《一纸情深》中,看到、理解、认识了作者刘文艳。她的灌注哲思的“情感”、她的人生追求和生命体验、她的“待人接物”以及她的家国情怀,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艺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哲学而艺术”的一种体现。
至此,我想说,对“真情是散文的生命”这一命题,她以自己的散文作了具体的、文字的、事实的论证;而且还证实:所谓散文的情感,是一种理性的升华,是理性极致发展而成的情感化理性。因此,她不是一般的感情,不是泛泛的感情,不是浅层次的感情。毕竟,不是有感情的散文就是好散文。
我在《创作心理学》中曾提出“感情家族”和“记忆家族”两个命题,前者为“情绪—情感—情操”;后者为“形象記忆—情感记忆—长时记忆”。情绪和情绪记忆是浅层的、短暂的、一过性的,甚至稍纵即逝的,而情感记忆则是深沉的、刻痕般的、进入记忆库的。形象记忆是形象的、鲜活的、晃动着人的身影的,具有细节和场景的;长时记忆则是深入心灵、思维深层的记忆。我以为,散文的生命的“情感”,就应该是作家的情绪记忆和情感记忆、长时记忆和形象记忆的融合,并经过思想和生活经历的“酶化”。“酶化”之后的情感记忆就进入情操的高层次,那是一种思想—道德—人格魅力的境界。刘文艳的散文正是她独具特色的形象记忆、情感记忆的产物,并且升华为情操和境界。她的几乎所有的散文篇章,都充满细节——生活的细节、鲜活的场景、突出人物个性化话语、行为和社会情感,对美德、魅力的“情操赞颂”,在她对母亲、外公、父亲以至丈夫和女儿的抒写中,都表达得淋漓尽致;尤其可贵的,是她对于树木花草的赞美和咏颂中,直白地表达出来了。比如《红枣连心》《任是无人也自香》《绿柳情思》等篇目。
综合这些陈述,将之融汇起来,就是:顽强的生命力、柔而不弱、不妖不艳、不惹眼、不张扬、不亲近闻不到芳香、素心高洁、不求闻达、不慕荣利、与世无争,只是诚实而朴素地生活,默默地无私奉献。是刘文艳赞美、欣赏也是冀望的一种生活态度、人生体验、生命追求的高尚境界。这样,她的情感散文,就由情感上升为情操,由文学进而为哲学了。
因此,所谓“情感是散文的生命”中的“情感”,不是我们素常所言的情感,而是“情感家族”中的高层次、深层次、道德层次的情感,是“理性”极致化发展而情感化了的情感;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哲学而艺术”中的“哲思”的情感。
(责任编辑 苏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