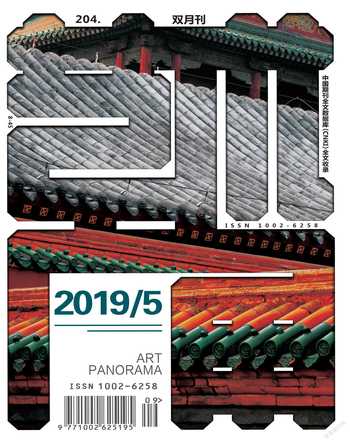从小说到电影:张恨水赢得市场何以可能
2019-09-10肇钒伊高桐
肇钒伊 高桐
张恨水是兴起于中国上世纪20年代文坛的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社会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他从上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进行文学创作,30年代奠定了他社会言情小说创作代表性作家的地位。30年代前后,是张恨水小说创作的鼎盛时期,影响甚广的代表作《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出自于此时,很多作品也被搬上银幕,受到市民热捧而风靡一时,形成了创造市场轰动效应的“张恨水现象”。这一现象在中国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的当下,因其作品频频被翻拍“触电”,在文学圈与影视圈仍持续性“发酵”。张恨水作品何以能赢得市场,其市场魅力何以经久不衰,回到铸就张恨水文学成就的文学现场,探讨那一时期张恨水创作状况,可发掘形成“张恨水现象”的原因所在。
一、雅文学、俗文学与张恨水作品的俗雅融合
文学历来有雅俗之分。高雅文学又称为“精英文学”,以承载较深远的内容与个性鲜明的审美艺术表现为特征,目的在于追求较高的思想与艺术价值。通俗文学以呈现消遣性、娱乐性的内容与形式为特征,目的在于遵循市场运作规律,满足受众消费需求。两种不同特征与目的指向的文学共存于文坛,相关雅与俗文学之间的分歧与关系转化并由此推动着文学发展的现象,也一直是文学史的重要现象。
30年代前后,中国文坛也出现了需要雅与俗文学互动的文学情态。在此之前中国雅与俗文学基本并行发展,以新文化运动为基础的精英文学,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立足于文坛,并成主流之势;而继承晚清通俗作品传统的旧派小说,以鸳鸯蝴蝶派为主力,在新文学的强大攻势下,向老派市民读者倾斜,虽处于弱势却完成了向市民通俗作品类型的转化。20年代末30年代初,雅与俗两种文学都意识到了自身的缺陷,开始向对方移動。“先是左翼文学因政治的需要,对‘五四’文学进行反思,认为自己没能掌握下层读者是绝大的缺失,一再地进行‘大众化’的讨论”[1],并在文学实践上做向市场靠拢的尝试,如“海派”小说与左翼电影;反过来,旧派通俗作家受新文学的感召,也意识到脱离社会发展,一味追随旧派市民审美趣味创作,也会丢失有新潮思想的读者,因而也开始注意对“雅”文学的汲取,在旧派通俗文学中努力融入文学的现代性新质。30年代前后,这些旧派通俗作品对于“雅”文学的汲取主要体现在“社会言情小说”中,而率先进行雅俗融合并取得成就的就是张恨水,他正是以大众广为认可的雅俗融合的文学创作(其创作拍成电影后更为大众熟知)为读者所接受,为市场所认可。
其时张恨水雅俗融合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表现。内容上,他坚持通俗文学的娱乐性、消闲性,尽量发掘所选题材的现代因素,表现与时代相关的思想;形式上,他坚持继承晚清的章回小说的体式,但又不断拓宽其功能,创造了现代性的章回小说体式。以他最为受众追捧的《金粉世家》为例,从1927年至1932年历时五年在《世界日报》连载,1941年拍成电影。作品讲述的是巨宦子弟金燕西与寒门女子冷清秋之间的爱恨情仇,围绕两位主人公相爱、结婚、离异的人生悲剧而展开,作者尽写豪门贵族的繁华绮丽、虚伪堕落。故事本身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其间人物地位的巨大反差、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家族内部的错综纠葛,都能不断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才子佳人的命运多舛、豪门贵族的盛衰沉浮,都是通俗作品获取市场效应的热门题材,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将其演绎得十分精彩。同时,《金粉世家》的“才子佳人”选择的是贵族之子与平民之女的婚恋,并通过平民之女冷清秋在面对自己婚恋悲剧命运时说出了新文化运动后女子才能说出的话:“我为尊重我自己的人格起见,我也不能再向他求妥协,成一个寄生虫。我自信凭我的能耐,还可以找碗饭吃,饿死我也愿意。”这种打破旧时代“门当户对”思想的男女主人公的设置与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表述,使张恨水的作品具有了时代性,无疑会赢得具有现代新思想意识的读者青睐。从作品形式上说,《金粉世家》虽都用旧小说的章回结构,但在注重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描写、半开放的结尾处理等艺术表现上,都见出张恨水对新文学的接受、对旧章回文学作品的改良与超越,这也是当时读者乐于接受的。
张恨水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交际明星》(1926)、《春明新史》(1924—1929)、《战地斜阳》(1929)、《斯人记》(1929)、《啼笑因缘》(1930)、《落霞孤鹜》(1930)、《美人恩》(1930)、《热血之花》(1932)、《满江红》(1933)等小说,其中多部作品在30年代就改编成家喻户晓的电影,张恨水可谓那一时期在平民百姓中最有影响的作家。虽然他的作品尚没有像新文学作家作品那样体现出超越时代的深刻意蕴,属于亦新亦旧的作品,但应充分认识与肯定他从通俗文学一域,以作品的大众化、平民化而推动文学由俗至雅、雅俗融合,进而拉动市场的文学努力。
二、都市、市民文化与张恨水作品的市民生活书写
市民文化不同于于都市中的高层位文化,它是由芸芸众生的市民体现的底层位文化,这一文化有着渗透于生活方方面面的传统承继,也因经济发展、政治风云、时代变迁而产生变化。市民文化扎根于民众,是世俗的大众文化。因此,书写市民文化的文学也容易为市民所接受。
30年代前后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局不稳,国民政府、各地军阀力量对峙纠葛,红色政权尚在襁褓之中,西方各种势力经晚清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继续从政治、经济上蚕食中国,同时西方先进思想经新文化运动开始为民众接受。体现于中国较大城市的市民文化,受四个方面文化的浸染与冲击:一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二是政治文化的冲击,三是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四是新文化思想的熏陶。它们共同作用于城市市民生活,构成着彼时市民文化的内容。张恨水作为侧重城市生活题材的通俗文学集大成者,眼睛始终紧盯世俗生活的文化变迁,其作品是三十年代前后那一时期的市民文化丰厚的承载者。
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以北洋军阀统治的20年代中期的北京为背景,1930年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时又应编辑要求添加了迎合上海市民审美需求的相关内容,是最能反映那一时期北京、上海上述四种文化特点的市民文化作品。就传统文化而言,小说与电影不仅描写了天桥唱大鼓等市民民间文化片断,也以关秀姑这一行侠仗义的女侠形象设置(这一形象是应编辑要求设计的),表现了市民对除暴安良的侠士出现的渴求,这是传统侠文化在市民文化中的反映。西洋文化对市民浸染最明显地体现在时髦女郎何丽娜身上,她的穿着用品洋派十足,斜插在头发上的西班牙扇面牌花、垂着长穗子的西班牙披巾、肉色的性感丝袜,浸人心肺的巴黎香水,用英语在夜总会高声叫香槟的做派,无不见出西方洋文化在中国城市的“登陆”。这种文化迅速在中国城市底层人们中蔓延,生于寒门的沈凤喜“吵着要家树办”几样东西——高跟皮鞋、纺绸围巾、手表、自来水笔、赤金戒指等。新文化思想也直接影响市民生活,它在小说中体现为官僚世家少爷樊家树爱情观的转变,摒弃门第观念、贞操观念,追求出身低微的在天桥唱大鼓的少女沈凤喜,见出新观念、新思想正潜移默化地进入市民生活,渗透于市民文化。而政治权力文化的作用在小说中则暴露出市民文化的负面效应,这表现为少女沈凤喜毁掉与樊家树的爱情,落入军阀刘德柱设置的陷阱中,小市民趋利而动的市井文化阴暗一面显露无疑。《啼笑因缘》写尽那一时期的市民文化,以书写与展映市民文化而“为广大市民读者所接受且能令人耳目一新正是它的高明处。”[2]因而,该小说连载于《新闻报》后,立即引起轰动,随即出版的单行本,创下市民读物畅销的记录,1932年,《啼笑因缘》被导演张石川拍成电影,在市民中的影响更为广泛。
张恨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1924年4月至1929年1月连载于《世界晚报》副刊,也是成功地展现30年代前后市民文化的作品。该小说围绕主人公杨杏园的社会交往与情感经历,编撰出七十多个“话柄”故事,涉及人物达两百余位,上有政客、军阀、遗老遗少、学界名流、世家弟子,下有听差、车夫、仆妇、乞丐、妓女、流氓无赖,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而且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戏园、电影院、舞厅、妓院、旅馆、大烟馆等市民往来的公共场所,“相当开阔地表现了北京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二十年代北京社会世相的长卷。”[3]如此作品为市民读者所接受,获得市场轰动效应是必然的。
三、文学、电影与张恨水的小说与电影互动
文学是古老的,电影是年轻的,一经问世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为电影提供肥沃的土壤,电影又为文学所借鉴。两者之缘在于本质的一致,都是对生活的艺术反映,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审美表现。但文学与电影又有不同,文学产生于尚无商业纷扰的人类早期,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它更多的用于文人雅士的抒情达意;电影则产生于商业发达的现代社会,它一出现就受到商业的裹挟,作为一种资本投入方式,它需要市场的回报。因而,在现代商业社会,当文学也需要市场的时候,文学与电影的互动就成为文学创作同时也是电影制作一个重要课题。
30年代前后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时期,经20年代电影的孕育、形成期,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故事片《歌女红牡丹》问世,随后便迎来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朝阳时期,产生了一批优秀故事片。这一时期为中国电影做出贡献的有两股力量,一是受新文学影响的左翼文学家与电影人;一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家与电影人。前者主张电影的思想性、社会教育功能,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左翼电影;后者主张电影的大众化、市场化,在20年代电影孕育时期为中国电影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中国电影起步于鸳鸯蝴蝶派。但到了30年代,左翼电影异军突起,通俗电影相对式微。然而,通俗电影在30年代与左翼电影相比渐弱的情况下,作为鸳鸯蝴蝶派一脉的张恨水却大红大紫。张恨水不是鸳鸯蝴蝶派早期的骨干作家,是在20年代末承继鸳鸯蝴蝶派创作风格的作家,并成为这一时期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小说爆红时期正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鼎盛时期,文学与电影的结缘自然使张恨水的小说很快触电,但最为重要的是,善于向一切有利大众接受艺术学习的张恨水,很快从电影中汲取了小说创作的灵感并运用于他小说的创作。取电影之有利于小说之处,增小说之精彩,再以精彩之小说,供电影之创作,张恨水成为这一时期小说与电影互动的成功实践者。
张恨水30年代前后的小说仅在当时十年内被拍成电影的就有《银河双星》(1931年,史东山执导)、《落霞孤鹜》(1932年,程步高执导)、《啼笑因缘》(1932年,张石川执导)、《黄金时代》(1934年,卜万苍执导)、《美人恩》(1935年,文逸民执导)、《秦淮世家》(1940年,张石川执导)、《金粉世家》(1941年,张石川执导)、《现代青年》(1941年,马徐维邦、李绮年执导)、《夜深沉》(1941年,张石川执导)等。此后至当下,其小说不断地被搬上银幕,其代表作《啼笑因缘》《金粉世家》更是有多种电影版本问世。时代不断变迁,受众代代更新,张恨水小说的改编电影却经久不衰,实在是文学与电影界互动不可多得的现象。究其原因,重要一点在于张恨水30年代前后小说创作善于从电影中汲取精华。张恨水的长孙张纪曾著《我所知道的張恨水》一书,书中有很多张恨水善于汲取电影精华的描述,其中一段写道:“1927年3月,北平中央影院放映《爱之花》,爷爷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去看了,看过之后连说‘不虚此行’。女演员克罗尔的表演,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克罗尔饰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她在荒岛遇到一个少年,回到家中,搬一把椅子,依傍父亲而坐,用手抱着双腿,含笑对父亲说了声‘I saw a man(我见到了一个男人)’,随即她把脸藏在膝盖上。爷爷说:‘看到此我心为之一动,自以为数年来作小说,专从白描上下手,未曾梦及此也。’”[4]电影的人物动作给予了张恨水小说创作如何进行白描的启示。白描本是张恨水长项,但他仍孜孜不倦向电影学习,张恨水小说善于汲取电影精华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在张恨水小说中能看到很多对电影的借鉴,如他曾承认:“小动作,也有人说以往并不多见,好像这也是我成功之一……电影的导演方面也有很多写小动作的地方,自然我也要随处留心,在写小说时,心有所得,自然要描写进去。”[5]张恨水说的电影“小动作“即是电影人物动作细节拍摄常用的“特写镜头“技法。还有电影的蒙太奇技巧、电影化的旁白处理等,都可在他的小说中找到借鉴、应用的痕迹。
自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文学艺术进入市场已成趋势,文学艺术像物质生产一样走向市场的生产属性突显出来。艺术“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6]而“生产”的普遍规律,重要一点即是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制约,消费需求促进生产,依市场消费需求改进的生产推进着市场消费,艺术生产亦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说,张恨水关注市场消费的文学努力,有其符合艺术生产规律的合理性,值得今天的文学界和影视界借鉴与继承。
注释:
[1][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0页、293页。
[3]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4]张纪:《我所知道的张恨水》,金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5]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