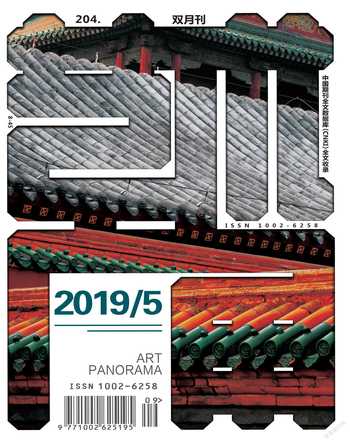回望与前瞻:中国科幻电影七十年
2019-09-10黄鸣奋
黄鸣奋
科幻电影诞生于19世纪末,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推动下迅速成为世界性现象。与此相应,对于科幻电影的发展,可以从国内外环境变迁及自身发展等角度予以回顾与总结。与其他类型片相比,科幻电影的主要价值不仅在于确立科技作为参考系的地位,而且在于解放观众关于科技的想象力,并引导他们对科技本身加以反思。在我国,科幻电影固然是技术意义上的舶来品,同时是本土生活的映射,甚至是综合国力的象征。我国科幻电影既激励公众关注科技进步的巨大影响,也促使他们全面省思科技本身作为双刃剑的作用,使之能够造福人类,而非相反。它伴随我国科技现代化走过了值得铭记的历程,也必然随着我国科技的腾飞、社会的发展创造新的辉煌。
一、直面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浪潮
据张衍考订,我国最早的科幻电影是新华影业公司1938年拍摄的《六十年后上海滩》。它讲述两个假死的人梦游未来的上海,见到会飞的汽车、自由变化家具的房间,以及可以调控天气的城市等未来科技。但片中的科幻元素只被作为逗乐的工具而已。[1]本片的构思显然受美国《五十年后之世界》(Just Imagine,1930)影响。除此之外,该公司还拍过《化身人猿》(1939)等作品,但数量很少。由于二战爆发,我国科幻电影的正常发展进程被打断,直到战后才得以恢复。新中国的成立、发展为科幻电影的繁荣创造了契机。我们可以将其历史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尝试期(1949—1977年)
从国际政治环境看,冷战(1947—1991)无形中建构了文化壁垒,阻碍了不同阵营的文化交流。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幻电影总体上不那么发达,苏联作为“老大哥”也只拍摄过寥寥几部科幻片,没有在我国产生多少实际影响。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作为红色中国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基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拍摄了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1948)、第一部故事片《桥》(1949)。195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立科教片组。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53年成立于上海,后更名为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1955)。它们成为中国科幻电影的摇篮。
从市场环境看,我国在解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前所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电影体制是事业型。在已知的范围内,大陆在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科幻电影只有一部,即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它改编自田汉同名话剧,由金山执导。与民国时期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六十年内上海滩》相比,突出了劳动者的情怀,洋溢着乐观主义情调。本片描写政府组织修水利,军民热情高涨。虽然有人(昆虫学家冯宇、青年作家胡锦堂)对进度表示怀疑,西方记者攻击这是“集中营”式劳动,但水库终于如期修好。20年后,这儿成为共产主义公社,实现气候控制,到处欢声笑语。人们接待故友重访,通过远程视频[2]欢送科学家前往火星。这部影片塑造了负责修建十三陵水库的民工和解放军的群像,以某代表团主要成员相隔20年的两次访问作为叙事对照,不仅肯定了上述工程所带来的生态效益,而且描绘了剧中人的成长,展示了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的社会理想。十三陵水库是1958年毛泽东主席提议修建的,确实是惠民工程。至于对1978年情况的想象,从今天看来颇为超前,像载人火星飞船、社员每人每天分配到一只大肥猪就是如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拍摄出多少科幻片。已知的仅有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小太阳》(1963),描写在太空轨道上建立反射镜以提高农作物产量。
(二)增长期(1978—2014年)
十一屆三中全会1978年召开,祖国大地迎来科学的春天,科幻电影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机遇,也出现过较大的波动。若加细分的话,这一时期包括三个阶段。
1.其兴也勃:1978—1992年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时期中国科幻电影春天的到来是以上海电影制片厂《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为标志的。它着重呈现了海外华人科学家的报国情怀。由于缺乏相应技术,其中的特效镜头只好土法上马。譬如,拍摄黄土倒入盛满清水的玻璃缸后散开的镜头,翻转画面,就成了电影结尾的核爆炸的“蘑菇云”。其后,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了《错位》(1986)。主人公是担任了局长的工程师,造出机器人替他开会,但无法忍受它介入其私生活,最终将其关闭。本片既包含了对技术官僚的讽刺,又展示了智能机器人的多重价值。络绎问世的还有珠江电影制片公司与香港天湖影业公司合拍的《异想天开》(1986),广西电影制片厂《男人的世界》(1987),长春电影制片厂《合成人》(1988),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霹雳贝贝》(1988)、《魔表》(1990)、《大气层消失》(1990)、《荧屏奇遇》(1991)等,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凶宅美人头》(1989)、《隐身博士》(1991)、《毒吻》(1992)等。
从国际环境看,我国这一阶段的科幻电影虽然不乏借鉴好莱坞之处,但主要是根据民族审美心理拍摄的,多数获得了观众的认可。美国《未来世界》(Futureworld,1976)等引进片在我国大陆电影院公映,带来了新鲜的审美经验和心理冲击。从市场反响看,此时期我国电影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到1992年才明显下挫。电影从总体上是卖方主导,观众对科幻片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不过,具体影片的票房价值仍有区别。譬如,《霹雳贝贝》符合儿童心理,比较火爆;《大气层消失》虽然挂在儿影厂的名下,但其内容过于成人化,在排片时处于不利的地位,观众数量自然有限。从媒体环境看,院线仍然是唯一渠道。不论家长带孩子去看电影,还是学校组织看电影,都是以儿童教育为背景的。尽管如此,由于缺乏分级制度,某些科幻电影未必适合低幼儿童观看,像《毒吻》就是如此。在该片中,环境污染使新生儿带毒。他问世伊始就毒死父母,后来又因接吻毒死了女孩。这类镜头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是值得反思的。
2.进入低谷:1993—2009年
从1993年到2009年,国内电影格局由于市场化、开放化和数字化而经历重大变革。上述变革对我国科幻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由于开放化的推进,大陆观众得以接触境外顶级科幻大片,国产科幻电影在他们心中黯然失色。二是由于市场化的推进,科幻电影的生产与制作再也不是电影制片厂的一统天下,发行机制也趋于多元化。贺岁片、古装片等迅速跟上潮流,科幻电影却有“找不到北”的感觉。三是由于数字化的推进,大陆电影业暴露出缺乏相关人才的弊端。正因为如此,我国科幻电影进入了低谷期。
在开放化方面,1994年11月12日,首部采用票房分账方式的引进大片《亡命天涯》在京、沪等六个城市公映。此后每年都有10部好莱坞或者中国香港影片通过上述方式引进。2003年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规定:香港公司拍摄的华语影片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可不受配额限制,作为进口影片在内地发行;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可视为国产影片在内地发行。2003年底,国家主管部门发布多个文件,鼓励境内国有、非国有单位(不含外资)与现有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合作成立电影制片公司或单独成立制片公司;允许外资参股与境内现有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合作成立电影制片公司。这为中外合拍科幻电影创造了条件。
在市场化方面,广播电影电视部在1993年颁发《关于当前深化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推动电影业加快转型;1997年推出“单片许可证”制度,允许电影制片厂之外的机构申请电影制作权;2004年首次将电影明确定义为一种产业。这些都是旨在繁荣电影的措施。尽管如此,我国电影业总体上仍在低位徘徊,科幻电影也进入了低谷期。清华大学王一鸣等曾对中美科幻电影数量加以比较,发现1995—2008年间中国大陆仅仅生产了一部科幻影片,而且是与美国合拍的,即时空隧道题材的动画电影《魔比斯环》(2006)。相比之下,美国同期出品了222部科幻影片。王一鸣对我国在科幻电影领域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进行了如下分析: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负面影响,传统思维习惯于寻根而非突破,应试教育妨碍前瞻性思考,大众科学素养有限,作品局限于堆砌科学知识、缺乏想象力。[3]上述统计数字所根据的是中国科学技术馆馆内课题组“基于展项的网络教育平台”申请书。至于这一申请书是如何统计出中美两国科幻电影数量的,不得而知。其实,在上述期间,美国所出品的科幻电影的不止222部(笔者已知的有240部)。中国大陆至少还拍摄了如下影片:《再生勇士》(1995)、《疯狂的兔子》(1997)、《力王中王》(2003)、《危险智能》(2003)、《北海怪兽》(2006)、《天生幻想狂》(2008)等,与香港合拍了《我的电脑会说话》(2004)、《长江七号》(2008)等。不过,若按年度平均的话,数量确实是太少了。
在数字化方面,我国电脑动画和数码特效艰难起步。例如,1997年北京电影学院建立了数字与艺术研究中心,上海电影制片厂1999年启动电脑特技制作工程。我国政府在2006年之后开始大力扶植网络动画。尽管如此,由于缺乏相應人才,国产科幻电影在制作水平上和国外大片的差距暴露无遗。例如,美国《终结者2:审判日》(Terminator 2:Judgment Day,1991)2000年在北京上映,精彩的视觉效果让观众赞不绝口。这是促使诸多影迷将兴奋点转移至国外科幻电影的重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3月,本土第一部电视电影才在电影频道推出。此时,更有潜力的数码媒体已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化而诞生。因此,我国科幻电影从总体上说未能随着电视媒体崛起搭上顺风车。
3.逐渐复苏:2009—2014年
2009年之后,我国科幻电影逐渐适应了市场化、开放化、数字化的大环境。业界对它的兴趣越来越大,投资规模越来越可观。
在开放化方面,我国业界认真学习国外同行的经验。《开心超人》(2013)借鉴了美国“超人”系列的理念。中外合拍的《超验骇客》(2014)、《像素大战》(2015)等影片都具备相当高的制作水平。与此同时,某些影片在彰显民族特色上下功夫,如《钢琴木马》(2014)等。本土因素和全球因素逐渐变得密不可分,像我国“太空熊猫”系列就是如此。它们以国宝级动物为原型,创意又远绍美国的《功夫熊猫》(2008)。
在市场化方面,类型片之间的界限模糊。譬如,《铠甲勇士·帝皇侠》(2010)、《梦回金沙城》(2010)等都是科幻和奇幻的混搭。我国《跨时空救兵》(2012)、《冰封:重生之门》(2014)是古装片和科幻片的混搭。“赛尔号”系列是魔幻和科幻的混搭。与此同时,高校师生成为实验短片创作的生力军,给商品大潮所席卷的科幻电影领域带来一股清流。
在数字化方面,本时期科幻短片实现了从DV、微电影再到网络大电影的华丽转身。相比之下,DV主要是从拍摄与制作设备定义的,微电影则是从产品本身定义的。后者的特点是微时(10-30分钟)、微周期(7-15天较常见)、微投资(每部万元左右),如台湾《NK战士》(2013)、大陆《麻辣拍档》(2014)等。后者借鉴了美国“变形金刚”,号称是“自行车金刚”,拍摄成本很低。2014年,爱奇艺首次提出“网络大电影”的概念与标准,引领了其后的热潮。点播逐渐成为电影业的重要收入来源。
(三)崛起期(2015年至今)
2015年以来,我国科幻电影迎来了崛起期。经过若干年的蓄势,终于在2019年春节作为贺岁片取得重大突破,《流浪地球》与《疯狂的外星人》成为标志性成果。主要原因有如下三条。一是就国际环境而言,我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向海外传播取得不俗成绩,鼓舞了文艺界的信心。刘慈欣长篇科幻小说《三体》2015年获得雨果奖,激发了公众对科幻文艺的兴趣。由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主办的全球华语科幻电影星云奖(2016)起到了促进作用。二是就市场环境而言,我国电影票房年收入在1999年跌至8.1亿的低点,随后开始回升,到2014年已经回升到296.4亿元。2015年猛增到440.7亿元,其后三年屡创新高,从2016年的457亿元、2017年的55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609.76亿元。就科幻电影而言,2016年上映的《美人鱼》(内地与香港联合制片)在内地收获票房33.92亿元,超越《捉妖记》,成为新晋内地票房冠军。经过长时间的蓄势,我国大陆科幻电影在2019年春节登上了新高度。以票房收入计,春节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达到22.02亿元,《流浪地球》则创造了46.55亿元的纪录。三是就媒体环境而言,网络大电影显示出可观的效益,基于融媒体的发展策略给科幻电影带来了新的机遇。据笔者统计,在已知的范围内,我国科幻长片产量在2016年首次突破100部,在2017年达到创纪录的138部。它们当中主要是网络大电影,爱奇艺、优酷等是它们的主要传播平台。由于国家主管部门提高对网络大电影的要求,2018年以来科幻长片总数明显下降,但质量有所提高。从创意的角度看,《流浪地球》至少有三条成功经验值得注意:一是在危机叙事中由中国人提出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解决方案;二是在市场定位中抓住过年、回家的要素打贺岁片之牌;三是利用数字技术精心制作,展现了与科幻语境相称的奇观。
在1997年之前,香港电影史是在英国殖民格局下书写的。至迟在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就已经拍出具有某种科幻内容的电影,如《大冬瓜》(1958)、《两傻大闹太空》(1959)等。欧美科幻电影的成功给香港业界人士以激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模仿性比较明显的《中国超人》(1975)、《猩猩王》(1977),它们是受美国《超人》(Superman,1941)、《金刚》(King Kong,1933)等影响而拍摄的。其后,某些电影渐渐将“港味”(以俗为雅)作为自己的特色。其中,“卫斯理”系列影片比较著名。香港回归之后,科幻片仍是其电影的重要分支,如《电子格斗战士》(1998)、《数码英雄》(1999)、《特警新人类2》(2000)、《DNA复制人》(2002)、《追击8月15》(2004)、《童梦奇缘》(2005),还有与内地共同制作的《长江七号》(2008)、《机器侠》(2009)等。2010年以来,香港就科幻影片数量增速而言明显不如内地,比较知名的影片有《全城戒备》(2010)等。与内地合拍的《美人鱼》(2016)是比较成功的生态科幻片,受到观众的好评。
祖国宝岛台湾的科幻电影起步于20世纪中叶。早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就出现了“神龙侠三部曲”,包括《神龙飞侠》(1968)、《月光大侠》(1968)、《飞天怪侠》(1968)。其定位是假面特摄片,具备科幻、超级英雄、侠文化等多种要素。70年代,我国台湾与日本电影公司合拍了电子人题材的《闪电骑士V3》(1975)、《闪电骑士大战地狱军团》(1976)等;独立拍摄了外星人题材的《火星人》(1976)、《关公大战外星人》(1976)等。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台湾科幻电影的题材扩大到时间旅行、生态灾难、变种人、类智人、交互界面、外星来客等,已知的相关影片有近20部。台湾的电影经常出现鬼魂的形象,即使科幻片也是如此。例如,在《诡丝》(2006)中,作为超自然现象的鬼魂和作为科学研究的反重力探索者通过连接两个能量场的晶状体(即“诡丝”)结合起来,鬼魂可以通过它来取活人的性命,这是此片产生恐怖效果的主要原因。不过,此片并未因此而趋于怪力乱神,因为它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就是对生与死的思考,主角叶起东在片末总结出“好好过人生”,剧情由此实现了“以诡为正”的升华。
二、科幻电影促进对科技发展的全面反思
顾名思义,科幻电影以科技为自身的参照系。不过,这里所说的“科技”并不单指科学原理或技术知识,而是指诸多要素构成的科技系统。后者包括由科技主体、科技对象、科技中介构成的科技社会层面,由科技手段、科技内容和科技本体构成的科技产品层面,还有由科技方式、科技环境和科技机制构成的科技运营层面。科幻电影不仅将上述系统作为坐标系以设定世界、塑造人物、构想情节,而且对科技系统本身的定位、价值、走向加以反思。从已知作品看,我国科幻电影做出了三大方面的贡献。
(一)展现科技社会风云
科技社会在广义上是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的社会,在狭义上是以科技人员为主角的社会。我国科幻电影将前者作为背景,将后者作为舞台,展现了令人回肠荡气的风云变换。比如,塑造科技主体的形象。在我国,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有过大起大落的变化。受商业化大潮的影响,科技人员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分化。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国内外科技界处于动态交流中,带来了各种机遇和挑战。上述社会现实都在科幻电影中曲折地得到反映。因此,我们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中看到了知识分子和劳动大军之间的距离,在《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中看到了科学家拳拳报国之心,在《来历不明》(2013)中看到科学爱好者的痴迷与执著,在《侵入脑神经》(2013)中看到了专业技术人员的良心,在《时空大魔王》(2018)中看到了发明家的正义感。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科技工作者由于主客观原因陷入窘境,以及他们摆脱上述窘境的努力,相关影片有《隐身博士》(1991)、《危险智能》(2003)、《蝶变计划》(2018)等。再如揭示科技对象的境况。科技主体以观察作为研发的基础,以实验作为探索的方法,以服务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由此建立了与观察对象、实验对象和服务对象的联系。我国科幻电影从创新的角度为观察对象定位,如描写外星人对地球人的观察,见于《火星宝贝之火星没事》(2009)、《不可思异》(2015)、《超能外星女友》(2016)等;思考实验对象所应享有的合法权利,见于《超能特工学院》(2017)、《暮色之战:异能部队》(2017)、《请叫我救世主》(2017)、《人工少女》(2018)等;揭示服务对象左右科技主体的作用,见于《智能天使》(2017)、《智能危姬》(2017)等。科幻电影还关注科技中介的功能。这些中介主要是指相关机构和个人。在《超能嗨战队》(2016)中,若没有杂货店老板开设的超能力研究所,四位屌丝就难以实现超级英雄的转变。在《功夫机器侠之南拳真豪杰》(2017)中,若没有位于中国西部要塞的机器人维修中心,人类就将被外星入侵者灭种。我国科幻电影不仅强调科技中介的重要性,而且揭示了相关的竞争、假冒、诱骗等现象,见于《逆时营救》(2017)、《美少女危机》(2017)、《我儿子去了外星球》(2018)、《第六超能力》(2018)等。
(二)畅想科技产品演化
科技之所以具備改造世界的力量,是因为它既提供了比人类身体更为强大而灵活的手段,又蕴含了真理性、规范性和创造性的内容,同时还因为它将上述手段和内容结合起来,建构了具备组织功能的科技本体。科幻电影之所以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此密切相关。就此而言,我国科幻电影的某些取向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设想新颖科技手段,如《小太阳》(1952)中的太空反射镜,《探魔导师》(2016)中智能型的潘多拉魔盒,《变脸英雄》(2017)中的变脸App,《双子起源》(2017)中的脑波同频器,《异能男友》(2018)中的VR异能头盔,等等。不过,和国外优秀作品相比,我国科幻电影在这方面的差距比较明显。有时编导想不出新奇的科技手段,只好从神话、玄幻或魔幻中寻求借鉴。二是构思趣味科学内容。科幻电影毕竟是娱乐产品,并非科普宣传,因此,不能不注重趣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像“天才J”系列电影(2018,已出品三部)所提出的偶然公式和命运公式,只能说是一种假说(甚至是伪科学),但由此所演绎出来的故事却引人入胜。至于拿科技范畴来开涮,像动画片《圣蛋传奇之猪公的骰子》(2018)描述以长老之屁的风力抵销黑洞的引力,只能算是不足称道的恶搞。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都很重视问题意识,后结构主义者强调“可写之文”。由此看来,科幻能提出值得深思的问题(或引导观众关注这类问题),是难能可贵的。像《男人的世界》(1987)所说的重男轻女就是如此。三是瞻望科技本体未来。在科幻视野中,科技本体是科技所生产出的生命体,如克隆人、机器人、生化人、类智人等,既属于“它们”(人造之人),又属于“他们”(具备自我意识的他者),同时还可能属于“我们”(进入社会生活,作为代理,甚至实现通婚)。就此而言,以机器人为题材的《错位》(1986)在当时是相当前卫的。近年来,由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这类科幻影片在我国大量出现,但在构思上不乏雷同之处(尤其是写人机恋的作品)。
(三)促进良性科技运营
科技在形而上层面体现为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在形而下层面体现为通过实验把握世界的方法。它既为社会创造了以求真务实为旨归的氛围,同时又有赖于社会为它的良性发展形成健康的环境。它以源源不断的成果引领社会发展,同时又需要预防走火入魔的机制。我国科幻电影因此在如下意义上找到了用武之地。一是探索科技方式的功效。科技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特有方式,贵在深入调查研究,对事物及其相互联系进行量化分析、实验检测和系统整合。例如,我国《伪梦迷情》(2018)描写主角柯昊明因大脑被摩根集团控制而颠倒现实与梦境。其恋人艾琳邀集小伙伴,根据梦境不同于现实之处在于零重力的科学原理制定方案,通过身体跌落实验使柯昊明清醒过来。二是瞩目科技环境的变迁。身处在可持续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环保已经成为我国科幻电影的重要题材。例如,《大气层消失》(1990)讲述剧毒品在运输过程发生泄漏、主角的爱犬为救灾而牺牲自己的故事,提醒人们:“这个地球上的天空应当是蓝的,这个地球上的水应当是清的,这个地球上的草应当是绿的。”三是反思科技机制的效能。科技界需要有保证自身正常运行的负反馈,需要强调社会责任(尤其是对人类未来负责),正如《神奇》(2013)所展示的。该片中的软件高手冰山发现公司推出的游戏有漏洞,可能危及玩家的神经系统,便向CEO报告,坚持让公众知道真相,虽然遭到解雇而不悔。
上述科技系统的三个层面在具体的影片中彼此联系,构成了科幻电影从整体上区别于其他类型片的依据,体现出特有的社会价值。
三、伴随科技革命发展开创未来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科幻电影已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尽管如此,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差距仍然是明显的。这种差距不只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科幻大片而言,而且是相对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而言。从理论上说,科幻电影与现实科技是水涨船高的关系。现实科技越发达,科幻电影的想象应当越超前。否则的话,科幻电影就丧失了引领科技发展、反思科技效用的功能。因此,科技电影必须跟上科技前进的步伐。
(一)瞩目科技腾飞的社会影响
电影刚传入时,我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队伍。如今,我国在科技人力资源数量方面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根据科技部的统计,2016年达到8327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687万人,远超美国同等学历水平科学家工程师的数量。研发人力规模居全球首位,投入强度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减小。[4]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人员在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所追求的宏大理想未能在现有科幻电影中得到应有反映,这是令人遗憾的。这方面真的大有可为。
科技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将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自己的对象,不论是观察对象、实验对象或服务对象。在我国,依靠上至“巡天遥看一千河”的高分卫星、下至无微不察的城市监控摄像系统,科技主体已经将几乎所有国民与来客都变成刷脸和大数据分析的对象;从医院开出的一张张检测单,到商家建立的一个个用户模型,科技主体乐于拿人的身体进行各种实验,反过来,大众几乎无人可以摆脱当小白鼠的命运;从主动推送到按需点播,科技主体依靠提供社会服务而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人气就是他们的财富。不论是互联网用户数量或移动通信用户数量,我国都已经排名世界第一,各种相关的通信商、内容商、技术商因此建立了庞大的市场。在科幻的视野中,随着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全景监视会达到什么样的细密程度?作为其反拨的脱网化会有什么样的举措?人类拿动物所做的各种实验会造就具有自我意识的类智人吗?具有比人类更发达智力的外星生命或人造生命会将地球人当成他们的实验对象吗?人类的智能是否会因为接受高科技所提供的日益贴身而贴心的服务而退化?服务者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向统治者转化?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为科幻电影驰骋想象提供了空间。
(二)构想科技发明的尖端产品
在实践中,我国科技发明已经随着创新创业意识的增强而迅速增长。这一点在专利领域得到了某种表现。自1978年筹建实施专利制度以来,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迅速增长,目前已经连续8年居世界首位。到2018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共计160.2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1.5件。[5]科幻电影编导或许可以从如此之多的专利中获得某种关于未来科技手段的启示,构思出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新作品来。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本支柱,代表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高峰,对人类思维和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留下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譬如,怎样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的定律统一起来,等等。中國科学家正在为此贡献自己的智慧。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岳良提出了“引力的量子场论”。还有一些理论爱好者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思考世界的统一性,甚至有惊人之语,如王江火宣布自己创立的“统一信息论彻底推翻了现代科学理论体系”,并在天涯社区邀辩。[6]这类基础理论问题的奥义并非常人所能理解,相关争辩却可以成为科幻电影创意的契机。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机器人大国。201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目标是经过五年的努力,形成较为完善的机器人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在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与特种机器人领域的研发和生产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虽然“机器人密度”还不高,但工业机器人销量已居全球第一,总保有量迅速增长;虽然我国还没有像沙特阿拉伯那样授予机器人公民权,却已经在2018年2月4日将世界首位机器人公民索菲娅请到央视《对话》节目作客。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下述战略目标:“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取得明显成效,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经济强国奠定重要基础。”这份文件提醒人们:“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等问题,将对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挑战,加强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7]由此看来,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很可能是我国科幻电影的重要题材。
(三)展望科技创新的运营前景
在我国,经历了五四运动以来一系列社会变革,“赛先生”已经和“德先生”一样确立了自己的声望。从总体上说,科技已经无须为自己进行合法性论证。反过来,它已经成为证明其他对象、目标或规划合法性的最重要的依据。“科学”不只是名词,而且是寓指合理性(甚至是真理性)的形容词;“技术”则作为现代化标志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各种项目的实施提供可行性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已经从传统意义上伦理主导型社会转变到现代意义上的科技主导型社會。尽管如此,科技本身包含的各种矛盾已经渐渐暴露出来。例如,科技难以解决属于伦理领域的道德修养、价值判断、社会立场、个人志向等问题;科技工作者并不是单纯为探索真理和真相而努力,当他们主要是为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行动起来的时候,伪造数据、骗取经费、沽名钓誉等丑恶现象便屡禁不绝;科技固然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创造了许多福祉,但也因其滥用、误用带来了许多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科幻”等同于“科普”,而应当强调批判性眼光的价值。
我国航天事业自1956年创建以来,在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定位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目前正在加快推进航天强国建设。2017年成功完成17次宇航发射。首颗高轨道高通量通信卫星实践十三号、首颗大型硬X射线空间探测卫星“慧眼”卫星成功发射,北斗导航全球卫星系统组网首发双星成功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完成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墨子号”量子卫星成功实现预定科学目标,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发现反常电子信号。[8]2018年18次航天发射全胜。按规划,我国今后将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宇航科技如此辉煌的成就、如此宏伟的规划,为我国科幻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恢宏的景观。目前这方面的作品还很少,理应引起关注。
科技进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40.8岁增加到2010年的74.92岁[9];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为3645.2亿元,2018年达到900309.5亿元[10];人均国民收入1987年仅为320美元,2010年达到4240美元,跨越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临界值,开始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11]2018年约为9900美元。上述成绩的取得,和科技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不难想象,未来信息科技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和知识更新,生物科技将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能源科技将更有效地化解能源和环境问题,宇航科技将拓展开发与利用太空资源的新可能。尽管如此,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我们不能不正视与科技相关的危机,如生态赤字的扩大、核战争的威胁、人类身体素质的下降、病毒变种速度的增加,等等。正因为如此,“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是科幻电影永恒的主题。
从总体看来,科幻电影近年来在我国大陆进入了相对高速的发展期,选材范围扩大,创意水平提高,编剧技巧优化,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尽管如此,和美国这样的“巨无霸”相比,我国在科幻电影领域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不论就影片的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是如此。要想使我国科技电影更上一层楼,可以从不同角度寻找途径。例如,就电影的产业属性而言,它需要更大的资金投入;就电影的艺术属性而言,它需要在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就电影的社会价值而言,它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既弘扬爱国主义,又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等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为了在新时代拍摄出更多具备中国特色、受到世界观众欢迎的科幻电影,我们要加强科技工作者与艺术工作者、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之间的对话,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中国科幻电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成就辉煌,展望未来,还有待拓展前路,走向更辽阔的远方。
注释:
[1]张衍:《中国早期科幻小说与电影中的科学呈现》,《文化学刊》,2018年第1期。
[2]“视频”一词在上世纪50年代即已出现。如王大伦《关于超外差式接收机(待续)》一文(载于《物理通报》,1956年12期),就使用了它。
[3]王一鸣、黄雯、曾国屏:《中美科幻电影数量比较及对我国科幻电影发展的几点思考》,《科普研究》,2011年第1期。
[4]科技部:《2016年我国科技人员资源发展状况分析》,http://www.most.gov.cn/kjtj/201803/P020180305380063904804.pdf。
[5]http://www.cnipa.gov.cn/twzb/gjzscqj2018nzygztjsjjygqkxwfbk/index.htm。
[6]王陈江火:《王江火向全世界正式宣布:统一信息论彻底推翻了现代科学理论体系》(2014年2月20日),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023831-1.shtml。
[7]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8]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2月28日发布,http://www.stats.gov.cn/tjzs/tjcb/dysj/201801/t20180105-1570147.htm/。
[9]岁磊:《寿命延长、二胎政策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2017年11月29日),http://www.stats.gov.cn/tjzs/tjsj/tjcb/dysj/201801/t20180105_1570147.html。
[10]国家统计局公布。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GDP。
[11]刘伟、蔡志洲:《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及展望》,《经济纵横》,2014年第1期。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