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猪形象在国产动画中的转型
2019-09-10董丽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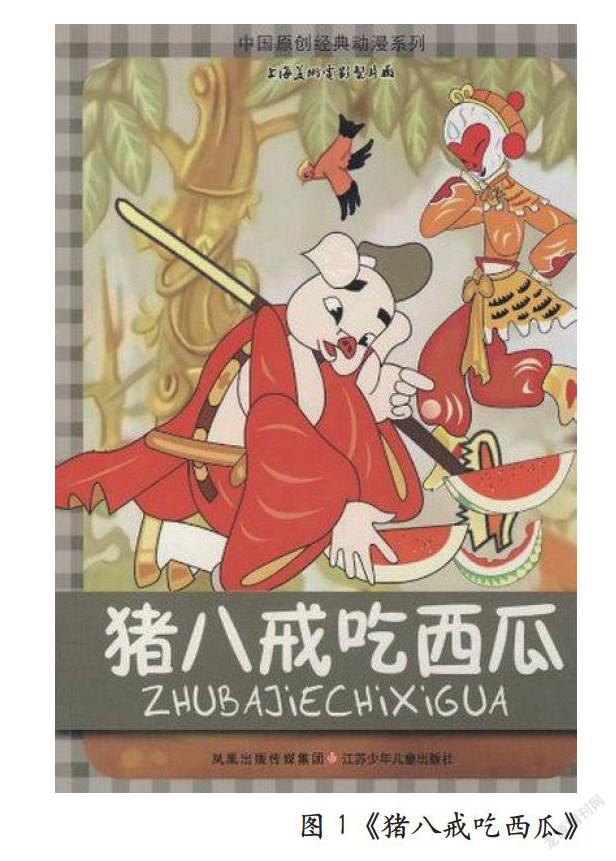





摘 要:猪形象在人类的精神流变与文化转型过程中有着典型的意义。猪作为动画中的主流角色,被赋予的文化品性一直发生着变化。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猪”形象由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逐渐转向孩童化塑造、人性化表达,肯定了凡俗的日常生活。
关键词:猪形象;国产动画;转型
猪,排在十二生肖里的最末位,但在动画演艺圈里,它的戏份可不少,无论国内国外,无论龙套主角,猪的出镜率可以算是名列前茅了。2015年登陆央视少儿频道的英国动画片《小猪佩奇》更是让猪一跃成为国际巨星。“数据显示,作为英国动画片主角的小猪佩奇,去年在全球实现了12亿美元的收入,强大吸金能力令人惊诧。但更引人深思的是,一只小豬为何打动了那么多不太年轻的成年人?”[1]陈雪柠侧重于营销策略手段和社交需求分析小猪佩奇的风靡;李昔则以最童话为线索,分析其主体构造、故事模式、造型颜色[2]。但均缺乏一种“历史化”的视野。小猪佩奇虽是英国动画,但它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说明它满足了这一代人的主观认同和现实想象。而在现代中国人所熟识的猪文化中,它往往被赋予好吃懒做、肥头蠢脑、胆小好色的贬义色彩。其中的转变,透射着一定的社会原因和大众审美文化的流变。《小猪佩奇》引发笔者思考,并借以分析国产动画中不同时期猪形象的呈现方式,以此说明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动画赋予猪人格化的改造,使其成为一定群体的符号象征和文化表征,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特征和文化内涵。
一、政治教化
中国动画创作从一开始就是“文以载道”的教化工具。万籁鸣曾说:“动画片一在中国出现,题材上就与西方的分道扬镳了。在苦难的中国,我们没有时间开玩笑。要让同胞觉醒起来,我们为了明确的教化作用而强调鲜明的创意,在某种程度上忽略应有的含蓄、幽默与娱乐性。”[3]“时代烙印也打在了动画的身上——带有政治隐喻倾向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定为体现动画教化功能的某种思维模式。”[4]中国动画在无法玩笑的历史境遇中成为与现实时政紧密配合的教化工具。
1958年的《猪八戒吃西瓜》(如图1)沿用了1941年《铁扇公主》(如图2)里猪八戒的形象。猪八戒造型很有象征意味。敞胸露乳的长袍活像一个因辛苦劳作汗流浃背的农民形象,束腰绳仿佛是可以随时拿下来擦汗的毛巾,再看猪八戒的九齿钉耙,也会让人想起锄地种菜。猪八戒的吃相更是狼吞虎咽、不嚼不品、干净利索。这种行为不仅是它动物本能属性(本我)的展现,同时映射出当时的社会普遍性,实际上是终日劳作而忍饥挨饿的农民形象。猪八戒在大树下一躺就能打鼾,如果放在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层面来看,也可视作为成日劳作而视睡若渴的农民原型。在这里,猪形象寄予了许多农民的因素,而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表现当时社会中最主要的群体,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同时,猪八戒对象征革命的代表孙悟空所表现出来的顺从也是政治期望的外化。对于猪八戒因自己吃完了一个瓜而得到了教训也是宣扬集体主义精神。
在1988年的动画短片《孤独的小猪》中,小刺猬、小羊、小兔子遇到困难想请小猪帮忙,可小猪却只想呆在自己的房子里,关上门窗拒绝任何人,“我不帮助别人,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忙”描绘了一只自我封闭的小猪。1998年《聪明的笨小猪》描绘的是《孤独的小猪》里小猪改过自新后与其他小动物在一起的快乐趣事。这两部作品的时间节点都是处于改革开放的周年纪念,很难不让人联想这是宣传政策的积极影响。
在特殊历史时期,政治借以动画从中鼓舞民族的凝聚力和宣扬政策,并借助猪形象的特点教化人民群众,承载起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责任。当然,猪形象除了承担政治宣传功能外,还是进行品德教育的载体。在动画中规范角色的言行,让观众从影片中得到教益是动画创作一直以来的标准。而猪的动物属性——被圈养,成为饭来张口的动物,使其成为很好的品德教育文本。
《猪八戒吃西瓜》中的猪八戒,因自己又懒又馋只顾自己饥渴独食一个大西瓜,甚至都没有给师傅留一块儿,因而受到悟空的戏耍,出了不少洋相,以猪八戒受到的训诫来教育人们不要像猪一样好吃懒做。1983年《小八戒》中讲述的是猪八戒执意要将孙儿小八戒捡来的钱罐占为己有,依旧在猪八戒的出丑中受到教训。这个故事的主题是教育小朋友拾金不昧,切勿好逸恶劳。《孤独的小猪》中,小猪因为自己的自私拒绝帮助其他的小动物后,在自己遇到危险时,也没有小动物来帮助他,甚至自己的家人都要抛弃自己。在小猪第一次恳求家里的大树帮帮自己后,大树嘲讽地说:“你不是不要被人帮忙的吗?”并没有一丝留恋而且头也不回地走了。最后在猪的悔改中得救,影片的告诫意图显而易见。动画中用这种奚落嘲讽的教育方式显然有明显压迫和禁锢的嫌疑,并且用强者的话语来规范其他生命的品性与精神世界。如1993年《十二生肖》中十二种动物在每消灭一个妖怪时都会牺牲一个动物。猪特辑中,大耳猪为了消灭能下雪冰冻周围一切的妖怪冷血公主,为拯救人类而自愿牺牲,它用自己的身体堵住冰窟窿变成了冰雕。动画想表达朴实刚毅的品性、乐于助人的美德及自我奉献的精神,同时动画所渲染的每一次奉献都要有牺牲的悲惨气氛,造成许多孩童的心理阴影。猪形象也成为了宣教的模板。
二、教化的问题与困境
教化作为动画的一种特殊功能,在国产动画中变成了它的主要功能,过于强调教化而忽视其趣味性和创新性,使寓教于乐陷入“欲教难乐”的境地。“那些说教式的道德训诫也‘因道损文’,某种程度上损害了童话故事的美学意味,它更像一颗糖衣药丸,剥去故事的糖衣,里面是苦涩的训诫药丸,被用来治疗孩子的各种缺点毛病。”[5]在动画教育叙事中,常有一种“强者”的声音来评定事情的对错,压迫和规范着单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教导观众,无视观众的精神需求。如《猪八戒吃西瓜》中猪八戒和孙悟空一同去找食物的途中,猪八戒累得停下休息,孙悟空却拧着他的猪鼻子催促他快走。《小八戒》中孙悟空对猪八戒的训诫:“有过不改,还耍无赖。你这呆子,枉去西天取经一场,死性不改,还要教坏儿孙。”《孤独的小猪》中小猪拒绝帮助其他小动物,结果自己的房子和篱笆纷纷抛弃了小猪并说:“太不像话了!”使其差点被狼吃掉,这些猪形象既没有话语权力又被控制。动画为了说教而说教,最终促使传统中国动画作品表现为一种自言自语的模式。“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这种理性精神无疑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却造成了文艺表现上的某种‘失语’,把无限的创意和生动的情感掩盖了。”[6]因此这种不平等视角下的自说自话,在弘扬自由、个性化的现代精神面前,人们越来越敬而远之。
另一方面,圆圆胖胖的猪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挤压中被塑造为扁平单一的形象,缺乏复杂性,容易被概念化。大多只是在描述简单的猪的生理属性,一味强调教化又只着眼于猪形象表层,猪形象表达的无限可能性被箍上了一条沉重的枷锁,无法走近大众,观众也产生视觉审美疲劳,缺乏情趣兴味。“国产动画角色的性格长期以来扁平化、脸谱化、单一化和概念化,缺乏立体、丰满的个性特征,很多时候是用抽象教条的说教来取代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角色形象苍白无力。创造出既有鲜明、生动、独特的个性,又能体现社会生活本质与规律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成为了中国动画吸引观众的重点。”[7]其实当你对一部动画有所感触的时候,你就被不自觉地“教化”了,所以与其做得有“意义”,不如做得有意思。
三、孩童化塑造与人性化表达
在全球化语境下,国外动画挟带着异文化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艺术趣味如潮水般涌入国内,现代人对外国流行文化的接受和欣赏,使其在享受物质条件的同时,审美趣味也变得更加多元。人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愉悦身心,更渴望看到时代文化、社会现象、流行元素的渗透,在此影响下,猪形象已悄然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具体而言,猪形象的转型有外在和内在两个特征。
(一)外在为孩童化塑造,即猪形象外貌特征趋向幼儿。过去是大腹便便、肥头大耳,但经过如今人为的“滤镜磨皮”看起来像圆圆嫩嫩、憨厚可爱的儿童。例如《麦兜》系列电影着力表现的人物麦兜(如图3),是一只粉色的没有脖子没有腰的小猪,豆圆的小眼睛和大大的鼻子,右眼上还有块深色胎记,总是爱歪戴一顶棒球帽,外貌并没有设计得非常俊俏,但是极乖巧可人,一上映便成为国民萌物。《猪猪侠》系列电影中的猪猪侠(如图4)有着一双水灵的大眼睛,总是一副过度自信的表情,头戴改良过的中式“虎头帽”,身穿红色制服紧身衣。这已经成为猪猪侠的经典形象,也是无数的孩子喜爱的英雄。可是猪猪侠作为英雄形象并没有设计夸张的肌肉、高大的形象、崇高的性格,而更像身边调皮的小朋友。猪小屁(如图5)是《人人爱我猪小屁》2017年原创视频中走出来的动画角色,其软萌憨逗的形象使猪小屁的原创表情包火遍表情吧、微博等网络各大平台。这些猪形象相比过去更稚气化,白白胖胖、饱含童真。
猪猪侠是始创于2005年的3D动画。其诞生到现在,随着大众审美的变化,他的造型也相对发生了微调(如图6),不难看出猪猪侠一路走来,除了在保留了一些猪的动物特征如猪鼻子外形体特征之外,皆愈来愈像个人,准确地说像儿童。近年来以猪为主角的动画形象皆有孩童化倾向。笔者认为这种倾向蕴含着成年人的心理补偿。《小王子》里有一句话:“所有成年人曾经都是个孩子,只是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我们长大后在残酷的社会中慢慢忘掉过去简单快乐的东西,变得社会化是现实生存的必要,但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渴望快乐和自由单纯的小孩。猪形象的孩童化是现代人们满足了物质需求后,对“本真”的渴望,是成人内心世界情感表达的外化。
图6《猪猪侠》电视电影系列2006-2017猪猪侠的变化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内在为人性化表达,即契合当下社会特征和现代人的品性,打动观众并得到受众的高度情感认同。
首先是不完美的性格建构。麦兜是一只平庸的小猪,既不聪明,也不富裕。《麦兜故事》中他的成绩单是差“一点”得“A”的“H”;怕一擦就缺一个角而舍不得用的同学送的雪白的橡皮;会固执地点餐“没有粗面,就来鱼丸吧。没有鱼丸,就来粗面吧”就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处于更年期的猪妈妈麦太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单亲妈妈,不得不尝试着各种工作,甚至在《麦兜响当当》中其他小朋友在暑假四处游玩时,妈妈带着麦兜北上武汉做生意。“跟大部分妈妈一样,麦太拼了老命都是为了她身边这个……麦兜”。麦兜虽然是主角,但是并没有强大的主角光环。作为一头笨笨又傻气的小猪,他成长的过程中也有许多失败、迷茫,如同现实生活中平凡普通的每一个人。在动画中,一改以往的刻板叙事,借以调侃幽默的表达来消解主题的严肃,既达到娱乐功能又引发观众的认同。
其次是投射现实的空间建构。这里是指创作者将当代人的生存环境或状态赋予了动画角色。如《麦兜响当当》中,麦兜每个周末都被麦太安排在图画班、游泳班、英文班等各类补习班,被寄托着笨鸟先飞的期望。这里借麦兜的成长引发了许多观众成长的回忆。《猪猪侠之英雄猪少年》中,展示了一系列代表现代文明的高科技,对应当下社会的科技未来感。《人人爱我猪小屁》中,猪小屁直接生活在现实世界,居住在大美现代化的房子里,直接表现当下生活,与当下流行特征结合,描绘身边的小故事使观者成功移情,从而产生审美愉悦。
最后是简单的快乐建构。麦兜最大的梦想就是去“坐落于印度洋的世外桃源,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白……”的马尔代夫;麦兜最大的希望是尝尝火鸡的滋味;麦兜最大的志愿就是当一个天天吃火锅的校长。理想有乘风破浪之远大,也有吃火锅那么朴素。麦兜没有高高在上的理想口号,只有对平凡生活简单真实的满足感。并且这个满足不是因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是要完美的外形或者变聪明,只想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时光。虽然最后他去的并不是真正的马尔代夫,那也是他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在麦兜把火鸡提回家的路上,也是他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麦兜的志愿被老师调侃,却是真正的人生的真谛。这也体现了在新世纪的社会变革中,大众文化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图景被简单的“快乐经济”所代替。追求快乐成为当代大众文化与娱乐工业的一种共谋[8]。
在注重人文精神的今天,猪形象的现代化转型逐渐摆脱了性格扁平化和固定化的传统塑造,追求贴近人和动物共同的表征,着力探寻并表现人性的深度,成为多维度、多层次、多差异的动画角色。同时观众能更多地在猪形象中找到共同的“话语”,感知相同的共性,进而认同角色的行为与感情,使猪形象实现了由大俗到大雅的转变。
四、角色个性与审美文化的建构
一个好的动画角色就像现实中的人物一样自然,一样拥有自己的个性和情感。“如今,观众已不仅仅满足于角色的‘演戏’,更要深入地看到动画角色内在性格和心理,动画片对于角色生命的创作,应该不仅仅是使它们都能动起来,而是要使它们在保持各自外形和性格的基础上,可以演绎各种不同的自己。”[9]如何在塑造角色的个性中,传达大众情感并且构建有价值的审美文化,是个很值得研究思考的问题。角色的个性有或大或小的差异,但大体包含以下几个要素:(一)真实性。动画虽然是一种夸张的表现手法,但动画的想象夸张不是绝对天马行空、脱离真实的,角色要传递情感与主题,就要当成真实存在的生物来构想,不能脱离性格与环境纯粹地设计,才能达到真实可信。这里的真实是指达到观众的心理真实,才能形成心理认同,在共鸣中得到娱乐。如麦兜与同学都是动物化的角色,而老师与校长是现实的人,妈妈则是半人半物,但丝毫没有违和感。麦兜成长过程中展现的傻气与可爱、快乐与烦恼、友情与亲情贴合了真实的香港生活,塑造了一个真实的生活化角色。因而得到观众的认可。(二)平等性,每个角色都有其权利和价值,不能为了突出主角光环,就过于捧高,视其为特殊角色。如猪猪侠的角色定位是拥有灵力的超级英雄,而在处理中却刻意突出平民出身、世俗且不完美的猪形象。“人格的不完美,才让观众觉得真实,更容易在角色身上找到归属认同感,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消解了生活与动画电影的距离,同时带来世俗化的风格和世俗化的消费过程。动画电影是大众的,没有世俗化内质的大众化容易成为一个缺乏历史内容的大众化,更不用说对中国动画电影大众化内涵的彰显。”[10](三)娱乐性。弗洛伊德说过,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得到快乐。动画成为心灵释放的场域,角色成为理想的自我。当代动画愈来愈倾向建构娱乐文化,即用狂欢的手法消解严肃主题,贴近生活内核,传达生活内涵,为观众建立一个(心理)真实、平等的动画王国,在趣味中隐藏感动,在狂欢中引起共鸣。但也要确立自己独特而有价值的话语体系,在愉悦中潜移默化地将狂欢变成时代的精神慰藉,构建现代情感意义层面的精神世界。
猪形象的转型彰显了当下人的生存状态、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动画角色的创作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用当代人的人生观与理想人格来塑造角色,从而创作出既能满足人们心理需求和审美文化,又能引导时代文明的动画作品。猪形象的文化意义演变仍在进行中。
参考文献:
[1]陈雪柠.动画篇主角意外征服年轻人[N].北京日报,2018-04-29.
[2]李昔.英国动画片《小猪佩奇》的最童话策略[J].电影评介,2017(6):86-88.
[3]许婧,汪灿.读动画——中国动画黄金80年[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5.
[4]朱剑,朱光耀.横空出世与象牙塔模式的成功——中国动画学派再讨论[J].大众文艺,2011(23):162-163.
[5]杜传坤.民间童话三只小猪百年变迁中的教育叙事[J].全球教育展望,2015(6):36-47.
[6]周鲒.动画电影分析[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53.
[7]刘宝云.中国动画创作观念的嬗变[D].保定:河北大学,2013.
[8]王海麗.国产动画片反面角色设计的创新与突破[J].中国电视,2014(10):80-83.
[9]于瑾,方建国.动画角色的性格塑造[J].浙江工艺美术,2008(2):60-63.
[10]郑曦.视觉文化时代:中国动画电影主体意识回归[J].文艺评论,2010(4):84-87.
作者简介:董丽娟,武汉纺织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动画艺术设计研究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