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影像的延展与异轨
2019-09-10曹恺
曹恺

按:自新千年以降,“影像”作为媒体艺术的基本样式,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主流的表现形态之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其自身亦形成了一部模糊的非线性历史,而这部历史因为其羸弱的发展轨迹和驳杂的血缘谱系,使得许多词源概念、语言逻辑、资料史实、陈述文体等都缺乏翔实性与可考性。
“映验场”(EX-CINEMA)作为一个意象性的专栏名词,穿越了从电影(Film)到录像(Video)、从新媒体(New Media)到动态影像(Moving Images)一系列历史语汇,以穷究于理、正本清源为栏目的既定目标,以达成一次媒体考古学的文本预演。

延 展
在“延展动画”的概念被正式定义之前,“延展”(Expand)作为一个附属于实验电影本体的定语,已经被先验地昭示在吉恩·扬布拉德(Gene Youngblood)创立的媒体政治话语系统里。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著作《延展电影》(Expanded Cinema)中,“延展”的开端被阐述为电影语言的进化对古典文学和戏剧形态的终结,而这种终结也让媒介外在的技术延伸具有了确定性的意义。
对延展电影的理论确立与研究,与在半个世纪前麦克卢汉媒介学的第一波热潮有着密切的关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其媒介信息理论中主张,一切媒介都将成为人类本体器官的延伸,而电影作为人类艺术视知觉的镜像,同样具备了这样的延展性。过去的半个世纪堪称是媒介剧变的爆发式突变期,时至今日,数字信息媒介已经完全取代了麦克卢汉时代的古典信息媒介(胶片投映、电视频道、广播波段),重新探究“延展”的方向和边界,却具有了数字时代的全新含义。
或许,延展电影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冈斯三面重幕。作为最早的实验电影人之一,法国哲学家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试图将其史诗影片的画面扩延到正常银幕之外,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压迫式的观影体验,于是将三块白幕组合成一个超级全景画面。这一事件也昭示了多重银幕(multiscreen)的概念的诞生。
但是,扬布拉德的“延展电影”理论却已经大大超越了冈斯当初的银幕扩延概念,他是用这个词对20世纪60年代以降美国地下电影现场进行的总体表述,其背景是激浪艺术(Fluxus)从德国威斯巴登出发到最终登陆纽约,这一艺术运动深刻地影响了当时视觉艺术与表演的方式。交互媒介(cross-media)作为一种新的思考与实践,包含了初始阶段的电子绘画和计算机影像,并整合在肢体舞蹈、音乐装置等多媒体剧场演出中。类似的延展模式被扬布拉德纳入在他提出的“全球化跨媒体网络”语境中,对一些未来形态的新概念进行了“后麦克卢汉”式的哲学思考和探索。
延展的维度
在当下概念中,电影(c i n e m a)及运动影像(moving image)的画面来自电影眼的光学或数字摄入,当然,也可以包括计算机数字生成的序列图像。但是,如果将影像本体的历史往前推移,就会发现19世纪“前电影”(pre-cinematic)时代的早期移动影像均来自于手绘图像,绘画性构成了电影史或运动影像藝术史的前传,这一特质在电影(film)媒介时代并未湮灭于摄影术的兴起,而是依赖其自身的语言特点发展为动画。21世纪以来,数字媒介和计算机技术的突变式发展彻底改变了影像生产的模式,从技术到观念上都促进了动画艺术的当代性与实验性的来临。
从“具有实验性的动画”到“实验动画”之现象及其研究,因为其依附于胶片媒介的材料属性,在艺术史的框架中长期被捆绑在实验电影系统内,其“动画性”特质并未被单列谱系,而是作为实验电影的一个分支隐身于“电影—胶片”(Film)的语境下。对动画的大众话语传播而言,动画的主流模样一直保持着好莱坞经典历史样式的承续。

把“实验动画”作为特定概念剥离出来,将“实验”作为定语前缀加以界定,主要还是为了更直接地探讨动画本体的内涵与外延,而将其叙事(包括记录叙事)的功能性暂时遮蔽。在这里,尤其是动画本体向外延展,在当代艺术的体系里得到了充分的生长空间。
动画就其延展性而言,大致可在本体性延展和功能性延展两个方向展开。延展动画的功能性是一个不间断扩展的变数,主要表现在其作为一种既定美学形态在日常社会中的实际呈现,比如电子游戏及其衍生品——服饰、玩偶、文具等,一般具有使用与消费的商品属性。而本文所论及的范畴主要是动画的本体性延展,即其所指的向心性的内在方向。
动画本体延展的两个维度,可分为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在空间维度上,延展动画主要表现为与当代艺术的交集,展现为多屏幕动画、动画装置、动画肢体表演、动画剧场展演等样态。在这里,当代艺术的开放性语言与动画美学的时间性表达形成了多向性的重叠结合体,具有一种复合型的视觉外化。
在时间维度上,延展动画更多体现了自身电影属性的内在延伸,这是下一节要重点论证的方向,也是实验电影的内核模式之一。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这两个维度又可以被概要地描述为交互式和沉浸式(immersive)两种形态。空间维度强调延展动画作品与观众的空间互动,甚至许多作品需要观众客体的二度介入协助,才能完成其最终的呈现。而时间维度则表现为一种沉浸式的自主体验,更重要的是延展动画所扩张出来的映像场域。
独帧与单格
进入时间维度,从动画本体的内在性来探求其延展的多个方向,首先必然要回归到其动画发生的第一帧画面,而在“元动画”的理论视角里,第一帧就是动画的最后一帧,这唯一的一帧包含了原画和一切关键帧与过渡帧。从这个观点而言,李少庄的《我城的相痕:第八章》就仅仅使用了一帧澳门艺术博物馆馆藏旧照,以澳门旧景作为画面切入点,对照片进行撕、切、割、折、叠等破坏性动作,再应用数字布光技术,使之产生光怪陆离的画面变化,时间性的运动被依附于“独帧”的相片,“相”片因历史的时间动作所弥留的“痕”迹而被改变,其内在静态影像因此而被改变为动态画面。
对于静照现成品的数字采样,是一种逐渐为更多艺术家使用的延展动画方式。从《照片回收》开始,雷磊一直热衷于对旧照片和旧底片进行再加工后的二度创作。在《周末》这部作品中,艺术家直接挪用了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摄影资料集——家具样本和人体动作图册,以排列、叠加、类比等各种方式的归纳与组合,找到静照与静照之间单格的逻辑——图像逻辑与时间逻辑,尤其是时间逻辑的复合运用,改变了原本静照被定格的瞬间,将之内在的时间轴点拉伸为时间线,重新构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私人记忆”。

现成品的回收和再生,是当代艺术的一种常见的工作方式,延展动画对此类现成品的使用,不仅仅关注到基于静照的印刷品,甚至可以涉及更为宽泛的出版物。譬如唐婉璐对世界地图的切分与重组,她罗列了全球88个国度对同一个词根——“妈妈”的发音,有机地拼接成一幅声音的世界地图《MAMA》,再逐一以减法使之歸零,展示了一幅世界如何消失的空白画面。这一进程遵循了声画“同轨—叠轨—异轨—零轨”的演绎。
另一种方式来自艺术家的直接静照,刘毅在作品《广场1号》中选择了欧洲城市广场上常见的古典雕塑作为客体对象,在获取独帧的图像后,通过后期剪接时的局部位移与运动节奏变化,使静止的塑像产生了动态的错觉,从而达成了静与动之间的逻辑转换。
由此可见,许多艺术家在探讨延展动画的生产时,需要回到胶片与视频的最小介质单位——独帧与单格,从一个静止的画面重新探讨延伸的可能性,并在最终成像时将这一探讨的时间结果以一种“动画式”或“类动画式”的成片表达出来。
这是一种解析动画语言内在逻辑的本体延展方式,类似的方式再借助计算机数字技术,可以产生更多的可能性。数字艺术家和理论家罗海德(Hector Rodriguez)一直以电影史上的经典画面采样作为其工作对象,寻求数字技术对移动影像的历史与美学重构所产生的意外结果。在其作品《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 Rain》中,他通过计算机程序编写篡改了王家卫《一代宗师》片头雨中武打的场景,将人物主体消失殆尽,仅仅保留了作为环境烘托的暗夜雨线。
对影像现成品的减法改写也可以采取反向二次元仿画,这在林建材的《Run Run Run》中可见一斑。这部短视频取材于早期邵氏经典电影中的一个镜头——一个奔向画面左下角的古装女子,他所做的工作是将这一镜头逐帧分解,并手工将每帧画面的背景涂抹删掉,只保留了古装女子本体,最后再重组生成为一条新的影片。这种方式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后西方兴起的“抽象电影”,一些先锋电影艺术家如道格拉斯·克洛克威尔(Douglas Crockwell)、诺曼·麦克拉伦(Norman McLaren)等直接在电影胶片上绘制抽象性的图案,逐格手工涂改、刮划、污染,乃至采用剪纸、逐格绘画、贴附布满彩色纹路的蜡块,再将其与正常胶片混合剪接,从而达到一种破坏性的视觉效果。麦克拉伦甚至在其中加入了他试验出的一种他称之为“怪异动画”(pixilation)的形式——以三度空间物品静照为对象模式。
异轨的文本
自2010年以降,基于文本演绎和文本结构的一种类型电影后知后觉地进入了中国内地人文学术界(而非电影和艺术的领域),并出现了两个比较集中的研讨话题:其一是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基于奥伯豪森宣言的“反电影”模型,其二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电影中反对电影”的观念。对此,笔者曾参与组织并主持了21世纪初在南京大学举办的两场相关学术论坛,与各人文学科的专家学者有过比较深入的探讨。在本文中,暂且先摒弃其更为宽泛的哲学与社会学层面上的学术探讨,而单单指向影像艺术语法研究,有两个概念影响了之后中国艺术家们的思考和创作,分别是克鲁格的泛蒙太奇理论和德波的异轨(Detournement)理论。
这两种理论的关键在于不仅仅是观念上的突变性引导,更是直接提供了具体的语言方法论。克鲁格透支了爱森斯坦的古典蒙太奇概念,使得非逻辑性的图像组织(静照与静照之间、静照与动画之间、动画与视频之间)成为可能,尤其是文本的直接入画,将字幕的辅助性解读提升到图像主体。
在此前后,一部分原本以纪录片为生产模式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类似方式进行工作,将自身影像创作的类型向实验的边界进行了一次扩延,由此产生了一批边界模糊的实验性作品。

对作为图像现成品的静照,运用二度拍摄的方式,通过镜头运动的节奏变换和局部放大,将一本寇德卡(Josef Koudelka)的经典摄影画册《混沌》(Chaos)转换为一部电影,是林鑫一次情绪失控下的创作冲动引起的结果,出乎意外的却是由此产生了一部与其以往作品截然不同的影像,除其图像再生的特性外,最重要的是将“静照”转换为了“动像”(moving image),而这种“动像”的内涵在某些层面上是与“动画”(animation)的灵性(anima)内质相重合的。
更早的时候,丛峰的创作也有过一次类似形态,不同的是他将镜头对准的不是静照,而是电视荧屏上正在播放的画面(短片《持遥控器的人》),这种方法的实质是将“视频”(video)转换为了“动画”。与此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的翻译者和研究者,丛峰在之后的创作中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了“异轨”的图像拼贴方式,《火的历史》作为其“地层”系列作品中的一个片段,用来自网络采样的图像现成品重组,阐释了一种回到电影初始模式的可能性——此类的文本电影或可以“诗歌电影”称谓之。
诗歌在灵性方面与动画的内涵是相吻合的,更多的差异来自更为理性的文本电影——“论文电影”或者“散文电影”。
把电影作为文本来写作,其文本性亦需要通过恰当的文体进行传达,在这里,文体的论述性与描绘性恰当与否、能提供什么样的视觉转换,是毛晨雨在2010年以降的写作难点,而拼贴式的泛蒙太奇模式成为最符合其文本的基本语言。虽然在毛晨雨自身最初的知识系统内,克鲁格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并不妨碍他不自觉地成为这一方法论的执行者。“荔枝姑娘”以一个寄名历史时代的形象化身,在毛晨雨近年來的写作中被反复提及。《荔枝姑娘:绿幕写》作为这一系列中的一部,似乎并不具备被单独评议的价值,而其整体性的描述与界定,可能更依赖于毛晨雨此类“散文电影”的文集样式的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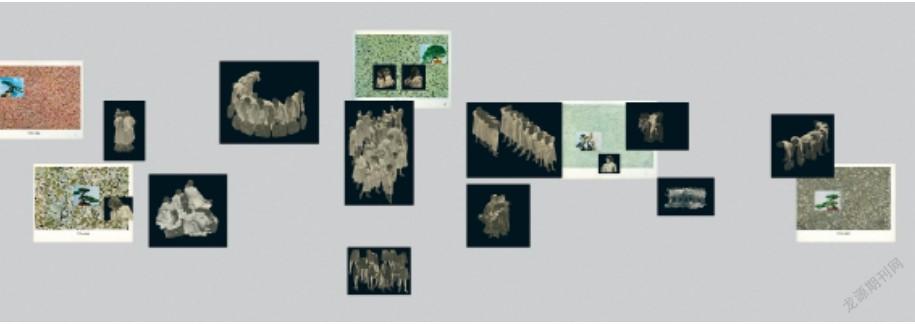
对于文本电影的作者来说,把一切视觉元素归类并二次定义为独帧(视频)或单格(胶片),然后再重新赋予其时间属性,打包组合生成为一轨新的运动画面,从其反向的角度来看,恰好符合了动画本体的内在延展性质。这种方式,也是文晶莹在《一人一心》的短片中所使用的模式。在视觉元素上的社会采样,来自公众参与的即兴表达的独幅画,以及其观念的文本阐述,被直接以类似连续播放幻灯片的方法所取代,看上去更像一种Power Point式的动画。
以上陈述了基于文本的几种模式(诗歌电影、散文电影、论文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类于“异轨”的理论表达,具体到视觉外化的方式,静照、图形、字幕、视频等被打碎重组为运动图像,并不完全依赖音轨的对位,而具有一种类“动画”形式的观感。基本符合了居伊·德波对“异轨”的定义——“对各种文本、图像、音轨、电影作品等进行匿名的自由挪用,以此来实现超越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统治的真正的交流。”
在异轨理论中所言的自由挪用方式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已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存在,互联网模式下的大数据库信息交换为此提供了一个完备的基础。文本电影的另一种称谓——“信息电影”或者“数据库电影”的概念也逐步被提及,当下低分辨率影像是大数据的构成要素之一,可以被实时下载并重新编码为拼贴的原材料。来自网络数据库的图像、文字和声音的重组与再构成为运动影像的新探索。在这个新的探索场域,此类拼贴式的异轨文本电影揭示了数字媒体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对影像的时间性结构不断打破、不断重组,并由此产生一个全新的视觉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