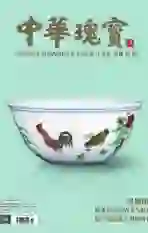苏绰:隋唐政治文化的奠基人
2019-09-10何德章
从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到西魏北周的军政贵族『关陇集团』及其后裔建立起强盛而繁荣的隋唐,是谁开启了以儒治国,融合胡汉、铸剑为犁的历史进程?
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追封已去世30余年的西魏度支尚书苏绰为“邳国公”。国公是当时臣子的最高封爵,隋文帝为何给隔代政权的臣子如此荣誉呢?这不仅因为苏绰为“前代名贤”,更重要的是隋朝继承了苏绰的治国理念。
中国历史上以强盛著称的隋唐,统治者均出自西魏北周时期的“关陇集团”(形成于西魏北周时期,延续至隋朝及唐代前期的军政集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概称为“关陇集团”)—隋文帝的父亲杨忠、唐高祖的祖父李虎均为西魏重要将领,隋文帝的皇后与唐高祖的母亲都是西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关陇集团的前身是西魏的“武川军团”,最初是一个反对中原汉文化的鲜卑化武人群体,最终却发展为支撑隋唐统一国家,推动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政治力量。促成这种精神蜕变的核心人物,正是苏绰。
宇文泰的难题
北魏时期,为防范草原游牧民族柔然汗国的侵扰,朝廷在长城一线设置了六个军镇,其将士多为游牧部落后裔、强行迁徙而来的民众及流放的罪犯,武川镇为其中之一。493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并推行全方位的汉化政策,激起了固守鲜卑习俗的六镇将士的不满,加之迁都后六镇的战略地位下降,将士们的仕途晋升及物质奖赏均大不如前,他们逐渐把对北魏朝廷的仇恨转化为对汉人及中原文明的排斥。523年,六镇发起武装暴动,失败后被收编,其中武川将士千余人被派往关陇地区镇压民众,经数年征战后发展为以宇文泰为首的“武川军团”,拥兵数万。前文提到的杨忠、李虎、独孤信等均来自武川镇,为这一集团的重要将领。
535年,宇文泰在长安拥立孝文帝曾孙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而此前一年,原六镇之一的怀朔镇镇兵高欢在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拥立孝文帝之孙元善见为帝,史称东魏。双方大打出手,然而东魏拥有二三十万精兵,又占据黄河中下游富庶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对西魏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西魏控制的关陇地区(今陕甘宁一带),自东汉中期以降就是民族关系最复杂、民族冲突最尖锐的地方—匈奴、鲜卑、氐、羌,以及当时见于史书的民族,大多在此处活动。各民族在相互碰撞、交融中,又分化、融合为众多语言、习俗有别的小族群。一旦时局动荡,便聚族而居、武装自保,经济则一片萧条。西晋至北魏135年间,各族先后在此建立了近十个政权,却无一能长期稳定。西魏建立之初,同样也未能有效统治。
作为西魏真正的统治者,宇文泰明白,“武川军团”是在镇压关陇民众暴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必须改变其“外来者”形象,消除关陇民众与武川军队、关陇各族群之间的敌意,实现国家的认同和团结,才能与东魏一争雌雄。然而如何着手呢?通过与苏绰的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对话后,宇文泰找到了解决之道。
“关陇集团”的精神导师
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确立了其立足荆蜀、联吴抗曹的战略,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三百多年后,宇文泰与苏绰的对话虽然不像“隆中对”一样在后人的小说、戏曲渲染下名扬千古,却远比“隆中对”更具历史意义。这一改变历史的时刻,不仅确立了西魏的政治走向,而且奠定了此后隋唐统一国家政治文化的基调。
约535年深秋的某天,宇文泰前往长安城西南的昆明池观赏捕鱼,这里曾是汉武帝训练水军之处,宇文泰对曾经强盛的西汉充满敬意,不断向旁人询问其事,随行之人便推荐了“博学多通”的苏绰。
苏绰(498—546年),世家出身,武功县(今陕西咸阳市武功县)人,“少好學,博览群书,尤善筭术”。他博古论今,侃侃而谈,尤其是谈及宇文泰最关心的“历代兴亡之迹”时,“应对如流”。兴奋之下,宇文泰拉着苏绰返回府第,“问以治道”,苏绰“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不觉已是通宵达旦。经过一天一夜的长谈后,宇文泰曰“苏绰真奇士也”,从此将政事交付苏绰。
历史并没有记录这场对话的内容,后人只能从相关史实中去探寻。其中,《孝经》无疑是苏绰向宇文泰反复强调的治国利器。苏绰之子苏威任隋朝宰相时,曾对隋文帝说:“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何用多为!’”隋文帝对此极其赞同。这虽有汉代以来儒者言论的影响,但主要还是苏绰的倡导及西魏北周政治实践的结果。
《孝经》据信是孔子对其弟子曾参讲授孝道的记录,不过两千字左右。苏绰“博览群书”,所读自然不只《孝经》,其告诫苏威之言,不过是在强调《孝经》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其他皆为枝叶。由于苏绰的倡导,西魏北周时期,君臣上下推崇、诵读、引用《孝经》事例不胜枚举。那么,苏绰为何独倡《孝经》呢?
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从魏晋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代独尊的儒学已趋于衰落,士大夫们热衷于探求老、庄的精神意蕴,撰写贵族化的精致诗文,却无视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疾苦。苏绰认为治国首要“治心”:儒家经典中,《尚书》佶屈聱牙,《周礼》烦琐枯燥,此类可供学者研习,却难以让民众亲近;《孝经》虽不在儒家核心的“五经”之列,但文字简短而浅近,汉代以来便是童蒙读本,因而更有利于西魏境内文化水平不高的鲜卑化武人及各族民众理解。更重要的是,《孝经》认为孝为德之根本、教化之源,“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将源于亲情的孝道作为安定社会的根本、沟通民众与国家的津梁,在心理上容易为胡汉各民族共同接受。
在苏绰的推动下,西魏北周形成了讲读《孝经》的风尚,并将儒学由学者研讨的经典,变成改造社会的实践运动,中华传统伦理由此深入人心,在动荡的时代中融合胡汉各族群,重塑和培植了中华文明的根基。
苏绰的治国之道
面对数百年来黄河流域族群撕裂、民族冲突不断的现实,苏绰既没有当时汉人普遍存在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观念,也没有像北魏孝文帝一样,强行要求少数民族改变语言、服饰以及姓氏,以遵从中华传统,而是要求官员率先垂范,宣扬儒家基于血缘人伦的孝道;要求百姓不分族类,都必须重视亲情,和睦相处,相互礼让;坚信所有族群都可以教化,各族达成共识,便可安定社会。
苏绰基于《孝经》的精神,制订了《六条诏书》,作为官员的施政原则。其中,“尽地利”“均赋役”“恤刑狱”为具体的政务原则;而“先治心”“敦教化”“擢贤良”三条,则具有文化复兴和正本清源的意义,影响深远。
“先治心”要求官员必须“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治心”同时要“治身”,即严格实践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的美德,为百姓做表率。
“敦教化”意在扭转魏晋以来“浇伪”“浮薄”的世风,培育“敦朴”“淳和”的社会风尚,“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以孝道教化百姓,使百姓以慈爱之心对待亲人,与乡邻和睦相处,相互敬让,不至于为蝇头小利伤害、仇视他人,如此便能“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
“擢贤良”则彻底否定了魏晋以来按门第选拔官员的制度。苏绰认为,即便是尧、舜这样的圣王,也会有不肖之子,公卿子弟哪能个个都是人才?因此从乡、州县至朝廷,各级官吏都通过实际考察,选拔品行端正而有才干的“贤良”。
《六条诏书》的实施,快速稳定了政局,也成功地改造了西魏统治集团,使之逐渐形成了一个遵循儒家伦理,亲民、清廉、高效、勤奋的政治团体,“变奢从俭,风化既被,而下肃上尊。疆埸屡扰,而内亲外附”。“武川军团”由此化茧成蝶,蜕变为“关陇集团”,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动荡,并走向强盛的隋唐。
苏绰为西魏定下的治国之道,经关陇集团的传承而延续至隋唐—隋文帝要求全国百姓背诵“五教”,培植孝道;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之语,历来备受称颂,其实是西魏以来长期政治实践的结果;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以教化天下。20世纪40年代,某些外国学者认为唐代的强盛是因为少数民族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寅恪先生公开著文反驳,认为唐代文明的根仍是中华传统—隋朝及唐初的统治者尽管有少数民族血统,但心理上认同中华,视隋唐为周汉文明的继承者。
苏绰以《孝经》治国,是一场远比北魏孝文帝改革更为深刻,也更为成功的中华文明复兴运动。由此,盛世华彩的唐代徐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何德章,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