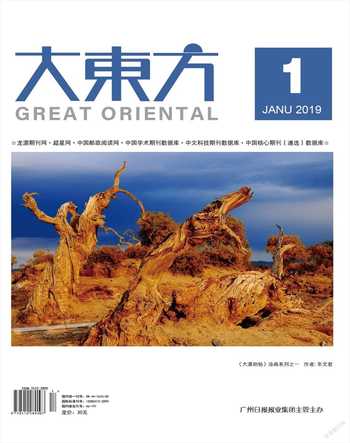《孝经》浅理解
2019-09-10王娜
王娜
摘 要:《孝经》这部著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位置。它以简洁的文字像人们阐述了“孝道”,是一部以孝道为道德根本的伦理著作,《孝经》不仅是用来规范人们尊卑有序的的典范书籍,也是被统治者用以达到自己统治目的的书籍,所以多个统治者为其做注,来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虽然成书的年代存在争议,但并不影响学者对《孝经》研究的热情,《孝经》在当代也并不全是迂腐,其中的传统美德还需要我们去探究。“孝”依然需要我们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关键词:《孝经》;孝;当代;启示
《孝经》浅理解
《孝经》是一部文字最少、研究最多、争论最多的关乎人伦道德,关乎人存于世安身立命的根本准则的经典论著。它以“孝”为基点,阐述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道德修养中的微妙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对《孝经》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其研究观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相同点是对《孝经》中“孝”之肯定,不同点是对成书作者、其理论的时代性以及政治色彩的批评、古今本之真伪、《闺门章》之有无的争论上。本文将综述上述不同点,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有关《孝经》成书作者的考證
有关《孝经》成书的时间,目前学术界根据《吕氏春秋》引用《孝经》这一事实,限定《孝经》成书时间最晚为公元前241年。但具体成书时间并不能确定,只有确定了成书作者才能进一步考证成书时间。由于古人作著立传多有不注名的癖好,导致很多古籍无法考证其作者,《孝经》就属于此类。因此只能从具有相互佐证,有关联的出土文献中推测其作者,故关于《孝经》的作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无明确历史资料考证的前提下,人们根据《孝经》观点主张以及相关历史资料记载,进行了大胆的推测,认为其作者可能有九种之多,分别为孔子、曾子、曾子众弟子、曾子弟子之子思、七十子之徒、乐正子春或者其弟子、孟子门人、汉儒和后人附会等[近年来《孝经》研究综述 肖永明 罗 山]。但也有人根据《孝经》观点主张与可能作者的思想以及历史背景下的称谓等进行了大胆的推测认为《孝经》非孔子、曾子所著,亦非曾子弟子子思所著,而是曾子的弟子经过提炼并结合社会背景的变迁所编著,是与时俱进的时代产物,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产物。个人认为《孝经》乃是大儒、至圣教育弟子的言行被弟子们推广并记录成书的经典著作,其观点可能与先圣有出入,但是符合当时统治阶级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为统治阶级服务,同时为其发扬光大起到了正性作用。
二、关古今本之真伪、《闺门章》之有无的争论的见解
《孝经》有今文与古文之分。《今文孝经》为颜芝所藏的由其子颜贞所献的用隶书写就的十八章《孝经》本;《古文孝经》传为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的用先秦籀文写成的二十二章《孝经》本。关于两者孰为正统的争论自《古文孝经》发现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两者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分,就其基本含义而言,名义上为两本,实乃一书,争论来争论去,闹得沸沸扬扬实在不雅。两者只是分章排列不同,内容相差无几,古文比今文多出四章,除了《闺门章》一章的二十二个字今文没有外,古文多出的另三章,其实是分割今文章节而成:古文《孝平章》第七是分今文《庶人章》第六而来; 古文《父母生绩章》第十一和《孝优劣章》第十二是分今文《圣治章》第九而来。另外,今文中的《感应章》列在《谏诤章》之后、《事君章》之前。而古文中的《感应章》则是列在《广至德章》之后、《广扬名章》之后。 这样,今文与古文的区别也就一目了然了。除了古文比今文多出一章,其余的只是在于各自的分章与排列不同,内容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这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因人为因素造成了这种分章与排列上的区别,也有可能是由于书的载体竹简的脱落造成了原书中文字先后次序的不同,所以两者的正统与非正统争论就显得没有任何意义。
《闺门章》之有无无碍于理解《孝经》大意, 古文学者认定是今文学者删掉了《闺门章》一章,而今文学者认为《古文孝经》多出的《闺门章》一章“语殊浅鄙不伦”,“谓刘炫伪增,无疑”。 至于《古文孝经》比《今文孝经》多出的《闺门》一章,我们并不能说应该有或者应该没有。毕竟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因为缺简、错简或是人为的删定等原因确实存在着差异,再加上《孝经》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鲁国,书写文字理应用古文,可是颜贞献时乃是用今文写就的,这就无法排除有学者根据记忆重新编写的可能,人为主观性造成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至于《古文孝经》的出现,乃是在《今文孝经》之后,虽是从孔壁中发现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沽名钓誉者以古文字为字体重新编写的可能,毕竟那个年代能通古文者应大有人在。所以,对于《闺门章》的有无,因为证据不足,所以不能妄下定论,只能说《闺门章》的有无并不妨碍我们对经文的理解与学习。所以大可不必因为其的存在与否而判定《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就为两本书,而争吵的沸沸扬扬。鉴于《古文孝经》与《今文孝经》这种种细微的差别,本人认为两者实为一本书的两个版本。
三、《孝经》理论政治色彩及时代性的浅谈
每一部经典著作能够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保存并流传下来,必定与其理论观点的合理性,被当时上至君王下至庶民所肯定,其中被以君王为首的统治阶级肯定是其发扬光大的关键点,因此《孝经》或多或少都具有时代性,并披上政治色彩的外衣,为统治阶级服务。
曾子身处在的战国的前中期,而那时正处在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其奴隶主统治奴隶的主导思想仍以“天命”、“天罚”、“受命于天”的神权法思想为主,然后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地位尊贵的人,从而巩固和加强奴隶主贵族的无尚崇高地位,因此墨子的思想从《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本孝》以及“曾子十篇”中窥见定格在“从父不从义”的“小孝”水准,与当时的主流“亲亲”、“尊尊”如出一辙,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嗅到大儒至圣的主张思想也未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性,带有浓浓的政治色彩。等到曾子的门人总结成书曾子语录时已处于战国中后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逐步形成,
“受命于天”、“亲亲”以及“尊尊”为统治手段的神权宗法思想受到了极大冲击,已经不能适应统治阶层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背景下,这时的“君权”超过了“父权”,“公法”超过了“家法”,“从义不从父”的思想很对统治阶级胃口,为统治提供了新的理念,被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因此在《孝经》中的“从义不从父”的思想已经与曾子所提倡“从父不从义”的思想背道而驰,问题上观点完全相反,已经从父权至上变成了君权至上,从孝的天下变成了忠的天下。
汉朝的统治者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单纯的运用法家思想来统治社会,并不是十分的理想,强权下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并不能真正的统治人们的思想,介于这种情况下,不仅要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还要有让人们认可的伦理纲常,所以汉朝不再单纯的运用法家思想来维持等级和权贵制度,而是将君臣的等级关系诠释成父子相生的关系,将大家庭比作小家庭,人们对待君王就应如同尊重父亲一般,用这样的理念来维护王权的权威性,这样王权变得权威,群臣关系变的和谐,社会也变得有了伦理纲常。在维系大家庭需要的是阶级的地位与尊重,而维系小家庭和睦的是家庭里面的孝,孝可以使小家庭亲人之间相处和睦,相互尊重,尊卑有序,好的小家庭氛围促就和谐社会环境。所以在汉朝时期,特别推崇孝道,当时没有科举制度而是举孝廉,这就看出对孝的重视,所以《孝经》备受推崇,以《孝经》为纲领。
并不是每部经典著作都能够得到帝王的青睐和认可的,而《孝经》受到了帝王们的热爱,帝王亲自作注,《孝经》研究政治化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重視《孝经》的方式发生转移,即是在诵读和以身作则的同时,更能深入到《孝经》的经文中去,以自己的见解来阐释经文大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孝经》作过注的帝王、皇太子据统计有六人。参照朱明勋《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经>研究》列表及《晋书》、《宋书》、《齐书》、《梁书》、《南史》等史书,分别如下:东晋晋元帝作《孝经传》、 晋孝武帝作《总明馆孝经讲义》、宋大明四年,皇太子作《大明中东宫讲义》、齐永明三年,皇太子作《永明东宫讲义》、梁朝梁武帝作《制旨孝经义》、梁简文帝作《孝经义疏》,统治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对经文大义加以阐发,肯定会有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曲解经文大义的地方,这样就使《孝经》研究趋于政治化。帝王注的《孝经》传播到社会上去,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感觉的冲击,认为当朝者是个孝子,或是个重视孝道的人,在百姓中赢得好名声的同时还可以接受统治者的思想,甘愿接受统治。并不是《孝经》看的多的人就是孝顺的人,也并不是可以给《孝经》做注的人就是可以做到孝道的人,这个道理在统治者的身上一样适用,并不是推崇孝道的统治者就是一个孝顺的人。上述中宋朝的皇太子,也就是后来即位后的前废帝,虽然为《孝经》作过注,而且还两次讲授《孝经》,但其本身并不是一个以孝出名的帝王,他即位后行为残暴,不仁不孝,杀兄戮臣,种种违背孝义的坏行为他都干尽了。由此可以看出来,统治者把《孝经》研究政治化,目的也只是约束平民百姓的行为,于其自身没有任何的约束。一旦达到目的就会揭去伪孝的面纱。由此可见《孝经》政治色彩浓重,在一定程度上沦为统治阶级加强和巩固政权的工具。
四、《孝经》在当代
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凡事都讲究公平、公正,更有很多人比较喜欢西方的家庭氛围,儿女长大后与父母分开生活,这些思想与我们古代的孝道都是相违背的,有句话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而我们当代的孩子,在读书后,工作时能够守在父母身边或与父母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都是少之又少,这不可以说是这些人的错,也不能说是这个时代的错,只能说是在这个时代为了更好的生存,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而将双亲放置家乡,这与我们的传统孝道是相违背的,但却与我们现代的生活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无可奈何。
《孝经》中有许多的孝道是我们所不能够认同的,认为很不可思议与不能够理解,就拿《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我们已经知道这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其中之“发”按经文意思乃“头发毛发”之意,古人从头发到胡须都都未曾敢毁损,一旦不爱惜受到损伤乃是大不孝之罪。在三国时期,曹操发兵宛城时规定:“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这样,骑马的士卒都下马,仔细地扶麦而过。可是,曹操的马却因田中飞鸟受惊而践踏了麦田。他很严肃地让执法的官员为自己定罪。执法官对照《春秋》上的道理,认为不能处罚担任尊贵职务的人。曹操认为:自己制定法令,自己却违反,怎么取信于军?即使我是全军统帅,也应受到一定处罚。他拿起剑割发,传示三军:“丞相踏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曹阿瞒“割发代首”以示军法纲纪之威严,取信于三军,一时间传为美谈,如若放在以美为首的现代社会,曹操之行无异于军中作秀,必定为“网络水军”所诟病、不齿。
虽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孝之始也。”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愚昧,也不适用于当代,但我想说的是,文中的意思还是有我们可以认可的,就比如说,现在的人因为失恋,压力大,就选择自杀,更有甚者父母不给买手机而选择自杀的青少年,这种做法真的是让人不能够理解,这就是一种不孝,这就应该被大家所不耻,无乱何种原因,你选择轻生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父母的不孝,这种类似的事情就应该以绝对的态度进行批评,这种风气绝对要杜绝。
虽然《孝经》中有与当今社会有不相符之处,但能为当今社会所取的观点依然很多,譬如“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说“孝道犹如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地上万物的自然生长,天经地义,乃是人类最为根本首要的品行。天地有其自然法则,人类从其法则中领悟到实行孝道是为自身的法则而遵循它。效法上天那永恒不变的规律,利用大地自然四季中的优势,顺乎自然规律对天下民众施以政教”。古人云“百善孝为首”,乃是取自大自然之规律,想必都听过“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的经典故事,《本草纲目》记载“乌鸦为慈鸟,此鸟出生,母哺60日,长者反哺60日,可谓慈孝亦”,束皙在《补亡诗》中也说“嗷嗷林鸟,受哺于子”,苏辙的诗中也提到“马驰未觉西南远,鸟哺何辞日夜飞”都说的是乌鸦由母鸟养大,在母鸟衰老不能觅食时,小乌鸦便衔食喂母鸟以为回报。由此可见“孝”乃是自然之规律,万物之本性。但放眼当今社会,有多少老人不能颐养天年,有多少老人不能安享天伦之乐,社会在发展,社会节奏在变快,人们变得物质与世俗,人伦在慢慢的丧失,经济在发展,人文在衰退,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时代号召的本意渐行渐远,所以重振《孝经》之精华本意显得尤为重要。
重振《孝经》并不是我们要按部就班的去学习里面的内容,只是我们要去学习里面“孝”的精髓,讲我们中华儿女的“孝”发扬光大,总之,我们研习《孝经》应当以其中之根本要义,大道至孝为本,继续发掘其深意并推广之,使古代文学之精华继续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光发热,添砖加瓦,为社会主义的人文建设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参考资料:
[1]四库·经部·孝经类·朱熹《孝经刊误》
[2]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张汉东,《〈孝经〉的作者及其思想》,[J].山东: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4]朱明勋·《清代〈孝经〉研究论要》,[J].四川:内江师范学报,第 20 卷第3期
[5]刘明月,二十世纪《孝经》研究. [D].黑龙江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6]渠延梅,《孝经》研究. [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7]肖永明,近年来《孝经》研究综述. [D].湖南:湖南大学,云梦学刊,2009.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