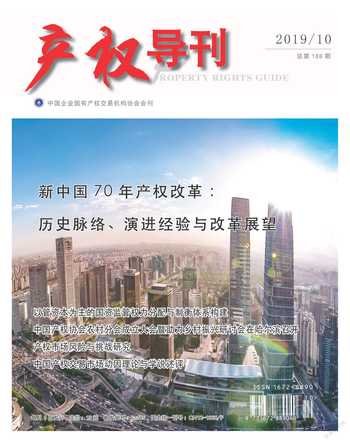袁仁国案启示:务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2019-09-10郑凯平
郑凯平


2019年9月6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原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受贿一案,一年前被贵州省纪委监委宣布审查调查的袁仁国被重新拉回公众视线。
官方通报显示:袁仁国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大搞权权、权钱交易,大肆为不法经销商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提供便利,严重破坏茅台酒经销商环境,非法接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大搞家族史腐败,放任家人、亲戚及身边人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以酒谋私获得巨额利益。
从茅台制酒工做起一路刷新任职“最年轻记录”、执掌茅台帅位18年、带领贵州茅台一路闯关夺隘问鼎全球白酒市值头名,这样一位功勋老臣,如今成为阶下之囚,袁仁国剧烈的人生反差,让人倍感惋惜、不胜唏嘘。
是什么让袁仁国一步步滑向深渊?当然是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具体来讲是茅台酒的“经销权”。这个“经销权”的诱惑力到底有多大?袁仁国掌握的这个权力又有多吸引人呢?
众所周知,茅台有“国酒”之称,悠久的历史、醇厚的口感、远播的盛名,自然也有高昂的价格。2006年以来,茅台集团在产品营销中采取特许经营模式。只要得到茅台酒专卖店、经销商的资格或批条,不用经营管理,转手就能获取巨额财富。以最为经典的53度飞天茅台为例,目前的出厂价为969元/瓶,指导零售价为1499元/瓶,但从实际销售价格看,北京市场已经突破2100元/瓶,个别地区已经直逼3000元/瓶,而且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也就是说,从出厂价到终端销售价,每瓶酒动辄有500~2000元的价差,也就造就了茅台酒“谁手上有酒,谁就能躺着赚钱”的现象。
手握茅台酒经销权的茅台集团高管,则身陷利益漩涡之中。在袁仁国之前,茅台集团已不止一位高管倒在这上面。2007年,原茅台股份公司总经理乔洪涉嫌受贿被捕,最终被判处死缓;2018年6月,原茅台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谭定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已认定其共受贿3460多万元,贵州省纪委曾以“只要送钱,就可以成为茅台公司经销商”来描述谭定华。
与乔洪、谭定华等人不同,袁仁国更是发掘了茅台酒经销权的其他“用途”。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20日的文章《贵州专项整治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文中披露袁仁国长期将茅台酒经销权作为攀附权贵、搞政治投机的工具,通过利益输送找“后台”、寻“靠山”,为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曾任贵州省副省长的王晓光等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获得茅台酒经销权提供帮助,并长期主动关照他们的经营。比如为了得到王晓光的庇护,袁仁国为王晓光及其亲属批了四家茅台酒专卖店,并经常主动为其增加销售指标。文章介绍,与袁仁国有关的“关系店”信息高达数百条,既涉及中管干部、省管干部,也有不少县处级、乡科级干部。茅台集团所在地的仁怀市,参与茅台酒经营的124名干部中,不少人利用亲戚、裙带关系,通过袁仁国或其妻获取经销权。原仁怀市人民检察院院长刘某某利用袁仁国得到茅台酒经销权后,竟辞去检察长职务,专心当起了“酒贩子”,成为仁怀官场一大奇闻异事。
一个茅台酒的经销权,牵出的是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集团等多个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腐败窝案,牵出的是被巨额利益败坏的政治生态,也牵出了对国有资产应当如何配置的深刻反思。
毫无疑问,茅台集团作为国有企业,茅台酒的经销权本质上属于特许经营权,是重要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配置应当遵循公开、阳光的原则,绝不能成为领导干部个人支配的私产。
2002年1月,十五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明确:自2002年起,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实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建设工程项目公开招标投标、政府采购、产权交易进入市场等四项制度。
2003年及随后的几年,随着国务院国资委和各地方国资委的成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的发布,企业国有产权正式实施进场公开交易制度,并在随后的十几年,进场范围逐步拓展到国有企业资产、国有企业增资扩股。北京市还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国有企业房屋租赁、国有企业涉诉资产、涉刑事资产等纳入进场范围,黑龙江省将国有企业采购纳入进场范围,珠海市则将公共停车位经营权、广告牌经营权招投标等纳入进场范围,均取得巨大成功。
以笔者所在的北京产权交易所(下称“北交所”)为例,2018年到2019年6月这一年半时间,北交所仅企业国有产权挂牌转让总增值金额就达到270.24亿元,增值率达到32.21%。也就是说,评估价100块钱的东西,经过产权市场充分挖掘投资人,充分发现市场公允价格,卖出了132块钱,有效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产权市场的公开、阳光操作,避免了权力寻租,避免了暗箱操作,從源头上解决了国有资产处置的世界性难题,产权市场的这套作法也成为重大的制度创新,得到各级党委、纪委、政府部门以及国有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高度认可。
为了确保国有资产交易的阳光、透明,产权市场根据“公开、竞争”的制度设计,制定了完备的交易规则、建立了科学严谨的交易流程、打造了严密的风控体系、开发建设了闭环的信息技术交易系统、实施广泛深入的信息披露,整套的制度设计,让产权市场的操作符合“依法合规、市场机制”的国有产权监管要求,确保了交易全流程的规范高效。
必须指出的是,产权市场的这套交易制度体系,是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处置国有资产的科学方法,同时它就像一个大筐,国有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资产处置、资产采购、招商融资以及茅台酒“经销权”这样的特许经营权招投标等,都可以装进这个筐里依托产权市场操作。试想,如果茅台酒的经销权通过产权市场公开交易,很容易将被滥用的“权力”关进产权市场这个“制度的笼子”,也很难出现袁仁国等“为所欲为”的问题,也不会倒下这么多干部,当地的政治生态也不至于败坏如斯。
事实上,部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产权市场的强大功能,自觉自愿地将持有的集体资产、国有资金形成的基金份额以及投资形成的股权、技术类无形资产、礼品等特殊资产等,通过产权市场公开处置。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国有资产作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有资产,作为党和国家执政的物质基础和支撑力量,它的管理和处置仅仅依靠自觉性仍有漏洞,它更应该成为一项强制性的制度,体现出制度刚性的一面,这有赖于各级党委、纪委和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化反腐败斗争,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中国产权市场作为源头防腐的重要制度性平台,应当也必将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为北京产权交易所推出的财经时事评论系列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