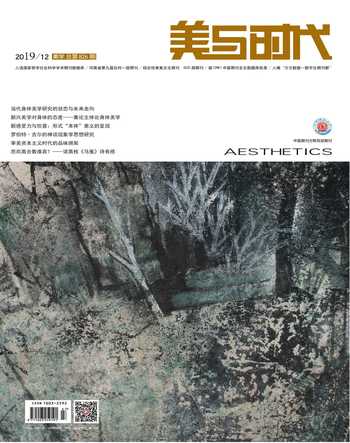略论国家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2019-09-10伊丹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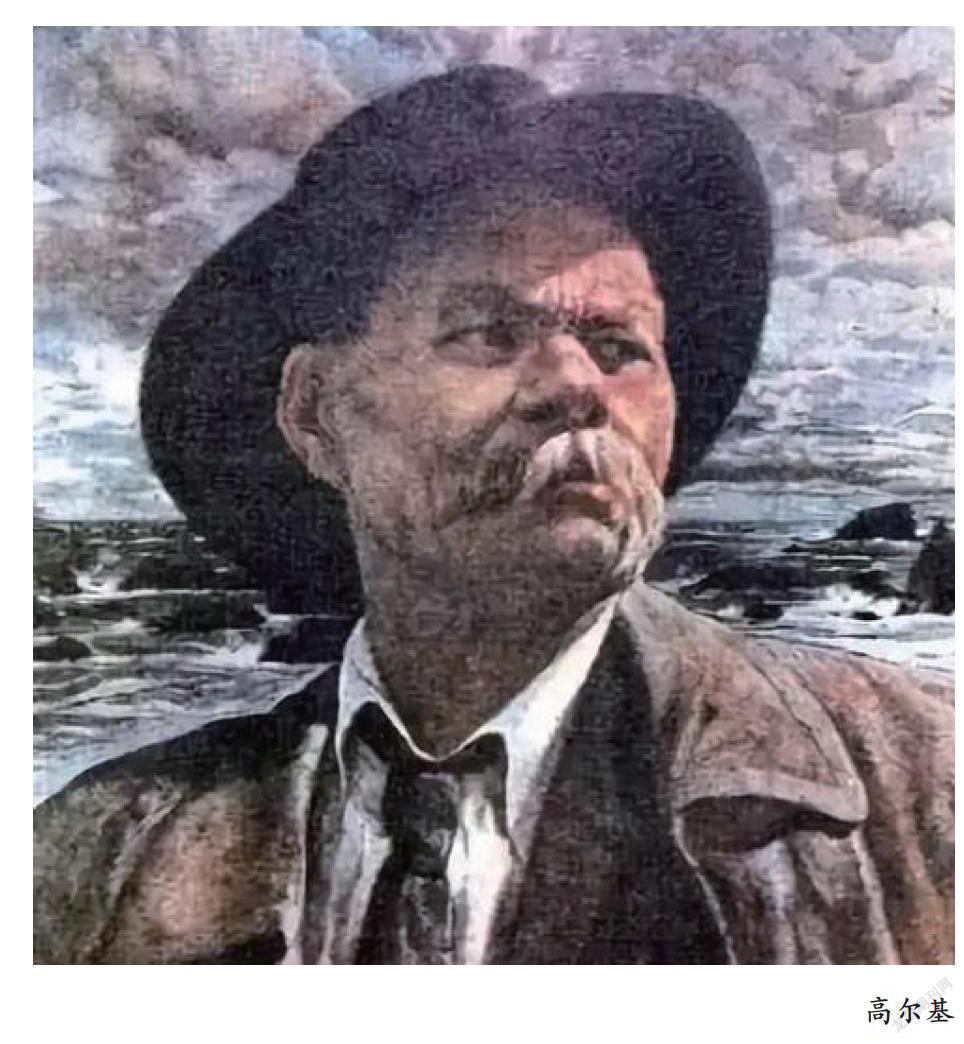
摘 要:在艺术作品的诞生和评价机制中,国家是一项值得深入探讨的因素。对此,不同学者也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高尔基作为苏联时期的文学泰斗,其一生的境遇及其文学创作在不同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高尔基的艺术创作与国家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
关键词:艺术创作;国家;高尔基;地位
关于国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地位,不同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观点。贝克尔的《艺术界》认为,“所有的艺术家都依赖于国家,他们的作品都蕴含了这种依赖”[1]150。他认为,国家总是在艺术品制作过程中发挥作用并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国家的利益可能会与艺术家的利益一致,艺术家需要在国家法律的条条框框中创作。这些都会使艺术家们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对自己的艺术创作进行调整,在这些调整中体现了艺术家对国家的依赖以及国家对艺术创作过程的某些限制。贝克尔认为政治对艺术有一定的压制性,很多学者则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薛雯、刘锋杰曾表示,“艺术与政治之间应当用想象来结缘,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却又各具特性,不会相互取代。”[2]这里意在说明艺术与政治的双向互动过程,即认为艺术和政治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改变的关系,二者之间不存在取代。所以,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我们讨论艺术的政治性,讨论艺术对社会在政治维度上的贡献性并肯定这一点,就是在证明艺术的有用性,证明二者之间的这种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也决定了艺术与政治之间可以影响,但是艺术不能成为政治实施的手段。正如文苑仲所说:“艺术绝不能充当说教的工具,其政治功能不在于‘介入’现实,而是存在于艺术的独立与自主之中,通过保持与现实世界的审美分离而发挥歧感效用,去扰乱所谓‘正确’的观看、言说与行动的方式,改变主体对自身的‘位置’。”[3]
总之,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时代和立场给出了不同的观点,本文无意对其进行全面的梳理或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空洞的探讨。艺术的影响和印记可以体现在许多政治斗争和革命历史中,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马赛曲》《国际歌》《自由引导人民》《格尔尼卡》等,艺术的光辉无处不在。当代的一些艺术家更是将艺术极好地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他们从艺术的角度,将关注点对准复杂、抽象的政治、社会问题,对此进行批判和反思。而我们熟知的大文豪高尔基,无疑是苏联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之一,同时也是反映艺术家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典范。那么,高尔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进行的文学创作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国家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以此论之,高尔基的文学成就与国家有怎样的关系?国家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本文将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一、高尔基的文学生涯
高尔基作为苏联时期的大文豪,一生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在不断发生转变,这些变化的价值观与他本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包括他与当局者的关系有密切联系,这些都反映在他不同阶段的文学创作中。
高尔基是伟大的作家,被誉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在1905年以前,高尔基属于文学圈内人,他的政治观点与知识界的主流思想一样,属于反对暴力革命的改良主义。1906年的法美之旅是他的思想左倾化的一个转折点。高尔基迅速接受并转向马克思主义观,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失去了活力和热度,他个人的思想转变也使他的革命性大大增强。这一时期描写工人运动的小说,比如《母亲》《仇敌》《夏天》《忏悔》等,高尔基深刻地描绘了工人阶级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以及革命的历史必然,论证了群众一旦掌握革命理论,就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以小说《母亲》为例,其中的人物雷宾对尼罗娜说:“跟着儿子走,走儿子的道路,他大概是第一个吧,是第一个!”[4]283这里的“第一个”代表了当时那一代人的先锋精神和整体的精神面貌,“母亲”则代表了整个时代的精神领袖。
而后的“十月革命”成为高尔基与列宁发生冲突的导火索,高尔基也因此被称为当时“不合时宜者”的代表,他基本上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主办《新生活报》为它发声。当新的当权者开始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残酷的封杀之后,高尔基以笔作为枪杆子,开始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他精炼的语言文字犹如一排排大炮将那些惨绝人寰的行径揭露得干干净净。他写道:“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列宁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场极端的獸性实验,列宁为了自己的试验让人民血流成河……”等。在高尔基的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这样的言论反复出现。从他对苏维埃政权种种猛烈的批判中我们看到一个承担着“社会良心”角色的高尔基,他坦诚、率真地揭示了十月革命初期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一题名本身也就意味高尔基艺术创作的现实性。此时,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既不是战友也没有变为敌人,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尤其在关于革命与文化的关系方面。一方面,高尔基承认俄国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但是执政党使用暴力对待文化遗产及科学家等行径违背了人道主义;另一方面,高尔基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在革命的发展中似乎已经变了味道,不得已,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即写出来的作品来与当局对抗。他说这个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斯大林曾说,这时的高尔基与反革命没什么两样,他是一具“政治僵尸”。
1921年,内心对苏维埃政权强烈的不满和失望的高尔基出国,先后在德国和意大利长住。国外生活的十年间,苏维埃政权的发展让高尔基大跌眼镜,因为它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壮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高尔基的相关言论转向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他说苏联“进入了新生时代”,“国内生活的进步越来越显著”,“我相信他们可以找到阿基米德支点”。高尔基言论的转变也可以体现出他对当局政权态度的变化。一开始,高尔基处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尴尬地带,后来,布尔什维克的发展壮大使他从对其专政的批判转而投向对党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的支持和赞美。
紧接着,高尔基在当权者斯大林的帮助下回国,回国后的高尔基似乎变成了一个对斯大林体制的吹捧者。相比于十月革命时的口无遮拦,高尔基变得小心翼翼,他和斯大林的关系也相当亲密,并慢慢参与到斯大林的政治游戏中,这决定了他价值观的转变。从1930年开始,高尔基对斯大林大加赞扬。1931年,他对斯大林的相关事宜的描述较为平实和单调,如“斯大林同志说……”;1932年,高尔基眼中的斯大林逐渐升格,他成为“列宁的忠实、坚定的学生”、称之为“我们的领袖”等;到1934年,高尔基对斯大林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斯大林在世界的作用和意义,增长的越来越快”,斯大林是“第二个列宁”等,从高尔基对斯大林的描述和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转变,以及在政治生活中对斯大林个人形象的完美塑造。
20世纪90年代,高尔基褪去了曾经的模样,对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他没有用他犀利的笔锋发出“正义的怒吼”,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党的传话筒。对于当权者斯大林而言,高尔基是当时塑造革命史最恰当的人选。俄国政党可以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然而,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独立却需一个有权威的知识分子做表率才更有说服力,高尔基在斯大林时期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这极好地体现了国家在高尔基艺术创作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二、高尔基的艺术成就
高尔基可谓是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他刚刚走进文坛时,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从《海燕》开始,他的浪漫主义风格逐渐发生转变,文学作品与现实的联系日益紧密,现实主义风格愈来愈明显,而《母亲》被认定为“是本奠定无产阶级文学史基的作品”。高尔基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反映了他在文学取向上的重要转变,这也为他创作革命题材的作品奠定了基础。
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位大文豪,除此之外,他还冠有革命文学家的名号。他用手中的笔杆子表现了革命斗争的必要性,他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革命精神又让人们备受鼓舞,去创造、去抗争、去革命。《海燕之歌》和《母亲》是高尔基用他的文学作品去革命的最好证明。1907年发表的《母亲》正值革命发展的低谷期,在“没有拿武器的必要的时代”成为时代的口号。高尔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武力革命是必要和正当的。这两部作品成为一支有力的革命进行曲,这与最初高尔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主张革命的政治观相一致。所以,回荡在高尔基作品中的主旋律始终是对革命和自由的高昂呐喊。事实上,高尔基前期的作品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包括他的自传体三部曲、流浪漢小说等。十月革命发生时,国内出现的流血事件和暴力行径让高尔基意识到传统的封建制度已经成了人民心中的精神毒瘤,即使实现了外在的解放,人们心中的奴性却根深蒂固。为此,高尔基的《罗斯游记》《日记片段》《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极好地展示了当时的民族问题,他还抨击了当时的民族心态。
总而言之,每一场革命都使得高尔基意识到了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俄罗斯,之所以连续不断的出现许多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精神文化水准偏低,而政治斗争则为民族劣根性的膨胀性显露提供了最肆无忌惮的时空。”高尔基的创作成就了自己,成就了当时的时代。因此,与其说是时代塑造了高尔基的艺术风格,倒不如说高尔基的艺术充分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也正是高尔基的作品从文学和艺术上保留了人们的生活、追求和梦想,也保留了时代的残酷、暴力和希望,高尔基在这种挣扎的希望中不断表现着斯拉夫民族所经历的历史阶段。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高尔基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文学成就,这种成就深深植根于高尔基对民族的深切眷恋之中,也植根于高尔基早期文学训练所达到的水平之上。如果能够摒弃苏联国家的影响单纯评判高尔基的艺术,那么他的艺术成就无疑已经达到了一种十分高超的水平。
三、结语
高尔基布满荆棘的人生和曲折的文学创作之路在俄国文学界和工人阶级长达四十年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所留下的大量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苏联时代的艺术形式,而且在世界文学殿堂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高尔基的文学创作之路充分体现了艺术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列宁时期的高尔基因为不能完全适应政治形势使其艺术地位始终处于比较低的状态,从他在这一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可见一斑;斯大林时期的高尔基完全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他与斯大林的合作也显得十分暧昧,高尔基的艺术地位直线上升,并且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前后两种巨大的反差反映了艺术家如果能够适应政治的发展需要就有取得声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所塑造的艺术家实质上能够代表某一时期的政治取向和审美要求。
显而易见,不能将国家与艺术的关系简单地化约为互相成就或者互相促进,这样的认识可能引起艺术创作和艺术成就中的一种悖论。艺术的创作与成就取决于艺术家的人生经历,别样的人生经历必定塑造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而高尔基所经历的人生恰恰是红色政权极其隆盛的阶段,这种阶段极易塑造政治家的御用文人。因此与其说艺术家是时代的产物,倒不如说任何有成就的艺术家都会将人生经历写进个人的艺术作品之中。当然,艺术成就的高低还与艺术所达到的整体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高尔基所在的时代是俄国苏联文学已经积淀了近千年的时期,因此高尔基是在继承斯拉夫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基础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本文以高尔基为例着重探讨了艺术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一个个案研究,不能将类似的研究推论至广阔的学术视野之中。这一探讨的意义就在于为艺术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典型性的案例,这个案例不能全面说明国家与艺术在何种程度和何种维度上的互动和交流,也不能表明艺术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简单的逻辑关系。只能说明高尔基的艺术成就与国家之间有着紧密的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因为这种相关关系直接塑造了高尔基及其文学成就。
参考文献:
[1]贝克尔.艺术界[M].卢文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2]薛雯,刘锋杰.艺术的反抗性——艺术与政治关系的一个维度的理解[J].文艺争鸣,2015(7):97-105.
[3]文苑仲.走向歧感现实,回归审美之真——雅克·朗西埃论艺术的政治功能[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5):155-160.
[4]高尔基.母亲[M].吴兴勇,刘心语,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伊丹丹,上海大学文学院全球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