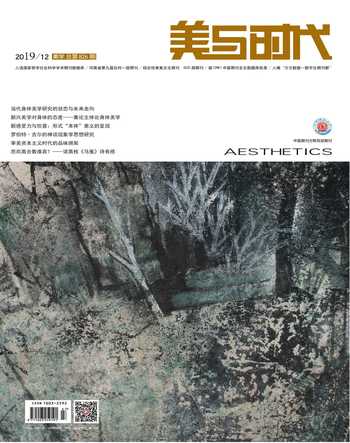电影《路边野餐》的审美疏离化分析
2019-09-10马静岚
摘 要:电影《路边野餐》被高度赞誉为“无法被复制的处女作”。得益于导演对电影语言的巧妙运用,审美疏离化是该影片在影视化叙事上的一大亮点。导演运用非线性叙事、非常规构图、长镜头调度、诗歌旁白等疏离化手段,使影片呈现出诗意效果,观众由此获得不一样的观影体验和审美感受。在商业气息浓厚的华语电影市场上,《路边野餐》的出现无疑为华语电影的发展注入了一剂新动力。
关键词:电影美学;路边野餐;审美疏离化;毕赣
在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上,毕赣的最新电影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成功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其上一部影片《路边野餐》也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在国内上映前,《路边野餐》已斩获洛迦诺、金马、南特等电影节多个奖项,引发国内观众期待。上映后更是获赞无数,“诗意”“梦幻”“深邃”等赞誉纷至沓来,更有评价称该影片“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大师级别的作品”。从叙事上看,影片贴近日常生活,故事文本围绕着生活在凯里的中年男人陈升展开,为了寻找侄子卫卫,他离开凯里,只身前往亦真亦假的小镇,而在这片神秘的区域中,他遇见了过去的妻子以及未来的侄子。但影片中穿插的各种细节却并非简单易懂,导演通过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奇异的构图和诡谲的运镜等疏离化技巧使故事被切割成碎片,时空不再统一,故事变得难以拼凑完整,影片如梦似迷,观众一时间无法分辨现实与梦境。大量疏离化手法的运用也奠定了这部影片的审美基调——诗意且忧伤,神秘又暧昧。在潮湿的亚热带环境里,虚无与现实交织,镜头在梦境、清醒、回忆、告别四者间不断切换。对于观众来说,《路边野餐》在形式上违反了人们的日常观影习惯,从而减弱了观众知觉的恒常性,理解和感受影片的难度增大,客观上延长了观众的审美过程。观众不仅以能更自由的方式体验影片的魅力,更能增添一份理性的态度审视该影片。
一、摒弃秩序感:非线性的叙事结构
疏离化(defamiliarization)又称为陌生化、审美间离,由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他强调“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为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为其石头……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觉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1]在电影《路边野餐》中,导演毕赣有意识地增加观众理解的难度,采取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延长观众的感觉。
在《重估线性叙事的价值》中,杨世真提出:“线性叙事乃是一种经典的叙事方式,在叙事时注重故事的完整性、时间的连贯性、情节的因果性,在这种叙事观念的背后包含着对世界的秩序感和确定性的信念和诉求。”[2]非线性叙事则呈现出相反的姿态,不再强调故事的完整性与情节的逻辑性,同时打乱时间顺序,由此与人们日常的时间观念以及观看传统线性叙事电影的经验产生断裂,审美的疏离化在令观众费解的同时抓住了他们的眼球。而非线性叙事可归结为以下两个特征:故事时空交错、情节逻辑混乱。
导演擅长运用闪回镜头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连贯性。影片中,看望侄子卫卫时,陈升视线落在家中的镭射球后,画面场景立即切换成歌舞厅,观众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当陈升和女医生光莲在诊所外聊天过后,画面场景又回到歌舞厅,陈升被他人邀请唱歌。四十秒过后,画面又转到了山洞里,陈升在等待卖香蕉的人。在荡麦时,陈升想要乘船到镇远,画面又跳跃到在水中不断下沉的蓝色绣花鞋等。通过这样的闪回镜头,导演重新对时间进行拼貼和组合,改变了故事整体的时间顺序。由于故事情节的连续性被消减,情节变得跳跃,颠覆了观众在日常中对于时间顺序的经验认识,导致观众感觉到时间空间都被打乱,在观影时难以准确把握时空关系。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连贯性在一定程度上使情节逻辑变得不再清晰。影片故事文本本身带有一定的逻辑性,在访谈中导演毕赣坦诚,《路边野餐》的创作缘起于奶奶的亲哥哥在镇远去世,但由于身体原因没法把衣服送去。由此毕赣开始做影片的结构,希望他影片的主角可以帮一个老人送一个物品到其他地方,在路上遇见过去的爱人、长大的亲人,而影片中的细节都是记忆性的东西。导演并不是简单直接地将故事呈现,而是运用疏离化的技巧,在叙事过程中对时空进行省略和跳跃。除了多次使用闪回镜头外,细节性的东西也散落在影片各处,物品作为符号被赐予深刻的涵义。同样的物品如望远镜、手电筒等可能出现在过去、现实与梦境中,这增加了观众辨别时间的难度,使情节逻辑看起来似乎更为难以理解。毕赣在访谈中形容影片“我不希望它有一个确定的指向,但里面有很多确定宿命的道具”。影片中,对陈升的梦境和回忆的展现是直接的、生硬的,不存在过多的提示。现实与过去,梦境与回忆之间的展现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界限。导演有意对情节作模糊处理,更能激发观众对影片的思考与追溯,让观众在观看过后去回味、去还原混乱的情节本身。
二、增添形式感:离奇的构图和诡谲的运镜
除去有意运用非线性叙事增强“疏离化”效果,在构图和运镜方面,“镜中镜”构图模式随处可见。导演运用固定镜头、平移镜头、圆周运镜及长镜头等方式,在营造诗意之余给人以新的审美视觉冲击。
《路边野餐》并没有运用正反打镜头这一从好莱坞沿袭下来的固定模式传递故事对话情节,而是采取了“镜中镜”构图模式呈现影像。镜子成为观众通往《路边野餐》的重要方式,却又产生一种疏离感,提醒观众“自我”只是在观看的位置上。诊所放置了一面镜子,在陈升与光莲对话的画面中,陈升占据了镜头的主体,光莲在镜头之外,却通过“镜中镜”构图出现在画面中。老歪在路边修理摩托车时,导演并不直接拍摄修理场景,而是将画面固定在摩托车的倒视镜上,老歪的动作通过镜子呈现。陈升在歌舞厅的时候,他的背后有一面大镜子,张夕的身影只在镜子中出现。陈升在荡麦剪头发时,人物没有特写镜头,画面是发廊的镜子,观众只能通过镜子理解陈升和张夕的互动。利用镜子成像的虚拟性以及镜子中人物的模糊性,导演毕赣再一次淡化现实与回忆、梦境与现实的边界,加深观众理解难度。
其次,时间在影片中不断被拆解和重塑。影片中有大量关于时间与记忆的意象,如钟表、手电筒、磁带与绣花鞋。有取自《金刚经》关于时间与记忆的文字描述: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而在运镜方面,导演也用了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时间与记忆。在电影一开场,导演运用圆周运镜对诊所进行了环绕式的拍摄,昏暗的环境、闪烁的灯光以及关于生死的话题都是在描述陈升“现在”缓慢、无聊的生活状态。除此之外,平移镜头则用来衔接现实与回忆、当下与梦境,空间的位移实则在提示时间在变化。花和尚在老歪家中聊天时,导演将镜头缓慢平移至墙边,墙上叠化了一趟正在行驶的列车,这是在提示卫卫的离开,而当列车过去后,镜头转接至陈升家中。又如陈升在桌球室与老歪对峙,画面忽然切换至陈升找寻仇家许英的场景,而在陈升与许英的对话间,镜头向左平移至一个放置在红色桌子上的玻璃杯,雨水不断滴落,当镜头再次平移后,场景切换回现实中陈升与老歪争执场面等。突兀的衔接与诡异的空间运动都在扰乱观众视点,使观众产生间离感。
最后,将近42分钟的长镜头是该影片的焦点。带有纪实性质的长镜头被导演巧妙地运用在荡麦这一梦幻的段落中,使这一段落时间的连贯性和空间的真实性得以保证,這恰恰是导演在加大模糊现实与梦幻边界的力度。“荡麦”正是导演运用审美间离而勾勒出来的非现实的存在,但陈升最真实的情感正是在此处显现。他希望与死去的妻子重逢,唱一首简单的情歌《小茉莉》;他希望未来的他仍然能在卫卫心中充当一个“英雄”的角色,“拯救”卫卫于困窘之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是,镜头跟随陈升所在车辆在小路上前行时,镜头忽然诡异地离开了前行中的车辆,突兀地转进一条岔开的小道中,这里所产生的间离感尤为明显。对此导演曾解释,“大家都知道电影是假的,我只有用恰当的方式和观众互动,告诉观众电影是假的,观众才能真正领会到里面的感情是真的”。
三、强化间离感:魔幻的诗歌
一般来说,对白、音乐与音响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电影语言,与场面调度、色彩、场景、服装等要素一起共同完善了电影语言独特的修辞规律。而在《路边野餐》中,配乐只有两段,由林强完成。而导演本人所写的几首现代诗则被巧妙地运用在影片叙事之中,由业余诗人陈升作为旁白朗诵,成为此部影片的“专门配乐”。诗歌内容本身极具魔幻风格和疏离化特征,在影片中的出现一方面可作为电影的时间轴标记,另一方面则使影片整体审美疏离化风格得到进一步构建。
诗歌是影片不同场景之间的过渡,为影片在极少配乐的情况下也增添独特的节奏感。在念“没有了音乐就退化耳朵/没有了戒律就灭掉烛火/像回到误解照相术的年代/你摄取我的灵魂/没有了剃刀就封锁语言/没有了心脏却活了九年”这首诗的过程中,影片画面从陈升家里切换到诊所的天台。而陈升从列车到出狱画面的转换,则是另一首诗:“许多夜晚重叠/悄然形成黑暗/玫瑰吸收光芒/大地按捺清香/为了寻找你/我搬进鸟的眼睛/经常盯着路过的风。”通过富有节奏感的朗诵,导演完成了从现实到回忆的切换。犹如影片的英文片名Kaili Blues所揭示的,影片基调是忧郁的、静寂的、诗意的,而诗歌的出现在进一步加深影片诗意之余让影片在较为缺少配乐的情况下增添了音乐效果,让影片音效不至于太过寡淡。同时,诗歌的配合使得场景的转换变得自然,诗歌成为导演标记时间的重要手段。
除去标记性的作用外,诗歌内容与影片剧情联系并不紧密。导演认为:“文学在我的电影里面就是文学,它其实是很少参与叙事,它只在一些神秘处有一些交汇而已。”[3]这种极少的交汇实则起到了提示剧情的作用。“没有了音乐就退化耳朵/没有了戒律就灭掉烛火/像回到误解照相术的年代/你摄取我的灵魂/没有了剃刀就封锁语言/没有了心脏却活了九年。”诗歌与陈升入狱九年对照,表达陈升入狱生活如同失去生命一般。除此之外,诗歌内容较为晦涩,形式上脱离日常语用惯例,观众间离感进一步加深。但晦涩的诗歌却与影片整体风格吻合。如同克莱夫·贝尔考察教堂、雕塑等艺术后所言:“在每件作品中,以某种独特方式组合起来的线条和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关系激发了我们的审美情感。”[4]诗歌乃至影片叙事性的减弱、形式的疏离化,都在激起观众的审美感情,引导观众在形式之中去体会影片中的迷失与哀愁。
四、结语
电影《路边野餐》营造了一个诗意朦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时间和空间不断被拆解和重塑,夹杂着主人公陈升难以释怀的过去、迷失于过去的现在以及渴望与自己和解的未来。导演对叙事、构图、运镜以及诗歌旁白等进行疏离化的处理,似乎制造了种种间隔,让观众产生间离感。但形式的创新,实则是在制造间离感过后,消除妨碍自由感受的阻力,让观众能以更自由的方式感受意境的梦幻与情感的真实。尽管镜头略显粗糙,但疏离化构成导演独特的诗意风格,破除了以往华语影片的审美定势,为未来华语电影的发展注入了一剂新动力。
参考文献:
[1]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主义论文选[C].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6.
[2]杨世真.重估线性叙事的价值——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比较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7:42.
[3]叶航.以无限接近写实的方式通往梦幻之地——访《路边野餐》导演毕赣[J].国际新视野,2016(3):94.
[4]贝尔.艺术[M].薛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4.
作者简介:马静岚,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